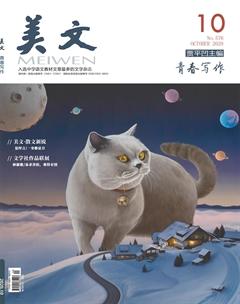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张佳敏
大约一百五十年前的某一天,在俄罗斯一家小旅馆内,一位客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声名日隆的大作家——忽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这是死亡带来的阴郁。实际上,那时他的年纪并不大,身体也很健康,然而他始终无法摆脱死亡压抑的阴影。
他是托尔斯泰,这一夜的恐怖对他日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今我们看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正是在这种恐怖余威下诞生的。
人们称之为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死了的人是否还能活着,可以存疑;但有的人活着,却已死了,应是无可置疑的。生死问题是这样空乏又沉重,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活着的事都搞不明白就不必去想那渺茫的死了;然而我们生的另一端连接着死,只有乐天派才会选择视而不见。当然,乐天有它的道理,而且很可能是唯一正确的处世观,但遗憾的是一些人生而躁动。他们要从死亡中榨出苦汁,作为生命的养料,这类人其实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就像沙漠里的仙人掌。人世一般的困难已打不倒他,同时也就令他失了兴味,于是他只有一步一步向终极发问,获取生存的意义。
英国作家艾略特名作《荒原》破题第一句话就是:我要死;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上述两人无时无刻不在死亡的黑洞边徘徊,然而我们如今看他们的作品,感到极度压抑、绝望的同时,又能获得无限对生的渴望。这就是从死亡中取出的生命意志,如同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为人类盗来希望的火种。
我们的每一脚步、每一声笑、每一声呐喊,都在向死亡靠近,向死亡呼唤。幸福的人平安终老,他们的一生是唱着颂歌投进死亡的行程;悲惨些的则哭着喊着被推进死亡之中。总之他们都将成为一堆白骨、毫义意义的元素堆积物,富裕的、尊贵的名流显贵同贫穷的、低贱的毫无二致,所不同的大概是前者的骨灰盒要更贵重华美些吧!然而这不过是后人温情而无聊的行为,正如孝子们都热衷于大办双亲身后之事一样,生人的一切努力只与生人有关,死者若有灵魂,只能充当一个旁观者罢了。
要说清楚,我们的讨论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从来不会有一个厌生者来讨论生死之事;若有,那他已不在生者行列了。另有一种人,即我们通常所说伪君子之流,也爱讲前途命运,甚至以为人类一切祸福全寄于他一身似的,其实不过是小心呵护一己荣辱的可怜虫罢了。这样的人,若生在毫无分量的地位那倒无所谓,天下多几个梦想者罢了;若在相当的位置上,那就麻烦了。
人类一点光明大概在于,从古至今都有一群先驱者,为了自身的一点困惑,也为了身边人的醉生梦死,而探索终归不会有结果的难题。莎士比亚是这样,哈姆莱特那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自我质问,在当代人看来大概也是精神错乱了,然而这的确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必得产生的疑惑。否则,“人”的概念只是从生存到死亡的一个毫无意义的短短百年。要说明的是,以功利观点来看,哈姆莱特对于人类进步没有多大作用:他不能提高GDP,也不能立即消灭人类的痛苦。
但是我从前大学时,因了哈姆莱特的这一句话,心灵受了极大震撼,被同学误解,以为我是脑子错乱了,立即报告给了辅导员。那位善良的女人立马把我找了去,轻声细语地与我沟通,询问我近期的困难。她那样关切,我很感动,然而我实在无法告知她我的困惑,只有老实地顺从她想象中的思路,编造了几条莫须有的困难。她一一为我解难,我表示感激,并说一定遵办。从此我不敢再发狂言了,也和同学们一样过着充实的大学生活。辅导员以为自己的辅导起了作用,一再与人说起这事,大概要一届一届传下去吧!这倒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差不多,狂人最后“候补”去了,我则成了一个正常学生,结局都不错。
或许在科学理性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如今,人得到了大大的思想解放,但同时也失去了一点意义。中国过去没有现代科学,且长期处于苦难之中,无暇思考形而上的问题;西方虽一直是现代科学的故乡,但同时也有强大的神学做后盾。但到了二十世纪,无论东西方,都趋于整体上的和平,且宗教也基本被剥下了所有神圣外衣,这时人在物化社会里彻底茫然了。在疫情期间,人们似乎很喜欢提及加缪的《鼠疫》,然而唯有书的名字才符合他们的想象而已。存在先于本质,人人都爱高喊这句名言,为了争取更大的自由;然而自由越多,庸碌也就随之展开了。
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个古怪的年代,人向理性回归了,付出的代价是庸碌——这是王安忆坦言写不出浪漫、高尚、宏伟作品的年代。
我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四年级左右,跟着大哥去县城广场上看耍杂技的。那里人很多,我看着他们,心里慢慢生出一個念头:他们心里都有一个“我”。在我看来,世界是“我”的世界,我用“我”的视角看待一切,包括观察他们。可是他们也有一个“我”,他们心底里时时刻刻都回荡着“我”。我可以将外部一切当作某种力量的对我迷惑的显示,那么他们也可以,比如把我当作一个没有生命的只会行走的小孩。当你独处一室,盯着自己名字或者默想自己的存在时,会为“我”而感动,而迷惘,而恐惧。这个我,此时此刻在思考;这个“我”,将在百年后化为尘土。
我那时还小,心里只感到不安,同时由于小孩心性,很快就抛下不想了;这恐怕是做小孩最大一个好处,想不通就不想了。后来十几年间,还会偶尔奔涌出“我”的困惑,我很想深入进去,但我不敢。我清楚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通过思考就可以想得通的问题;也许,一有不慎反而会彻底失去“我”,成为一个疯子。我对于疯子并不歧视,用俗语同样也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说:身处的世界不同而已。他们的世界,雾中有影,沙上有印,风中有声,而我们的则是明晰理性的。作为一个所谓的正常人,只要有一个正常的“我”,就不可能踏越雷区到另一个世界去。
凡人只能小心谨慎地一步步向那隐藏在黑暗或者光明中的地方走去,一旦感到危险,即刻退回来。心理医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探路者,一些人走得远了,就回不来了;另一些人,则幸运地把握了一个度,得以在两个世界来回穿梭。
这样的人终归是少数,大多数人选择逃避,免得自寻苦恼,其实这也是生活态度之一。假若我们没有遇到阿尔扎马斯的恐怖,那便学习童年时代的自己,快快乐乐地过下去吧!假若撞见了,老实说,托尔斯泰最终也没有解决的难题我也不能乱给意见。但是为了结尾,我提供一个“歌德方案”,他也同样有这个困惑,他在《浮士德》中这样说:
凡自强不息者,到头皆能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