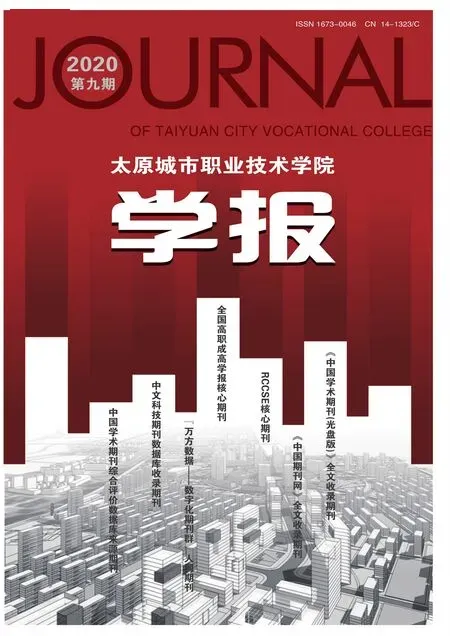专业学习共同体视阈下高职外语教师职业高原破解路径研究
■莫 俊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江苏 无锡 214028;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高度重视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培养。高校中青年教师是高校开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工作的主力军,已有研究发现在他们的专业发展生涯中,职业高原是一种带有明显普遍性、规律性及影响力的藩篱(陈斌岚、李跃军,2016),易导致教学质量下降,不仅影响到教学管理的正常运行,也会阻碍教师个人的发展(李楠,2008)。高职院校以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为主,学术科研任务为辅,这种“教书匠”式的定位使高职教师普遍产生职业高原现象。由于外语专业师资队伍的性别、职称、学历结构不平衡(王守仁、王海啸,2011),加上在现行考评机制下被边缘化(王守仁,2016),与其他专业相比,高职外语专业教师更易受到职业高原的困扰。
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职业高原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涉及社会因素、组织因素、家庭因素及个人因素四个层面(修文荣,2006)。对此,政府从顶层设计出发,于2018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提出了“加强院系教研室等学习共同体建设,建立完善传—帮—带机制”的具体实施路径,旨在通过搭建学校层面的教师发展平台,从而实现全面提高高校教师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创新型教师队伍的目标。所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大量的文献理论回顾,研究以教研室为单位的专业学习共同体(组织层面)通过对职业目标(个人层面)的引导对职业高原产生影响的机理,以及家庭—工作冲突(家庭层面)与职业高原的关系,旨在探究以下问题:一是当前以行政化教研室为主要形式的外语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现状如何,能否有效克服职业高原?二是与企业员工相比,高校教师的职业目标有何特殊性,专业学习共同体能否对其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三是高职外语教师在家庭—工作冲突方面现状如何,与职业高原有何关联?
一、文献回顾
(一)专业学习共同体与高职外语教师职业高原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Professional LearningCommunity,PLC)源于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后被定义为一个具有共同学习愿望、特定角色身份的教师学习群体(Dufour,2004)。我国关于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研究自2001年兴起后蔚然成风,近20年来主要围绕如何构建教师(以高校教师为主)专业学习共同体并以此推动教师专业发展这一议题进行,兼及对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推进课堂教学活动的探讨,并深入到基于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教师培训策略研究方面(张兆芹、刘紫馨,2018)。以往研究认为专业共同体形式的教研室组织有利于打破高校英语教师教科研究的孤立局势,能较好地在情感、知识技能等层面促进高校英语教师实现专业发展和科研成长(李明霞、兰杰,2017),有学者由此论症了基于专业学习共同体理论的高校教研室建设策略(李俊,2017),并对复杂系统下教师学习共同体的运行机制展开了探究(何霞,2018),相关实症研究验症了专业学习共同体建设在帮助高职外语教师提高其教学能力(郭燕、徐锦芬,2016)、科研领导力(陈先奎、孙钦美、毛浩然,2016)方面的显著作用,并论症了以此为背景的高职外语教师个性化学习路径(马瑜,2019)。
在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测度方面,众多研究以Hord(1997)的五因素模型为基础,发展出《专业学习共同体评估量表》(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Assessment,PLCA)(Huffman&Hipp,2003)、《专业学习共同体评价量表改编版》(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Assessment,PLCA-R)(Olivier,et al.,2003)等主流量表。由于国外的主流量表多以整个学校为单位采用宏观分析框架,同时均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开发,唐进(2019)从中西方文化差异与外语学科的特殊性出发,在PLCA-R的基础上,以“教研室”为框架编制了《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量表》,该量表包括专业领域基础、专业实践与应用、支持性条件、领导方式和集体认同5个维度。
职业高原(Career Plateauing)最早是指个体到达职业生涯中的某个阶段后,获得进一步晋升的可能性很小(Ference,et al,1977),其内涵随后从垂直晋升层面拓展到水平流动的停滞(Veiga,1981)以及工作职权的增减(Feldman&Weitz,1988)等方面。在职业高原的测量维度上,以层级高原(hierarchical plateau)和工作内容高原(job content plateau)两维度划分法(Milliman,1992)较为通用。职业高原理论自问世以来,主要被用于分析企业组织中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问题,现有的研究在操作层面围绕职业高原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症研究,主要涉及工作绩效、组织承诺、缺勤率、离职倾向、工作中心度、工作满意度以及工作投入等(谢宝国、龙立荣,2005)。该领域的研究随后逐步扩展到政府、学校等组织机构,但目前国内外学界对高校教师的职业高原问题关注相对较少。
(二)职业目标与高职外语教师职业高原
所谓职业目标,可以界定为个体努力奋斗想要获取的职业结果。本研究根据高校中青年教师的职业特点与追求,借鉴Seibert,et al(2013)的区分标准,将职业目标划分为外职业目标(外在激励型)和内职业目标(内在激励型)两类。外职业目标是指职业生涯过程中外显的、具有能见性的标记,通常包括以下内容:职务目标、技术等级目标、经济收入目标、社会影响目标、工作内容目标等。内职业目标是指在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中个人自身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收获了知识、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职业技能、转变了陈旧观念、内心得到了丰富与升华。以往的研究表明,内在激励的员工更容易专注工作,有更高的满意度(Seibert,et al,2013)。
(三)家庭—工作冲突与高职外语教师职业高原
工作和家庭冲突是一种角色间冲突,源自工作和家庭领域的角色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冲突具有方向性,可分为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两类。家庭—工作冲突(family-work conflict,FWC)是指员工家庭角色的履行干扰了工作角色的履行(Green haus&Beuteu,1985),现有研究发现造成家庭—工作冲突的大多是家庭领域变量,如家庭资源和家庭投入等(张伶、张大伟,2006)。由于高职外语教师群体以女性为主,因此本研究主要选取家庭—工作冲突维度进行测量。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无锡地区四所高职院校,采用网络问卷进行调查,向在职外语教师发送问卷链接。调查回收问卷63份,样本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由表1可见,本次调研获得的样本主体是教龄在20年以内的中青年教师(84.1%),其中教龄7-20年的教师占74.6%,他们正处在职业生涯的实验和歧变期(Experiment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与重新估价期(Reassessment)的分歧口(Huberman M,1993),如缺少及时的良性引导,将陷入职业高原问题严重的职业倦怠。

表1 样本的人口学特征
(二)研究工具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效度,本研究均采用成熟量表对变量进行测量,且所有量表采用likert-5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完全不符合),2代表不太同意(不太符合),3代表不确定,4代表基本同意(基本符合),5代表完全同意(完全符合),所得结果使用SPSS20.0软件进行分析。
职业目标。采用Seibert,et al(2013)的职业目标量表。该量表共有9个题项,并将职业目标分为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两个维度,其中外在激励有4个题项,信度系数α=0.74;内在激励有5个题项,信度系数α=0.65。
专业学习共同体。采用唐进(2019)编制的本土化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量表。该量表共有32个题项,包括专业领域基础、专业实践与应用、支持性条件、领导方式和集体认同5个维度,总量表的信度系数α=0.944,各分量表α系数在0.728和0.881之间,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家庭—工作冲突。采用Netemeyer,et al(1996)的家庭—工作冲突量表。该量表共有5个题项,信度系数α=0.87。
职业高原。采用Allen et al(1999)的职业高原量表。该量表共有12个题项,并将职业高原分为层级高原和内容高原两个维度,其中层级高原有6个题项,信度系数α=0.83;内容高原有6个题项,信度系数α=0.85。
控制变量。本研究将教师的性别、教龄和职称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三、数据分析和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调查结束后,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将58个子项按照各自所属维度,对10个变量做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统计结果见表2。基于此表,可以做出如下分析(见表2)。
1.传统行政化教研室形式的专业学习共同体整体发展水平较低
从分析专业学习共同体的5个维度可知,得分最高的“专业领域基础”(M=3.88888,SD=0.54814)也未达到“基本符合”的标准,可见传统的行政化教研室学习共同体的运行效能和整体影响力水平不高。
(1)在“专业领域基础”维度,得分最低的是“教研室的重大决策一般能体现教师的共同价值观”(M=3.6667,SD=0.6956)和“教师合作是解决教学问题的有效途径”(M=3.746,SD=0.8793),仅在“提高学生的能力是大学外语教师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一项上达到“基本符合”(M=4.0794,SD=0.655),反映出高职外语教师在教学目标上达成了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共识,但在共享愿景层面尚难形成一致,对教师合作的效能存有疑虑。
(2)在“专业实践与应用”维度,认可度居于前三的是“教研室定期开展相互听课、评课和公开课”(M=3.9524,SD=0.8693)、“教研室主任与普通教师一样参与专业培训”(M=3.873,SD=0.793)和“教师会根据本班的实际情况选择教学内容并调整教学进度”(M=3.873,SD=0.8326)。相对于得分最低的“教师有机会出国进行短期学习或中长期深造”(M=2.9524,SD=1.2238)而言,“教研室教师合作完成教研或科研项目”得分倒数第二(M=3.6825,SD=0.7793),也体现出高职院校“重教学、轻科研”的一贯特点,同样印症了高职外语教师对教学科研合作上的保守态度。
(3)在“支持性条件”维度,得分最高的是“师生之间是相互信任与支持的关系”(M=3.9365,SD=0.7593)和“同事之间相互信任与支持”(M=3.8413,SD=0.745),这反映出一种和谐融洽的师生同事氛围,得分最低的“教研室有专门的教师专业发展经费预算”(M=3.0794,SD=1.0821)和“教研室有促进教师合作学习的正式制度或不成文规定”(M=3.4127,SD=1.026)则体现出高职院校在支持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体制机制短板。
(4)在“领导方式”维度,值得肯定的是“教师能通过教研室主任接触到教研室与学校发展的关键信息”(M=3.8413,SD=0.9539),以及“教研室主任是专业与管理方面的专家,能在必要时候给大家提供支持”(M=3.6825,SD=0.9972),可见教研室主任在管理沟通、支持教师发展方面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教师参与教研室管理事务”的权限得分最低(M=3.5238,SD=0.9977)。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5)在“集体认同”维度,得分最高的“教研室的发展目标也是我个人的工作目标”(M=3.7302,SD=0.8074)反映出高职外语教师的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有较为显著的一致性。但“将来即使学校其他部门能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我也不会考虑离开目前的教研室”选项得分最低(M=3.4286,SD=0.9455),又折射出高职外语教师对工作现状的不满足心态。
2.内职业目标是高职外语教师的主要工作价值取向
如表2所示,高职外语教师的职业目标体现在价值取向上以内在激励为主(M=4.2508,SD=0.58023),这是与企业员工普遍追求外在激励相比显著不同之处。单项分析可知,高职外语教师居于前三位的职业追求为“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学习和成长”(M=4.4603,SD=0.6432)、“在职业生涯中发展个人技能”(M=4.3968,SD=0.6101)以及“希望通过工作对他人或社会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M=4.2381,SD=0.7559),后三位的职业追求为“成为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M=2.9841,SD=1.0548)、“在单位里被看成是一个能干的人”(M=3.5714,SD=0.9283)以及“在职业中获得经济回报”(M=3.746,SD=1.0772)。
3.家庭—工作冲突对高职外语教师的干扰程度较低
从总体来看,高职外语教师群体在家庭—工作冲突层面的问题并不严重(M=2.53016,SD=1.00525),各题项得分均在平均值以下,得分最高的选项是“来自家人或配偶的要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工作”(M=2.7778,SD=1.1701),干扰程度不显著。
4.高职中青年外语教师群体存在层级高原焦虑及工作内容高原倦怠
调研可知,高职外语教师群体的职业高原症状整体不算严重(M=2.73545,SD=0.4388),层级高原问题(M=3.037,SD=0.59827)较工作内容高原问题(M=2.433,SD=0.56045)显著,这一结果与中青年教师的职业阶段特质有一定程度的匹配性。但从分项结果来看,值得关注的是在层级高原维度中青年外语教师对“能够晋升到更高一级”较多持悲观态度(M=3.8571,SD=0.9133)。在工作内容高原维度,得分较高的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不断扩充能力和知识”(M=4.3016,SD=0.6871)和“工作中没有机会去学习和成长”(M=3.9048,SD=0.9108)。以上反映出高职中青年外语教师在常规教学工作和专业化发展上存在明显的职业高原瓶颈。
5.不同性别、教龄、职称的高职外语教师在各维度均未见显著差异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性别、教龄、职称的高职外语教师之间的差异,本研究先对性别变量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各维度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随即分别对教龄和职称两个变量进行了单因素ANOVA分析,经方差齐性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后发现各维度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变量的相关性统计分析
图1列出了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可见职业高原现象与专业学习共同体(r=-0.429**,p<0.01)和职业目标(r=-0.249*,p<0.05)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同时,职业目标与专业学习共同体(r=0.294*,p<0.05)显著正相关,职业高原与家庭—工作冲突(r=0.324*,p<0.05)显著正相关,本研究验症了专业学习共同体对抑制职业高原作用的影响机理。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基于对四所高职院校外语教师的问卷调查,本研究从专业学习共同体和职业目标取向出发,构建了一个分析高职外语教师职业高原形成机理的框架模型,用来研究以行政化教研室为主要形式的专业学习共同体、职业目标如何对职业高原产生影响,同时分析家庭—工作冲突与职业高原的影响关系。实症检验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存在和运行对高职外语教师的职业高原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尽管传统的行政化教研室形式的专业学习共同体总体运行效能不尽理想,但以此为基础的专业学习共同体在共享愿景(专业领域基础)及合作学习与应用(专业实践与应用)层面效果良好,也对职业高原现象产生了显著影响。调研数据显示出支持性条件维度对职业高原的影响同样十分重大,但从描述性统计情况来看,反映出制度支持层面明显存在短板,需要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加大制度建设、经费投入及相应资源投入的力度。
第二,专业学习共同体对职业目标有显著的正向引导作用,两者共同对职业高原形成抑制作用。调研结果显示,共享愿景(专业领域基础)及合作学习与应用(专业实践与应用)两个维度显著正向影响高职外语教师的职业目标,与此同时,显著负向影响职业高原的主要是内职业目标(内在激励)维度。这一结论与高职外语教师以内在激励为主的职业目标取向吻合,也与工作内容高原维度反映出的工作中成长机会缺少问题相一致。换句话说,职业高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解决的关键还是要通过建立共同愿景、倡导团体学习与合作、改善心智模式等途径来最大程度地激发教师的内职业目标。具体而言,就是要增加工作的多样性、挑战性,提供不断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在不断磨练和提高高职外语教师的职业技能的过程中克服职业高原现象。

图1 专业学习共同体对职业高原的影响机理
第三,家庭—工作冲突的存在会显著加剧职业高原现象。一方面,家庭—工作冲突对工作内容高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家庭生活要求和压力会对常规教学工作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加剧职业高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由例行公事型的教学工作产生的职业高原使得家庭—工作冲突因素成为一个压力的宣泄口和退避路径。
(二)理论意义
目前,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教师队伍的培养,并提出了加强院系教研室等学习共同体建设的具体实施建议,但现有研究少有关注教师的职业高原问题,也未见以学习共同体为切入点对抑制职业高原的作用机理展开实症研究。本研究借鉴新开发的本土化《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量表》,以传统的行政化教研室形式的专业学习共同体为研究对象,选取专业学习共同体、职业目标和家庭—工作冲突为研究变量,通过定量研究方式诠释对职业高原现象的作用及影响机理,对于进一步拓宽高职外语教师的职业高原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第一,本研究从专业学习共同体、职业目标和家庭—工作冲突等层面构建了一个研究高职外语教师职业高原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厘清了高职外语教师职业高原的生成机制及影响因素。高职院校教学型高校的基本职能定位导致一成不变的常规教学工作成为职业高原现象形成的主要根源,也与高职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诉求形成了现实的矛盾,本研究系统性地对组织层面、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各因素与职业高原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有助于丰富和完善高校教师职业高原问题的深度研究,也为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准确剖析职业高原的成因、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拓展了理论思路。
第二,本研究深入剖析了专业学习共同体通过内职业目标作用于职业高原的机理。内职业目标是高职外语教师的主要工作价值取向,行政化教研室形式的专业学习共同体在共享愿景及合作学习与应用方面的良好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教师的内职业目标,从而共同对职业高原现象产生了抑制作用,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理论预期。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主要从心理层面揭示了高职外语教师职业高原问题的破解路径,为学者们继续聚焦微观心理层面挖掘高校教师职业高原的根源提供了理论借鉴。
第三,本研究检验了家庭—工作冲突与职业高原现象的相互作用。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家庭—工作冲突纳入高职外语教师职业高原现象形成的理论框架,并检验了家庭—工作冲突与工作内容高原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这一研究尝试对于清晰诠释高职外语教师心理诉求、家庭因素与职业高原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高校及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第一,本研究能够提高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及教育决策机构对高职教师职业高原问题的关注。在现有的高校评估体制下,高职外语教师普遍存在职称晋升途径不畅的层级高原,以及重复性常规教学工作带来的工作内容高原。多数中青年教师处在职业生涯的实验和重估期,由于年复一年单调的教学工作或者教学研究受挫,以及缺少及时的正向引导,而很快进入职业高原现象严重的保守和抱怨期(Huberman,1993)。这一问题的存在既对教师个体的专业化成长形成了重大阻碍,也不利于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对此,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应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措施,及时帮助高校青年教师消除职业高原现象,教育主管部门也要做好顶层设计,从政策制定层面扶助青年教师成长。
第二,本研究提出了通过专业学习共同体激发内职业目标从而破解职业高原现象的实施路径。传统化教研室形式的专业学习共同体在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与实践等层面减弱职业高原现象的作用机理已得到了验症,针对目前教研室共同体存在的资金投入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短板,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应予以充分重视,加大投入力度。鉴于教师的职业目标取向以内激励为主,破解青年教师职业高原的具体实施策略包括鼓励教师参与广泛多样化的工作任务、提供有助于提升职业技能的进修培训机会、对教师取得的成就及时给予阶段性精神或物质性奖励等等。就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而言,有必要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在社会上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教师的待遇及社会地位。
第三,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家庭—工作冲突和职业高原现象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家庭—工作冲突并非形成青年教师职业高原的主要原因,但家庭因素与职业高原的产生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特别是一成不变的工作内容在相当程度上对教师的工作热情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侧面上使得部分青年教师将重心向家庭倾斜。因此,高校相关职能部门有必要采取针对性措施,通过提高工作挑战性、多样性、趣味性等方式帮助青年教师平衡好家庭与本职工作之间的关系。
五、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对高职外语教师职业高原研究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都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本研究在对职业高原的影响因素的探索中,从组织层面、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对各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但各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仍有待深入挖掘;二是对四所高职院校进行的调研限于样本容量,对高职外语教师职业高原形成机制中性别、教龄、职称等可能存在影响的变量探究力度不足,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推进。
自从学习型组织理论进入我国学术界视野以来,学校教师共同体的相关研究蓬勃发展,其成效也不断得到验症,但正如万哨凯(2017)所述,多数以行政化组织为主体的高校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侧重于关注日常教育教学任务的布置,难以顾及教师专业成长的需求。在互联网+教育的时代,相关研究应与时俱进,围绕自发性教师学习共同体、教师网络学习共同体等的构建及效用进行纵深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