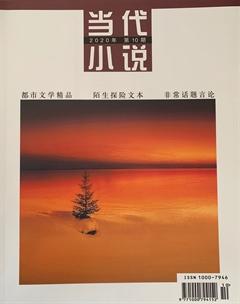安力古
宫敏捷
日常开车,万不得已,月仙都会绕开西施桥走,而今天,却又无可奈何地开着黑色的本田,听着轮胎与地面摩擦出的沙沙声,驶了上去。一大早,远道而来住在浦阳大酒店的生意伙伴,也是合作多年特意从深圳赶来,要去自己的食品加工厂参观考察的老朋友,打来电话说,他不喜欢吃酒店的自助早餐,不知道诸暨有什么特色小吃,他想去体验一下。月仙想在电话里告诉他,从他所住的浦阳大酒店出来,左转进入浦阳江大道,顺着人行道走四五百米,红绿灯处的路口边,有一家次坞打面馆,那是诸暨最有特色的小吃,也是诸暨做得最好的次坞打面馆。转念又想,不管从生意的角度,还是西施故里的待客之道来说,自己都应该去一趟,亲自带他过去品尝一下为好;再说,为了生意上的事情,她忙得焦头烂额,也差不多个把星期没有去一饱口福了。
“你等着,”月仙说,“我过十几分钟就到酒店,带你去吃。”
“我出来了,”朋友说,“我六点钟就起床,现在都在浦江边跑了一圈,看看风景,也顺便活动活动腿脚。”
“现在到哪里了?”
“西施桥上,”朋友说,“太阳出来了,从这个角度给浦阳江拍照,角度最好,也最漂亮。”没等月仙回话,朋友呵呵笑起来,又说:“我带着单反的,你不知道吧,我还是个摄影爱好者呢。”
“是嘛!”月仙迟疑一下,说,“那我就到西施桥上接你吧。”
西施桥的一边,城市道路宽敞平直,一眼便能看到城市的纵深与开阔,另一边却是一个接近四十五度的缓坡,不管直行,还是左右转,也是这样的坡度。尽管有了心理准备,车子从平坦的一边开上西施桥时,月仙的胸腔还是不由自主地起伏起来,内心在往里收,似乎在聚合某种力量,抵御与初冬的寒风一起扑面而来的悲伤情绪。风是从浦阳江的河道里裹挟而来的,朋友正好站在西施桥的中间,端着单反相机,取景框越过成排的法国梧桐,对着浦阳江的上游,也对着缓缓升起的红日,还有那些江天之间,丝丝缕缕的红彤彤的飘带一般的云彩,一个劲地猛拍。神思恍惚间,月仙一脚刹车,把车停在朋友身边的辅道上,嘀嘀按两下喇叭。朋友看着她,咧嘴一笑,又抓紧时间拍一张,才收起相机,跑了过来,拉开副驾驶的门,坐在月仙身边。
“麻烦你了。”朋友说。
“客气,”月仙淡然一笑,“这是我应尽的地主之谊啊。”
或许拍到了自己喜欢的照片,朋友难掩兴奋之情,一点也没觉察到月仙内心的不适和神色的异常。月仙说着话,适度加了几下油门,车子很快驶过西施桥,左转来到月仙刚才想在电话里告诉朋友的那家面馆门前。他们在路边,找一个停车位停好车辆,刚好走到面馆门前。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男人,他面皮白净,留着板寸头,急匆匆走出来;他的身后,一个老太太站在面馆门前,离着五六米远,一脸严肃地对他喊道:
“先生,先生,你还没开钱呢?”
男青年没有理她,而是对着月仙,笑眯眯点一下头,眼神里,有一股热热的风,吹过月仙的面庞;热风里,似乎还掩藏了其他难以言说的东西,朋友觉察到了,却不明就里。月仙对男青年笑笑,年近四十的也略有松弛的脸上,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她听到老太太又在门边说:
“你怎么吃面不开钱呐?”
“我吃自己家的面条,开什么钱?”男青年说,“老太太,你得讲道理啊!”
“你这个年轻人,”老太太说,“吃面不开钱,又反过来说我不讲道理了。”
男青年不再理她,迈开脚步,一溜烟跑了。老太太小声嘀咕着什么,脸扭曲着,似乎要哭出来;她看了月仙和她的朋友一眼,眼见着他们来到门边,也不打声招呼,背过身去,迈着蹒跚的步子,慢慢走到屋里,对着正在厨房忙活的一个青年女子,也是面馆的厨师说:
“那个男人,吃了我们家面,没开钱就跑了。”
青年女子面色清秀,鼻梁高挺,玉润的脖颈之上,五官被宽檐的厨师帽与白围裙一衬,出奇地立体与精致。她跟刚才跑出门去的男青年一样,没怎么招呼月仙,也只是跟她点头示意一下,看着她笑笑,笑容里的意思倒是很明显,似乎在说,“来了啊,你请随便,自己找地方坐吧。”随后,她在围裙上的口袋里,掏出二十元钱,放在老太太的手里,说:
“谁说人家没给钱了,這不是吗?”
“我还以为他没给呢。”老太太似乎还很委屈。
“又来客人了,”女子说,“你问问他们,要吃什么面呢。”
“好。”老太太说。
“注意看着哦,”女子说,“他们吃完了,要记得找他们要钱。”
“好。”老太太又说。
老太太或许是想到了自己刚才的失误,有点想笑,脸上的肌肉搐动几下,拧出来一丝怪异的神色,嘴也歪了,眼也斜了,看着还有点狰狞。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她是一个和蔼可亲又单纯可爱的老太太。她白白胖胖的,有着一头花白的短发,穿着一套布满碎红小花的棉衣棉裤;不管坐着,还是站着,她的手都不由自主地挥动着,似乎在打着什么节拍,脑袋也跟着这节拍,摇摇摆摆的。月仙和朋友,找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扭头看,冬日的暖阳刚刚从一棵被砍去枝丫的法国梧桐上爬上来,在一片枯黄的叶片上,一颠一颠的,似乎又要滑落到浦阳江里。
这家面馆,是将一套临街的住宅简单改建来的。入户门拓宽了,加装上两扇玻璃门,厨房、洗手间都保持原样,客卧变成了储物间,客厅和主卧打通了,变成了一间近五十平米的大餐厅,错落有致地摆上几张黄色的原木条桌。餐厅的墙面,画有一幅雅致写意的中国画,讲的是次坞打面的来历;画面中,刚刚打败陈友谅的朱元璋,正和他的部下们,志得意满地坐在一家街边店铺里,身子压低在一张长条桌上,用筷子挑着劲道十足的面条大快朵颐;朱元璋的身边,还站着一对谨小慎微又战战兢兢的年轻夫妇。月仙的朋友光顾着看墙上的画,没注意到老太太已来到他们身边,嗫嚅着说:
“你们——想好要吃什么面了吗?”
“不用想,”月仙半仰着头,调皮地看着她,眼睛一闪一闪的,笑着说,“还是老样子,给我们来两碗吧。”
“老样子?”老太太说,“老样子是什么?”
“你不记得我啦,你好好想想,”月仙说,“我每星期都要来你这吃一碗的。”
老太太摇摇头,用右手的食指,点着自己的面颊,很认真地想了想,又对着月仙摇了摇头。
“你去问她,”月仙指着厨房里的女子,对老太太说,“她自己知道的。”
老太太又在两人的注视下,迈着蹒跚的步子,朝厨房里的女子走去。恰好又有一个年纪跟她差不多大的老太太走进来,迎面跟她打招呼,她扭头看着人家,认真审视一会儿,却不作任何回应,径直走进厨房里。刚进来的老太太并不在意,迎面跟月仙打了个招呼;月仙热情地回应了她,还给她解释说,自己是陪外地来的朋友,特意来尝尝诸暨有名的次坞打面的。朋友等她与进门来的老太太简单聊几句后,小声地对月仙说:
“你好像跟店里的人都很熟呢?”
“经常来嘛。”月仙说。
“那个老太太,”他指的是餐馆里的这个,“你们都认识她,她却不认识你们呢,这怎么回事。”
“她何止不认识我们,”月仙说,“她连自己儿子都不认识了。”
“谁是他儿子?”
“在门前被老太太追着要钱那个。”
朋友张着嘴,用气息哈出一个轻微的“啊”音。
月仙解释说,老太太两年前,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了,别说别人,她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她本来记忆力就差,是生孩子时造成的。老太太天生抗麻药体质,生头胎的姑娘时,难产,得打麻药剖宫。别人打一针麻药管够,她得打两针。这对她的脑神经伤害很大,自此,记忆力慢慢衰退;隔了三年,生二胎的儿子时,也是这样。孩子生完,她的记忆力更差了,经常忘东忘西的。大家都以为,她是因为产后虚弱,才会这样的,一孕傻三年,不都是这样说的吗?等身子骨养好了,记忆力自然也会跟着恢复的。她自己却不这样认为,“拿着初高中的同学合照,却好多人都叫不出名字了。”她经常吃惊地对家人说。于是一个人上街,花百十块钱买了一串珍珠,请人把至亲的名字,刻在上面。没事了,取下来像执珠念佛一般,一颗一颗捏着,想象每一个亲人的面孔和叨念他们的名字,生怕自己有一天,真的把他们的名字和面容忘记了。
她以前是医院妇产科的大夫,给孕妇们做产前检查的同时,有那么几年,自己本身也是个孕妇,或哺乳期妇女;双重的身份,宽厚的性情,以及高明的医术,使她深受孕妇们喜爱。许多人生老大时,找她做产检,生老二了,也专门找她看,不管排多长的队伍,都毫无怨言地耐着性子等着。这个城市,还未出生,便被她通过B超观察过,或者隔着肚皮抚摸过的孩子,至少有上千个。她知道自己岗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意识到身体出了问题,便主动去给院长反映自己的健康状况。医院经调查属实后,给她另行安排了文职工作,她也干不好;让她在行政大楼传送个文件,她拿在手上,楼上楼下走几圈,有的部门送达了,有的部门连门都没进去过,又把文件带回来,搁自己办公桌上,最后她连这些文件是做什么用的,都忘记了。医院只得什么也不让她干,白拿工资养她几年,便提前给她办了病退手续。
当然,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她的丈夫也是因为她的身体原因,提前从部队转移到地方来工作的。他是诸暨本地人,在舟山岛那边当兵,隶属海军某部,跟她弟弟在一个连队,是她弟弟的班长。他们都不出海,属地勤保障部队。他们就是经她弟弟介绍认识的,通信半年后,他请假回来见她一面,两个人在医院门前一棵高大的麻栎树下,站着说几句话,感情便定了下来;又通了半年的信,他们再次见面,就是结婚了。婚后,依然一个在诸暨的人民医院工作,一个在舟山的部队上工作;不过,等他转业回地方工作时,已经是连级干部了,在市消防大队当教导员,整天跟熊熊燃烧的烈焰打交道,比在海军部队上还要辛苦,只不过,一家人能长期团聚在一起了。
也因为她的身体,儿子虽然大学毕业,却不愿去外地参加工作,在本地找工作,一般性的,他又不愿意干。爷爷奶奶一辈子,都是在诸暨的街道上开面馆卖次坞打面,一直到他们去世;姐姐和弟弟的童年与少年,都是在面馆里度过的,复杂的技艺和秘制的配方,两人打小就熟稔于心。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想接过爷爷奶奶的衣钵,也开一家次坞打面馆,没想到,一家人都很支持。爷爷奶奶的面馆,早已转手他人,他们一家,只得另起炉灶。姐姐早已外嫁,婆家在浦阳江的那一边,离这里好几个街区,其实,也就在妈妈当年上班的诸暨市人民醫院附近,嫁的还是妈妈当年一个同事的儿子。经过几年的打拼,姐姐早已事业有成,她重新在他们家原来那栋房子的二楼,买了一套更大的房子,给一家人住;原来的房子,简单改建一下,变成了现在的这家次坞打面馆。前几年,退休在家的父亲,还跟着弟弟一起打理,主要是帮忙购置各种原材料。每天一大早,骑一辆自行车,呼呼啦啦跑过西施桥,到那一头的菜市场,购买最为新鲜的各种食材。打面、配菜、煎煮、烹饪、熬汤以及现场售卖,更多是弟弟与他的妻子负责。
老太太呢,她似乎对这一切了然于心,又浑然不知。弟弟说,开这个面馆,不只是解决生活问题,也是想让妈妈,一辈子生活在自己最为熟悉的地方,方便她保持记忆,找回记忆,也让她尽可能多地跟人接触,跟人交流,而不是整天把她关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样对她的身心健康,更为不利。面馆也给她安排了一份工作,让她帮客人点菜、送菜和收钱。虽然她很多时候,无法把这三件事情连接起来,她甚至都不能把自己所做的事情,与自己面对的客人连接起来。有人说,水里游来游去的金鱼,只有七秒钟的记忆,老太太的身体状态极差时,比一条金鱼的记忆,只好出那么一点点。往往是第二天一起床,她连家里人谁是谁,都不知道。
也因为当年打了太多的麻药,也有可能是家族基因的原因——外婆到了古稀之年,患上老年痴呆症,生活都不能自理,到死,都不记得身边围着的一大群亲人,分别叫什么名字,跟她又是什么关系——让她还不到六十岁,便在记忆力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她由此为自己另行搭建了一套认知与记忆系统,身上还发生了许多常人难以感受且不能理解的东西。为了让她记住身边的亲人,爸爸每年都要带全家人去拍一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面,又标注上每一个人的名字和与她的关系。很多时候,她一起床,便会惊恐地哇哇怪叫起来,指着身边睡着的一个男人说,“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爸爸惊醒过来,跟她解释清楚了,她又会坐在床上,用被子紧紧裹住自己,发好长时间的呆。姐姐或者弟弟,有时也会帮助爸爸,陪她聊天,跟她讲这个家里,她亲身经历的各种事情。他们娓娓道来,注重细节,放大温情时刻,也放大她在事件中的作用和意义。她想起了什么的时候,便会接过去说:“哎呀,奶奶明天就要过生日了,七十岁,是大寿,我得好好准备一下。”或者说;“我工作的第二年,被评上先进工作者,年终表彰时,医院奖给我一本带有毛主席语录的笔记本,还给我配戴大红花呢。你等着,我把笔记本拿来给你看。”又或者,她会突然说:“不好了,老师来电话,说弟弟在学校发高烧了,我得赶紧过去一下。”更多的时候,家里人只是把全家福照片,放在她的手上,她脸上的表情立刻活泛开来,指着身边走来走去的人说。
“你是爸爸!”
“你是姐姐!”
“你是弟弟!”
然后,一家人开心地笑起来。她的记忆在微笑中,水波一样荡漾,有时深,有时浅,有时近,有时远;过往的点点滴滴,像一块块粉红色的礁石,散布在浩渺的水域中,但总有那么一块,时常会被她记忆的波纹轻轻掠过;她便会条件反射式地站起来,走到镜子前,整理一下衣装,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一个人开门默默地走出去,站在楼下的路边,眼睛始终望着西施桥的方向。她的一生,更多时候,是被等待所填充满的。恋爱时,等待爸爸的来信,结婚了,每一周,每一月,每一个节假日,都盼望着,他能休一回假,从舟山岛赶回家,与她团聚。等他终于回到身边,不再离开时,她依然在等待,但她已经忘却等待的初衷与目的。爸爸看着她下楼,过几分钟,也跟着下去,绕着楼房转一圈,从西施桥方向,从她视线的远端,慢慢朝她走来,站在她的面前,她却把他推开,带着惶恐的眼神看他,也带着哭腔说:
“赶快走开,我丈夫就要回来了。”
爸爸从身后,拿出全家福照片,指着照片中的自己给她看,于是,她就扑进他的怀里,像个孩子一样,锤他的胸口,哭出声来。她六十二周岁那一年,爸爸请人,他当年一个叫俞龙飞的战友,而今也是山下湖那边,一个珍珠加工厂的厂长,给妈妈定制了一个吊坠。先将一个金光灿灿的金疙瘩和细胞小片,填充到珍珠贝里,等珍珠贝分泌的珍珠质完全将金疙瘩完美包裹且成熟后,再取出来,让工厂的雕刻师,将珍珠本身的质地,雕刻成一朵盛开的玫瑰花,镂空的地方,又露出黄金的材质来;金子的黄与珍珠玉润的白相互勾勒,相互渗透与包裹,成就了一种浑然天成又晶莹剔透的美。吊坠周边,又用细小的珍珠颗粒,组成一个心形,将它包围起来。这样的珍珠一共七颗,代表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姐姐和弟弟。其中代表爸爸、姐姐和弟弟的那三颗,离吊坠的距离最近,也相对要大一些。这三颗珍珠上,又各刻有一个甲骨文一样的符号,从左到右,是这样的:
这是爸爸和妈妈的秘密。一家子人,以及看到过这三个符号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问爸爸,他故作神秘,说自己也不知道,觉得好看,便刻上去了。妈妈知道吗,没有人知道她到底知不知道。吊坠和环绕着吊坠的心形珍珠,被一根柔韧的红丝线串起来,天天挂在妈妈脖子上,是妈妈生日那天,爸爸亲自给她戴上的。妈妈一开始不舍得用新吊坠,替换她脖子上自己之前购买的那条项链,爸爸便给她读了一封,是当年他们在医院见面不久,自己给她写的一封信。妈妈幸福得脸都红了,耳根子上,都飘着云霞,张着嘴,乐呵得半天都闭不上。从那之后,这串吊坠便天天挂在妈妈脖子上,任谁也拿不走。
“妈妈,”姐姐说,“给我看一下呗。”
“不给,”妈妈说,“这是我的。”
“我知道是你的,”姐姐说,“看一下就还你。”
“我又不知道你是谁。”妈妈说。
“给我看看,”弟弟说,“可以吧?”
“你自己写的,”妈妈说,“你还要看啊?”这么说着,她的脸立刻又羞红起来。
姐弟俩,笑得都快岔气了。妈妈缜密的逻辑,直接的反应,也让人搞不清楚,她根本不认识他们,还是故意跟他们逗着玩的。她神气活现地在家里走来走去,把丈夫当成了自己的公公,把女儿当成了自己的婆婆,又把儿子,当成了当年的丈夫。爸爸当年写给她的信,被她装在一个褐色的漆皮盒子里,上面挂了一把小铜锁,钥匙早丢了,盒子从来都没有锁上过,就摆在她的床头柜上,方便她随时取阅。每一封信上,爸爸的落款,都写上自己的名字,陈启明,也写明了写信的时间,时间跨度从他们相识那一年,到爸爸转业到地方工作那一年,大概有十五六年。写信的时间是哪一年哪一月,妈妈认知的当下时间,便是哪一年,哪一月;信里书写的事情,也同时将她带入当下的情景里。
“妈妈,”妈妈对姐姐说,“你进来一下。”
姐姐配合她,瞬时入情入境,跟她走到被妈妈装扮得粉嘟嘟的卧室里去——墙纸、蚊帐、床单、被褥,全都是粉红色的——妈妈返身关上门,紧张地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好的,”姐姐吞咽着口水,点点头,说,“你说吧。”
妈妈从枕头下面,取出一张照片来,没说话,先递给姐姐看,一边审视着她脸上的神色。姐姐接过来,看到的是爸爸年輕时,穿着海魂衫,戴着白军帽,站在一个军用码头上所拍的照片;背景是蓝色的无垠的大海,远处,是一个白白的点,似乎是一艘已经远去了的军舰。爸爸侧面而站,神色刚毅,眼睛盯着那个远去的白点,两撇眉毛间,蕴结着英气和无声的杀气。
“你谈恋爱了?”姐姐不动声色地问,“就是这个人?”
“弟弟介绍的,是他们的班长,也是我们诸暨人。”妈妈小声地说。
“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姐姐问。
“他又来信了,”妈妈用征询的口气说,“想请假来医院,跟我见个面。”
“可以啊,”姐姐说,“见个面好,见到人了,才能踏实交往。”
“见面那天,我想穿那件白底碎花的衬衫去上班,就是你上个月扯布给我做的那一件,你说好不好?”
“白大褂罩着,”姐姐逗她说,“人家也看不出来你穿的是什么啊?”
“他来了,”妈妈说,“我就把白大褂脱了。”
有时候,信里的时间,是弟弟出生前几个月。妈妈会从房间里走出来,跟在沙发上摊手摊脚斜躺着看电视的弟弟坐在一起,对他说:“预产期,是六月六号,你一定要来陪我,跟我一起进到产房里。”
“好的,”一样入情入境的弟弟说,“我知道了。”
“你要跟部队的领导讲清楚,”妈妈交代说,“不是我非得要你回来,我知道军人是有天职的,但是我的身体状况,跟别人不一样,有可能,我上了产床,就不能活着出来了。”
“我知道了,妈妈,没事的,放心吧。”弟弟说着,把妈妈搂在怀里。
信里的时间,也有可能是爷爷花甲之年的某一天。妈妈也会从房间里走出来,把信在爸爸面前晃了晃,说:“爸,启明来信了,他说,你和妈妈没日没夜地忙,要觉得累的话,面馆就不要开了,身体要紧。你天天骑个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的在路上跑,也不安全。在家把孙女孙子照顾好,他在部队上,工作也安心了。爸,这都是启明信里的原话。”
爸爸写这封信的年代,爷爷的年纪,也跟当下爸爸的年纪差不多,而今的爸爸,一样做着当年爷爷所做的事情,天天骑自行车,到西施桥那边,去给面馆买各种食材;爸爸听了妈妈的话,不需要入情入境,因为妈妈转述的和交代的事情,与当下自己所从事的,也十分契合。他似乎是透过几十年的烟尘,自己交代自己。他听了,带着复杂的感情,也像弟弟那样,想去搂一下妈妈,妈妈却惊恐得落荒而逃。
为了配合妈妈,重温她过往的生活,姐弟俩都偷偷看过爸爸写给妈妈的信;好多封信里,都出现过珍珠上那三个符号,但信里,却没有解释那三个符号是什么意思。要想知道,或许只能在那串吊坠上去找答案。可除了她信任的人,其他人是很难让她放心地把吊坠取下来,交给他们看的。她最为信任的人,是爸爸。不是说她的心里,一直都記得,爸爸便是自己的丈夫,那个陪伴了自己一辈子的男人。而是在她错乱的时间系统里,她在每一个心理年龄段,都能确凿无疑地,喜欢上同一个男人,且坚贞不渝。放心地让他牵着自己的手,闲暇时,在浦阳江边铺设的栈道上,慢慢地散步,絮絮叨叨地,不厌其烦地,给她讲述他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有时候,她会感动得哇哇大哭起来,爸爸便轻轻抚摸着她的背,耳语说:
“羞不羞啊,好多人看着的呢。”
偶尔,在大海边培养了钓鱼爱好的爸爸,会带她去浦阳江边钓鱼,她一开始还兴致勃勃的,盯着水里的彩色浮漂看一会儿,又觉得索然无味了,起身在爸爸的视线里,沿着江边的栈道走动。一不小心走得远了,她也就忘记了爸爸,还一个人坐在江边钓鱼呢,更不知道,自己只要原路返回,要不了多久,又能回到他的身边。她会越走越远,在法国梧桐的树阴下,吹着江风,沿着江边栈道曲里拐弯地一直走下去,不休息,也不找人问路,越走,心越焦躁。并非她已经意识到,继续走下去,会把自己给走丢了,不过是脚下乏力,身心疲惫后的生理反应。反倒是沉溺于钓鱼乐趣的爸爸,忘乎所以中,突然意识到妈妈已经离开很久了,才立即丢下渔具,飞身沿着栈道奔跑着,气喘吁吁地把妈妈找回来。重新让她认识自己是谁后,再把刚才自己四处找她,而她差点丢了的情景讲给她听。她才会真正面露惧色,紧紧抓住他的手,怎么也不愿意松开;回到家里,想到自己刚才差点走丢了,后果又该如何严重,她依然久久不能平静。此时的她,最为脆弱,也更加依赖爸爸,变成了他少不更事的女儿,眼巴巴看着他,眼里蓄满了泪水。这样的情绪,得等她美美地睡一觉起来,才能平复。但也有例外的时候,不过这一次,走丢了的不是妈妈,是爸爸。
爸爸傍晚时分,又骑着自行车,从西施桥上跨过浦阳江,去菜市场为面馆储备一些紧缺物品,再也没有回来。时间过去很久了,家里人也没意识到,毕竟爸爸还有停下自行车,在浦阳江边看钓友钓鱼的习惯;晚餐时,弟弟依然在家里的餐桌上,摆四套碗筷,等不来爸爸,弟弟,弟媳和妈妈,三个人吃开了。吃着吃着,妈妈意识到,有点不对劲,指着身边的那套空碗问弟弟:
“怎么多了一套碗筷呢?”
“那是爸爸的,爸爸买东西去了。”弟弟说。
“爸爸——爸爸还没回来。”
“没有回来。”弟弟说。
妈妈放下碗筷,一如既往地来到楼下的餐馆门前,站在路牙子上,巴巴地看着西施桥的方向。她和家里人都不知道,爸爸已经出事了。也是那个时候,月仙开着黑色的本田,从平坦的那一头缓缓从西施桥经过;左转弯后,她发现路中间躺着一具尸体。他是被一辆载重的东风大卡车撞倒,且从身上碾过去的,整个胸腔都是扁的,完全没了人形。一片青菜的叶子,遮挡住他的脸,似乎故意不让人看见。红灯闪烁的警车停在卡车身旁,警察正在驱赶围观且走得太近的人群。月仙匆匆瞟一眼,看到死者身下那摊血,乌黑乌黑的,分成几股,沿着路面的坡度,流出去七八米远。也是这一眼,她还瞟到死者所骑的自行车,以及被严重扭曲的自行车压在下面的一个蓝色的塑料菜篮子,辨认出死者的大概身份。面馆里的一家人,最后也是通过她,才知道爸爸出了事故的。此后的一周,说不出来家里哪里不对劲的妈妈都闷闷不乐的,也吃不下饭去。姐姐连着几天,放下生意,陪在她的身边。其中一天晚上睡觉时,妈妈对姐姐说:
“我们家里少了一个人了。”
“少了谁呢?妈。”
“我不知道,”妈妈说,“我们家里比以前空了。”
“谁也没少,”姐姐说,“妈妈,家里所有爱你的人,都在你身边的。”
“不对,”妈妈说,“你以前不是睡在这里的。”
姐姐听得出来,妈妈无法表达的意思是,她身边以前睡着的,是一个男人,现在怎么变成一个女人了。她问道:“妈,你要我睡哪里啊?”
“我不知道。”妈妈说。
妈妈背过身去,假装自己睡着了,再也不搭理姐姐。姐姐看着她的后背,再一次感受到了妈妈对自己的敌意。单纯的,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敌意。爸爸之外,姐姐和弟弟,是妈妈唯一信任的两个人。不管是她把姐姐当成母亲或者女儿的时候,以及把弟弟当丈夫或者儿子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是她无比信任的依靠。但妈妈在脆弱的时候,会在弟弟面前,表现出对爸爸才有的依恋,对姐姐,有时候却是无法言说的敌意。其中原因,还是姐姐开车带一家人,去绍兴旅游时,才弄明白的。
也是在这样的初冬时节,他们一起游览了鲁迅故居、周恩来故居,去坐乌篷船时,还遇到了爸爸战友俞龙飞的妻子。她跟妈妈年纪相仿,但保养得宜,看起来似乎又比妈妈年轻几岁,眉眼间,腰肢上,还藏有妖娆的风韵。当年做好吊坠后,俞龙飞还亲自开车,从山下湖给爸爸送到诸暨来,两个人在家里喝着海半仙同山烧,叙了一晚上的旧。爸爸问俞龙飞怎么不跟着来玩,女人说,他那个工作,忙啊,整得他跟太阳似的,离开他,地球都不知道怎么转了。女人带着两个年纪也跟他们姐弟俩差不多大的女儿,结伴与他们坐一条乌篷船,随后又一起在咸亨酒店吃饭。女人认识妈妈,妈妈不认识她。她跟妈妈讲话,妈妈一句都不搭理。女人也不介意,一路上,热切地跟爸爸聊各种事情,燃情岁月的过往,油盐酱醋的当下,以及就坐在眼前的儿儿女女。畅快的话语里,总是隐藏着各种隐忧,让他们始终不能释怀。一边聊,还相互碰杯,就着茴香豆、西湖醋鱼及其他几个热菜,喝下去一壶温热的绍兴黄酒。也是通过他们的聊天,姐姐和弟弟第一次知道,原来妈妈脖子上的珍珠上,刻着的那三个符号,不是什么甲骨文,也不是其他文字,而是极少听说过的彝文。
“你怎么会懂得彝文呢?”女人问。
“以前我带过的一个兵,是四川凉山的彝族,我跟他学过几句。”见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爸爸犹豫一下说。
“妈妈脖子上的那三个字怎么读?”姐姐问。
“安力古。”爸爸说。
“什么意思呢?”弟弟也急切地想知道。
“我哪里知道,”爸爸笑了,说,“我真是觉得好玩,才刻上去的,感觉很有艺术色彩,你们不觉得吗?”
“大姐应该知道,”女人转向妈妈,问她:“大姐,你知道安力古是什么意思吗?”
妈妈还是不理她,自从遇上这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后,看到女人与爸爸聊天的亲热劲,妈妈便一句话不说了。她不吃饭,埋着头,两只手在桌子底下,绞来绞去。姐姐太熟悉她这种气鼓鼓的表情和满心委屈的样子了。每次她回到家里,饭后坐在客厅沙发上,与爸爸肩碰肩地聊着什么事情时,坐在一旁的妈妈便是这副样子。她对女人的问话充耳不闻,反倒歪着脑袋,对自己的女儿幽幽地说:
“我要上厕所。”
姐姐起身,带着妈妈往厕所里去,进了厕所,妈妈在姐姐的耳边说:“我不喜欢那个女人。”
“怎么的了?”姐姐问。
“她喜欢爸爸,”妈妈说,“我看出来了。”
姐姐哑然失笑,这一笑,也解开了自己心里的谜团。她看着妈妈脖子上的吊坠,明白了珍珠上的符号是彝文,念着安力古,却又不知道安力古是什么意思。同样不知道安力古是什么意思的,还有一直在絮絮叨叨地,给朋友言说老太太故事的月仙。他们说话的当儿,被老太太追到门边要钱的青年男子回来了,一只手提着一袋青菜,一只手提着一瓶味极鲜酱油。面馆又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客人,他跟每一個人都打一声招呼,才把东西送到厨房里;这时候,月仙和她朋友的两碗三鲜面出锅了。青年人在厨房放下东西,回头给一直站在收银台边,时不时瞟一眼月仙和她朋友的老太太说:
“妈,你也抬一碗,我们给客人送过去吧。”
“谁是你妈?”老太太说。
“你啊,”青年人说,“妈!妈!妈!”
有那么几秒钟,老太太端详着儿子的脸,若有所思地笑笑。好像他们相互间,离得很远似的,她对儿子招了招手,让他贴身站到身边来,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
“那个女人,是不是月仙?”
“我不知道,”儿子说,“你去抽屉里拿出照片,自己对照一下。”
老太太听了儿子的话,真的去到收银台的柜子边,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照片看了看,这才走出来。她也在厨房门前的案板上,双手抬着一碗三鲜面,颤颤巍巍跟在儿子身后,送到月仙与朋友的餐桌上来。她看着月仙,笑得有些痴傻地说:
“月仙,真的是你吗?”
“妈,”月仙娇嗔地说,“你怎么才把我认出来啊!”
一直听月仙讲老太太故事的朋友,恍然大悟后,也跟老太太一样,傻乐起来。眼睛却盯着老太太脖子上的吊坠,看了又看,末了问月仙:
“你确定珍珠上的符号,读着安力古吗,要真是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意思?”
月仙起身,搂着妈妈脖子,在她脸上亲了一口;顺手从她脖子上,拉出吊坠,让朋友认真看了一下。朋友看后,笑了起来。他告诉月仙,自己的籍贯是贵州威宁,老家有很多彝族;他的初高中同学,很多都是彝族。他自己不是,但从小耳濡目染,也认识几句彝文,尤其骂人的或谈情说爱的。月仙不想知道其他的,只迫切地问他:
“安力古是什么意思?”
“我爱你。”朋友说着,顺手抬起单反,给站在一起的月仙、月仙弟弟及他们的妈妈,拍了一张照片。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