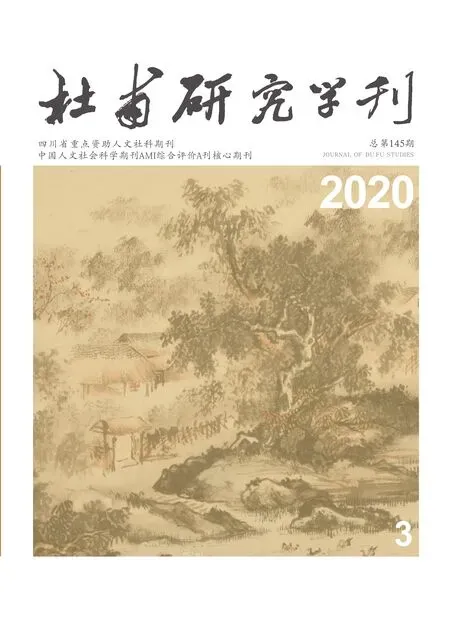杜甫乐府诗的史诗性审美
吴淑玲 颜程龙
“史诗性”是一个来自西方的美学概念,也是中国当代小说和宏大叙事的电视剧们努力实践的审美追求。对于史诗,黑格尔给过定义:“史诗以叙事为职责,需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①但对于“史诗性”作为一种审美范畴,还较少有人对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详尽的研究和界定。从对理论意义的“史诗性”理解所获资料看,国内较早对“史诗性”进行内涵阐释的是王先霈的《论史诗性》,他从“主题的民族性”“题材的宏伟性”“画面的全景性”②三个层面阐释“史诗性”。胡良桂《史诗与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在探讨人类童年时期的史诗特点(人类童年时期创世立业的丰功伟绩、主角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民族理想无意识的沉积)的基础上,对当代小说的史诗性特征概括为“关注于社会的公共生活、总是联系着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创作思维的外向性、作品内容的客观性。”③段金柱《论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史诗性追求》谈及这一审美范畴时认为其特质是:“反映和表现一个民族、时代的普遍精神和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全面深入而又生动细致地描绘社会风貌,有完整杰出的人物和崇高的美学风格。”④以上基本为传统史诗性审美的范畴。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文学书写转向日常生活,吃穿住行、柴米油盐在一个历史时期里也成为人们对生存关注的视角,成为社会变化的信号,于是,普罗大众的世俗生活也作为历史画面的再现,颇受关注,这扩大了史诗性审美的内涵。如刘大先在《何谓当代小说的史诗性》中提及“普通人的幸福生活作为目的的总体性思考,体现出当代小说的史诗性所在。”⑤这些潜意识审美的变化,被美学专家捕捉到,开始建构新的审美范畴,其中赵彦芳对现代美学意义的“史诗性审美”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建构,其《史诗性范畴的美学意蕴及精神寻踪》认为:
作为审美范畴之一的史诗性,广泛存在于各种叙事艺术中,是艺术价值的一种重要尺度。……史诗性的传统审美特征体现为民族性、整体性、英雄性、全景性等四个方面。在后现代语境下,与史诗性相关的进步叙事、宏大叙事和英雄叙事等被抵制,史诗性变异为后史诗,呈现出平民性、日常性、世俗性等特点。⑥
但整体性和全景性并无本质区别,日常性和世俗性关联甚密,故上段应精炼为传统史诗审美的民族性、英雄性、全景性和后史诗审美的平民性、日常世俗性。此文发表于中国文学理论最高级别的刊物《文学评论》上,可以视为对“史诗性审美”这一审美范畴的内涵的规范性定位。本文拟对标这种规范审视杜甫乐府诗⑦。
杜诗具有“诗史”价值已为学界公认,研究者颇众。查阅杜甫与“史诗”“诗史”相关的关键词所获得的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杜甫诗歌“诗史”内涵的文章,概括而言主要是三个方面: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反映了诗人的生活史,是具体而微的历史画面的再现;一类是研究“诗史”的来源及其属于杜甫专称的过程,延及不同时期对杜甫诗史的接受(或认同或反对)。第二类问题与本文关系不大。第一类更多是以“什么是”“写什么”为目标,且学者更多关注重大事件、实录精神、生活画面,依然是传统审美上的理解,虽然其中也有少数学者谈及写自身、写日常,但尚未延及审美范畴视域。若从“史诗性审美”视域全面感受杜甫乐府诗的美学意义,似乎还需要再做一些工作。故此,本文根据新变化了的对“史诗性”审美范畴的认识,对杜甫乐府诗进行全面的审美观察,以期方家指正。
一、杜甫乐府诗以“和”为本的民族性
杜甫乐府诗整体呈现对和平安宁生活的无限渴望,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和”为美的集体意识的诗化呈现。
相对于海洋开拓文化和海盗掠夺文化,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更注重本土劳作,因而更热爱和平,以“和”为本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和民族性特征,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典籍里,充斥着大写的“和”字,那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平的向往,是中国“和”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⑧“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⑨“公称丕显德,以予小子扬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师;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⑩“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从这些元典中,不难体味到中华民族集体意识中对“和”的执着的肯定和追寻,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性中的趋“和”因素,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中就是对和平安宁的良好愿望,这一点在杜甫乐府诗里体现得非常充分。
杜甫乐府诗以“和”为美的追求目标,首先在于对和平生活的深刻眷恋。杜甫生在和平年代,成长于大唐盛世,对盛世和平的记忆深入骨髓,他在晚年的七言古诗《忆昔二首》其一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将开元盛世的和平安宁作为世间理想。但“安史之乱”将这一切毁于一旦,令诗人心痛不已,他除了反映战争的罪恶,更深情地传达了对开元盛世的无限怀恋:《无家别》中的贱子“归来寻旧蹊”,“旧蹊”是他记忆中家乡的美好景象,但已经是“园庐但蒿藜”,毁灭了他怀揣的对“旧蹊”的温暖,在这破灭中能够感受到贱子和诗人共同的对往昔的无限眷恋;《垂老别》中的老人“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忆昔”二字,引发了对开元盛世的美好回忆,这位生活在开天盛世四十余年的老人,感受着今天的悲哀,他“迟回”中的叹息,是对盛世时代的无限留恋和无奈挥别,而这也是他在“子孙阵亡尽”后发出“焉用身独完”悲号的原因,是他“投杖出门去”“长揖别上官”的责任担当,是他为寻回“少壮日”的生活做最后之搏的精神动力。《蚕谷行》中,诗人大声呼唤:“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在杜甫的审美理想里,销甲助农,农田尽耕,蚕谷有成,男耕女织,方是他《忆昔二首》中的盛世美景!“焉得”之问,是求而不得的深层忧虑,潜藏着对和平生活的无限期望。
杜甫乐府诗以“和”为美的追求目标还表现在他对战争的特别厌恶。不争,休战,方能“生生”。但唐玄宗后期却是四处征伐,穷兵黩武,造成了大唐社会诸多不“和”。杜甫对这种不“和”反映敏锐,写于天宝十一载(752)的《兵车行》就揭示“武皇开边意未已”造成的农业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通过参战士卒的絮絮叨叨,表达了对无休止的征战的强烈不满,用“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的画面揭露统治者不肯“生生”的罪恶。写于天宝十二载(753)的《前出塞九首》以士卒“戚戚去故里”的形象传达不愿参战的情绪,以“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的指责表达对开边战争的不满,以“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的议论,表达了治国不该以杀人为手段,更不应该以拓土为目的,而应该有更高明的“制侵陵”手段。这几乎可以看成杜甫“战胜于朝廷”的观念。《后出塞》中,他用“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直指统治者开疆拓土满足私欲的目的,破碎了期望“战伐有功业”“及壮当封侯”的参战“男儿”的人生目标,揭开了开疆拓土的战争的真实丑陋的一面。而当避不开的战争发生的时候,他一方面通过战争的惨烈场面曝光着战争的罪恶,一方面更希望统治者重用真正有能力的将领,以达到“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的和宁世界。
胡良桂在谈及小说主题的民族性时说:“史诗性长篇小说主题的民族性,首先要求作者对自己的民族怀着深沉炽热的爱,他内心深处,积淀着世代相传的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忠诚的儿子,与本民族的人民大众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并谙熟本民族的历史,熟悉本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稳固的心理特征,把握住本民族的灵魂。”这种民族性,在杜甫的诗歌里,无处不在。杜甫是深爱大唐王朝,深爱大唐人民,仅就他的乐府诗而言,在反映民族灾难的文字中,无不潜含着对国家和民族的爱,他不断提及盛世王朝的繁荣,或者描绘期望的和乐景象,或者揭露战争的罪恶,都彰显着他对和平的渴望,是对我们民族文化里“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和”的民族性高度契合。
二、杜甫乐府诗的英雄审美:大唐不灭之魂
传统意义里史诗中的英雄性往往指向伟岸形象、崇高品格、奉献精神,杜甫的乐府诗并没有像西方史诗中那样的英雄,也不以歌唱英雄为主,但在杜甫的部分乐府诗中,史诗性审美的英雄性仍然存在,它体现在,当面对国家灾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英勇无惧、甘心奉献和勇于担当。《悲陈陶》中“四万义军同日死”的惨烈场景,《悲青阪》中“青是烽烟白人骨”的悚惧场景,都展现了无数生命的逝去,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不惧死亡和勇于面对死亡的英雄主义精神。“血作陈陶泽中水”,“青是烽烟白人骨”,分明是对英雄的无声赞歌。《新婚别》《垂老别》则是用人民的参战表达了对平叛的支持和勇于面对死亡的英雄般心理。《新婚别》中的女子,丈夫在新婚当晚被抓,她不是没有抱怨,但在衡量形势之后,她反而鼓励丈夫“努力事戎行!”她当然知道战场的危险性,但她却将“兔丝附蓬麻”的小女人心态变成了识大局、顾大体、稳定前线军心的烈女,以“对君洗红妆”的方式与丈夫诀别,等待丈夫凯旋。《垂老别》中的老兵,深知“安史之乱”的糟糕形势,邺城兵败带给他的是“子孙阵亡尽”的悲惨命运,但看着“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满目疮痍,这个经历过开天盛世的老人浩叹一声“焉用身独完”,便“投杖出门去”“长揖别上官”,为追回当年的盛世社会“安敢尚盘桓”,勇敢地去面对那个身不可独完的世界!而他“卧路啼”“衣裳单”的老妻,并不要求他留下来照顾自己,也没有牵牵扯扯地不忍分离,而是明知丈夫“此去必不归”,却还在劝其努力加餐饭。他们是普通的百姓,是平常人,但残酷的现实激发了他们身上的英雄气概,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大唐王朝中兴的希望。
三、杜甫乐府诗的全景性:灾难社会的整体映像
对于史诗性的长篇小说而言,其全景性不仅要求有宏大叙事、宏观伟构,而且要求将众多人物、无数场面熔铸在一起,形成巨大的艺术概括力,造成统一的全景式画面。虽然诗歌不是小说,不可能拥有小说那样多层次多视角的宏大场景,但诗歌一样能够反映时代的全景。
赵彦芳《史诗性范畴的美学意蕴及精神寻踪》对史诗的全景性认识是:“从空间来说,大到整个世界的广大背景,小到具体人物的具体生活场所。”以此审视杜甫的乐府诗,其关注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自上而下各色人等的社会生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生存状态的方方面面,背景不可谓不大,场景不可谓不具体,其全景性体现在可以让读者全方位了解当时的社会。
杜甫诗歌总体而言还是抒情性作品为主,但其乐府诗叙事功能很强,关注客观社会更广,反映社会阶层更多,就其反映历史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完全可以视之为拥有全景性的特点。如果说,杜甫的全部诗歌更多诗人自我生命的轨迹,反映社会的深度更多是透过诗人的体悟,而其乐府诗则更多客观地、广泛地、深入地关注生活,是当时社会的原生态反映,其史诗性更接近历史全局的本真,更能触及社会矛盾的本质,更能昭示历史的变迁。就人员层次而言,有统治者、王朝军队、安史叛军、乱中小吏、苦难百姓,自上而下各色人物;就历史性场面而言,帝王出逃、贵妃暴死、王孙落难、万卒赴死、战场白骨、凋敝田园,均有所表现。从史诗性审美的全景性视角审视,无论场面宏细、人物层次,他的乐府诗都是全景式反映,他描绘了战乱中的具体场景,涉及社会的各阶层人物,甚至国家的整体策略。杜甫曾经拥有的最高的实际职位,也就是一个从八品上的左拾遗,后来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远离朝廷,他更多的时间充其量就是一介士子,但他时刻关注时局,关注军国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如《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基于国家安定、人民安宁、人心所向,对开疆拓土提出质疑,《塞芦子》《潼关吏》针对国家防御策略提出的卡关固守思想,《留花门》基于民族相处认知而对使用回纥兵平叛的后续问题提出担忧,都能体现出其审视社会时总揽全局的特点,这是全景叙事所必须的关注视野。
就反映社会的深度而言,杜甫乐府诗对民生的关注也是全景式的,通过他的乐府诗,可以了解唐王朝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安史之乱”前后,杜甫从京都到河南,从关中到秦州,从秦州到成都,从成都到梓州,从梓州回成都,从成都到夔州,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关注到所到之地的民生,记录揭示了社会生活中最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兵车行》)的凋敝凄凉;河南相州一带因战乱“园庐但蒿藜”“人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无家别》)的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四川梓州农村“西望千山万山赤”(《光禄坂行》)的颗粒无收景象;夔州妇女“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负薪行》)的苦难生活;川西近蕃地界“大麦干枯小麦黄,妇人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大麦行》)的惨遭劫掠等等,都是记录当时社会乱象横生,揭示社会生活中的深层矛盾。从他的乐府诗中,我们看到的既是具体的人和事,也是整个社会人和事的缩影,尤其当我们把这些乐府诗作为一个集合来看时,它就具有了宏大叙事、众多场景、完整社会的属性。
四、杜甫乐府诗的平民性
艺术上的平民性主要指向作家的艺术精神。杜甫的出身不能算贵族,但也绝不是普通的平民,“奉儒守官”是他的家庭背景,也是他的身份底色,诗书世家才是他所标扬的值得骄傲的出身,“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也是他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虽然说过“杜陵有布衣”,但最后还是以“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与“平人”区别开来。之前的文学研究有指杜甫为“地主阶级”之说,并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他自己把自己放在士阶层确是事实。但他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体验了最底层百姓才能体验到的寻求生存之路时失却尊严的可悲可哀,故而他的诗才有了平民性的基础。
“平民性主要分为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方面,它采用雅俗共赏的语言和文体,直接关注现实世俗生活,抒写平民性情感,揭示平民的生存境遇。”这是王珂研究打油诗时对平民性书写做出的判断。杜甫的乐府诗并非打油诗,但就语言和情感而言,可以用王珂所提供的平民性方向来审视。就写什么而言,杜甫无疑在用乐府诗反映普罗大众关注的社会生活,这无需多言。而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则需说上几句。
首先是语言选择的平民化色彩。杜甫的律诗是他一生成就最高的诗体,是后世典范。他自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其诗语言或华丽典雅,或沉郁厚重,或严谨精练,或淳厚精警,或清新俊爽,典范佳制超越唐世众多诗人,但多是书面语言,而其乐府诗选择的是最接地气的对话体,最适合普罗大众阅读传播,读起来口语化色彩较浓,自然流畅。这是杜甫乐府诗平民属性的重要标识。
其次是作者身份的设定。杜甫的乐府诗,有些是写在诗人作为普通士人身份时,有些是写在诗人为官时,但诗人将自己置身于广大民众之间,以其民众一员的身份属性关注普通百姓所面对的社会生活和沧桑巨变。杜甫关注底层人物在战争中的遭遇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态,这使他的诗歌更接地气,更具平民化色彩。
与杜甫同时代的诗人储光羲、高适也有关于玄宗时期的拓边战争和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的诗歌作品,不过与杜甫作品差异较大。如储光羲,涉及战争的诗歌不多,仅有一首关涉百姓,即《效古二首》其一:“大军北集燕,天子西居镐。妇人役州县,丁男事征讨。老幼相别离,哭泣无昏早。稼穑既殄绝,川泽复枯槁。”写到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而到安史乱中,仅有的几首涉乱诗,却没有关注平民,如《登秦岭作,时陷贼归国》只是关注自己而已;《观范阳递俘》只是关注“四履封元戎,百金酬勇夫。大邦武功爵,固与炎皇殊”;《次天元十载华阴发兵,作时有郎官点发》只说“三陌观勇夫,五饵谋长缨”“神皇麒麟阁,大将不书名”,均不及百姓。高适本是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边塞诗人,他较早关注现实征战生活的《燕歌行》成为边塞诗的名篇,其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等对士卒的关注赢得了后世多少赞叹!但这类诗作在高适的诗篇中并不多见,他更多关注功名,关注自己,如《古大梁行》:“全盛须臾那可论,高台曲池无复存。遗墟但见狐狸迹,古地空馀草木根。暮天摇落伤怀抱,倚剑悲歌对秋草”,虽有战火遗迹,却无百姓生活。高适反映“安史之乱”的作品很少,仅见的一两首价值不大,如《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竟然为那个睢阳之战不救张巡、许远的小人唱赞歌。
储光羲《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高适《李云南征蛮诗》)语言和身份设定都在高层:储光羲说李云征南蛮是“斩伐若草木,系缧同犬羊”,归来的辉煌是“龙楼加命服,獬豸拥秋霜。邦人颂灵旗,侧听何洋洋”;高适认可“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的征南诏战争,希望征战将领“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而杜甫的乐府诗如前文所述更关注普通百姓在战争中的苦难遭遇,他写的是他亲见亲闻亲历之事,仇兆鳌注引胡夏客云:“《新安》《石壕》《新婚》《垂老》诸诗,述军兴之调发,写民情之哀怨,详矣。”
总而言之,“其实从社会角色看,贯穿杜甫一生的都是平民化的角色,不仅跟地主生活不沾边,甚至很少真正进入过统治阶层的行列。”他乐府诗的写作视角及写作语言,都是平民化诗人的身份。
五、杜甫乐府诗的日常性:世俗生活作为社会图景入诗
日常性原本是一个哲学术语,指人的日常生活对人性的潜在塑造。依据西方一些哲学家如列斐伏尔等的表述,人是生活在每日所交集的生存环境中,并在这些环境的差异和冲突中建立互相的关联,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场域中确立人的品性。它具有平凡的内涵,应该不涉及重大事件,因为重大事件往往带有突发性、重要性、非常性、不确定性、不平凡性。赵彦芳《史诗性范畴的美学意蕴及精神寻踪》谈及当代写作时的日常性时说“传统史诗性作品中的宏大题材被世俗的日常生活所代替”时,似乎还多少有些遗憾,认为这些是反史诗性,但同时承认“后现代对传统史诗性的反叛、解构并没有终结史诗性,反而给史诗性带来诸多变异和可能性”,并呈现出新的特点,日常性就是其中一种,其表现为世俗生活折射社会原貌。
关于世俗性的含义,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笔者理解的世俗性,应该是与神的庄严性、崇高性、神秘性等相对应(不是相反的)的普通性、凡俗性、人间性等,这些审美特性,均与杜甫乐府诗的日常性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所谓普通性,是指这些富有日常场景的乐府诗中,没有庄严的正义和是非曲直,它只是生活的最普通最一般的生存状态,砍柴,打猎,游玩,种粮,求食;所谓凡俗性,是指这些诗作中不具备神的高高在上的救世姿态或崇高的道德制高点,而是关注最凡俗的聊以为生的吃喝拉撒睡;所谓人间性,是指这些诗歌中不是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不是英雄史诗中英雄的高尚情操和无所不能,而是最能体现人间烟火气的生活起居、柴米油盐。
我们无意于用今人的后史诗性概念去扣杜甫的乐府诗,只是希望以日常性世俗性审视杜甫的乐府诗,认识杜甫乐府诗具有的后史诗性的特点。由此审视,大约《贫交行》《大麦行》《光禄坂行》《冬狩行》《负薪行》《最能行》《岁晏行》《蚕谷行》等,能够发掘日常生活环境的差异和冲突,属于日常性生活话题,反映出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社会生存状态。
以《大麦行》为例。该诗展示的是百姓劳动果实被劫掠的情景。韩成武师分析说:“大雨解除了旱情,农民辛苦劳作,终于迎来了麦秋。可是,川陕交界的四个州,集州(今四川南江)、壁州(今四川通江)、梁州(今陕西褒城镇)、洋州(今陕西洋县),又发生了胡羌前来抢收的事。百姓无力抵抗,蜀中官军又不肯涉远前去保护,眼睁睁地看着粮食被抢走。杜甫闻知,痛愤地把此事记入诗中:‘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岂无蜀兵三千人?部领辛苦江山长。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归故乡!’(《大麦行》)”在这首诗里,边域百姓的日常生活被搅扰得不得安宁,而军队又不肯为他们奔走,直逼得这些老百姓希望长上翅膀远走他乡。这既是对党项、奴剌等窃掠行为的控诉,也是对军队不肯护佑百姓的揭露。诗人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寻求万千百姓的出路,是呼吁关注,是引发同情,是希望解决,是在日常叙事中主动承担一种社会责任和使命。还可以再以《负薪行》进行一些分析: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
此诗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这是一位身遭丧乱不能出嫁的女性的悲剧,用韩成武师的话概括之:“夔州还有一种风俗是男人当门守户,女人外出劳动。她们砍柴,背盐,干着本该男人们干的重活,却又因战乱,无夫可嫁,有许多人四五十岁还没有婆家。”从世俗性认知来看,女子长成嫁人,是正常规律,“四十五十无夫家”,是对“食色,性也”的世俗生活的破坏,因丧乱而不嫁,则把这种对世俗生活破坏的原因归类到深层的社会矛盾。在来自中原的杜甫的认知里,男人主外,女子理家,而夔州女子却因为劳累太甚伤害外在形象,双鬟垂颈,野花山叶为钗,丑老难嫁,令人同情。这是普通的、凡俗的、人间化的悲剧,是日常场景中一个时代的特定地域的生存状态的形象化描述。
生活在人间,生活在乱世,生活在困窘的状态下,生存必然是最现实的日常问题、世俗问题,似乎并不高雅,但却最具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下层社会的生存状态。有人说,日常世俗叙述也能见出作家品性。如果我们一定要用日常性世俗性审视杜诗和杜甫品性,那么,杜诗的日常性世俗性叙述则是杜甫品性的一种体现。杜甫乐府诗的日常性审美、世俗性审美,让我们从普普通通的生活中品味出杜甫所经历的时代的酸辛。
从史诗性审美视角综而观之,杜甫的乐府诗拥有反映民族心理的特性,能够揭示人民在平叛战争中勇于牺牲、为大家舍小家的英雄气质,将自上而下方方面面的唐朝全景性生活展现在我们面前,作者写作身份具有平民性属性,也能够从日常的、世俗化的生活中折射时代风貌,其作品具有超越以往的深刻,反映了时代巨变社会的生活本质,全方位全视角地描绘出那个时代的生活景观。相对于那个时代的其他诗人,杜甫乐府诗的史诗性特质让他疏离于唐代其他诗人乐府诗的更重抒情、更追求高华流丽的特点,让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代乐府的叙事功能,反映宏大叙事视野里的沧桑巨变和后史诗性视野下的庸常社会生活,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时代的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画面。
注释:
①[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7页。
②请参阅王先霈:《论史诗性》,《社会科学》1984 年第6 期第111-114页。
④段金柱:《论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史诗性追求》,厦门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刘大先:《何谓当代小说的史诗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94页。
⑦杜甫乐府诗的准确数字,目前学界依然有争论。本文依郭茂倩《乐府诗集》和葛晓音先生研究成果,并加入自己理解,确定杜甫乐府诗53首,旧题乐府22首:《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前苦寒行二首》《后苦寒行二首》《少年行》三首、《大麦行》;新题乐府31 首:《兵车行》《贫交行》《沙苑行》《丽人行》《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哀江头》《哀王孙》《洗兵马》、“三吏”“三别”、《留花门》《光禄坂行》《苦战行》《去秋行》《冬狩行》《负薪行》《最能行》《折槛行》《虎牙行》《锦树行》《岁晏行》《客从》《蚕谷行》《白马》《天边行》。与葛晓音《论杜甫的新题乐府》不同处,葛晓音断定杜甫新题乐府32首,其中包含《大麦行》《自平》,不含《天边行》。笔者认为《大麦行》旧题虽郭茂倩根据童谣推测,但没有新证据前依然归入旧题乐府,《自平》从音律、节奏、风格看都不类乐府,也不是叙事性三字题,不计入乐府。本文作者之一吴淑玲与韩成武合作论文《杜甫乐府诗的体类特征》统计数字有误,含《自平》,现纠正之。《天边行》依据葛晓音先生定义,归入新题乐府。则实得杜甫新题乐府共计31首。
⑧(宋)朱熹:《周易本义》,《新刊四书五经》本,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