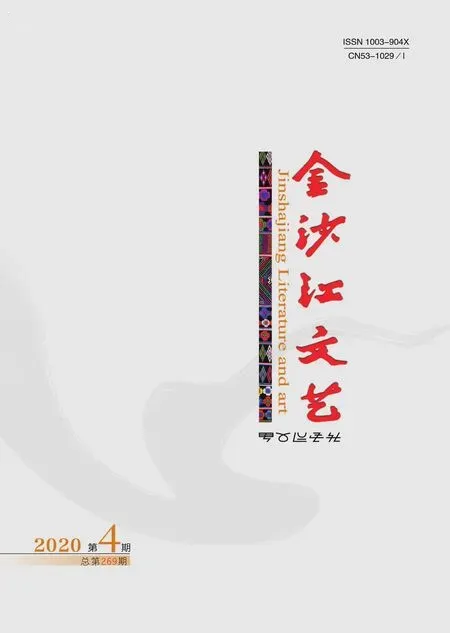娥眉
苏杨文静
冷白的月似一枚亮亮的小铜钉子敲在夜空上,横云浪荡漫渡,城郭寂静无声。
娥眉苦。娥眉照灯埋头验看自己水灵葱段般的指头,蔻丹抹不匀、晾不透,只开个脂粉盒子便刮出一道痕。烛火晃得苟延残喘。愁兮愁兮,娥眉心烦意乱,摔开妆奁,又就着昏黄的铜镜细细打量自己。
鹅蛋状脸盘子,灰浓纤细两道柳叶弯眉,微厚的嘴唇连了两道浅浅的鼻纹,端端也算个中上之姿的美人。她掀了掀眼皮,两手捏起兰花指在左右脸颊上往耳朵一提,妄图消灭嘴侧两道沟壑。
疲啊疲,不过这段日子窗外猫叫春吵得娥眉晚睡了些,她便有疲态,就连下巴上都隐隐作痛地泛了红。
怎么着呢?才芳龄二八好女,便瞧着像隔壁二十五的如画了。
她直勾勾盯着镜中的自己出了神,心情抑郁,一股烦躁怨气在胸口起伏。梆子顺着院外敲过来,一声声硬戳戳地听着心烦意乱,打更的人不紧不慢地捏着嗓子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那声音在巷子尽头竟还有回响,灌着娥眉本就不怎么耐烦的耳朵。
“燥你娘的屁!”娥眉的尖嗓子与砸窗户声一并在黑夜中响起,打更人被吓一跳,茫然四顾又不晓得谁骂了自己,只得跺脚喷了几句粗话,继而将梆子敲得更响地顺着巷子走远了。
长夜漫漫,娥眉躺在榻上清醒无比,只是死死瞧着镂花木窗格透进来的月光,一寸一寸地微亮。她想抬手抓一抓,却伸手到一半又觉得可笑,转而无力捂住自己的眼睛。
没有出路,没有出路。如何是好?
窗外隐隐传来似是小儿啼哭的猫嘶,她烦闷地用力翻过身,阖眼只求速速安眠。
翌日清晨,娥眉躲了吊嗓子的早课,就着淡黄晨光在房中梳妆。
娥眉听了隔院中咿咿呀呀此起彼伏的高唱声,一阵嫌恶从心底涌起,竟觉得一声声地像是村中的大鹅叫。
“吊什么嗓?再吊一二十年又未必成邱桂云!”她嘟嘟囔囔,往窗子外隔院的红墙扔了个白眼。再用起功来也不过是在这个小戏班里矮子里装高,鸡头还够不上凤凰尾巴上一根毛。
将手心里的胭脂打在两腮,她对着昏暗铜镜媚眼如丝,只嫌眼下因睡不好青了些。
“怎么着呢?又没有谁近看。”再往鬓上簪了朵珠花,还算满意。漱了杯早茶,拎着帕子娇娇柔柔地下了楼去。
戏班里的秦山迎面过来了,一双温厚软白的手讨好地递上一包糕点:“娥眉还未吃早饭吧?这是我方才西街买的新鲜桂花糕呢。”娥眉眼波水汪汪一转便抿着樱桃小嘴笑开了,温柔万分地接下:“谢过秦山哥,这几日班里忙,累着你了呢。”
隔壁吊嗓子声似乎都软了几分,小猫尾巴似的一下一下挠。眉目清秀的少年挠挠头笑:”没有的事。“娥眉摇摇帕子便弱柳扶风般与他别过,眼角眉梢处处摇曳。转回屋中拆了盒子,她轻轻柔柔拈起一块还冒着热气的糕点,饶有兴趣地回想秦山害羞的神态。
秦山哥真俊。她歪头扶着香腮,想着想着便笑了,又一转念:俊是俊,就是穷,还呆。顾及此,娥眉凝眉审视着两根手指间四四方方的糕,忽然失望,只觉寡淡。
她重开妆奁,复一丝不苟地描眉画眼,再郑重地抿上唇红,只见镜子里的女子也只刚刚算得明艳。若不打扮也是这般好看便好了,这么想着,娥眉手摸索镜边,又寻思起了邱桂云。
邱桂云上次唱《长生殿》的鞋是缀银丝流苏的,裙上也是烟里雾里的淡色莲花,那么素的行头怎么就衬托出那么浓的一个美人?娥眉百思不得其解,只想着邱桂云的衣裙,自己便也想穿一身莲花,指不定能别样的好看呢?
娥眉在熏笼的烟雾中肃静了,听闻邱桂云那一身缎子都是德隆庄上品,一匹便已经三两银子,贵得人心尖儿颤。娥眉当机立断,转身便翻箱倒柜寻觅自己家私——几个荷包寻一遍,妆奁里外摸一遍,连绣花枕头背后都细心搜了。
统共只得些闲散银子,娥眉小心翼翼地用小秤杆称量,共得一两三钱。
一阵凉风从窗外冲进来,刮得娥眉鼻头一酸,也不顾头上什么珠花了,直直便往榻上倒。娥眉算个美人,且是小戏班子里最出众的那一个姑娘,嗓子亦不错。当戏班子接了什么庙会或是小户人家的邀请,她也能非常出彩。
不过,天下戏班子千千万,每个戏班子里都有个最出众的小旦,娥眉淹没其中,不过沧海一粟。每个这般的女子或多或少有些骄矜,或多或少获得过些赞美与殊荣。当然,这骄矜亦是小家子气的骄矜,是夏夜里的萤火和星子,挥一把轻罗小扇也能吹灭几枚。
众星捧月,千千万万个娥眉千千万万枚星子,月亮却只有一轮,那便是金光辉煌云里雾里的邱桂云。
邱桂云是最受追捧的角儿,她的戏虽未一折千金,但听闻上回相国府寿宴用二两金子才请动。据传当晚相国府灯笼汇成了河流,马蹄声迎来送往络绎不绝,宾客各色穿戴能晃花了人的眼,拜寿的全是四方权贵,那才是真正的车如流水马如龙。
而寿宴人声鼎沸不过一刻,蓦地一声洞箫便不知何处飘起,四下渐渐静了,只见原先铺天的喜庆绸布一层一层坠落,像闺阁的三进三出,曲径通幽,犹抱琵琶。
最后一方绸幕款款叠落,露出了灯火昏黄的戏台。玉一般的美人如月低垂,微一动身,层层叠叠的藕色纱衣跟着飘起,那纱摆上用水墨朦朦胧胧描了相国府鳞次栉比的亭台楼阁。她眸光流转,一对笼烟眉似蹙非蹙,泼墨般的长发微挽,似乎可抬手邀明月。端的神仙般人物。
邱桂云不爱做戏折子里的寻常打扮,她唱腔名动天下,只有别人仿她的,她从不学老样式。娥眉自认只是姿色上略逊于邱桂云,然千千万万枚星子都这么想。
穷。娥眉揉着额角,心里难受。一两三钱,连半匹德隆庄的缎子都买不到。“怎么就无论如何都穿不起了呢?怎么人不及她,衣服也不及她?莫不是一辈子都比不上她?”娥眉气恼,竟下了狠心,翻出自己所有不常戴的镯头首饰草草塞入包袱便要出门。
“首饰就是为了给人看的,你们不常见人,那不如我当了你们。”娥眉木着喃喃,脑子发起烧来,一心要典当了它们去换得与邱桂云原模原样的一匹布。
正是正午,日头正盛。娥眉面色严峻,一个人疾步走在檐下,只觉人海苍茫各自奔忙,自己连件想要的衣服都穿不起,是微不足道却令她几欲落泪的凌辱与委屈。
要典当的首饰里有什么呢?有她当时心心念念硬是攒了三月的赏钱才小心翼翼捧回来一次都不舍得戴的翡翠耳坠子,有唱得满堂喝彩时主人家赏赐的老玉镯头,还有婵娟嫁人时边哭边哆嗦着塞在自己手中的银丝帕。
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几件家当,她夜里掰着指头都能数清却仍然为之窃喜的物什,而今竟要全没了!可是娥眉有什么办法。她低惯了头,竟已然酿出了一腔无根仇恨,而今只是耳目发烧含着热泪地想要邱桂云那一身行头。即便她不会穿着出门赶集去,但好歹能贴着身好好地摩挲一下德隆庄的缎子究竟是多么好的缎子。
她从来没穿过德隆庄的衣裳,她穿不起,但一想到自己可能一辈子都穿不起,酸涩的泪就已止不住要外涌。
手中的布包越攥越紧,娥眉一手凉飕飕的汗。
迎面颠颠地跑来几个追逐打闹的孩童,撞得她一踉跄。娥眉本就凝神思虑,而今一撞却如同被打醒般,她瞪着眼睛,忽然如同一盆烫水浇在雪上刺啦啦响后的无望疲惫,步履蹒跚地挑了块阴凉便坐下。
“姑娘有什么烦心事?”不知多久,一个嘶哑的声音忽然于小贩叫卖的间歇在娥眉身旁响起。她一时未反应过来,只是下意识往身边望去。
是个身着破旧污脏道袍的老道士,正好挡了日头,只剩一圈勉强看得清的模糊黑影。娥眉心生厌烦不想搭理,青天白日里又是哪里来的老神棍想骗人钱财?
日头更盛了,周围喧嚣声音仿佛大起来,娥眉心口像是被谁一扎。等她蓦然清醒,那老道士已经不见,街市小儿嬉闹声、小贩叫卖声与行人絮絮的话语如同织机上的经纬,一梭又一梭结结实实、密密匝匝地堆砌,晒着正午的太阳似乎蒸腾出梦般的蒸汽与朦胧。她晃了晃脑袋,屈指揉着额边,余光却瞥见不知谁掉在自己跟前的一个香囊。香囊普通平常,石青色的缎子上绣了对锦鲤,闻不出是什么香气,娥眉只觉熟悉。
与她从西市称来、总留不住多久气味的月季桂花丸子不同,这是一种有根有枝有节的、实打实的扑鼻香。
她紧紧捏着那枚香囊,手微微颤抖,将它凑近鼻端嗅着回去吧。人忽然像是浮在这人世上的粟子了,像是所有朦胧的吵闹托起了她,一睁眼竟是泪眼婆娑起来。大热的日头将所有不忿与狰狞给晒得发亮,亮到刺眼,刺得她忽而脱了力气,不过瞬息便在这污浊尘土里偃旗息鼓。
手慢慢垂下去,娥眉的眼神倏然黯淡熄灭,心内莫名空无一物,只一个念头——不典当了。
小院中灯火通明,娥眉扶正发髻,画了浓墨重彩的妆,耳坠子翠得像湖泊。她抿着殷红的唇对镜眼波流转,金步摇的流苏垂在耳后,微微摇曳出一种逶迤的姿态来。左右顾盼,竟这般满意。
饮酒作乐声从帘外与脂粉气的夜风一并拂来了身畔。葱白的手指捏起个兰花形状,将这靡靡的一帘烛光掀起一缝,是邢妈妈从廊那头喜气洋洋地来了,嘴里唤着:“娥眉,焦公子要见你呢。”
“这便来了。”她娇滴滴回,轻盈盈起身向邢妈妈迎去。
焦公子是开春方来此地,传闻家底颇丰,长得也清俊。正是刚建成新府邸,请了这戏班子去热闹一番,娥眉用一把软得跟水般的嗓子赢了满堂喝彩。焦府的老太太亲将她唤到跟前慈爱地夸过一回,正在兴头,偏头便将身侧美妇人鬓边的金步摇拔下赏了娥眉。当时焦公子坐在堂侧,望着娥眉笑得春风和煦。她退下前,脉脉地往焦公子悄悄望去一眼,今日这光景,便是他领了她那一眼的风情。
待得娥眉款款走进,灯火通明间她便一眼撞见焦公子的笑,他束发端正,一身天青的衣衫合了娥眉的意。娥眉微微漾起嘴角,悄无声息地将灯下焦公子的一身行头打量个遍,发冠上一支白玉簪也似是上品。
她的笑意淌到眼底,不经意将下颌含低了些,施施然坐在了焦公子的对面,上次焦母赏的金步摇蓄着光,落在焦公子眼里更多一种颜色。
见方从月色中出来的俏人儿无声地含羞望着自己,焦公子端起酒盏:“上次贵妃扮相的眉眼过艳,没望真切,今宵再见,娥眉姑娘真是美人。”
趁着低头起盏,娥眉带着三分得色的眼珠子微微往眼底溜了一转,再徐徐抬眼:“公子谬赞,奴不敢当。”
香得流蜜的酒淌过喉咙,絮絮的话语碎纸似缠绵飞进娥眉的耳朵里。她作态地歪在桌上,手撑着香腮,眨出了满眸的水光,只似是无辜地拿着焦公子望。她觉得此刻的自己便是朵鲜花儿,芍药或者牡丹什么的,香喷喷又娇俏俏,美得如在云雾中,忍都忍不住地想要卖弄,那些尖刻躁动的心绪仿佛全沉在脑后,已被她馥郁四溢的枝叶与香气全部覆住。而焦公子便是赏花人好了,他只需看着,或可抚一抚,再或者便将她撷走了也可呀。
娥眉醉眼望出去,已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那端盏的手指像要烧起来,烧出一寸寸翎羽来。抑或她便是那酒,沸腾着,想要把自己泼出去了。
焦公子俊,真俊,和秦山那穷呆似的。她闭着眼,仰头笑出几分志得意满来。
酒香扑得人昏昏,梨花一团一团沉沉抱起来。
月亮圆满一轮,静静悬着。
春末,梨花凋零的时节,娥眉由一抬小轿进了焦府,成了妾。
秦山很是心痛了一番,在戏班子小院里紧紧扯着娥眉的衣袖不肯言语,从来脉脉含情的眉眼似乎一不留意便要下泪。娥眉新妆,一对眉毛挑得高高的,亦挂起假意不舍的笑,抚着秦山的手背,口中念:“秦山哥,此事便这么砸在人头上,我不过一名孤女,左右无依靠,又怎么能拒?邢妈妈也劝我许久,我打小在戏班讨生计,此次如何能让邢妈妈没脸?”
秦山一言不发,仍是死死攥着娥眉的衣袖,一院的天光泻下来,将他眼下新添的乌青照得分明。娥眉叹气,又道:“世事这般无常,我原知晓你的心意,本也想过待你有些气候我们便厮守的光景。奈何大户人家娶妻纳妾便如集市上强买强卖,我又能怎么的呢?”
只见那双手仍是不放,在娥眉眼里已有些不识好歹死乞白赖的意味,她按下不耐,藏起眼底几分嫌恶,好言相劝道:“秦山哥,等我入了焦府定会常常想起你的,你先放了吧?”说着,心一狠往鬓上拔下一支珠花塞进秦山手中,“以后秦山哥睹物如见人,我过几日便要成焦府的娘子了,此生便不可再见得,望秦山哥珍重呢。”
秦山赠了她一个翡翠镯头,她半推半拒地收了,瞥了几眼转身掷进妆奁,接着便敲锣打鼓地嫁了人。
亭檐灰青,梁柱重红,珠帘沉得似掀不起。娥眉没了颜色衣裳,再染不得指甲。在园子里喂了只花猫儿,在死闷时用来逗趣。
刚嫁进府,娥眉随焦公子在书房。研墨,剪灯花,呵欠也只能偷着打。焦郎虽性子放纵,但满腹墨水并不假,每每想吟风弄月与娥眉风雅几句,奈何娥眉常哑口。渐渐地,他便百无聊赖挥手让娥眉回去。
不知怎的,娥眉总觉得日子就像被裹上了锦缎,一层一层,要裹死陪葬并不丰厚的自己。她不得再唱戏,不得上街,不得撒泼。在戏班子里她痛恨吊嗓,在焦府却总想哼哼。她端正了镜子,扯下一缕头发绕着指头对镜子斜眼看去,眼波仍是脉脉的,却再不知除此还有什么可以留得住她的焦郎了。
她无数次扒着自己的脸细细瞧,眉毛仍旧浓密,眼睛也勉强水灵,至于那两道浅浅的鼻纹,她像出嫁前一般两手捏起兰花指,在左右脸颊上往耳朵一提——多标致的小娘子。
多标志的小娘子……
娥眉仿佛行将就木,只缓慢地合上妆奁,呆呆往窗外望去。
暗绿草木披着日光无声摇曳,满耳只得虫鸣与鸟儿翅音,园子成日里不过来往二三人。无人交谈,无人唤她。她眼中空空,只觉此生从未过过这样难熬的夏天。
第二年开春,娥眉为焦府生了一个孩子。
她总是在梦里记起那个烛火乱晃的夜晚,手臂被绑缚的绸子勒出血痕,脸上不知是泪是汗,头发腻在脑后,像一团脏污。她狰狞哭叫,憋了一年的声气似乎都在这时发泄。许多时刻,她以为自己已经要被撕开来,血水却带着更大的痛袭入。
待得第一声孩儿的啼哭传来,娥眉嘶哑的嗓子终于得以休息。人间忽然安静,她就这么躺着,盯着空空的横梁,眼泪扑簌簌掉进头发里。身体仍然抽搐发痛,她勉强侧头,看见许多人围着她刚刚出生的儿子,每一个的脸上都是如此真切的喜上眉梢,她是个被人摆弄蹂躏过后丢弃的娃娃。
他们撕开了她,却忘了缝上。
娥眉的嘴唇颤着,张开又合拢,却没有力气发出声音。她一次又一次张口,却只是徒劳地吐气。痛啊,娥眉想喊痛,血是不是还在流?血是不是会流干?她不知道此时的自己像一尾濒死的鱼。
儿子生得好瞧,娥眉爱极了,这是她的骨血,是她孤苦单薄在人世间艰难钻营留下的唯一凭证。那样血肉外翻的痛,几乎已经要走娥眉半条命,她不再敢照镜子,也太久没见焦郎了。
一个闷坏人的午后,娥眉的儿子不慎跌进小湖,被捞得及时,只是躺在床上发热。焦郎一回府便急匆匆来看儿子。娥眉惶恐,竟不知如何是好,忙盛装打扮,却惊觉自己的腰身粗至这般,面目也肿起来,眼下有了乌青与浅纹。面容赶用脂粉填补,腰身忙以衣带紧勒,将往日得的珠翠首饰缀在鬓边,抹当年与焦公子初见时涂的口脂。
她太久不出街,不知外头的年轻女儿家如今是什么打扮。等焦郎来了,看见本就老态初显的妾裹着陈旧花色的衣服,臃肿的身体靠在桌沿,与屋子里昏暗的光线融为一体,像个死气沉沉的古董。娥眉一见他便咧开嘴笑迎了上去,却不想焦郎望着她鲜红的嘴巴,逃也似的走了。
我是枯死了的花吗。娥眉问自己。
生儿育女,血液干涸,不再盛放。原本葱白柔软的手,她只用来抚摸自己的脸颊,扶起鬓上的珠钗。而今沾染儿子的屎尿,扶着门框,等郎君到天明。郎君嫌她不懂诗书,郎君道她没了颜色,郎君说她不再动人……她低头嗅着自己的袖口,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却仍是嗅到了那一股骨子里朽坏的气味。
三日过后,仆人从儿子落水的塘子里捞起了娥眉的猫。
娥眉安静蹲在地上,一言不发地望。那猫已死了。她自打夏初便再没见过它,以为它是去别的哪户人家谋生了。原来是被锁死在了这府里。
猫瘦,毛发全贴在那薄薄的皮肉上,包着骨头。娥眉恍然觉得这是一只死鸟,这么瘦,这么弱,这么痛不能言。
埋了吧,娥眉发着苦,勉强对仆人说。
焦府再没有猫了。
脖颈像被什么勒住,娥眉头疼欲裂,使劲蹬脚。眼前尽是云雾,月光洒下,不见尽头。这是何处?四下无人,一片荒凉。她仓皇乱跑,脚下不知踢走了什么东西。娥眉慌忙弯腰摸索着拾起,颤抖着拿至眼前,竟是个似曾相识的香囊,她强自镇定,仔细辨别,只见那石青的缎子上,绣了一对锦鲤。
不知何方咿咿呀呀声渐起,像鬼哭。娥眉怕,抱住脑袋不敢动。耳边忽而传来器物破碎声,她被吓得一哆嗦,头痛戛然而止,缓缓睁眼。
竟是换了一处,娥眉惊慌,哆嗦着摸胸前的被褥,侧头竟看见出嫁前的妆奁。隐约听见有人喊自己,却是邢妈妈骂着推开门:“都日上三竿,你这小蹄子怎的还在睡?还不利索起来去吊嗓子!”
娥眉懵懂,慢慢起身梳洗,坐在镜前恍然一望,竟是自己未嫁时的脸。
这是三年前,她不敢置信地想着。没有焦郎,没有嫁人,没有花猫,没有贵妃醉酒,三年种种烟消云散,是娥眉一场惊梦方醒。
戏班子的夜晚总是热闹的,娥眉带着刚从戏台下来的妆面在小厨房里吃饭,听见前院还演得热闹非常。同座的如意兴致勃勃拉住她的袖子,眼睛明亮地瞧着她,口中忙忙道:“娥眉姐姐,我听闻秦山哥属意于你呢,你可听说?”
秦山?娥眉垂下眼来微微一勾唇角,略带得色。那场噩梦后她想着要收了心,便对秦山情意绵绵起来,二人正是悄悄打得火热之际,那翡翠镯头也冰莹莹戴在她腕上。
却不想如意下一句便是:“你可千万莫应了他,他家那光景是有上顿没下顿,前几日还被邢妈妈骂了,咱们班子里不过几个男子,老鼠窜上了供桌,那秦山竟连打都不敢打,腿都软了三分,可见不但穷得掉底儿,还是个没一分胆气见识的人。”
戏台上锣鼓喧天,如意的声音尖利十分,不知又在聒噪些什么,娥眉呆望着面前一碗白面,木木地应了。
是夜,不知哪里来的簌簌声扰得娥眉睡不着觉,她起身点了灯四处细瞧,忽而见绣鞋底下窜过一只大灰老鼠。一声惊叫破嗓而出,眼见那老鼠要往自己爬来,娥眉赶紧抄起身边的凳子便用尽力气狠狠砸了下去,没几下,老鼠便失了声儿。
娥眉一寸寸地挪开凳子,只见那老鼠被自己砸得七窍流血,僵在地板上,只一根赤裸的大尾巴还在抽搐。
虎口撕裂,辛辣的冷意从指尖迅速往头顶窜,娥眉吸气越来越急,两只手颤抖着捂不住嘴,她终是将冰凉麻木的手掌上移,猛地捂住自己的双眼。
一声尖利的哭啸刺破了沉睡的夜,屋顶正要叫春的猫儿被吓得扑棱一下窜开,就连靠在城墙根儿小憩的打更人都被震得一抖,随即吧唧两下嘴巴,在依稀的灯火里又翻个身继续睡去了。
翌日,街坊间传起流言,说是东市的戏班子里疯了个戏子。
这边,娥眉精神抖擞地大操大办,将屋子翻得底朝天,什么银丝帕耳坠子统统打了包,满脸喜色地掂在身上往当铺去了。她前脚刚出院子,后脚邢妈妈便慌慌张张关了门,两三个戏班子里的黄毛小丫头悄悄跟在娥眉后头,望着她抱着一包银子从当铺出来,一拐便进了德隆庄,一路上撞了许多人,却仍是什么都望不见、兴头旺盛地只管往前撞,可见真是疯魔了。
娥眉五指紧紧地抓着绣了莲花的锦缎,像是抓住一条随时要溜走的鱼,只有把指甲深深抠进去才拿得紧。
它们那么凉,那么服帖,那么合她的身子,像是已经等了她三年。
娥眉咧着嘴呵呵傻笑,盈了一包热泪,心里什么也不记得,她只知道春天去了夏天要来,夏天去了便是秋天。猫会死,花会枯。
这似水流年攥碎不得,给人不得,四海皆是断壁残垣。戏唱不完,但这一辈子总是要死的。往哪条路走,人都是要死的。
但在这样荒唐的人间滚滚尘雾里,她终于,穿上了德隆庄的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