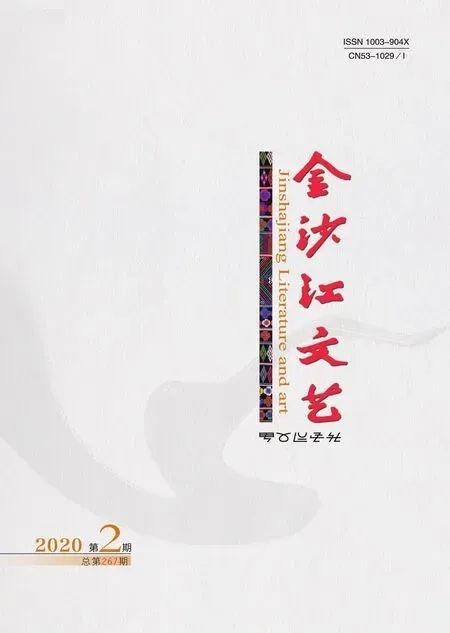散文三题
路文彬(北京)
我的沉醉史
在我看来,一个滴酒不沾的人,不管男女,都多少是有些无趣的人。朋友欢聚,没有酒,就像一幕始终听不见笑声的喜剧。我理解那些喜欢用酒量试探友情的男人们,只有在开怀畅饮的时刻,你才能将白昼的矜持放下,将心底的褶皱向对方展开。酒精的确可以让人们燃烧,烧尽身上所有水分,仅剩下真诚和勇气。当然,它也会暂时烧光你的理智,让你随心所欲,以至不得不在灰飞烟灭之后,咬牙切齿要重新做人。
就像我曾经的一个同事,每次醉酒,都得找领导谈心,把领导当作下属,开始是和颜悦色,最后便破口大骂。而在第二天一早,他必是第一个来到单位,毕恭毕敬地站在领导办公室门前,等待向领导作痛彻心扉的道歉和检讨。于是,就有些不够厚道的同事,只要对领导心生不满,便要请他喝酒,然后等着他去找领导谈心。好在我们的这位领导也爱酒,所以颇能理解这名下属的酒后德行,尽管心胸并不那么宽广,却对此人表现出了非凡的宽宏大量。
差不多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同事有些傻,独我欣赏他的可爱,他用风险向我证明了酒的确是走心的,酒后完全可以不听脑袋的使唤。或许,欣赏他还出自一个个人层面的原因,那就是我从来无法醉到他那个境界。不管喝了多少,哪怕吐得翻江倒海,我的头脑也依然清醒。一次单位聚餐,白黄红先后上场,我不知怎么就喝多了,一位女同事顺路打车送我回家;中途吐了两次,大脑虽不免恍惚,却仍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包括她一路夸我酒德不错,我也记在了心里。
后来读到别尔嘉耶夫在自传里的这句话:“特殊之处是我从来都不会醉酒,我能够喝很多,但却从来不会醉,众人皆醉独我清醒。”即刻,我将别尔嘉耶夫视为了知己。
至于自己的酒量到底是多少?其实我也一直没搞清,反正喝得断片或者不省人事,那对于我是不可想象的。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那阵,是我最喜欢白酒的时候,也是喝酒聚会最多的时候。朋友们都认为我能喝,不过是因为从没见过我的醉态,而且向来面不改色。记得一个高中同学要在家宴请他的一个哥们儿,特意找到了我,他说他这哥们儿至少一斤的量,请我去陪陪。我二话没说,欣然奉命前往。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这哥们儿没喝到半斤就坚决不再继续。事后,同学告诉我,他那哥们儿被我在酒桌上的表现给镇住了,担心不是我的对手,因此不敢再拼下去。第一次,我了解了社会上还有这样喝酒的,把酒场当成了战场,随时观察着对方的实力,喝不过就撤。这样有心机的喝酒,已然丧失了喝酒的乐趣,不喝也罢。不过一场酒,大不了烂醉如泥,又有什么可丢人的呢?
说到丢人,不禁想起了我的发小飙君。一次我们到一个多年未见的小学同学家里喝酒,一直喝到大半夜,醉得回不了家,被安排在了一间黑咕隆咚的屋子里躺下。他不停地喊着难受,要我送他去医院。我笑话他没出息,说去医院太丢人,忍忍就过去了。当时的我浑身也挺难受,像发烧似的,但我心里十分明白,如果去了医院,以后说起来不亚于一次出丑的经历,会成为自己喝酒史上的一个污点。况且我以为,就是去了医院,医生应该也没什么好办法。
如今想想,还真有点后怕,飙君自小肝脏就不大好,40出头的时候便因肝病不治离世。多少年少时的鲁莽无知,化作了中年时的悔恨和遗憾。
也是这位飙君,见证了我最初的醉酒史。那时我们还是五年级的小学生,一天中午放学,我们五个同学里,忘了是谁提出想找个地方来场聚会。我自告奋勇,说可以去我家,因为我家没人,还有猪蹄可吃。大家顿时欢呼,流着口水兴冲冲跟我去了。
聚会没酒怎么能尽兴?我们中间最富有的胡勇同学掏出一块钱,派飙君去小卖部买了一瓶老白干,还买了几袋藕粉冲了权当下酒菜,因为猪蹄太少,实在不够吃。我拿出家里的酒杯,大家你一杯我一杯,就像喝水似地干了起来。飙君是我们当中最不受重视的一个,所以喝到的酒最少,基本是由我们四人将那瓶度数不低的老白干给瓜分了。
把一瓶酒喝完,没吃任何主食,我们便回学校准备上课了。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就走散了。可能是因为头晕,我坐在了教室外面的地上,飙君坐在我对面,忽然呕吐了一口,引起我一阵嘲笑;我喝得可比他多多了,也没像他那样啊。这时,我们的班长跑过来,说胡勇和另一个同学倒在半路上,被救护车拉走了。我顿时意识到,我又惹麻烦啦,这次的麻烦可能比我以前惹下的所有麻烦都要大……
中国没有禁止未成年人喝酒和买酒的法律,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允许坐在酒桌旁陪客,象征性地喝上那么一点点。也许就是这样的习惯练就了我后来的酒量。但是,随着目睹越来越多的亲朋好友在酒醉中沉沦甚至死去,有一天,我决定像告别香烟一样告别白酒。走心的酒怎么能走向沉沦和死亡?
从此,我让啤酒成了我的醉爱,把沉醉降级成微醺,我知道,这样才是享受心醉的正确方式。如果不能保持清醒的记忆,我便无法真正领会沉醉抑或微醺的世界。醉着并醒着,最该是我们善待这个世界的可爱模样吧。
海边的那些小店
在威海的环海路,不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小店,有酒吧,有民宿,也有书店和咖啡屋,还有花店和糕饼屋。生意看上去并不景气,却是令我羡慕的存在。它们安静地待在那里,与世无争,似乎只是为了等待,等待它们所爱的人。即便始终并无人来,仅仅就是等待着等待,这超脱的神秘气质也足以让我心生几分肃然。
尤其是到了冬天,北风呼啸,白浪汹涌,依旧欢喜这里的只剩下了海鸥,盛夏的人流早已散尽,仿佛劲风横扫过的沙滩,不留一丝往事熙攘的痕迹。当然,并不仅是海鸥制止了这里的无情,还有岸上的这些小店,真正的往事都固守在了它们那里。别看它们寂寞,寂寞的心灵最有故事。它们呆呆地望着大海,这本身便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它们讲述着时光,时光倾听着它们。
暮色淹没了大海,小店里的灯火次第亮起,那些灯火同样开始讲述起故事,一个有关温暖的故事。望着眼前这灯火,踽踽漫步的我忽然意识到,其实,寂寞从不曾寒冷,就像海上那孑然独立的灯塔,时刻抚慰着疲惫的航船。尽管我尚不疲惫,但温暖总是一种召唤,情不自禁,便朝着一家酒吧的灯火走去。不过,我并未把自己当作一名它所等待的顾客,而是将自己理解成了一个闯入者,我的到来或许会导致它正在讲述的故事戛然而止。
可是,就在我推开店门的一刹那,因歉意产生的不安便随即消失;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身旁墙上一幅萨特坐在巴黎某个酒吧里的个人肖像,下方印着萨冈写给萨特的情书中的一句话:这个世纪疯狂,没人性,腐败。您却一直清醒,温柔,一尘不染。
这顿时使我想起自己刚刚读过的一本书 《存在主义咖啡馆》,特别是想起其中萨特、波伏瓦以及阿隆于1933年坐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痛饮杏子鸡尾酒,畅谈存在主义哲学的美好情景。那时的他们都还年轻,而我却已不再年轻。这个充满存在主义味道的酒吧一见面就给了我无与伦比的亲切感,以至于我不能不相信它真是在等待我的到来。
我的眼睛湿润了,一脸殷勤笑容的中年男店主注意到了我的眼睛,问我:是不是外面太冷啦?
不,我说,是屋里太温暖啦。
酒吧里只我一个客人,我在靠窗的一处位置坐下,那里矗立着一个书柜,瞟过一眼,看到的是卡夫卡、杜拉斯、春上村树等人的小说。
店主向我推荐了一款新到的比利时精酿,介绍完酒水的品质,他便走到前方的舞台上,抱起吉他哼唱了一首香颂。我不识法语,但 《玫瑰人生》 是我相当熟悉的曲调。我为他浑厚略带沙哑的嗓音鼓掌。
这一定是个有故事的男人,我想。等他唱完,我起身邀请他同饮。
我请客。我说。
你是第一次来,我请吧。他说。
几杯酒下肚,他真就讲起了自己的故事:早年在法国留学学习绘画,后在北京做了多年的经纪人,有一天,忽然就厌倦了那座人山人海的城市,于是携着妻儿寻到了这里……
这里赚钱怎样?我问。
他笑了,笑得有点尴尬。在这里不能为赚钱。他说。
那为什么?
所谓的情怀吧。
可情怀怎能当饭吃?
所以……我还同时做些别的。他没有说别的具体是些什么。
事实上,我也不清楚他所说的情怀究竟指的是什么。每天看海发呆吗,抑或是饮酒作画?莫名其妙的是,他的这种人生状态却着实惹得我艳羡不已。一时间,我领悟到,是忙碌和人群将我驱赶到了这里。同这位酒吧主人的相遇,不正是同我自己的相遇吗?
不知不觉,已是午夜,我感到了深深的醉意;在这迷醉中,我渐渐发现了清醒的自己。乐音弥漫的空间里,仍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和他,或者说我和我。与其说我是在听他的故事,倒不如是我在讲自己的故事,讲给这酒听,讲给窗外的海风听。昏黄的灯光下,桌上花瓶里的那束鲜花正释放着勃勃生机。
告辞时,他说:谢谢你今晚的陪伴。
我要付账,他坚决不允。
我没再坚持,因为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他的情怀。我相信,以后我定是这里的常客。我愿意支持这海边的每一个小店,仅仅为了它们的等待。
环海路上的狂风毫无收敛,但愈发的寒意对于我浑身的热度俨然已丧失了攻击力。我没有回家,径直向月光下的大海走去。我想要确认一下它和这些小店的关系,到底是谁陪伴着谁,又是谁等待着谁。
回过头去,所有小店的灯火都已熄灭,却又有一家小店的灯火格外耀眼地亮起。我知道,那就是我的小店,霓虹灯闪烁着招牌上的四个大字:等待戈多。
晚安,陌生人
喜欢夜跑和夜间漫步,常常会丢下正在翻阅的书本或是进行中的写作,推开门,便一头扎进那酽酽的夜色里。黑夜之于我是永远的召唤,就像它召唤着灯火的到来。灯火并不照亮黑夜,它只是深情注视黑夜,陪伴黑夜守护大地的睡梦。而对于我,那灯火就是黑夜温暖的眸子。我无法想象没有灯火的黑夜,就像无法想象没有骏马的草原。如果没有灯火,或是没有星月,我又怎能相信那黑夜是黑夜,虽然它比我的黑夜更是黑夜。
跑着跑着,或者走着走着,我便消融在了茫茫夜色里,我不需要方向,因为黑夜不会让我迷失;就在身体隐逸的那一瞬间,我的灵魂开始了不羁的漫游。无须考虑向左还是向右,我仅仅介意人群和车流。我之所以喜欢威海的冬夜,正在于那狞厉的海风可以驱走人群和车流。于是,只剩下了我,剩下了孤独得忍不住骄傲的我。属于我的,不仅止于大海和沙滩,还有这整个夜晚,包括星空。当然,我无法占有它们,我不过是同它们一起存在。它们的存在始终向我敞开,我走向它们,通过它们走向我自己。相反,那人群和车流总是让我找不到自己,唯有逃离,我方能重新开始呼吸。
我无惧于海风的无情,它恰恰是我在黑夜的同谋,所以,我似乎没有感受到它的温度,而仅是听见了它寂寞的呼号。再则,灵魂亦无感于冷暖,灵魂只聆听孤独的回声。喧嚣的白昼扼抑了回声的咽喉,因此灵魂只选择在深夜出没。即便海风的呼号可能略显聒噪,但那毕竟属于黑夜唯一与我亲近的力量。我喜欢它的热烈,它拥抱着我,狂吻着我的脸颊,在我的耳畔不停嘶吼……谁说冬夜的海风是刺骨的?没有灵魂的躯体本来就太过冰冷,它感受不到所有以异己形式到场的热情。要么拒斥,要么迎合,这便是它一贯的生存之道。
为何那个女子同样无惧于海风的撕扯?她的衣着看似那么单薄,而且距离海水又是那么的近,击碎在堤岸上的巨浪几乎扑打在了她的身上。骤然间,我仿佛遇见了 《法国中尉的女人》 里的那位主人公萨拉,又联想起 《海上夫人》里的艾丽达……海水对于她并没有危险,可是在这样的深夜,孤身一个女子……想到这样的危险,我不由得心生作为一个男人的耻辱和罪恶。
不,夜晚从不制造危险,它只诞生安宁,或者提供奇遇。此时此刻,这位女子的灵魂正随着自己的长发、围巾和衣摆迎风飘扬。即使有逼人的寒冷,她的灵魂从中体验到的也仅有自由。有时,自由恰恰就丛生在那令人寒冷得无所适从的地方。
蓦然,她回过头来,她发觉了我的存在。她的举止明显有些惊慌,这使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贸然侵犯了她的世界。我只好若无其事地继续向前走去,还吹起了口哨——《忧郁星期天》 的旋律。这女子就此刷新了我的黑夜,抑或说在我眼前点亮了一处格外生动的灯火,这灯火告诉我,孤独绝不孤独。
风莫名其妙地突然就中止了声息,让我清晰地听见了自己的脚步声,还有清脆的回声;只是,这回声有些异样,并不合乎我的节奏。我停下脚步,那回声却依旧,我转过身去,望见那女子朝我走来。不,她没有朝我走来,她立刻停在了那里,目光移向大海。
当我接着起步,我又听见了回声,不,是她的脚步声。走到下一个观景台,我发现她也跟了过来,但仍然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承认,我已抑制不住搭讪的冲动,但理智却在提醒我,对于另一个灵魂,你应该感到的不是好奇,而是亲切。所以,不必发问,只需倾听。不为倾听而在的言语只能是种粗暴的搅扰。
好吧,我甚至不再回头,只是倾听着她的脚步。那一直追随我的脚步,是由于对于我的亲切,还是由于我给了她所需要的安全感?
前方灯火的疏落意味着我夜行的尽头,当我转身而行时,她也转过了身。我们还是那样的节奏,不一样的是,我落在了她的身后。真希望我们就这么走下去,走下去,直到融化在这夜色里,变作不灭的灯火。
然而,她却放慢了脚步,似乎有片刻的犹疑之后,她坚定地朝岔路拐去,消失于那片住宅群里。
我愣在原地,意识到没有了她的脚步声,才开始确认她已然从我的眼前彻底消失。
晚安,陌生人。我冲着她消失的方向高喊一声,为了证明这一切不是梦幻。
晚安,陌生人。
我确信,这不是回声。看,不远处的楼窗上随即亮起灯火,黑夜又睁开一双亲切的眸子,注视着我这个执着的夜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