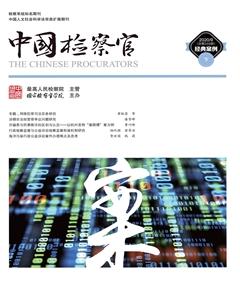涉烟非法经营罪争议问题研究
潘雪峰
摘 要:在涉烟非法经营犯罪中,“运输许可证”不应包含在司法解释规定的许可经营的范畴内,无证运输行为不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从行政犯的本质特征和实质解释的方法来看,持烟草零售许可证从事批发业务属于超范围经营,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家庭经营、合伙经营、“转证”及“借证”经营的行为是否属于未经许可经营的判断应坚持刑法独立评价,从刑法谦抑性角度看不宜一概入罪处理。
关键词:无证运输 超范围经营 无证经营 行政犯 实质解释
在我国,烟草是最典型的须经国家许可才能经营的专营、专卖产品。司法实践中,涉烟犯罪是经济领域多发犯罪。经对 H 省涉烟犯罪情况进行调研后发现,涉烟非法经营罪不仅在涉烟犯罪中占比最重,而且还占到全部非法经营犯罪案件的七成左右。尽管烟草专卖法律规范体系较为完备,但由于非法经营罪本身的适用问题较为复杂,加上我国烟草专卖体制的特殊性,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内部对于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存在认识分歧,导致涉烟非法经营案件屡屡被作无罪判决或不起诉处理。本文对其中的主要争议问题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具体案例作简要分析。
一、无证运输行为的司法认定
[案例一]2017年9月25日,徐某某、尤某某驾驶汽车从E市出发到广东拖运卷烟。卷烟装运结束后,徐某某、尤某某在未辦理《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的情况下,驾驶该车从广东返回E市。同月28日凌晨1时许,徐某某、尤某某驾驶该车途径E市某高速公路服务区时,被E市公安局交警和烟草专卖局查获。经现场检查,徐某某、尤某某驾驶的汽车载有“芙蓉王”“黄鹤楼”“红金龙”等7个品牌的卷烟,共计2000条40万支。经E市烟草专卖局核价,上述7个品牌的卷烟共计价值人民币33.4377万元。经烟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上述7个品牌的卷烟均系真品卷烟。
由于是在运输途中查获,无证据表明徐某某、尤某某是该批卷烟的实际经营者,也无法查明二人明知他人非法经营卷烟而受雇进行运输,此类情形下能否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存在认识分歧。有观点认为,即使二人不是实际贩卖者,由于我国对烟草专卖品的运输同样实施许可制度,二人在未办理《烟草专卖品准运证》情况下实施了无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行为,也应构成非法经营罪,依据是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烟草解释》)第1条第5款“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该规定在对相关许可证明列举后以“等”字结尾,说明是不完全列举,为无证运输行为入罪留有了余地。
但本文不赞同上述观点,将单纯以赚取运费为目的的运输行为评价为经营行为,已超出了法条中“经营”一词的含义范畴,而且烟草专卖品与毒品等违禁品不同,无证运输烟草的行为并不具有值得科处刑罚的社会危害性。刑法中“等”外未列举的行为应当与“等”前列举的行为具有相当性。相当性在具体理解时需要把握两点:一是在社会危害程度上是否相当,二是是否同样有刑法处罚的必要性。相较于无证生产、批发、零售行为,无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行为尽管违反了行政许可制度,但对市场经营秩序和烟草专卖制度的冲击程度较轻,因此烟草专卖法中也只规定了无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给予行政处罚,并未规定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故本文认为,《烟草解释》未将准运证与生产企业许可证、零售许可证等并列在条文中表述正是考虑到运输行为毕竟和刑法第225条“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有所不同,因此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二、超范围经营的司法认定
[案例二]2018年9月20日,居住在J市A县的范某某从B县、C县等地收购卷烟运输回J市市区进行销售,在下高速时被J市烟草专卖局查获,现场查获卷烟约1314条,8个品种。经烟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卷烟均为真品卷烟,价值为258710元人民币。经查,范某某具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经营场所为J市A县东风村,这批货准备一次性销售给J市市区几家定点零售户。
本案中范某某的行为除了前述的无证运输行为,还存在以下违反烟草专卖法规的行为:一是从B县、C县等地零售户收购的卷烟属于从非指定烟草专卖部门进货的违法行为;二是范某某准备将1314条香烟运回J市销售给其他经营者,涉嫌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务;三是范某某所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规定的经营场所为J市A县东风村,但其将1314条香烟运至J市其他地点销售,超过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规定的经营地域。这三项违法行为均可归纳为超许可经营,此种情形下能否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存在疑惑。
2011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以(2011)刑他字第21号文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关于被告人李明华非法经营请示一案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被告人李明华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但多次实施批发业务,而且从非指定烟草专卖部门进货的行为,属于超范围和地域经营的情形,不宜按照非法经营罪处理,应由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实践中,司法办案人员根据该《批复》的精神,对于类似超范围和地域经营的案件一般都做了出罪处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超地域经营不属于未经许可经营基本能达成共识,但对于超范围经营的问题则有不同认识。有观点认为上述《批复》所针对的是具体案件,《批复》中所称的“超范围和地域”,只在“李明华案”这个个案中具有特定性,对出罪条件的把握和应用不能无条件扩大到所有涉烟刑事案件中。[1]还有观点认为,《批复》中并没有对超范围经营和改变经营性质的行为进行区分,实践中不能将已经改变经营性质的行为简单认定为超范围经营行为。根据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一次销售卷烟、雪茄烟50条以上的,视为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务。《批复》中的超范围经营应当指虽然超过了烟草专卖法规规定的一次性零售的许可标准,但卷烟直接流入了市场消费领域,因此从本质上看仍然属于零售行为,例如向以操办红白喜事、宴会等一次性消费为目的客户销售50条以上香烟的情形。而如果零售户以其他经营者包括其他批发者、零售者等非消费者为交易对象,则实质上以赚取批发利润为目的,此时就不是超范围经营,而属于未经许可从事烟草批发经营业务,仍然符合《烟草解释》第1条第5款的规定,涉嫌非法经营罪。
本文认为,上述观点虽然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并没有领会《批复》的精神内涵。首先,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24条的规定在法律上属于一种拟制,即将一次性销售卷烟、雪茄烟50条以上的视为无批发许可证而从事批发的行为。但这种以量定性的划分标准来区分批发和零售行为,主要是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并不适用于刑事责任的认定。况且,根据烟草专卖法规,能够取得批发许可证从事烟草批发业务的只能是各级烟草公司,一般经营主体不具有从事合法批发业务的现实可能性。因此,《批复》认为李明华多次实施批发的行为属于一种超许可范围零售的行为具有法理上的依据。其次,非法经营罪属于法定犯,又称行政犯,相对自然犯天然的反伦理性和反社会性,行政犯是国家出于管理、控制社会的需要而在刑法中规定的犯罪。行政犯入罪前必然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但行政违法不等同于刑事犯罪,违法概念也不等同于犯罪概念。一般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实质界分,在于客观上有没有发生值得科处刑罚的法益侵害的结果和具体危险(严重的法益侵害性)。[2]因此对于行政犯的认定应当坚持实质解释的原则,对所侵犯的法益和案件具体事实进行实质评价。刑法并不处罚所有的法益侵害行为,只是处罚严重的法益侵害行为。[3]实践中,由于部分卷烟价值较高,50条以上卷烟的金额就可能达到非法经营罪的入罪数额标准。对于出于获取批发利润为目的,向其他烟草零售者批量销售卷烟的行为从行政法角度看确实涉嫌改变经营性质违法从事批发业务,但从刑法上法益侵害的角度来看,不管销售对象是谁,一次性销售50条以上卷烟的行为并没有对消費者的生命健康权造成危害,也没有造成国家税收损失,对烟草专卖秩序的影响程度也十分有限,没有刑罚处罚的必要。对于以售卖卷烟赚取利润的零售户来说,分批售卖50条和一次性售卖50条卷烟在实质上并无二异,将此作为划分合法和犯罪的界限并不合理,也难以被社会公众所接受。
三、无证经营的司法认定
[案例三]2017年4月14日,金某某在W市一路口从一辆商务车上取货时被执法人员查获,当场收缴其非法购进的黄鹤楼卷烟(软蓝)200条,后在金某某家中收缴黄鹤楼等37个品牌规格卷烟704条。经烟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被收缴卷烟均为真品卷烟,货值金额共计人民币l29677元。经查实,金某某名下无烟草零售许可证,但金某某的母亲高某某名下有一副食店,并办理了烟草零售许可证,金某某与父母共同生活,并参与该副食店的经营管理。
[案例四]2015年1月14日,皮某某在没有取得烟草专卖品零售许可证和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的情况下,开车到河南省L市购得大量卷烟,准备运回湖南省H县销售。2015年1月15日晚,皮某某驾驶其满载香烟车辆从河南返回湖南途经某高速路口出口时,被G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当场查获。现场从其车内查获涉案黄盖芙蓉王1200条、白沙(和天下)香烟200条。经烟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该批卷烟为真品卷烟,价值407200元。经查实,皮某某与李某某合伙经营一家烟酒专卖店,二人签订了书面的合伙协议,该店办理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并登记在李某某名下,李某某负责店面的日常经营,皮某某负责进货。
[案例五]2017年12月31日,W市烟草专卖执法部门在沈某的烟酒专卖店查获中华(软)卷烟75条。经烟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被收缴卷烟均为真品卷烟,价值5.25万元。经查明,该店烟草零售许可证登记在另一名男子杨某名下,2017年5月杨某将涉案烟酒专卖店转让给沈某,同时将烟草零售许可证交给沈某,事后沈某未按规定向当地烟草部门重新申领许可证,但至案发前,当地烟草公司每个月仍然正常地给沈某的烟酒专卖店供货。
上述三个案例,分别涉及到家庭经营、合伙经营以及私下转证经营的问题,严格意义上看都涉嫌无证经营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上述情形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中“未经许可经营”还是视为“有经营许可”则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设立烟草专卖制度的目的就在于限制人员和渠道来进行烟草专卖品买卖,是否属于“未经许可经营”应该严格根据许可证记载的登记人信息来认定;另一种意见认为家庭经营、合伙经营作为市场经营活动中的合法经营形式,并不被烟草专卖法律法规所禁止,即使出现违法经营的情形也应当与典型非法经营卷烟行为相区分。同理,“转让证件”“借证”经营的行为虽然是烟草专卖法律规范中“无证经营”的一种表现形式,但与真正的无证经营的违法性及社会危害性不能等同,“转让证件”“借证”经营行为的违法性完全可以根据行政法律规范来处罚,没必要上升到刑罚层面,不宜作为犯罪处理。
本文赞同后一种意见,行政法的价值在于维护公共秩序、实现令行禁止,采取的是行政许可、强制、处罚等手段。行政违法行为的认定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必要的扩大解释,但刑法对犯罪行为的界定及解释在坚持保护法益的同时强调自由保障,因此不宜随意扩张解释。为了维护烟草市场的正常秩序,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在行政执法领域对“无证经营”在较大范围上进行认定存在一定合理性,但行政法上的“无证经营”并不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未经许可经营”。打击涉烟非法经营犯罪的目的是维护正常的烟草专卖市场秩序,许可证虽然不在行为人名下,但行为人作为家庭成员或合伙人在许可证登记的经营场所实际参与卷烟经营管理,特别是经营收益也归属于共同经营的商户时,与持证人本人经营没有实质区别,应当认为是一种被许可的经营行为。同理,在大多数“转证”“借证”经营情形下,行为人仍然在有许可经营的门店内进行正常的卷烟零售经营,烟草公司也正常地向行为人的店铺供货,在外部看来同样与持证人本人经营无实质区别,而且烟草专卖行政执法部门也没有对此类行为进行及时纠正,虽然行为人违反了相关行政法规范,但应当与典型的非法经营犯罪相区分,换句话说,这类行为并非立法设想的“典型犯罪”,即与典型的未经许可非法倒卖烟草专卖品的贩烟行为在不法程度和社会危害性上不具有相当性。从刑法谦抑性的角度来看,在行政惩罚措施足以规制不法行为时,没有必要再动用刑罚处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案例中,行为人均在许可证指定的门店里实际参与经营,因此才被视为在许可经营范围内,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与该许可证毫无关联的贩卖烟草专卖品的行为则仍然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其他人名下的许可证就不能作为其逃避刑法打击的“护身符”。
烟草专卖品“高需求”“高利润”的特点能带来“高税收”的效应,对国家和地方经济的贡献较大,国家实行烟草专卖制度,成立政企合一的烟草专卖机构进行经营和管控,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经营模式。不过,正是由于这一体制的特殊性,公安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来自地方政策方面要求从严打击的压力。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应尽量减少对经济关系、经营活动的干预。从近年来出台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对非法经营罪的法律适用呈逐步收紧的趋势,司法实践也秉持着审慎的态度。通过《烟草解释》《批复》的规定也可以看出,适用涉烟非法经营罪应该把握的界限是保障和维持烟草专卖经营模式的基本秩序,涉烟非法经营犯罪是典型的行政犯,其本质侵犯的是社会管理秩序之类的团体法益,因此更应该注重对社会危害性的实质评价,只有在发生值得科处刑罚的法益侵害和具体危险时,才能适用刑法处罚。
注释:
[1] 参见魏彤、吕祚成:《论改变经营性质类涉烟犯罪行为刑事违法性的认定》,《中国烟草学报》2017年第12期。
[2] 参见阮齐林:《刑事司法应坚持罪责实质评价》,《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
[3] 参见张明楷:《避免将行政违法认定为刑事犯罪:理念、方法与路径》,《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