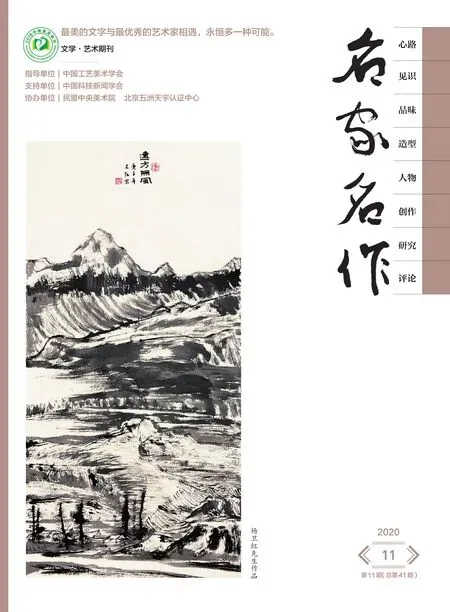论隐喻的诗性智慧
陈玲玲
本文所谈论的隐喻不仅仅是修辞学意义上的隐喻,更主要的是人类精神活动层面的隐喻。以下将从人类学和诗学的角度分别对隐喻的观念和诗性智慧进行论述。
一、人类学:隐喻是人类基本的和原始的思维方式
隐喻是人类基本的和原始的思维方式。人类面对陌生的世界最初就是运用早期的隐喻思维来认识新事物,表达新的经验。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对人类原始思维进行了描述,他指出人类的原始思维具有原逻辑的和神秘的性质,构成这个思维的集体表象是受互渗律支配的。“原逻辑”不是说原始思维没有逻辑或者不合乎逻辑,而是指它遵循跟现代逻辑结构不一样的特殊逻辑。“原逻辑”不是说原始思维是非逻辑的或反逻辑的,它只是遵循互渗律而对事物的矛盾律不关心。原始思维对事物之间的相似和联系更感兴趣,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神秘的“互渗”:互相关联、作用、感应、影响。“互渗”是原始人类按照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对事物之间具有的某种神秘关系的一种联想,用以解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现象的发生是在一定的神秘性质的条件下由一个客体传给另一个的神秘作用的结果。这种在原始思维的运作中起主导作用的“互渗律”带有隐喻性质。“互渗”与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出的原始巫术思维“相似律”和“接触律”的特征相类似,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感应(基于相似或接触的联想)相互作用。
现代逻辑思维排斥一切直接与它矛盾的东西,同一关系只能建立在对象完全相同的基础上(a 是a,a 不是非a)。而原逻辑思维把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的东西,同一能建立在事物间具有相同属性的基础上(a 即是非a,只要a 与非a 在某一属性上是相似的)。比如人与他的画像,事物和它的名称等都被原始思维看成是同一的东西。不仅如此,不仅相似即同一,事物还能通过接触、转移、感应、远距离作用相互渗透和包含,使有生命体与无生命体互通,主体与客体互通,认为自己同时与可见和不可见的存在物生活在一起,这种思维想象到的东西都包裹着神秘因素,事物的发生都是由神秘的和看不见的力量引起的,它使原始思维带有神秘的性质。
列维·布留尔认为在原始人类的思维中有一种受神秘的互渗律支配的集体表象,“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引起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感情。”[1]这些集体表象构成了个人的意识和知觉,它们通过存在物和客体之间的互渗而相互关联。集体表象涉及的东西有:住宅、武器、植物、动物、睡眠、疾病、死亡、梦、天体的升落、云、降雨、打雷、石头等。
原始思维这种“原逻辑的和神秘的性质”使原始人类所感知到的外部世界与我们所感知的世界不同,他们知觉到的是物物相通,生命万物间有神秘的联系。他们相信自己与某种动植物,与风和雨一类的自然现象,与星座、太阳、月亮有神秘的血缘或亲缘关系,社会集体与其周围的生命群体有亲族关系。列维·布留尔考证巴西北部的一个部族称他们自己是水生动物,而邻近的一个部族则自夸是红金刚鹦鹉。斯宾塞和纪林研究过澳大利亚土人认为太阳是巴伽农女人,以一定的亲族关系与部族的其他所有氏族联系着。我们看到在原始思维中,人既可以是人,又可以是长着漂亮羽毛的鸟,太阳既可以是太阳,又可以是有亲族关系的女人,他们实际上是同一的。原始思维具有把不同事物同一化的作用,使运用一种事物去隐喻另一种事物成为可能。隐喻思维正是建立在原始思维的原逻辑的和神秘的性质基础上的,在产生初期,它与原始思维实际上是同一种活动。
原始民族最初就是运用早期的隐喻思维来认识未知事物,表达新的经验。他们的概念性极其微弱,逻辑思维还不发达,只能用已知事物的具体意象来表达未知事物,传达自己的某种朦胧感受,他们凭自己的感官印象接触、体会外界事物,思维方式未脱离具体事物和形象。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类比和联想发现它们的感性现象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建立起来的,用已知的具体意象来表达新的事物和经验,认识就得到了增进,这实际上就是隐喻思维的过程。
隐喻从根本上来说是在两个不同事物之间建立联系,用一个事物来理解另一个事物,用一种事物替换另一种事物。人类早期的隐喻思维只关注事物的外在现象的相似性,并不考虑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原始民族最初就是运用这种原始感性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的。我国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中,在太阳中间站立的是一只三脚乌鸦(金乌)。鸟的形象同时也是太阳的化身,它们的羽毛就是光线变成的。“巨蛇勾勒出大地表面的形状;‘小花蝉’的鸣叫产生了声音;甲虫在水面上飞舞便诞生了河塘;绿色的蚱蜢孕育了草原,因为它们蹦到哪里,哪里就长出青草;‘黑暗的女主人’猫头鹰闭目入睡时夜幕便降临了。”[2]
人类原始的隐喻思维带有普遍性,诸如神话叙述、诗歌创作、图腾信仰、巫术礼仪等都是带有隐喻性质的活动。原始民族把世界想象成整体,觉察不到事物之间的区别和对立,有时即使觉察到了也不感兴趣,因此可以单数与复数同一部分与整体统一,也可以允许同一个事物在同一时间存在两个或几个地方。原始的隐喻思维是具体的整体的思维。隐喻所产生的基础即世间万物皆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所有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都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彼此息息相关、声气相通。
二、诗学:隐喻是人类诗性智慧的代表
文学艺术遵循着人类早期的隐喻思维和语言的模式,让我们的思考投向诗和文学艺术的审美空间,诗人的心灵在本质上仍然是神话时代的心灵,维柯把神话时代人们的心灵态度称为“诗性智慧”……“浑身是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3]认为正是在这些推理能力薄弱的人们那里产生了真正的诗性的词句,表达出最强烈的情感,具有崇高的风格,令人惊奇和赞叹。人类的诗性智慧无疑与从事艺术活动的心灵态度相吻合,诸如强烈的感受性、情感性,对宇宙、自然的诗意想象,对世界的直觉的感性的反映,这些都带有艺术思维活动的色彩。
神话与诗就是人类对世界诗性反映的产物,是人类诗性智慧的产物。人们认为自然现象和事物也和自己一样有生命、有情感,通过想象赋予它们某种人的外在形态和性格,赋予它们内在生命,创造出诗和神话,并对世界作出象征性的解释,这体现出人类早期的隐喻思维。比如人们把天想象为一个巨大的有生命的物体,把打雷扯闪想象为一些体力极强大的人在发怒,用咆哮来发泄他们的暴躁情绪,并称之为天神或雷神。在中国创世神话——盘古神话中是这样描述的:“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千八岁,天地开辟,阴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脚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星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4]
在神话的诗意想象之中,在人类诗性智慧里蕴含着人类思想的原始隐喻,即天人合一的原始隐喻。因此隐喻是作为人类精神活动存在的,人与自然的隐喻关系为诗和其他艺术提供了创作源泉。万物息息相通,生命万物间神秘的相似性使诗人的灵感和幻想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这是人类诗性智慧和隐喻思想的意义所在。诗人们以全部的心灵和感官去领会外界的一切,进入我与物同,人与外部世界同一的境界,万物相通,互相呼应,诗和艺术正起源于此:
自然是一座殿堂,那里的活柱石
不时传出一些隐隐约约的话语;
人们在这象征的树林里来来去去,
树林子以亲切的目光向你注视。
仿佛是来自远方的悠长的回音,
终于融汇入自然的幽深的怀抱;
仿佛是浩漫无际的星夜和白昼,
香气、颜色和声音在此呼彼应。
有些香气新鲜得如儿童的肌肤,
柔和得如双簧管,翠绿得如牧场;
另外一些——烂熟了,还自矜丰富。
那永无止境的品物在不断扩展,
如同龙涎香、麝香、安息香和篆烟香,
一起欢唱着心灵和感官的狂想。
(波德莱尔《呼应》)
“‘在世界的儿童期,人们按照本性都是崇高的诗人’,神话或诗的创造在原始社会中都是全民族的事”。[5]难怪诗人和艺术家对一去不返的神话时代向往怀恋,恨不能徜徉林野、放浪海天,从而恢复人与自然的原始亲缘关系,找回人类原初的生命智慧,体验人类思想的原始隐喻——通向美的自由想象之路。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文学的意义与功能主要呈现在隐喻和神话中,人类头脑中存在隐喻式的思维和神话式的思维这样的活动,这种思维是借助隐喻的手段,借助诗歌叙述和描写的手段来进行的。”[6]文学艺术遵循着人类早期的隐喻思维和语言的模式,虽然抽象推理思维由于能深入事物的本质,探究事物的内蕴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但在需要直观形象、诗意想象、强烈情感的艺术活动领域,隐喻却大放异彩。隐喻思维和语言在表现人类精神世界和感情体验的复杂性,揭示文学艺术的内在意味和深层意蕴等方面显示了其特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