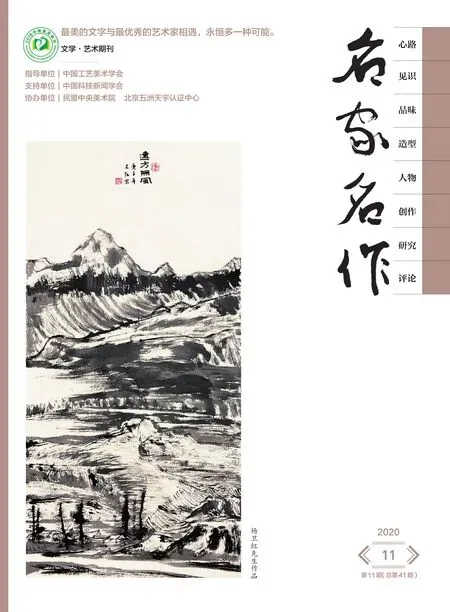浅析徐坤小说对“新写实小说”的发展
——以小说《狗日的足球》中的城市书写为例
张 影
一、引言
当历史逐步向21 世纪推进,进入崭新的现代化世俗生活时,人们开始将关注点投入以个体或家庭为中心的住房、薪资、美食、娱乐、旅游等日常生活主题中。由此,城市中出现了“小资”的消费形象,这一形象多是城市中工薪阶级的白领、知识分子们,他们不再对温饱有所担忧,更多地追求着精神文化上的享受。但又由于消费主义、社会现代化转型以及私人空间的扩大化,生活在城市中的这群人不免产生选择的困惑,甚至因强烈的渴望而导致道德“失范”以及文化认同的缺失。基于此,在当时也涌现出了许多反思世纪之交以来人们生活状况的小说,徐坤的短篇小说《狗日的足球》便是其中的典型作品。
而根据徐坤自己所承认的创作受到了新写实小说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徐坤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的小说创作仍旧延续了新写实小说日常化、世俗化的叙事特点,同时也在新写实小说所引发的关于如何挖掘世俗生活背后的精神内容的问题上有了深刻的发展。此前学界对徐坤小说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女性生活的书写关注较多[1],还在“重读新写实”的专题中兼论了徐坤的女性主义写作特征[2]。但其小说中对“新写实”的发展或超越却极少被充分提及。而笔者认为《狗日的足球》作为世纪之交时期创作的小说作品,徐坤在描写中有意告别了新写实小说中较为平面、单调的生活还原,以局部的文化视角来呈现沉湎于追求精神生活的都市小人物面貌。因此,本文意在从城市书写的角度,发掘小说《狗日的足球》在呈现人与社会复杂关系时对“新写实”小说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启发对当代文学发展流变的思考。
二、精神文化层面的城市生存
当我们追溯到90 年代初新写实小说的兴起时,能意识到当代小说的书写对象真正告别了英雄时代,进入了由凡人琐事组成的平民世界。而徐坤所创作的《狗日的足球》正是被放置于这样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时代之中,沿用了新写实小说对人物和场景的选择,即把故事安置在相对私人、封闭的小家庭之中,同时以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关注点,如“柳莺”“杨刚”和他们生活圈子里的其他朋友。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薪阶层的凡夫俗子,他们是城市中容易被遗忘的群体,却也构成了城市庞大的民间基础[3]。因此,小说虽并不以描述典型的城市文化为标榜,但其中借助城市中局部文化视角的“光束”,探寻“怀抱”生活的个体在外部社会的实感体验,倒也为人们认识城市生存的另一面打开了一扇窗口。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摆脱了此前新写实小说中的“一幅原色调的生活画卷:买菜、送孩子上学、住房、请客、送礼……”[4],由一种衣食住行的生活向具体欲望的生活形态延伸了下去。
(一)城市群体的认同危机
欲望化的生活在小说中主要聚焦在一个私人空间变为公共放映厅的未婚小家之中。这种生活空间向公共性质的转换着实影响了男女主人公固有的生活模式:国际足球赛事的播出时间扰乱了原本的作息、家中络绎不绝前来的足球发烧友们占据了两人的生活空间……杨刚一直积极地从家中布置等方面去实现这一转变,其目的是:“正儿八经地做一点样子给别人看看哪!”[5]毕竟从文中我们能感受到,“足球”是人群聊以沟通的象征媒介,所以就连杨刚这样的白面书生也不惜将自己的生活与之捆绑,这样才能免去被逐出群体的内心恐惧。可见,杨刚并非为了自己真正的偏好而去享受这种足球文化赛事,而是想要借此寻求一种人群里的普遍认同。可以说,这个名叫“杨刚”的男人,实际性子里却透露着无法成为真实自我的“软弱”。而足球世界同样还“吞噬”了女性的生活,文中写到柳莺试图离开这个被“侵占”的小家,另寻他处以获得清净。但之后她还是做了进一步的“妥协”,她因丈夫的原因开始关注足球,迷上马拉多纳,同时和邵丽也因足球而获得了交谈时的共鸣。可见,她们会成为足球“发烧友”,实际上也是为了能与男性群体获得同一种“语言”,同时和同性之间得以交流。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杨刚还是柳莺都是在艰难地在达到所谓群体认同的目的,他们在足球所侵占的生存环境的压力下对自我不再坚持也难以坚持,他们丧失了真实的自我,变得“狂热”或者不适。因此,这一私人空间公共性质的转换,实际上正显示了都市人们生存背后的某种群体认同危机。
(二)危机面前的沉湎热情
如果说新写实小说中的小人物们面对世俗生活时,还流露着对其无可奈何的妥协,那么以杨刚为代表的新世纪“小资”青年,在面对上述困境时则表现出的是一种主动拥抱、接受生活的态度,甚至几近无距离的忘我投入。这种沉湎并非体现在柴米油盐的物质满足上,而是注重追求欲望的宣泄和群体文化精神的满足。正因为此,徐坤小说一反新写实小说所呈现的陌生、冷静的焦虑感,并充斥着浓厚世俗生活气息的温情环境。小说中就曾这样描述看球时的人们:“呷一口啤酒拈一粒花生米,看到忘情处喉咙里便发出一种低沉的颇类似于叫春的声音,被他招来的同伴们这时也一律的呜呜噜噜的嗓子眼里吭叽着欢实。”[5]可以说,这是没有任何尖酸的冲突矛盾的,一切都是真实而市井的。人们欢愉地“在一粒小小的皮球上”做抵抗,积极地温习重组前的那份群体文化认同感,温习他们先前的自我,人们对个体意义的追寻开始有了新的方向。而足球就是人们投放生活激情与文化价值的地方,熬夜观赛、贴球星写真、现场看球等一切狂热的行为举止也正是人们迫切投身于群众性生活、急于寻找“现世的灯来灼灼照亮他们被文明痿顿的当下生活,或许也能开蒙了他们的溟茫来世”[5]的缩影。似乎只有积极且沉湎地“透过一个小小的玻璃罩儿来集体进行回顾和留恋”[5],才能寻求到在城市中的一些寄托、一些文化认同。
(三)激情下的道德失范
通过柳莺眼中的足球世界,我们能发现这种沉浸的激情始终被人们自觉地扩张着,挑衅着惯常的道德秩序,以至于那些歹毒、粗野、放纵的行为方式和言论方式在足球竞技的大氛围之下变得毫无约束。运动员能把“力与美的搏击隐没于斤斤计较的商业算计之中”,观看者也能用“几万人的粗口汇成一股排山倒海的声浪”[5]发泄着自己的情绪,无论是在家还是在球场的观看席位上。“一切歹毒的粗野在足球场上被赋予了堂而皇之的命名。”[5]可以说,道德“失范”在足球活动中得以驰骋。那么,是足球赛事本身对其提供了某种必要性、合理性的解释吗?其实不然,这种“失范”的混乱现状正反映了人们内心的躁动不安和空虚。人们因生存空间挤占而焦虑,因无法在人群中认清自我价值和存在感而惶惑。而足球的活动热情给予了人们“爆炸的借口和由头”,在其中的宣泄和道德无拘束便是人们欲“把单调沉闷的日子捏出个响”[5]的体现。
三、小结
20 世纪90 年代新写实小说由于把对现实的关注停留于个人泛泛的日常琐碎,使其对现实的透视力、批判力只能浅尝辄止——无法触及欲望化现实中个人感受的根由。而作家徐坤在《狗日的足球》中虽然依循着还原“原汁原味”日常生活的原则,但却摒弃了新写实小说对生活形态普遍化的泛泛表现,绕开人们惯常停留关注的中心地带,进而开辟了一片个人文化娱乐的空间。把局部文化视角融到生活实感之中,充分展示某种人群危机和价值失范。同时呈现出城市中人们应对生活困境积极沉湎的态度,较之新写实小说中行走匆匆、迫于接受生活的人们而言,这是一种崭新的生活姿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对20 世纪90 年代新写实写作潮流的一种延伸和发展。而这种关注城市精神文化向度、个体心灵体验的书写日常生活真与美的写作命题,也将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起点,开创拥有人文关怀、精神超越向度和社会批判功能的文学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