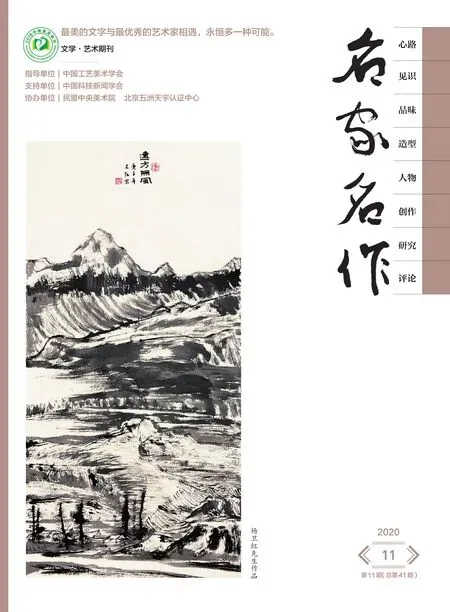论勒克莱齐奥小说《沙漠》中的追寻主题
许欣妍
一、引言
1980 年,作家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凭借小说《沙漠》获保尔·莫朗文学奖,2008 年又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法国《读书》杂志的读者调查中,被评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法语作家之一。小说《沙漠》讲述了两个发生在20 世纪,以沙漠为背景的故事,此时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加速阶段,并不断对外进行殖民扩张。
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发端于20 世纪初期英国剑桥学派,大成于加拿大批评家弗莱《批评的剖析》,盛行于四五十年代的北美,吸收了人类学家弗雷泽著作《金枝》中关于早期人类文化中的巫术仪式、神话、民间习俗的研究成果,以及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及原型理论,作为神话原型批评的奠基之石。
神话原型指反复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一种特定的叙述结构,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一个经典情节,也可以是一个人物,或是大自然中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或符号。作家们对《希腊神话》《圣经》这类经典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叙事结构进行总结,在自己的作品中戏仿,置换变形,进行再创作,其中蕴含的哲理和旧时神话一样,都能唤醒人们内心深处从原始社会遗传至今的特定情感。
勒克莱齐奥作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未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直到2008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内才陆续展开对其作品的研究。迄今为止,学者大多是对作品中叙事艺术、文化冲突、人物形象及生态美学等进行研究,其余则是对其创作历程和创作思想的总体介绍,在上述成果中,极少有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其作品进行分析。
纵观作家笔下如《诉讼笔录》《奥尼恰》《流浪的星星》等,许多人物以及故事情节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古代神话中的一些经典桥段。小说《沙漠》则具有鲜明的追寻主题特征,小说情节与人物内心发展的三个阶段与神话原型“追寻母题”的三个过程相一致,即出走——成长——回归。两位主人公各自历经的三大阶段正是作者借助经典《圣经》中《出埃及记》这一古老神话的外衣,进行置换变形,将小说中心思想通过三个阶段展现出来。《出埃及记》是基督教徒们耳熟能详的故事,讲述的是摩西带领族人离开故乡埃及,跨越红海、穿越沙漠、经历艰险,在“摩西十诫”指引下,最终找到了“流着奶与蜜”的迦南之地。本文将利用“追寻母题”模式对小说《沙漠》进行解读,探究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为解读类似作品提供参考。
二、被迫出走
20 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先进文明”的代表西方殖民军开始对北非的“落后文明”进行无耻的掠夺和屠杀。到20 世纪中期,非洲大部分都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保护国”。
小说开篇第一个故事,作者简明交代时间和地点“萨吉埃特·埃尔·哈姆拉,一九零九年——一九一零年冬”,为躲避殖民军围剿,北非牧民被迫离开故乡,前往老教长口中所说的“福地”。故事开头,作者用大量笔触描写沙漠的荒芜,日酷夜寒,环境恶劣,“疲倦和干渴像一层粗糙的外衣,包裹着他们,干燥使他们的舌头和嘴唇发硬,饥饿折磨着他们”。人们衣衫褴褛,跋涉在没有尽头的沙漠。此刻,被迫出走的牧民和北非即将消失的古老文明一样,在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侵蚀下,无奈放弃家园,另寻出路。
与牧民出走穿插讲述的,是住在沙漠边缘的姑娘拉拉的故事。时间快进到20 世纪70 年代,拉拉住在西撒哈拉沙漠边缘的贫民窟里,在那里度过了简朴幸福的童年。与小说开篇不同,作者以沙漠的美丽自然风光展开叙述,波涛奔腾的蓝色大海,浪花与阳光交融在一起,大自然所有元素都给人无限的快乐,充满生气与活力。这里没有现代文明的熏染,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质朴的生活。与追寻主题中英雄被迫出走的情节一致,长辈为拉拉安排的婚事点燃了主人公出走的导火索,拉拉被迫离开故乡。老渔民纳曼口中的大城市马赛,在拉拉心中,代表着自由、民主和希望。一天早晨,拉拉离开了姑妈家,“她甚至都没有看一眼睡在房间里面裹着被单的阿玛”。
小说穿插叙述的两个故事中,主人公或是因生存危机,或是因自己对未来人生的追求与现实格格不入,都做出了相同的选择——离开故乡,这是英雄追寻之路中的第一步——被迫出走,与圣经中《出埃及记》摩西带领族人离开埃及,寻找迦南之地的情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成长蜕变
追寻主题式的小说通常在第二阶段——成长部分运用大量笔墨。主人公踏入新世界,感知与原来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文明,内心在这一阶段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时,主人公会由刚开始对新世界充满新鲜感,转而认识到五光十色表象背后的本质,内心产生困惑、挣扎、迷茫,最后探明本心。《沙漠》中努尔和拉拉的心路历程与神话原型中追寻路上的英雄一样,由探索到反思,再到醒悟。
(一)充满希望
努尔是即将消失的北非文明的代表,因科技飞速发展而逐渐落后于时代,不堪现代文明的炮击,被迫寻找新的栖息之所。作者对努尔的心理活动的描写,也正是大多数古老文明部落人内心的真实写照。刚踏上旅途,努尔那炯炯有神的双眸,放射出“近乎神性的光芒”,牧民们怀抱希望,“巩膜里闪烁着熠熠光彩”。正是在传统信仰的支撑下,牧民们没有停止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重建家园的向往,全新的生活鞭策着人们翻越千山万壑。作者极尽描述人们刚开始行进途中发出的各色声音,昭示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冀。人们在这沙漠生,在这沙漠死,从未停下的,是他们对美好家园的追寻。
与努尔不同,拉拉主动出走,是新时代独立女性的代表。拉拉童年时经常去老渔民纳曼家里,在他口中感受到大城市的美好,“公园里到处都是鲜花,橘树,石榴树;楼房像山一样高;马路一眼望不到头”。还有“无尽头的码头,巨大的吊车,像大楼、像城市一样大的巨轮”。拉拉由此认为,在那里能实现自由平等的生活。于是,拉拉毅然离开,出走路上,拉拉“看到日出感到高兴,心想那就是她不久将要到达的地方,那里,天空和大地都充满着太阳放射的第一束光亮”。
(二)自我怀疑
经过长途跋涉,牧民们精疲力竭,越来越多的人在路途中死去,努尔内心开始滋生不安与苦恼,并产生对自我和信仰的怀疑。在老教长的带领下,牧民们到达有着高大棕榈树、流淌着清澈泉水的城市。然而,这里却对他们大门紧闭。饥饿折磨着人们,老教长亲自到城门前求取食物和土地,得到的只是敷衍,“城市的人不信任来自沙漠的人,城门整天紧闭着”,人们之间的信任感在文明进步中逐渐丧失。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次“长征”的道理,只是机械、绝望地重新启程,在迷茫中寻找遥不可及的、新的家园。“人们向前走去,找不到生命,也看不见任何希望”。
同样是为了寻找“福地”,拉拉坐船前往法国马赛。在轮船上,她“不顾路上的劳累,使劲地眺望”。当她到达港口时,岸上人们冰冷的眼神、法国警察歧视的目光就给了她当头一棒。作者将这一章题为“奴隶的生活”,显然在暗示读者,马赛的生活并没有她想象的轻松和畅快。在拉拉逐渐熟悉这座城市后,痛苦地发现,对外来者,马赛更像是一个人间地狱,“恐惧是空虚、苦恼、饥饿,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它仿佛是从臭气熏天、令人恐怖的地下室那敞开的气窗中散发出来的,从阴暗的院子里升起,进入了像坟墓一样冰冷的房间”。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拉拉仍然无法适应,“她真想大声喊叫、呼号,来打破这寂静,驱走黑夜的沉闷。可是,喉咙卡得紧紧的,发不出声来”。作者通过拉拉所见所闻,向读者展示了充满歧视、不信任,混乱无序的资本主义城市景象,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鞭挞。此时的拉拉和努尔一样,对前路充满迷茫。
(三)成长蜕变
老教长带领牧民东奔西走,但徒劳无功,队伍支离破碎,殖民军队不断地向前推进,摧毁了一切抵抗力量。恶风夹杂着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野心,强劲地吹向手无缚鸡之力的牧民。在殖民军强大的炮火下,寻找新家园的希望轰然倒塌,和平与希望的大地最终只是一个泡影,仍然是被侵虐者终身无法企及的他乡。望着沙滩上遍地的碎尸,翻倒在地的马匹,努尔和幸存者们噩梦初醒,彻底看清了自己与殖民军之间巨大的力量悬殊,在技术的支持与殖民观的侵蚀下,他们没有丝毫胜算。人们终于醒悟,安葬好同伴后踏上了南下归家的路,“他们走向南部故国,走向任何别人都不能生存的地方”。
另一位主人公拉拉的美貌被一位摄影师发掘,他将拉拉的照片刊登在杂志上,拉拉因此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财富和名声。可她并不习惯成名后的生活,仍然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穿梭,用自己的脚步感受城市的温度——这里游荡着和她一样的异乡人。作者把这座城市叫作“黑暗的城市”,在这里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基本生活保障,甚至还失去了原本的归属感以及故乡所能带给他们的温暖,在这里他们只能是边缘人。
拉拉在马赛认识了一个名叫拉第茨的小乞丐,为了生存,他经常在车站周围行窃,有一天,正在行窃的拉第茨被警察发现,逃窜时不幸被一辆大客车当场撞死。“离这儿不远,棕榈树园子边,一位脸色阴沉的年轻妇女,一动不动,像个黑影,使劲望着”,小乞丐凄凉的下场惊醒了混沌中的拉拉,她终于明白了自己与这座城市的距离,这正是她代表的民族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不协调之处,她的灵魂、思想终究不能以所谓的“先进文明”作为栖息地。在探寻本心的路上,拉拉幡然醒悟,明白自己想要的是精神富足、没有歧视、平等自由的质朴生活。
四、回归
在作为故事原型的《出埃及记》里,族人们到达了充满自由和梦想的乐土,他们的出走是为了历经考验,达到对自身精神上的一种洗礼,从而表现出对上帝的虔诚。但在《沙漠》中,作者有意将《出埃及记》这一原型的结尾进行改写,留给北非牧民的结局只有血腥的屠杀和毁坏殆尽的废墟。作为北非文化的代表,牧民遭受殖民军的追赶与屠杀,两种文化之间诸多的差异导致二者之间相互对立,由此产生矛盾。在殖民者眼里,异族文化都是需要被征服和掠夺的对象。老教长带领牧民们追寻新家园实质上就是追寻属于北非人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感。在科技发展造就强大武器的打击与殖民文化的蚕食下,部落子民最终失败,长眠于追寻路上。所谓的西方主流文化消灭了异族文化,“异族”文化者始终无法融入新世界,只有返回故土;古老文明也会随之消逝。以努尔为代表的北非文化的幸存者如何重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作者通过笔下人物,试图找寻民族文化的生存根基。
蜕变之后的拉拉也选择了回归,在清晨坐上回乡的船,一路难抑兴奋的心情,拉拉的回归是个体自主选择的回归,作为边缘者、异乡人,拉拉在马赛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始终无法融入“主流文化”,虽然她努力追寻两种文化的对等,通过做模特打入上流社会,看似成功,反而丧失了真正的自我身份。最终,回归故乡的拉拉在熟悉的海边沙地里,靠着“像巨人铁臂一样有力的粗大的树枝”,生下了与牧民阿尔塔尼的女儿,开始全新的生活。拉拉产女,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心灵的全新蜕变——回归纯粹、自由的生活,没有歧视,没有金钱的诱惑。作者在此讴歌、赞美沙漠的自然风光,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相知相融的紧密联系,这与现代城市文明中人类利用自然,将自然当作攫取资源的无生命体是迥然不同的,作者呼吁人们与自然建立起亲密、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
五、结语
纵观勒克莱齐奥的文学作品,不同文化身份之间进行对话,不同民族身份的人都在找寻精神归宿,虽然形式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他们追寻的,是人与自然达到真正平衡状态的理想社会。
《沙漠》中,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一种是理想的,极具包容性的,以大自然各种生命为代表的自然空间,一种是压抑的,具有排他性的,扼杀生命和抢夺资源的城市空间。前者象征原始、自由、和谐的大自然,后者则是充斥着冰冷机器,充满戒备的城市荒漠。作者借助神话的外衣,在作品中将神话原型中的情节置换、变形,从而达到戏谑和讥讽现代文明阴暗面的艺术效果,揭露出现代文明在物质和精神上带给人们的双重打击,通过对神话原型的戏仿,作品展现出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强大张力。
作者一生游历世界各地,笔下的角色也走遍了世界各个角落,身份认同危机是贯穿所有作品的主题,也是笔下人物追寻一生所要解决的困惑。当今社会迅猛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带来的不仅是多样的物质选择,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迷失。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寻求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变得更加迫切,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无根化的感受在现代人身上成为致命的根源。如何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中寻找人类本源,如何从消失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身份的象征,作者在《沙漠》中反映的正是对身份认同的迷茫和心灵归宿的恐慌与寻求,是哲学层面的现代追问,借小说表达对现代社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