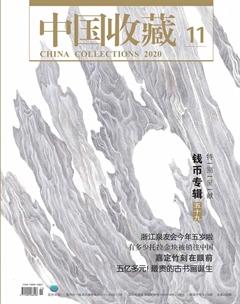云游四方他们带些啥
刘明杉
行脚又称游方、游行、“飞锡”,是禅僧为寻访名师、提升自我修持或教化他人所作的广游活动。行脚僧也称游方僧、云水僧,他们或结伴同行,或独自云游。禅僧行脚在于参禅悟道,而悟道并非易事,敦煌写本P.4660《禅和尚赞》中就感叹了悟道之难。“百行俱集,精苦住持。戒如白雪,秘法恒施。乐居林窟,车马不骑。三衣之外,分寸无丝。衣药钵主,四十年亏。……亚相之子,万里寻师。一闻法印,洞晓幽微。于此路首,貌形容仪。”
国际僧人之间的跨国行脚活动,促进了各国不同禅宗教派的交流。密教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结合的一种教派,公元六、七世纪时,印度大乘佛教开始密教化。8世纪以后,密教在印度已居主导地位。唐开元年间,密教传入我国。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中印度摩伽陀国人)、金刚智(南印度人)和不空(原籍北天竺,一说南天竺狮子国人)三位密教传人先后来到洛阳和长安,在当地广建曼茶罗灌顶道场,先后译出密教佛典,招收门徒,形成密宗。唐后期密教盛极一时,密教造像及法物应运而生。
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中印度求法,赢得当地人民敬仰。唐人段成式见到贞元二年与空海、最澄同乘日本第18次遣唐使船来华求法的日僧金刚三昧,他是日本唯一一位入竺僧人。唐开成三年,日僧圆仁以请益僧身份随遣唐使入华求法。巡礼五台山,在大华严寺﹑竹林寺随志远禅师等人学习天台教义。在长安住资圣寺,结识知玄,又跟大兴善寺元政﹑青龙寺法全、义真等人学习密法。向宗颖学习天台止观、从宝月学悉昙(梵语字母),历时10年。唐大中元年携佛教经疏﹑仪轨﹑法器等归国。于日本京都比睿山设灌顶台,为延历寺第三代座主,继承最澄遗志,弘传密教和天台教义。住寺10年,使日本天台宗获得很大发展。朝鲜半岛也有不少僧人来华求法,如长庆四年新罗和尚玄昱入唐,拜于章敬怀晖门下。13年后的开成二年归国,栖止于南岳实相山,受敏哀、神武、文圣、宪安四王归敬,晚年在慧目山开创高达寺。长庆初年,无染国师入唐参禅。
僧人在行脚游方中携带大量经卷、法器、生活用品等,促进了禅门各派之间的物质交流。因物品的呈现具有直观性,这在禅宗的跨国传播中更有意义。僧众看到行脚者从异域携来的物品,更容易通过对它们的应用,领悟其中蕴含的禅理,进而实现对外来教义的理解与吸收。如日僧金刚三昧在中印度见绘有玄奘法师麻履及匙箸的画受人顶礼;日本临济宗初祖荣西禅师由宋携回茶种,将中国禅院茶礼引入日本,促成了日本禅院修行的吃茶风气等。
洁體用品
杨枝和澡豆,是行脚僧随身携带的洁体用品。杨枝又称齿木,功能是清洁口腔,据唐代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曰:“每日旦朝,须嚼齿木。揩齿刮舌,务令如法。盥漱清净,方行敬礼。若其不然,受礼礼他,悉皆得罪。其齿木者,梵云‘惮哆家瑟诧,‘惮哆译之为‘齿,‘家瑟诧即是其木。长十二指,短不减八指,大如小指。一头缓须熟嚼,良久净刷牙关。若也逼近尊人,宜将左手掩口。用罢擘破,屈而刮舌。或可别用铜铁,作刮舌之篦。或可竹木薄片,如小指面许,一头纤细,以剔断牙,屈而刮舌,勿令伤损。亦既用罢,即可俱洗,弃之屏处。……或可大木破用,或可小条截为。近山庄者,则柞条葛蔓为先;处平畴者,乃楮桃槐柳随意。预收备拟,无令缺乏。湿者即须他授,干者许自执持。少壮者任取嚼之,耆宿者乃椎头使碎。其木条以苦涩辛辣者为佳,嚼头成絮者为最。粗胡叶根,极为精也。”嚼齿木原为印度风俗,义净在印度见“五天法俗,嚼齿木自是恒事,三岁童子,咸即教为。圣教俗流,俱通利益。既伸臧否,行舍随心。”
在敦煌莫高窟146窟中,有一幅五代时期的壁画《胡僧揩齿图》,绘一胡僧赤裸上身,高昂着头,右手撑地,左手执齿木洁齿。(图1)“澡豆”是用于沐浴和洗衣的天然洗涤剂。两汉以后,海外香料贸易开始繁荣,豆面等去污原料与香料混合,即成散发香气的澡豆。据《十诵律》卷38 曰:“佛在舍卫国,有病比丘苏油涂身,不洗痒闷。是事白佛。佛言:‘应用澡豆洗。优波离问佛:‘用何物作澡豆?佛言:‘以大豆、小豆、摩沙豆、豌豆、迦提婆罗草、梨频陀子作。”据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10 曰:“诸苾茤以汤洗时,皮肤无色。佛言:以膏油摩。彼便多涂腻污衣服。佛言:以澡豆揩之,复无颜色。”
化缘之器
《敕修百丈清规》卷5中谈到钵,“梵云钵多罗,此云应量器,今略云钵,又呼云钵盂,即华梵兼名。”器身呈矮盂形,肩部凸出,钵口和钵底均向中心收敛,口径小于最大腹径。这种设计可令化缘来的饭食不易溢出,又利于保温。
《四分律》卷9 云:“ 钵者有六种,铁钵、苏摩国钵、乌伽罗国钵、优伽赊国钵、黑钵、赤钵。大要有二种,铁钵、泥钵。”“大者三斗、小者一斗半,此是钵量如是应持、应作净碗。”该书卷5 2曰“佛言:不应畜木钵,此是外道法。……时瓶沙王以石钵施诸比丘,……佛言不应畜此,……瓶沙王作金钵施比丘,……佛言比丘不应畜金钵,此是白衣法。若畜如法治,时王瓶沙复作银钵、作琉璃钵、作宝钵,杂宝作钵,施诸比丘,比丘不受,……佛言不应畜彼,畜银钵、琉璃钵、畜宝钵、畜杂宝钵,佛言不应畜,汝等痴人,避我所制,更作余事。自今已去一切宝钵,不应畜。”佛家禁用木、石、金、银、琉璃、宝、杂宝作钵,并以此鉴别在家和外道。
陕西临潼庆山寺是唐武则天时期营造的皇家寺院,在该寺塔基中出土了一件黑陶钵(图2),圆唇,敛口,圆底。胎质细密,胎体光滑,此黑陶泥钵符合律例规制。而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懿宗迎真身纯金钵盂(图3),钣金成型,圆唇,斜腹下收,小平底。通体光素,盂口沿錾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廿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金钵盂一枚,重十四两三钱,打造小都知臣刘维钊、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臣弘慤”。按《四分律》所言,“畜金钵”属于“白衣法”
柱杖规制
锡杖由锡、木柄、樽(铜套)三部分组成。锡是杖头,成塔婆形,附有大环,又悬数个小环。北宋善卿在《祖庭事苑》卷8中载:“西域比丘行必持锡,有二十五威仪。凡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挂于壁牙上。今僧所止住处,故云‘挂锡”。僧人至施主家门前托钵乞食时,以振锡替代敲门,使人远闻即知。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34曰:“杖头安鐶圆如盏口,安小鐶子摇动作声而为警觉。”行走时镮振动出声,以警策路上的虫蛇等。
义净认为汉地锡杖违反本制,依其《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自注:“言锡杖者,梵云契叶罗。即是鸣声之义。古人译为锡者,应取锡作声,鸣杖锡,任情称就。目验西方所持锡杖,头上唯有一股铁棬,可容三二寸。安其錞管,长四、五指。其竿用木,粗细随时。高与眉齐。下安铁纂,可二寸许。其鐶或圆或匾,屈合中间,可容大指,或六或八,穿安股上,铜、铁任情。元斯制意,为乞食时防其牛犬,何用辛苦擎奉劳心。而复通身总铁,头上安四股,重滞将持,非常冷涩,非本制也。”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懿宗供养迎真身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图4),钣金、铸造成型。杖头有垂直相交银丝盘曲的桃形双轮,轮顶为仰莲束腰座,上托一智慧珠。双轮每股各套錾花涂金银锡环三枚,共12枚。双轮中心的杖顶有三重佛座,座上饰忍冬团花、如意流云、宝相莲瓣,其上承托代表大日如来的五钴金刚杵。杵上又承托代表“地、水、风、火、空”的五大莲座,象征五形世界,座上有一摩尼珠。杖体中空,杖身上、下分别錾刻一周以联珠纹、莲瓣纹等为栏界的团花忍冬纹、团花蜀葵纹等花卉图案。中段主体錾刻手执各式法物,身披袈裟立于莲台之上的缘觉僧十三体,其间衬以卷枝蔓草鱼子纹。锡杖双轮上錾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慤”。
这件通体金银制成的华丽锡杖,即是义净诟病的“重滞将持”者。正如《佛说得道梯隥锡杖经》所载:“持锡杖威仪,法有二十五事。持锡杖十事法,一者为地有虫,二者为年朽老故,三者為分越故,四者不得手持,而前却,五者不得担杖著肩上,六者不得横著肩,手垂两头。七者出入见佛像,不听有声;八者杖不得入众;九者不得妄持至舍;十者不得持杖过中。”锡杖不但难以随身携带,繁缛的律仪也限制了它在行脚中的实用性,因而逐渐蜕变为法会仪式上专用的道具法器。
锡杖的实用功能退化后,禅僧行脚开始使用形制简易的竹、木拄杖。实物如日本东大寺藏镰仓时代木杖(图5),表面涂漆,曾为重源上人所持之物。重源原是镰仓前期醍醐寺真言宗僧人,受法然的感召皈依净土宗,曾入宋求法。据《祖庭事苑》卷8载:“今禅家游山拄杖,或乘危涉险,为扶力故。以杖尾细怯,遂存小枝许,串铁永者是也。行脚高士多携粗重坚木,持以自衒,且曰‘此足以御宼防身。往往愚俗必谓禅家流固当若是,岂不薄吾佛之遗训乎。”批评拄杖多用粗重坚木,禅者以此炫耀,实则违背佛家使用柱杖的规制。据宋人道诚《释氏要览校注》称,禅杖“以竹苇为之,用物包一头,令下座执行,坐禅昏睡,以软头点之。”在此基础上,汉地禅堂出现警人清醒用的警策棒,亦称香板。即一扁平长木板,一般长四尺二寸,上部稍宽,将近二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