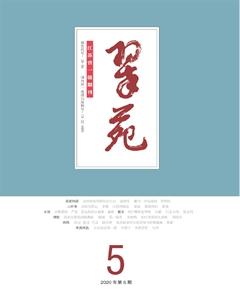活过爱过写过
陆克寒
一
1830年10月,一部小说在法国巴黎面世,题名叫作——《红与黑》,副标题为:“一八三零年纪事”。小说作者署名“司汤达”(中文亦译“斯丹达尔”),他的真名实姓是:马里-亨利·贝尔。
其时,这位贝尔先生年近五旬,他出生于1783年1月,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中年人士了。尽管时常出入富丽奢华的巴黎社交界,游走于时尚而夸饰的文艺沙龙,期待着某一天命运垂顾,暴得大名,一步便出人头地。但他终究未遇知音,无人提携,因而始终声名低微,不过就是位边缘角色罢了。而我一直以为:人到中年的司汤达,当他现身于巴黎社交界沙龙,渴望在那里获得激赏和天赐良机的时候,却分明又对之投以鄙夷的目光,他不掩饰内心的轻蔑,并且放出犀利的言辞刻意冷嘲热讽。此间情形一如《红与黑》中于连·索莱尔坐在德·拉莫尔侯爵的客厅一角,面对一屋子养尊处优的贵族,他内心既钦羡又仇视,他被自己的对立情感绞痛。我相信于连此番心理征象,便是司汤达本人拥有的切身体验;或者说,他就是将自身的这份心理体验,倾注在笔下人物心间,让人物代自己倾诉和表述。
但《红与黑》初版并没引起多少反响,它的境遇非常落寞,据说初版销售量仅有区区七百多本。要说这小说写得真不合时宜,在金碧辉煌、沸反喧天的巴黎浪漫主义舞台上,它像一只不小心闯入的灰色猫,上了场却发现没有自己的角色,只得尴尬退下。那是浪漫派风云席卷、风头劲爆的岁月,少年得志的雨果恰如朝阳一般升起,大仲马已凭早年的戏剧创作崭露头角,诗人谬塞已然赢得众多拥趸,而德拉克洛瓦热烈奔放的画风正引爆更热烈奔放的呼应……司汤达虽也高举着浪漫主义旗号,在1820年代前期问世的小册子《拉辛与莎士比亚》中,他就高调宣称:“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但他之所谓浪漫主义,其精髓却是——“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现实状况”“表现他们时代的真实”“因此感动他们同时代的人”。司汤达高扬浪漫主义大纛,是为抗衡势大力沉的法国古典主义传统,而其浪漫主义概念之精神内涵,却分明是“现实主义”——尽管这个语汇尚未在历史中登场亮相,但其直面现实、工于写实的创作品质,却早已在历史中伏脉流深。
事实上,《红与黑》便是这条历史伏脉的最新果實。它悄然登场,却不为人识。小说副标题——“一八三零年纪事”,即暗示小说叙事的社会写实、面向和追求,就此与浪漫主义的流行时尚豁开界河,悄悄勒转马头,不声不响地分道扬镳。而就在《红与黑》中,司汤达有一回竟中断叙述,他从故事背后跳将而出,直接向读者声言,并且声腔铿锵——
小说是路途上人们手中的一面镜子。它时而在您眼里反射出蔚蓝的天空,时而反射出路上泥潭里的污泥。而背篓里带着这面镜子的人会被您指责为不道德!他的镜子照出了污泥,您就谴责镜子!①
这是一位具有坚定的文学信念的作家,他的文学信念又支撑了他的文学自信。《红与黑》初版的冷遇,让他再次亲身感受到巴黎社会及其“文学场”的势利一面。但对于自己的作品,他依然保持着坚定的自信。他说:“到1880年,将会有人了解我”“我抽了张彩票,得奖的号码是:1935年拥有读者”“我一定要为20世纪而写作”。而我无意断言后来的文学史果然响应了司汤达的预言,我只想指出:就在1880年,法兰西文学的后起之秀左拉,深情赞美前辈作家司汤达为——“我们的大师”和“先驱”;而在20世纪琳琅满目的法国文学史撰述中,司汤达通常与巴尔扎克一起,被视为“现代小说”的奠基人。
二
我是在故乡小镇百货商店一隅,那节图书柜台里,偶然发现有本《红与黑》。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上大学回家过暑假。其时,距离上述司汤达预言中的1880年,又过了一百年;而距离《红与黑》1830年面世,则有150年之遥。尽管司汤达生前准确预言了他和他的小说的未来命运,但他绝对不会预想到——他的小说中译本会在遥远东方的某个江南小镇,与20世纪80年代的某位文学青年邂逅。
自从1944年赵瑞蕻先生首译《红与黑》,迄今80年未满,先后面世的不同中译本(含翻译修订本),总计不下于30种。如此品种可观的中译本,既反映了这部19世纪法国小说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广受喜爱,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其在20世纪以来广泛而巨大的世界影响力,即此足可佐证:司汤达当初所言——“我要为20世纪而写作”,听似自嘲,却非虚言,其间隐含着坚定的自信和自许。并且,他的自信和自许最终获得了文学史的支撑,他走在了文学史前头。他活着时遭受的冷遇,后来反证着他文学实践的先锋属性。他当初的文学边缘处境,日后成为文学史一脉流向。
韦里耶算得上是弗朗什-孔泰地区最秀丽的小城之一,城中尖顶红瓦的白房屋绵延散落在一座丘陵的斜坡上,成片丰茂的栗树勾勒出山丘任何些微的陂陀起伏。杜河的水在城墙根下数百尺的地方流淌,城墙从前是西班牙人建的,如今已衰败不堪。
《红与黑》从外省小城韦里耶起笔,朴素的环境描写只为人物出场而从容准备。小说故事场景依次从偏远小城韦里耶,到省城贝藏松,再转至首都巴黎,其实就是为主人公于连渐次扩开生活舞台和生命背景。这是小说空间的展开,而与此扣结着的,则是小说时间,它聚焦于——“1830年”。那是法国拿破仑时代结束后王政复辟的特殊岁月。精于叙事之道的司汤达自然明了:唯有将时间元素与空间元素不动声色地交织在一起,才有可能编排好小说叙事的经纬和脉络。
而你无论从哪一方面观照,《红与黑》都是一部编织得非常讲究的长篇小说。司汤达将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的故事,置放于韦里耶的乡间市镇背景中展开,而将于连与德·拉莫尔小姐的故事,安排在巴黎上层社会的背景中铺陈,两个恋爱故事之间,以于连在省城贝藏松的故事作为过渡——是过渡,也是间歇,叙述即此表现出节奏,犹如编织讲究轻重缓急。并且,司汤达虽然在小说中为于连设置了两场惊世骇俗的爱情,但他实不愿小说叙述停留于爱情展示的层面,他别有雄心勃勃的叙事抱负。他的叙事展开两个面向:他一面敞开主人公的恋爱故事,一面敞开现实社会实况,并且,他以人物活动将恋爱故事与社会实况交织在一起——这是司汤达小说叙事编织的又一处用心表现。至于小说细部的叙事编织,其讲究处在《红与黑》中几乎比比皆是,犹如碎金闪烁,叫人时时感佩司汤达的叙事缜密与细致。
三
但司汤达不仅仅是叙事编织的高手,他对叙事的讲究与用心也不仅仅停留于小说形式的层面。在我看来,更能体现司汤达小说创作的价值所在,并且,使其小说真正获得“现代小说”品格的,是他对人物心理的深度发掘与表现。《红与黑》不仅敞开人物恋爱故事,也不仅敞开现实社会实况,更为深切的是——小说敞开人物内心世界。这是司汤达创作最为强劲的聚焦处,构成其小说创作的叙事纵深。司汤达小说的深度心理表现,恰是20世纪小说的主流追求;正是在此意义上,司汤达成为“现代小说”的伟大先驱。
《红与黑》中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均带着自己的心理征候出场。司汤达显然意识到人的心理状态构成人的个性,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便是不同心理状态之间的复杂关联。他在小说叙事中敞开人物的心理状态,并且,在不同人物心理状态的关联中,精微而遒劲地刻画着人物形象。于连的情感和精神,为“拿破仑崇拜”激发,底层“英雄梦”遂凝结为他无法遏抑的热烈向往,而在王政复辟时代也便成为推进其命运的心灵原点。德·雷纳尔夫人虽然已经拥有圣洁的母爱,但爱情的缺失在其情感世界中既形成了某种空白,事实上也积聚着亟待补偿的能量,只是她本人起初还懵懂不察,却被老于世故的小说家司汤达一眼觑破。他悄然安排于连来到她身边,就此引燃她久被压抑的激情。某位家族先辈惊世骇俗的情爱故事,激奋着德·拉莫尔侯爵小姐,青春少女沉迷于“非凡爱情”的满心期待中,实在等不及了,她便自己着手“制造”——其实是“仿造”,她仿照祖上先辈的传奇制作自己的“非凡爱情”,自以为她的故事一如前辈故事轰轰烈烈,却不知所有的“仿造”本质即是平庸。司汤达藏身于他的小说中,冷眼逼视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动声色地照出他们的全部心思。他们都是有心思的人,他们沉落在各自的心思里,他们被自己的心思主宰。
而当我们深加察究,便会发现,司汤达常常让他的主要人物身处心理冲突的缠斗中。平民出身的于连,对贵族上流社会既羡、又恨,他一面鄙视它的浮夸与陈腐,一面却又不得不仰仗它而求飞黄腾达。德·雷纳尔夫人一方面沉浸在与于连的真切爱恋中,另一方面又沉溺在道德谴责的内心煎熬里。德·拉莫尔小姐既钦服于连的才华与勇气,她崇拜他,但内心深处的贵族傲慢,却使她鄙视他的出身。《红与黑》三位主角的内心世界,均充斥着对立而对撞的情感倾向,它们构成他们内心无法调和的心理冲突。这样的心理冲突是如此剧烈,有时竟如刀锋一般锐利,它使人物心理趋向充满着不确定性,也使小说情节发展充满着一种紧绷欲裂的紧张感。阅读司汤达的小说,我常常感受到一种高强度的叙事张力,它使得小说情节的发展具有多向度的可能性,因而难以捉摸和预判。我要说,这是一种需要身心投注的阅读体验,从中不断生发着阅读快感与欣悦,正是一部“好小说”带给读者的情感体验。而我更要强调的是:司汤达小说的情节张力,从根本上说,源于小说叙事得以充分表述的人物心理张力。
四
丹麦杰出的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其声誉卓著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将两位同时代的法兰西文学大师——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放在一起比较;他说:
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看见了和巴尔扎克并肩而立的另一位法国作家,而在他们那个时代,任何人绝不会想到把他们相提并论。他当时的文学生活悄然无声,默默无闻,正如巴尔扎克吵吵嚷嚷,风头十足一样。在今天法国年轻一代人眼里,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正如拉马丁和维克多·雨果一样,是清楚明白地相互补充的。把这两个作家的名字相提并论,或许只就这一点来说是不很妥帖的:一个写了将近一百部小说,另一个所写的长短勿论的小说不过两部而已。然而,司汤达这两部小说的质量是了不起的,足以使这位作家和现代小说之父并列而无愧。②
勃兰兑斯的叙述,点明了司汤达小说创作的价值终为世人认可的史实,而他有关两位作家创作数量与质量的看法,实乃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看法,绝非仅为其个人所见。巴尔扎克的个性既虎虎有势,其本人又为累累债务时时催逼,他得仰仗一杯杯咖啡维持日夜消耗的创作精力,立等着用手稿换得现钱来还债、开销。他既来不及潜心琢磨,也无法做到精雕细刻,他写得既快且多,仅“人间喜剧”便包含了92部小说——难怪雨果后来感叹,他说:巴尔扎克的“作品比岁月还多”。而司汤达则像一位勤勉的工匠迷醉于手头的工艺,他默不作声地精心打磨着自己的故事和叙述。尽管他渴望著有朝一日声誉鹊起,但执笔书写之际,他总会表现出真正手艺人的沉静品质,他写得耐心而从容,出手的成品自然有限。但他数量不多的小说,几乎均是质量上乘的精品,他精细而精巧地编织着他的小说叙事,将一应活计妥帖处理,不露痕迹,却能处处感受到他的讲究——讲究而不露痕迹,这才是叙述的真功夫!并且,他在小说叙事中敞开人物内心世界,他对人物心思及其内心冲突的表现,使小说叙事获得心理表现的纵深和高强度的张力——这更是叙述的大才华!
1842年3月22日,傍晚时分,司汤达照例在巴黎街头溜达,却突发脑溢血,被送入医院抢救,第二天凌晨去世,享年59岁。他的葬礼或许是19世纪最寥落的葬礼了,仅有三人参加,情景一如《红与黑》面世时遭受的冷遇。但可宽慰的是,为他送葬的三人,除了他的妹妹和堂兄外,还有一位是——作家梅里美,他是司汤达的知音和追随者,当时已崭露头角,而日后他和司汤达的名字一起被镌刻在法兰西文学史册上,星光辉映。
司汤达的墓志铭上刻着——“活过 爱过 写过”。这是他一生的总结,简练而明晰:“活过”,概括着他一生经历的丰厚内容;“爱过”,显示这“活过”的生命具有情感质地和神圣品格;“写过”,点明长眠人的作家身份,更暗示其生命具有某种永不泯灭的品质。
想想真有道理:一个人不仅“活过”,而且“爱过”,并且“写过”——这个人应该永垂不朽!
参考文献:
①司汤达著 边芹译《红与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445页。
②勃兰兑斯著 李宗杰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