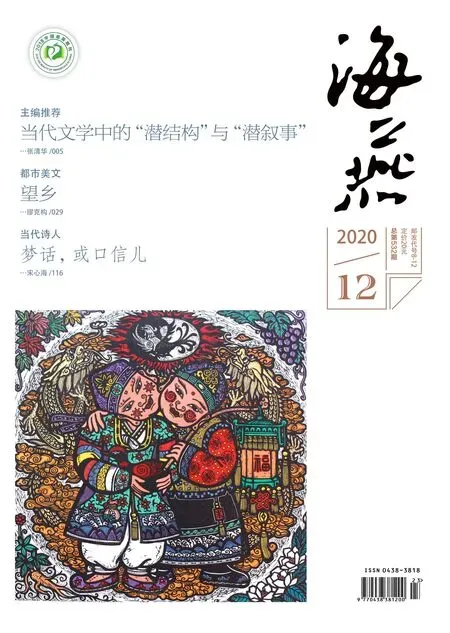读诗记(六)
文
全是爱
在布拉格诗人墓前,供奉着无数鲜花,清清亮亮的波希米亚玻璃器皿里,有清清亮亮的水,上面漂着燃烧的红蜡烛,而那清水里,有我的泪。在我模糊的泪眼中,闪过坟地里生长着的被捷克民族称作“母亲的魂灵”的小叶儿花,那是与马哈同时代的诗人爱尔本命名的:
母亲死去,
被送进了坟墓,
孤儿们留在了人世;
他们每天清晨去到墓地,
为了找回自己的母亲。
妈妈可怜这些小乖乖:
魂儿悠悠返回家,
化作朵朵小叶儿花,
盛开在自己的坟头上。
小叶儿花啊小叶儿花,你是母亲的魂灵,难道不也是诗人的魂灵吗?诗人死去,被送进了坟墓,读者尚在人世,他们经常到墓地去,带着鲜花和泪水,为了找回自己的诗人。诗人化作了朵朵小叶儿花,开在自己的坟头上,前可以见古人,后可以见来者。
可惜没能找到我心仪已久的诗人塞弗尔特的墓。我在所有埋葬着“妈妈”的坟前徘徊,看他如何找回母亲:
那是一面镶着椭圆金框的镜子,
背面的水银已经渐渐脱落,
几乎照不清楚人的模样。
妈妈的半辈子呀,
都是用它来照着梳理头发,
她是那样的秀丽端庄。
镜子挂在窗户旁的一个小钩子上,
它瞧瞧我,看看你,
怎能不舒坦地微笑?
妈妈曾是那般欢乐,
连一丝皱纹也不曾有,即使有,
也是为数不多的啊。
她常常在小磨坊里,
哼着华尔兹舞曲,
还和爸爸一起,
幸福地跳上几步。
当她追忆青春年华,
她便忍不住地瞥一眼闪亮的镜子。
她从梳子上摘下脱落的头发,
把它缠成一个小团儿,顺手给炉火加餐。
当她把发团往炉门里扔时,
我看到了妈妈眼角旁的条条皱纹,
已是一把张开的小褶扇。
天长日久,镜框变了形,
境面也裂了些小缝,
它里面渐渐发了霉,
后来终于裂成了两半。
妈妈就用这破了的镜子,
继续梳理着她的鬓发。
时光飞逝,妈妈的头发渐渐斑白,
她已经不再去照镜子,
习惯于待在僻静的地方。
每当有人来敲门,
她便匆匆忙忙走出来,
头上系着一块黑色的头巾。
如今,我又走进屋来,
但我心绪不宁。
没人再站在门槛边等我了,
也没人再将我的手握得那样紧了,
我不知所措地四下顾盼:
那面镜子仍旧挂在墙上,
可是我已经看不清它,
泪水模糊了我的眼帘。
(星灿 译)
写作这首《妈妈的镜子》的人,就是我特别心仪的诗人,被捷克人誉为“本民族伟大的经典诗人”的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1984年,“由于他的诗富于独创性,新颖而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全面发展的自由形象”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多想找到那面镶着变了形的金框的已经裂开的镜子。我确信它的存在,它出于诗,但来自生命和生活,应该进入捷克国家博物馆。
塞弗尔特,你知道吗?就因为喜欢你的这首诗,我多少回凝视镜子,妄图在那些镜子的深处,看见你笔下的“妈妈”。可是看来看去,却总是看见镜子里的我,和我的母亲。
我也写过一些关于母亲的诗,写过似乎永远不会走路、总是一阵风似的奔跑着的妈妈,写过《娘的脊背》《母亲的灯》,或许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写母亲的缘故,有文学前辈曾非常认真地劝导我说:“也写写你父亲吧。”让我不知说什么好。塞弗尔特,我该怎么回答?
对母亲的爱是一切动物的天性。恰恰因其是天性,古今中外,表达这种爱的人就格外多,使其成为诗的基本母题之一。但多数人靠的是原始生命力的推动,一不留神,情感就扎了堆儿,很难拥有特立独行的艺术表达。将一个儿子对母亲的爱凝聚在一面镜子中,将母亲的一生浓缩在一面镜子中,塞弗尔特,这是你的发现和创造,你的“这一个”母亲的形象,是有史以来最明亮的母亲形象,没有变形却又成了天下所有母亲缩影的折射。
塞弗尔特有数不清的好诗,顺便抄一首只有短短四行的《安慰》:
姑娘,姑娘,你为什么皱起眉头,
莫非你遇到了整日阴雨绵绵?
而那边那只小蜉蝣该怎么办啊,
它的一生都遇到阴雨绵绵!
(贝岭 译)
诗行单纯到了不能再单纯,内涵却又丰盈到了十分。如果说它单纯,明明白白,不用我说;如果说它丰盈,坚实饱满,那其中只可意会、无法言说的意味,说也说不透。索性不说吧,只体会诗题:这是一个诗人给我们大家的诗的安慰,如此浅显又深沉博大,如此忧戚又豁达风趣,还有比这更值得让人安慰的安慰吗?
以上是我在《诗人雕像诗人墓》一文中写到的塞弗尔特,意犹未尽。他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诗艺炉火纯青,不见丁点儿刀斧之痕,晚年甚至不用任何比喻和韵脚,只是用朴素的、类乎散文的语言表达极为本质的东西,抒写他复杂的内心感受和他对人生真谛的认识。在捷克,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他的诗集。
塞弗尔特给世人留下《全是爱》等三十九部诗集和一部回忆录《世界美如斯》。诚如其回忆录副标题“故事与回忆”所提示的,在《世界美如斯》中,诗人没有采用一般回忆录按生活经历依次叙述的写法,着墨更多的也不是他本人的曲折身世,而是通过一则则小故事缅怀他漫长一生中所遇到的人和事,记叙了一些见闻和感受。在我对其中的《母亲出嫁的小教堂》一节与他写妈妈的诗篇交替着阅读时,意外地从非常客观的叙述中体会出他如何行使了诗人主观主义的权利。他说:
如果有人感兴趣,向我了解父母的婚姻状况时,我恐怕要用纯粹是今天的术语来概括这一婚姻关系的特点了:那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人和平共处。父亲是社会民主党人,母亲则是一个娴静、温和的人,喜欢上教堂,借以摆脱刻板的日常生活,摆脱每天例行的机械劳动。上教堂是她的诗。领圣餐她却不常参加。不如说只有在生活中遇到不幸,她认为那是上帝的惩罚,需要求得上天的宽宥时才去。
就这样,在和睦共处中他俩各以自己的方式对生活做出反应。而生活往往并不顺遂,战争时期还经常挨饿。饥肠辘辘的滋味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母亲扑倒在日什科夫教堂冰冷、潮湿的方砖地上,当她虔诚地向圣母玛利亚倾诉自己的烦恼,徒然想把泪水串成念珠挂在圣母的纤纤手指上时,她的内心无疑感到了片刻的宽慰。而我则往返于两人之间,从这边跨到那边,从红旗歌到“千万次歌颂你”,也许就在一天一晚的时间内。
但愿读者不要认为我以一些无聊的个人琐事在此啰唆不休。现代诗人就往往完全从主观立场出发将诗歌拋到读者面前,以强调它的可能性,使它更有说服力。在我这不很重要的文学体裁中,我不免也要吹嘘一下这种主观主义的权利。不过这一文学体裁有其局限性,因为它不仅是可能,而且也往往就是真实的。我要证实时代错了,不管时代如何揭露我——虽然我还不很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塞弗尔特出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郊外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他未上完中学就跨入了社会,从事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1921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泪城》出版,他以贫苦大众的立场观察布拉格,以写实和抒情风格描绘了工人区发生的痛苦事件,表达了诗人对这个城市畸形生活的控诉和对未来的渴望。此后,塞弗尔特一边主持编辑刊物,一边体验母语内部的奥秘,对自己生命中潜意识、直觉、梦幻的成分进行挖掘,确立了他作为优秀诗人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投身抵抗运动,告别了超现实主义诗风和“话语实验”色彩,写诗揭露法西斯的残暴,歌颂人民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以后,诗人的思想变得开阔而深沉,他参与过捷克作协的领导工作,并连续出版了许多优秀诗集。在这些诗中他歌颂母亲,歌颂爱情,歌颂祖国和大自然,并追忆往事,沉思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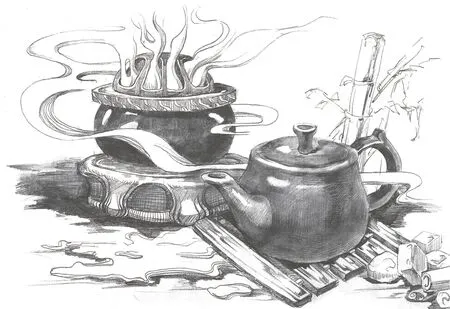
有论者指出,塞弗尔特一生的写作是朝着活力和自由展开的。围绕“活力”与“自由”,他不同时期的诗作无论是倾心于叙述性还是咏唱性,无论倾心于日常经验还是倾心于直觉,无论是隐喻还是日常口语,无论是使用自由体还是借鉴类古典抒情诗和民歌的形式,都做到了感情饱满而淳朴,措辞准确而内在。我却觉得,他的写作,是以活力和自由,朝着爱展开的。他那部诗集的名字《全是爱》,鲜明地概括了他一生的写作。
他的人,全是爱。
他的诗,全是爱。
前面我提到他的《妈妈的镜子》,那是诗集《妈妈》中的一首。说到这个书名,还有一个小插曲。诗集编好了,塞弗尔特花了好长时间寻找书名,怎么都觉得不合适。他的朋友费卡尔读过他的书稿,信手在封面上写下一个极普通的词:妈妈。正是这最朴素,在所有语言中发音都惊人相似的两个字,表达了人类最初、最直接、最普遍的爱。诗集《妈妈》的卷首,是这首《窗旁》:
春来了,路边的树儿
迎着春光开了花。
妈妈静默无声,
脸朝窗外,泪珠儿滚滚淌下。
“你为何哭泣,为何悲伤?
告诉我,你这般难过为什么?”
“我会告诉你的,会告诉你,
等到有一天,树儿不再开花。”
雪纷飞,冰霜冻在
玻璃窗上。
窗外一片阴沉,
妈妈无声地编织着什么,
两眼噙着泪花。
“你为何哭泣,为何悲伤?”
“我会告诉你的,会告诉你,
等到有一天,不再大雪茫茫。”
(星灿、劳白 译)
诗中母子二人的“对白”,意味深长。在季节枯荣的两端,母亲脸朝窗外,表情滞重,空气比妈妈的静默无声更加沉凝。她“滚滚淌下”的泪珠儿和回答,使解读的空间越来越深越来越远。我们忍不住要搞清楚那个让妈妈忧伤的“有一天”究竟是哪一天。不是说冬天来了春天就不会远吗,为什么那一天树儿不再开花?不是说到了冬天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吗,凭什么不再大雪茫茫?
于是我们想,有可能妈妈是在说她离开这世界的那一天。那一天即使树儿还在开花,大地上还是白雪茫茫,但对于她,两眼一闭一抹黑。或许她只是为自己生命必定的终结而流泪,为想到再不能看到儿子及眼前的一切而忧伤。以这样的方式表现母亲对儿女对人世的眷恋,进而表现诗人对母亲的依恋,诗意的纵深让人叹服。
换一个角度想,是不是母亲扫了一眼窗外,蓦然想到末日,有了一些担心?她老了,活透了,她知道,人活着,注定死,那个日子,到了时候一定要来。她为春花流泪,为飞雪流泪,为这个世界将被神明所弃流泪。表面可怜的妈妈并不可怜,她在向往,向往时间能减弱它的冲击,她珍惜美,留恋美,懂得悲悯。
当然还有更多解读的可能,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和适度的敏感,需要我们了解一点宗教,或者懂得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有更多的生命感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写这首诗时,诗人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从诗人“我会告诉你的,会告诉你,”这样的语气来看,这是倾向于沉默的对话,或者说是默默的内心独白。此时此刻,“妈妈”可能就在身边,也可能已经到了天堂。
和我曾经提到的《安慰》不同,那首短诗单纯到了十分,这首也短,却容纳了如此繁复的意蕴。
塞弗尔特写亲情,也常常写到爱情,是个一生痴迷于爱情的诗人,他有一首四行短诗《爱情》:“即将死于霍乱的人们/吐出铃兰花香,吸进铃兰花香的人们/即将死于爱情。”爱情,对他来说似乎意味着一切,犹如他在《皮卡迪利的伞》中的表白:“我一生都在寻找/在这里一度有过的天堂,/只能在女子的唇际/与她那丰润的肌肤间/充溢着温馨的爱情里/寻得踪迹。”
在塞弗尔特这里,女人大概是神话人物,所有的女人加起来是一个女神。只是,他不是抽象“她”,而是具体“她”,让“她”活生生地活在语言里,让你感受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他的《爱情之歌》这样写道:
我听见了他人听不到的:
光着脚走在天鹅绒上的声音。
邮戳下的叹息声,
琴弦终止时的颤音。
有时我有意避开人们,
我看见了他人看不到的:
那充满在微笑中的
隐藏在睫毛下的爱情。
她的头发上已卷起了雪花,
我看到了灌木丛中盛开的玫瑰。
当我俩的嘴唇第一次碰到一起时,
我听到了爱情悄然离去的声音。
即或有谁要阻止我的愿望,
那我也毫不畏惧任何失望的袭击。
别让我跪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狂热的爱情才是最美最美的爱情。
即使是狂热的爱情,在两个身体到一起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悄然离去。这种感觉不一定是每个人的,却是真实的,相当普遍的,到了诗中反而让人觉得独特,是因了诗人的真诚和言说的能力。再看《那些轻轻的亲吻之前……》:
当那些轻轻的吻
在你额头干涸之前
你弯着腰去喝
水晶清明的水
从来没人怀疑
你是否将接触那些嘴唇
某些时刻
不耐烦的血
从内部模铸你的躯体
比雕塑家的塑泥上
跑动着的手指更迅速
也许你会将她
年轻的头发放在手掌里
让它们掠过双肩
就像打开的鸟翅
你将沉重地追逐它们
那儿
在你眼前
并且在空气之下的深处
是那倾斜的,恐怖的
和甜蜜的空虚
渗透着点点滴滴的光。
(贾佩琳、欧阳江河 译)
许多人认为这首诗是塞弗尔特处理复杂爱情经验的典范之作。塞弗尔特中年之后写爱情,常常同时融进对“时间”“死亡”等意向的开掘。这样一来,爱情的浓烈与人生的短暂被扭结成一体。或许读来以为塞弗尔特是对爱本身忧心忡忡,其实是因为他知道爱的珍贵,他才痛惜人生的短暂。
此诗一开篇,诗人的心境明澈如水,爱人那“轻轻的吻/在你额头干涸之前”,湿漉漉的让你确信爱情的永恒,你将有无尽的“水晶清明的”生命之水,它们哪里会干,就像不停地吻着,多么滋润。从第二节开始,“时间”的主题出现了,转折出现了:时间若水,在流逝,“不耐烦的血”沉积下来,形同淤泥,开始“从内部模铸你的躯体”,如果不是成为泥人,那就重又回到土中…… 那可怎么办呢?不同的人将有不同的选择。偶然听我妈妈对我爸爸说:“我想走到你前头去,又怕你吃不惯别人做的饭。”顿时让我有了满眼闪闪的“点点滴滴的光”。
晚年的塞弗尔特,有一首《别了》,也有译者译成《那么告别吧》:
对世界上的成百万行的诗句
我仅仅增加了一点点。
他也许不比一只蟋蟀的唧唧叫声更聪明。
我知道。原谅我吧。
我正在走入尽头。
他们甚至不是最初的脚印
踏在月球的尘埃中。
如果偶尔他们毕竟闪出光芒
那不是他们的光芒。
只因我爱这些语言。
那能使一双安详的嘴唇
战栗的语言
将使年轻的恋人们相吻
当他们漫步穿过金红色的田野
在落日下——
这日落比在赤道上还慢。
诗歌从开始就跟随着我们。
犹如爱情
犹如饥饿,瘟疫,战争。
有时我的诗就是那么令人不好意思地愚蠢。
但我不请求原谅。
我相信寻找美丽的词语
是更好的事
较之杀戮与谋杀。
(安妮 译)
诗人回望来路,以温和朴素的话语,为诗一辩。诗人“正在走入尽头”,生命的时日所剩无多,于是他请求读者原谅,更请求诗歌原谅,他认为自己没有写出像“最初的脚印踏在月球”那样令人类感到卓异的诗篇,甚至有时“令人不好意思地愚蠢。”但是,诗人也有着自豪,因为爱的深沉,他的诗篇使一双双安详的嘴唇战栗。诗人说,如果自己的诗篇“偶尔毕竟闪出光芒”,那也不必感谢他,“只因我爱这些语言。”去感谢语言吧。最后一节,语义平和而坚定。诗人由开篇的请求“原谅”,发展到“我不请求原谅”。前一个请“原谅”是基于诗人个人,而后一个“不请求原谅”则是为诗。诗人一生都在寻找并表达诗意,在他看来,这是美好的事,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了!正是在这缠绵和慨叹中,我们看到了一颗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