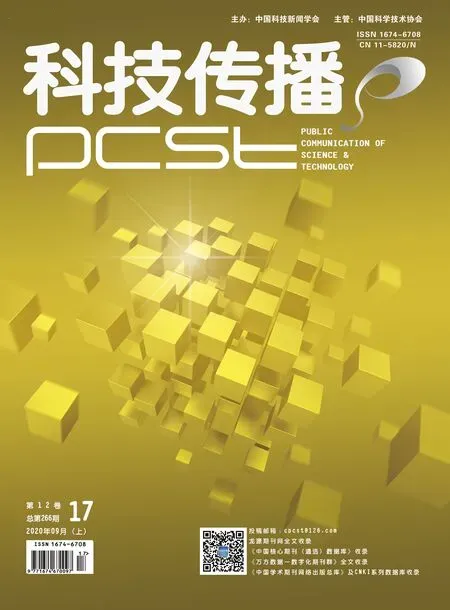传播学视域下我国集体记忆研究的发展与转向
储加音
1 集体记忆与媒介
记忆对人类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作为早期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领域的研究对象,记忆被定义为“个体对其经验的识记、保持以及再认或回忆”[1],用来解释个体如何在人脑中留存和理解过去的事情或经验。随后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发现,记忆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它还具有集体或社会的属性。最初发现这个问题的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他在1925年明确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并指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能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2]
学者们研究集体记忆主要是从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视角出发的。前者探讨的主要是集体记忆的留存与传播,而后者则突出集体记忆是现在对过去的重建。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2],它存在于社会中的任何群体和机构之中,大到社会阶级或者军队,小到一个公司甚至家庭。每一个族群根据现实对集体记忆进行重构,族群中的个体从中进行记忆并汲取力量,其承载的传统价值由此被延续下来。上述两种视角为集体记忆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路径,但二者并不矛盾,可以同时存在。随着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不断深入,回答“集体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3]。
从哈布瓦赫探讨语言是记忆必备的基本沟通工具之一开始,传播学领域也注意到了集体记忆与其学科的关联。王明珂在总结集体记忆的研究时指出,“集体记忆依赖媒介、图像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4]刘国强同样认为,大众传媒通过选择历史素材建构集体记忆,完成意义的生产和传播[5]。近年来,“媒介记忆”等概念的出现继续扩展和细化了传播学与集体记忆的理论联系。可见,研究媒介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承是至关重要的。
2 集体记忆研究在传播学视域下的应用
无论是何道宽根据麦克卢汉的媒介定义总结出的三次媒介革命(拼音文字-印刷术-电子媒介)[6],还是邵培仁归纳的五次传播革命(语言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互动传播[7],新兴传播媒介的出现总能有力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作为记忆的载体,刘燕指出,媒介形态的每一次革新都深深影响着记忆的方式和传播手段[8]。虽然在探究集体记忆的建构时一般是围绕“建构者是谁”和“如何建构”展开的,但“媒介即讯息”意味着这个问题并不能一概而论。相较于在特定时空形成集体记忆的传统媒介环境,互联网环境中模糊的时空界限和活动的权利关系颠覆了以往的建构方式。因此,要分析如何在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上建构集体记忆的问题时需要分开讨论。
2.1 由传统媒介建构集体记忆研究的发展
在传统媒介主导的时代,集体记忆的建构主要是由精英控制的。他们利用传统媒介,通过有选择的记忆或者遗漏去建构社会记忆,让受众“写入”有助于巩固精英权力、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然而,不同的媒介在建构方式上体现出了一些区别,下文将以我国部分研究成果为例进行说明。
1)印刷媒介。宋磊英收集并总结了从2009年以来《人民日报》有关汶川地震的纪念性报道,从灾区重建、救灾物资、英雄人物、纪念活动、灾后文艺五大议题出发,通过凸显和遮蔽的方式为大众建构了充满正能量的集体记忆,以重建灾民信心并塑造强大的国家形象[9]。
陈婧总结了从1995年到2018年《人民日报》在不同历史时期建构的有关“慰安妇”的集体记忆。纵观20年,《人民日报》从前期宏观的叙事报道逐渐聚焦到带有人文关怀的人物故事,从不同角度唤醒国人内心深处的创伤,强化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主义。当个人记忆凝聚成民族力量,民族伤痛被个体感知,这段集体记忆也随之强烈而平和地延续下去[10]。
李红涛和黄舜铭借助文化创伤理论,分析了1949年到2012年《人民日报》建构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研究表明,报道通过“耻化”叙事关注历史并引发当下的思考,“纪念事件”和“否定言行及回应”则构成报道主题。然而,文章并没有一味地正面评价作为官方权威话语平台的《人民日报》建构集体记忆时的思路。作者指出,受害者在报道中更多充当仪式化的角色,其主体性受到削弱,从而导致创伤情感和认同感很难感染到更多受众。同时,南京大屠杀借助其他历史事件的“再现”也难以突出其独特性[11]。
2)电子媒介高雅以“慰安妇”题材的电影作品入手,分析通过影像建构集体记忆的方式和价值。与文字为载体的新闻报道不同,电影中书写的“慰安妇”集体记忆是颠覆性的。通过“外聚焦”和“内聚焦”视角的结合,以及宏观和平民的交叉叙事,“慰安妇”不再单一呈现为民族受到欺侮的符号,而是有着自己生活和故事的生命。同时,看似柔和的记录方式配合色彩和音乐的恰当应用,起到了重塑国家形象的作用,反而更能激发大众对这段历史的集体记忆[12]。
陈杰在探究文化类电视节目《国家宝藏》的集体记忆建构时提到,传统文化不能直接转化为国民的文化自信,而集体记忆却可以以“中介”的形式促进这种转变。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被综艺化地表达、仪式性地呈现和重构,穿插式建构的集体记忆“让国宝活了起来”[13]。
吴迪指出,一些具有强烈民族认同感的传统节日,例如春节,是集体记忆的最佳载体。而春晚作为30年来庆祝春节到来的重要仪式,在大年三十当天将来自四面八方的国人聚集在一起,通过故事艺术化的讲述方式呈现与观众相同经历的生活片段,以唤醒集体记忆。同时,春晚利用拜年、倒计时等固定模式对集体记忆进行累积性和穿插性的建构;重建不同年龄段观众年轻时期的集体记忆,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近年来,媒介融合的大势发展将春晚固定的4小时延展为更长的记忆周期,为集体记忆的建构赢得了更好的效果[14]。
总体来说,我国对于在传统媒介中建构集体记忆研究的主题更多偏向于“苦难”和“纪念仪式”这类单一的具体事件,研究方法也多采用文本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从上述研究也不难看出,从铅字印刷的记忆到影像呈现的历史,被建构出来的集体记忆在样态上更加灵活,传承效果更加生动、真实。事实上,媒介技术的向前发展并没有让原有媒介停下建构集体记忆的脚步。旧媒介试图与新媒介融合,寻找更利于集体记忆传播的塑造形式。口口相传的历史利用纪录片等形式的影像呈现集体记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这一点也将在互联网繁荣时代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2.2 互联网繁荣时代集体记忆研究的转向
周海燕指出,互联网的高度互动性对集体记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有积极的影响。互联网为集体记忆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是当前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的热点之一[15]。虽然互联网在集体记忆层面在某种程度上给人类记忆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但它也会为公民化书写带来可能,对个体的赋权会给官方建构的集体记忆带来竞争,对集体记忆建构的研究可能会发生转向。因此,了解互联网繁荣时代集体记忆建构是非常必要的。
集体记忆在网络媒介中的建构与传统媒介相比看似只是更换了载体,但其建构的方式和复杂程度却大有不同。胡百精就集体记忆在互联网环境下要面对的冲突和挑战提出了见解。首先,互联网赋予了大众书写集体记忆的权力,精英群体不再垄断集体记忆的唤醒、转述和弱化。其次,由于互联网模糊了时间和空间的边界,集体记忆的建构机制也因此发生了改变。海量的信息、每一个都是“头条”的新闻让大众丧失了接收和思考它们的时间,网络上的集体记忆不再拥有向历史致敬的神圣感。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身处不同地理位置的人们来到同一个虚拟空间。虽然这有助于全球化集体记忆的构成,但网络空间里匆忙的交往不仅很难建构起牢固的集体记忆,来自“他者”的评价和介入也可能会颠覆原有的记忆,造成族群内部集体记忆的冲突和断裂。此外,互联网可储存大量数据,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强大的搜索功能找到想要的信息。例如百度百科词条在内的外在记录模式使大众鲜少将需要铭记的事物或文化内化在记忆中,留下的只是知识的存储和叠加[16]。可见,在媒介逐渐去中心化、集体记忆趋于碎片化、记忆效果不稳定的互联网繁荣时代,沿用以往理论已经无法回答“建构者是谁”“如何建构”等问题。
理论研究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实证研究的转向。麻月婷分析网络媒介对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集体记忆的建构时,选取人民网和微博、论坛等平台分别作为官方记忆场和民间记忆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官方网络媒介借助全媒体报道优势,有选择性地多元呈现成就、创伤、反思三大记忆主题;民间则对官方记忆进行补充和反刻写,从而使互联网环境中抗战集体记忆的建构走向开放和平衡[17]。此类对特定历史事件的文本研究很有必要,一方面它们探讨了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建构方式上的区别,另一方面也间接为理论研究者提供了向更深研究层次探索的素材。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李天一事件”“郭美美事件”等新媒体事件大量涌入大众的视野,普通网民参与生成集体记忆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例如周葆华和陈振华将视角转向受众,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影响大学生群体集体记忆深刻程度的因素,以及容易记忆的内容等[18]。钟智锦等人建立了2002年至2014年的新媒体事件数据库,同样以网民为主视角,通过情绪分析看不同类型和结局的新媒体事件对集体记忆的影响[19]。事实上研究视野从文本到受众的扩展,恰巧说明研究者更清晰地认识到集体记忆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没有明确的起点和落点。研究方法上多种量化手段的尝试也能更好帮助他们了解互联网环境下集体记忆的特征和变化。
3 讨论与展望
根据媒介发展脉络对集体记忆研究在传播学领域的梳理来看,我国研究者为厘清集体记忆的建构机制和意义价值等方面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但到此还是远远不够的。媒介的叠加创新和媒介间的有机融合都让集体记忆表现出不同的样态,例如春晚向移动端延展以增加大众互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日报》创建抗疫相关微博话题带领大众书写集体记忆等一系列变化都值得研究者展开讨论。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多的大数据分析工具可以辅助研究者完善之前在量化研究方面的不足,追踪互联网环境下集体记忆建构和效果的变化。总之,人类文明是需要记忆的,因为它是社会团结的基础,也是力量的源泉。集体记忆研究在传播学领域的发展和转向应该受到学界的重视,而每一个研究背后映射出的社会变迁更值得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