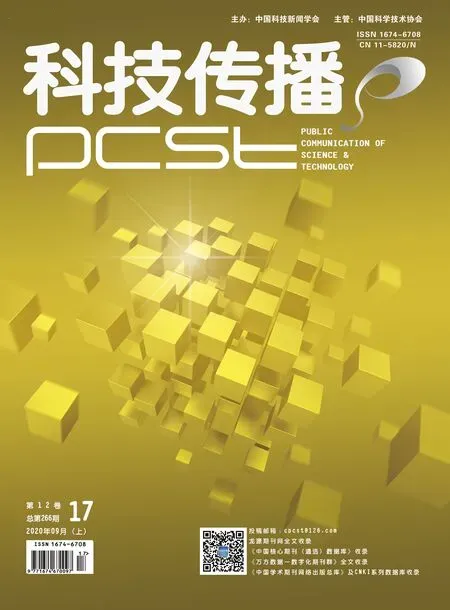信息即媒介:赛博空间中的媒介研究
罗 敬
在智能技术与智能城市作用下,技术身体已经成为“我们的身体体验是对于技术建构起来的身体体验”[1]。美国哲学家唐·伊德 (Don Ihde)笔下的体验主要指向赛博空间但也是现实空间的。智能城市,依靠技术与数据驱动的智能化城市实现了现实空间与赛博空间的二元融合,这就为被技术和信息浸润的身体,即赛博人[2]的传播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智能城市“这样被信息网络全覆盖的复合空间中,身体体验的不仅仅是实体空间,还要叠加上虚拟城市的网络世界”[3]。于此而言,赛博人必定借助一定的媒介穿梭于现实空间与赛博空间。智能技术被视为这种媒介,在一定程度上说,智能技术仅是现实空间的媒介而非赛博空间的,文章认为后者的媒介是信息而非智能技术。下文从媒介的再认识、赛博格及赛博空间的生成机制论述信息作为媒介的可能性。
1 媒介的再认识
媒介,英文media的汉译词,源于拉丁文medium,有中介、工具、手段等意。纵观传播研究史,媒介定义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黄旦认为,媒介主要有三层意涵:一是作为感官或体验的中介物;二是指向技术层面,如媒介技术、资本或新闻媒体事业;三是作为一种资源,是前二者的融合,即作为一种跨时空社会交往的技术或机构[4]。李沁在综合“百家”观点后认为:媒介是技术性的存在,主要以媒介环境学派为代表;媒介也是技术本体与人关系的延伸,如媒介即延伸;媒介还可以以时代进化划分为媒介群[5]。再观汉语媒介一词,其由“媒”与“介”逐渐演化为“媒介”。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媒,谋也。谋和二姓。”《周礼·媒氏注》中写到,“媒,谋和异类使和成者。”于此而言,“媒”即为介于两人之间的第三者,其发挥中介作用。“介”是象形字,指居于二者间的中介物。媒介一词的最早使用,有西晋与五代两种说法,至晚清,“媒介”一词发展出接近现代的意义,一是其由作为婚姻介绍的“媒人”延伸至任一起中间作用的人;二是指代对象由“人”延伸至“物”。
总的来说,既有媒介之意与实践主要指向人与人、物与物或人与物之间,换言之,媒介是物质性事物的中介。文章认为媒介之意还可以继续拓展,这种拓展即是一种延伸也是一种回归。延伸是指将媒介指代对象由事物延伸至事物的属性,如信息、空间等;回归指的是媒介之意即为两者之间的中介,其发挥的不一定是工具性作用也可以是关系性作用。进一步说,媒介之意不应被指代对象所局限,一切指代对象都是媒介之意的延伸。
2 赛博格的信息化
“赛博格”(cyborg)源于控制论,它是一种嵌入了电子设备或机械设备的生命体。最早的赛博格并不具有生命,诸如英国神经心理学家格雷·沃尔特(Grey Walert)的“乌龟”(tortoise)机器人、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bert Wiener)的自动扫描雷达。赛博格具生命特征始于美国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她将赛博格定义为:“一种有机控制体,一种机器与有机体的结合体,既是一种社会现实也是一种虚拟创造。”[6]如科幻作品中的各种生物与机器,现实生活中安装了人工脏器的也可视为赛博格。在哈拉维的助推下,赛博格打破了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的二元论,其典型的人类形象为重新思考人的本质提供了视角。从哲学上说,赛博格意味着我们从人类主体进入到了后人类主体。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指出,生物技术与身体的可能性使得人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再认识该主体。在美国人工智能专家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vec)看来,后人类是一种信息,因为人的意识可以直接下载到计算机并转移到纯技术建构的身体中。莫拉维克的观点或过于激进,因为后人类也可以是物质信息实体。美国学者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认为,赛博格是现实空间的信息延伸出来的可能性。当数字符号使信息可以脱离其物质载体,如文字可以脱离书籍,而符号技术被嵌入了人类的身体,这就形成了赛博格。因此,赛博格化的后人类主体实质上就是物质信息的实体。更进一步的话,赛博人即为一种身体+技术+信息的后人类,其体验空间既有现实空间也有赛博空间。
3 作为媒介的信息
就城市传播的媒介而言,一是城市中被运用的各种传统媒介及新媒介;另一种是将建筑物及城市自身视为媒介,如“作为媒介的外滩”“作为媒介的城市”。当传统城市演变为智能城市时,媒介是各种类智能设备、智能机器人抑或智能城市本身。毋庸置疑的是,上述媒介的确存在于智能城市中,这些观点也助推了智能城市媒介研究的发展,但这些媒介更多的是技术工具。智能城市作为现实空间与赛博空间的融合,现实空间意味着传统媒介依旧适用,但于赛博空间而言,作为事物的媒介技术仅是诱发装置,作为事物属性的信息才是媒介。
赛博空间是纯粹的信息空间,该空间中只有信息别无他物。20世纪80年代,在加拿大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科幻作品中首先出现了赛博空间一词。牛津大学计算机系的迈克尔·贝内迪克特(Michael Benedikt)认为赛博空间是由计算机与互联网共同作用产生的平行与现实空间的虚拟空间,任何计算机都能接入的新型空间[7]。在美国学者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看来,赛博空间是是计算机生成的维度,它“表示一种再现的或人工的世界,一个由我们的系统所产生的信息和我们反馈到系统中的信息所构成的世界。”[8]总的来说,赛博空间作为现实空间的延伸,它是计算机与人类知识的结果,是一种纯粹的信息空间,是对物质化的抽象,甚至虚拟出现实空间不曾有过的可能性。赛博空间作为一种源于现实空间的信息空间,其发展与延伸是现实空间与自身不断反馈的结果。反馈的中介不是其他而是信息本身,用海姆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把信息移来移去,我们围绕数据寻找出路。”[8]
技术身体是现实空间与赛博空间的连接媒介,是进入赛博空间的界面,不是赛博空间里的媒介,而信息才是赛博空间的唯一媒介。在海姆看来,界面是“连接电子线路的硬件适配器插头”,也是“用来窥视系统的视频硬件”,还是“人与机器的连接,甚至是人进入一个自足的网络空间”[8]。赛博人的技术身体即为一种界面——人与智能技术的连接。因身体的裹挟,当赛博人由现实空间进入虚拟实在的赛博空间时,她需借助技术身体将自身或需求转化为可在信息空间呈现的信息形式,如各种角色。而进入虚拟空间的不是人的身体,而是各种代码。于此而言,技术身体就是一种界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技术身体并未进入赛博空间,因为技术身体只是将现实空间中信息人一切物质性的东西转化为信息,而所谓的虚拟体验也没有发生在赛博空间而是现实空间,技术身体凭借其界面功能将赛博空间的信息转化为了现实空间中身体能感受到的信息。因此,赛博空间中流通的是信息,信息是媒介,而技术身体担负着转化信息的界面作用。
4 结语
信息作为媒介的可能性意在突出3个偏向:一是智能城市传播的核心在信息,同时,信息还“制造”出了赛博空间,该空间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越发明显;二是当信息成为未来的核心后,人也将随之信息化。按后人类主义思想的观点,人被信息环境信息化到一定程度时,同技术与身体的边界逐渐消失一般,信息与身体的边界也将逐渐消息,而人也就成为信息。或许这种认识过于激进,但毋庸置疑的是,未来的传播主体将被信息环境信息化并具信息的特征;三是当赛博空间成为更为重要的传播场域后,如何认识未来的传播空间、传播主体和媒介将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面向。探讨这些问题的最佳时机就是现在,智能技术与人的可能性已经向我们“招手”,类后人类社会的智能城市已渐行渐近,不要等到思想的列车停止了再去关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