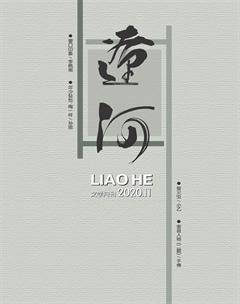故乡有条前沟
安海

故乡有条沟,就在老村堡门前方,因此村人把它唤作前沟。老村处于丘陵地带,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站在那里,让人真切体会到“塬、梁、峁、沟”这些词就是为这里的土地准备的。前沟深有数十米,最阔处达几百米,沟体不规则地向西、向北、向东北分叉延伸,像一棵千年古树的树根。村人所说的前沟主要是指由此伸向东北的那一条最长的沟。记忆中的这段沟,是有潺潺的泉水和绿油油的草滩的。在那个时兴修建水库的年代,村人在沟里打了土坝,修了水库,用以拦截泉眼的流水以及雨季顺沟而下的洪水来浇地。但村人仍叫这水库为前沟,而不是水库。不过,水库修成以后,人们一叫前沟,别人便明白这只是指水库,像是经过约定好的一样默契。他们世代生活在这沟畔,沟的概念已深入内心,不单只是一个苍白的称呼。例如他们把相隔不远的另一个村的一条沟便叫作水沟,只是因为那条沟的泉水要更加茂盛。
前沟里真正有了水,村里便破天荒地有了几块水浇地,种白菜、种芹菜,也种白麻。收菜的季节,全村出动,包括我们孩子。对于一个历代没有水浇地的丘陵村来讲,那不亚于节日。至于白麻,收割后要斩掉叶子,放到麻潢里沤。麻潢就是一个小水池,专门用来泡白麻的。那些去掉叶子的绿色麻杆被捆成一捆,一捆捆叠放到麻潢里,便没人管了。正是盛夏时节,在烈日的暴晒下,一股独特的臭味逐渐从麻潢里飘了出来,当这臭味达到一定程度时,有经验的村人便知道,白麻已经沤好了。于是就穿着雨裤下到麻潢里,把那一捆捆已经变色的臭哄哄的麻杆捞出来,立在地上暴晒。晒干后的麻杆从根部开始剥,一绺绺白色的麻丝便被剥了下来,这便是家乡有名的白麻了。这些白麻扎成团,交到生产队,成为村集体收入的重要来源。小时候,我最爱守着母亲看她坐在那里和那些婶子大娘们剥麻。母亲的手灵动、轻盈,那绺绺的白麻在她手里跳跃着,谈笑间身边已落下一层白色的麻杆,而怀里却是一团散发着淡淡清香的白麻。那时候我很困惑:为什么当初在麻潢里臭哄哄的白麻,在经过阳光暴晒后剥下来会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呢?
在夏季,前沟成了村里孩子们游泳的地方。村人并不把游泳称作游泳,而是叫“洗澡”,虽然时有家长骂,老师罚,但每天中午还是有不少光溜儿的身軀在沟水中快乐地游弋。对这些小伙伴们的勇敢,我多次心生羡慕之情,但却始终没有胆量下水去试一试,主要不是怕挨骂,而是我似乎天生对水有一种畏惧感。还记得那时老师查看学生是否游泳的方法便是用手挠他的皮肤,倘是游过,那么一挠便会有一道明显的白道,否则没有。到了冬天,来自西北方向的白毛风吹过后,前沟的水便结成了厚厚的冰。冰面平滑,在上面划冰船、赶尖牛,体味着一种超常的运动,虽冷但其乐无穷。
我现在就站在了老村的沟沿上,眼前便是莽莽苍苍的前沟。站在沟沿上,童年的往事还恍如眼前。但现在,前沟却什么也没有了。多年前的一场大洪水将那截土坝冲开了一个大口子,泽及村人的那一沟水便在老村人急切的目光中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呼啸着狂奔而去,似乎没有丝毫的留恋,之后也没有再回来过。而村里已经包产到户,再也难以聚起人来修坝了。前沟的泉水开始还流着,但不知何故后来竟也干涸了。没了水的前沟开始变得苍白起来,连沟底的草也失去了往日鲜亮的绿色,变成灰白色。开始还有人到沟里放牲口,后来连放牲口的也少了。有时候在雨季,洪水还会光顾前沟,但却并没有丝毫要停留的意思,只是把它当作了一条过道,只是路过,就像我们曾经路过的许多地方一样,或许连印象都没有。
我在沟沿缓缓地走着。早晨的空气新鲜而干燥,还夹杂着一种前沟所特有的泥土的气息。虽然这是一种贫瘠的气息,但却很纯粹,纯粹得令我迷醉。每次回村,我都要到沟沿上来,或者就下到沟底去。在沟底原来是有一片树林的,就在土坝的外边。当然现在它还在,但成材的树木已经被人砍掉了,剩下的都是一些从树根自生的幼树,或者枝桠交错的各种形状的残树,看了让人心寒。不过,春风吹来,它们一样会发芽吐叶,将绿色高高挂起,并招风引鸟,显示自己的存在。有时候回村带着女儿,她总是要我带她到沟底去,去看她眼中的小树林。虽然这树林实在也称不上是树林,但与我所居住的那座小城相比,还是可以冒充一下的。何况还有前沟,有前沟长满褶皱的沟体,有那洪水冲刷的沟渠,有那爬满沟坡的尖草和野花,还有那北面沟壁上过去挖掘的连环洞窟。这一切,都是近乎原始的,是自然天成的。自然的东西与人工的相比,总是充满了捕获人心的力量。女儿每次来,都会高兴地乱跳乱跑,围着我问这问那。那一串相连相通的洞窟,如今已经少有人迹,许多地方已经坍塌,连上去的梯路甚至也没有了。女儿有次好奇地要进洞去,但原来上洞的地方已被风雨磨蚀得光光的,实在爬不上去,便只好作罢。而小时候我是经常和小伙伴们到洞中去的,玩捉迷藏、玩打仗、玩生火做饭。洞窟的地上有一层厚厚的土,是细细的沙土,沙土中有一种米粒大小的虫子,它待的地方必是一个圆锥形的沙窝,只要看到这样的沙窝,就可捕获到它了。捕捉时口中还要念着一种儿歌,歌词却早已忘记了,念完后用双手从圆锥窝外围将沙土捧起,虫子便在手中的沙土里了。这种虫子的样子也早已忘记了,其实吸引我们的并不是虫子本身,而是捕获它的过程。有一次同村的二蛋从他当民兵连长的叔叔那里偷到一枚雷管,就在洞窟的边上挖了个小洞,然后点燃了导火索,我们都躲到很远的地方,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听到期待中的那一声巨响,大家都极其失望地走了。这些高大相连的洞窟像有些地方的窑洞一样,据说是当年备战备荒时的杰作,但备战备荒的功没有得到发挥,无意中却成了我们童年的乐园。
我沿着沟沿缓缓地走着,从西到东,不知不觉远离了村堡。东边的天空已经很亮,但太阳还没有爬出来。我看到前沟纵深处的沟壁,直挺着,像大地的一个横截面,硬生生地将这块土地的秘密暴露无遗。在这个横截面上,黄土、灰蓝的胶土、粗砂土以及细砂土一层层地堆积着,重叠着,像是在述说着什么。前几年,有国家的考古人员被前沟的这种独特地貌所吸引,对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结果发掘出大量的古动物化石和石器。因此前沟后来被认定为人类旧石器早期遗址,前沟的这种地层也被称为泥河湾地层,据说其年限距今已有一百多万年。一百多万年,实在是太久远了,远的让人简直无法想象。因而在喧闹了一阵子后,村人便又恢复了平静,似乎这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确,这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不要说一百万年,就是一千万年,他们不都还得种地吗?在他们心目中,前沟无论有什么化石什么石器都不如有水好。因此,对于这件事,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来,充其量也只是好奇而已。那些考古发掘出的动物化石和石器如今被保存在县博物馆里,安置在明亮的玻璃展柜里,下边做了详细的文字注释,在灯光映照下,显得光影迷离。每次陪外地的朋友到博物馆去,我都会带着他们到那个展柜前,郑重地对朋友说那里就是我的故乡。
据说,包括前沟在内的相距不远的“泥河湾遗址”有可能是世界人类的发源地。据说,在距今一百至二百万年的时候,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湖泊,属于热带地区,气候温暖,雨水充沛。在湖岸边,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高大挺拔,种类繁多的大小动物来往穿梭。而我们的祖先古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茹毛饮血,狩猎捕鱼,用石斧石刀开凿着一条通往文明的路径。后来,由于地壳的变动,湖水消失了,气候变冷了,一切生物也都被长埋于地下。而这只是百万年前的事,如今这里却什么也没有。前沟一片荒芜,甚至连过去曾经拥有过的水也游走了。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人类历史如此,何况地球的历史呢?
太阳已经出来了。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前沟那一览无余的沟壁,也照耀着老村的土地。前沟的边上就是老村的田地,勤劳的村人们早已经在地里忙活半天了。前不久刚下了一场透雨,使播下的黍子出齐了苗,这对于十年九旱的老村来讲,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出齐了苗子,就有半年的收成了,村人这样说。现在正是薅黍苗的时节,将多余的苗子除掉,剩下的就会吸风纳露般快快地生长了。不断有村人和我打着招呼,这些我唤作婶子大爷的村人,面色苍重,赶早便去侍弄这些黍苗,装满心间的是满怀的期望。由于下了及时的雨水,由于长齐了可人的黍苗,喜悦之情就直接爬满了他们面部纵横交错的沟壑间。我注视着田地里这些唤作黍子的作物,它们大都已有一拃高,绿色的叶面上有着平行的叶脉,并覆着一层白色的细绒。这是一种极其古老的作物,有人称它为五谷之首。有一个阶段,我曾经跋涉在那部古老的《诗经》中,在那里,黍子是我常见到的一种风景。“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自昔何为,我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今适南亩,或耘或耔。”茂盛而茁壮的黍苗,蓬勃在历史的天空下;浓郁而迷人的黍香,彌漫在诗意的空气里。据有人统计,在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黍字共有二十八例,位于所有作物之首,而在对殷商甲骨文的统计中,黍字在卜辞中更达到一百零六例。这些都足以说明在我国的远古时期,黍子是一种极其普遍的作物。这种古老的作物,带着远古的气息,乘着诗歌的翅膀,穿越千万年的历史时空,充盈着我的目光。的确,百万年前的盛景早已随风而去,只留下这空空阔阔的前沟,还有沟旁这依然如故的古黍。前沟作为一种风景已然走进村人的生命里,而黍子也还在充实着家乡人的肚腹,延续着家乡人的血脉。
太阳升高的时候我听到了母亲的呼唤。她那苍老低沉而有力的声音沿前沟逆沟而上,我知道她是在叫我回去吃饭。我拾起她的呼唤,开始往回走。陪伴我的,右边是苍苍茫茫的前沟,左边是广阔的黍田和黍田中劳作着的父老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