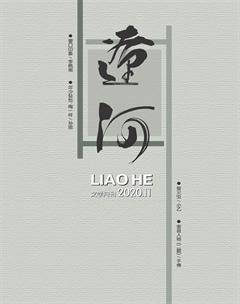酒葫芦(二则)
李建军
吴二宝倏地站起身来,冲着韩三爷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两枚军功章,在昏暗的屋里熠熠生辉。
宇高兄是县里某局的副局长,但就是个副科级干部。然而,在一个人口百万的大县,从一个乡村少年走到这个位置,也是了不起的了。有一次在一起小酌,他跟我讲起他舅舅的故事。
我就这么一个舅舅,前两年刚去世。说起他一生的爱好,就是好喝酒。村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酒葫芦。即便是早些年日子过得艰难,他也没断过酒,当然那是供销社里最低廉的山芋干酒,散装的,五毛钱一斤。
我舅干庄稼活也是一把好手。早些年,每回下地干大活,也就是干那些出大力流大汗的活,比如三夏大忙收麦子、插秧,比如秋收割稻,比如寒冬天割芦柴……这时候,他都会带上一个酒葫芦。这个酒葫芦并不揣在身上,而是放在地头上。
比方说这天是在大田里割麦子,我舅和几个庄稼汉同时开镰,从这边地头割到那边地头,再另起一垅,从那边地头割到这边地头,一个来回,刷刷刷,他就把人家甩下半程的距离。到了地头,他直起腰,舒展一下身体,便拿起酒葫芦,美美地犒劳自己,喝上一口。
那个摆在地头上的酒葫芦,成了他干活的强大动力。哪怕累得筋疲力尽,这口酒喝下去,我舅心里就像窜起一股火苗,身上就像拧紧了发条,油加上了,电充上了,血补上了,力气又回来了。
我舅喝酒,对下酒菜从不讲究,拍个黄瓜或炒个花生米,他就说了不得的好。日子艰难时,一根大葱,一粒大盐,照样下酒。
我舅有两个儿子,但没有闺女,这是他一生的遗憾。闺女是爹的酒坛子,逢年过节,闺女拎酒回门,是习俗也是情理。我舅说他没这个命。他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表哥,我舅为他们盖了宅院,娶了媳妇,分家自立门户,他们却没给我舅买过一瓶酒!这样的儿子,听说在村里还不是少数……可悲可恨可叹,不提他们了。
我是我舅的外甥,外甥是舅家一条狗。我知道我舅这点嗜好,每次去看他,一定会孝敬他一两箱酒。你知道,现在这些白酒啊,低于百八十块钱一瓶的,还真拿不出手。我送给我舅的酒,也就这个档次的。但我舅却一瓶也舍不得喝,全都拿到村里的小店,换成八块钱一瓶的小烧喝。
这事我是后来知道的。我对我舅说,几块钱一瓶的白酒不能喝,都是酒精勾兑的,喝了伤身体。我舅说,外甥啊,你买这么贵的酒送给舅舅,孝心你舅领了,可你舅哪敢这样遭践呀,这要是喝刁嘴可了不得!你舅就喝几块钱一瓶的,一辈子喝顺溜了,就这挺好。我想,那就这么办,最差也要送十几二十块钱一瓶的二锅头吧,多送几箱,牌子正宗,不会有假。哪知我舅连忙摆手,说外甥啊,你还是送那贵的给我,我自个儿拿去调换。我外甥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孝敬我的當然是高级酒,这全村上下没有不知道的!我舅一脸陶醉。
我舅活了八十多岁,无疾而终,也算是喜丧。我接到报丧的电话,就开着车朝村里赶。到了舅家,我舅的遗体已经穿了寿衣,安放在灵堂里。给我舅主持丧事的老人对我说,你舅已经咽气不短时间了,可是出了桩怪事。别人咽气后,嘴也抿上了,眼也合上了,可你舅到现在还张着嘴睁着眼,怎么摸溜也不行,像是这凡间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了呀。我一看,还真是的,我舅死不瞑目、死不合嘴这是为什么?老人又说,你两个表哥也都祷告过了,不管用,听说你舅生前最看重你这个外甥,你再想想办法。
我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舅舅啊,你这一生好酒,是不是凡间的酒还没喝够?
我赶紧跑到我的车跟前。是的,我的后车箱里有瓶好酒,我舅一辈子都没喝过的好酒。我拿了酒跑到舅舅的灵前,启开酒瓶,朝我舅的嘴里倒了一口酒。
我舅的喉咙隐约动了一下,还隐约响起咕噜一声,我舅一直张着的嘴闭上了,眼睛也合上了,我舅舒舒坦坦地去了天国……
丑女情结
董之瑜如今是个成功人士。有次一起喝酒,他说,他的出身成分不好,父母原来都是小学教师,受牵连发配到生产队劳动。那个年代,有一段往事,他至死难忘。下面就是他讲述的这个影响他一生的往事。
我从上小学起,就惧怕上学。那时,贫下中农子女上学是不用交学费的,但四类分子的子女却要交学费。每次开学后,老师都要在课堂上强调:四类分子子女听好了,这两天要把学杂费带来!不交学杂费不准上学!班上就我一个四类分子子女,全班同学鄙视的目光“刷”的一下集中到我身上。那时虽然年少,可也要脸呀!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十五岁那年我初中毕业,考了全校最好成绩,但还是因为成分问题,不准我上高中了。实际上,那时我也认命了,不想上学。我实在受不了每学期让我交学费时那种歧视的目光。我感到一种解脱。
回到家,我就是生产队里一个整劳力,当然是干最苦最累的活。这也没什么,关键是我一年年长大了,婚姻问题又成了父母的心病。
记得我十八岁那年,有天夜里,我睡在西房,房里还有我的两个弟弟,一个比我小三岁,一个比我小六岁,他们睡得跟猪一样沉,我心里却有种骚动,睡不着。忽然,听到睡在东房的父母那边传出低低的声音。先是母亲的一声叹息:“小瑜今年十八了,要是找不到媳妇,过两年就更难找了。南乡他大姨头晌跟我说,她那庄上有个闺女不错,高个子,大眼睛,长得雪俊……”我听得心里怦怦跳,兴奋又紧张,这么好的条件,她能嫁给一个四类分子的子孙?果然,母亲接下来叹了口气:“可惜是个哑巴……”我愣怔了一下,头脑一片空白……这时,只听一直沉默的父亲说:“哑巴有什么不好?小瑜要能娶了她,往后两人还不吵架哩……”是啊,哑巴有什么不好,这么漂亮的哑巴姑娘,我真想见一见。
可是,就是哑巴姑娘,人家父母也没有同意。
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我把找对象的目标放低,聋哑、麻子、瘸子……只要不是瘫子瞎子,长得丑也没关系。一时间,只要看到丑女,我便两眼放光。用现在的话说,丑女才是我的菜!
咱庄的张三丫,稀稀的黄头发,虾皮眼,大龇牙,塌鼻子……年龄还比我大三岁,我有意去接近她,朝她献殷勤。我感觉她并不讨厌我,好像对我也有点意思。没想到,有一天,她找到我说,你跟董大扣捎个话儿……董大扣是我本家兄弟,他家成分是贫农,长得不如我,上学时还留了好几级,那个笨啊……原来,她想让我帮她跟董大扣穿针引线。
唉,本庄最丑的女子都瞧不上我啊!
后来,咱庄的李秋生到外县干瓦工,带回来一个俊媳妇。庄上人说,李秋生是连哄带骗,生米做成了熟饭,把人家姑娘弄到手,骗回来的。
我也萌生了外出干瓦工的想法。
于是,这年开春,我到邻乡的山口大队干瓦工,认识了在工地上做饭的江小芹。那是水利工地,修水渠,大伙儿白天干活,晚上就住在工地上的临时工棚里。江小芹皮肤有点黑,偏胖,不算漂亮,但也不丑,比张三丫强多了。据说她父亲还是大队干部——想到这一点,我心里有些发怵,迟迟不敢有所表示。倒是江小芹主动。她上午从庄上赶到工地,做中午和晚上两顿饭,大伙儿吃过晚饭,她还要收拾一下才回去,这时天已黑下来,她回庄上要走四五里路。这天晚上,她对我说:“董之瑜,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朝庄上送一送……”这个忙我岂能不帮,梦寐以求啊!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江小芹说,董之瑜,你跟他们不一样。我说,咋个不一样?她说,就是不一样嘛,你是个书生。
两个年轻人,都有那个意思,关系迅速升温,从牵个手,到搂搂抱抱,到亲吻,有一次我差点就得手了,江小芹也没拒绝……但关键时刻,我突然下不了手了。
我想到咱莊上刚发生的一件事。咱庄孙大明家是富农成分,他和邻庄的张翠花偷偷摸摸谈恋爱,致使张翠花怀孕。张翠花的父母发现后,硬逼着女儿把孩子打掉,也不让她嫁给孙大明。张翠花绝望之下,上吊自杀,一尸两命,那个惨呀!
想到这儿,我害怕了,我怕害了江小芹。我宁愿打光棍,也不能害了人家。
江小芹见我这样,觉得我不是轻浮之人,反而更喜欢我,执意要带我去她家里,见她父母。
我忐忑不安地到了江家。她家备了一桌菜,还有酒。
她父亲是大队会计,叫江士锦。
席间,江士锦问我哪庄的,我照实回答。
江士锦“哦”了一声,盯着我看,又问:“你爸叫什么名字?”
我愣了一下,硬着头皮如实回答。
江士锦的脸色陡然沉了下来,一连串地问:“你爸是不是大个子?是不是原先当过老师?……你家什么成分?”
我支吾着,语无伦次:“是,是……我家,我家成分……”
江士锦一拍桌子,大怒:“你什么玩意儿!你家是地主成分!你想找我闺女做亲,门都没有!滚远活的……”
我吓得夺门而逃。
后来我才知道,江士锦和我父亲是初中同学。
从那天起,江小芹不来工地做饭了,我也再也没有见到她。
后来,你们也知道,时代变了,恢复了高考,我考上了大学。
上大学时,有个家境优越的美丽姑娘看上了我,对我有所表示,但我装聋作哑,不敢接受。我知道,曾经的“丑女情结”已在我心里打上了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