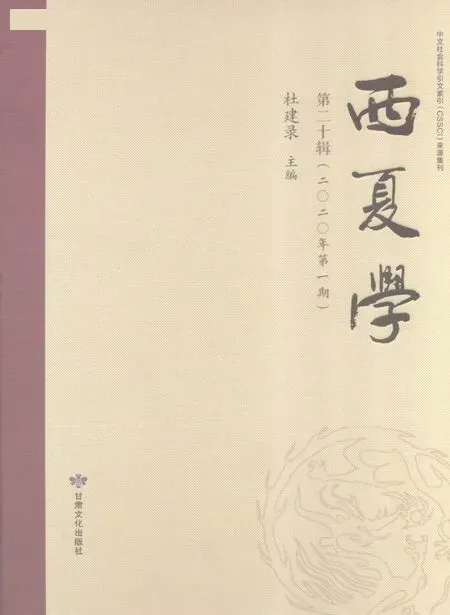论宋仁宗朝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攻守理念的转变
——以好水川之战的演进为中心
王战扬
宋朝在延州之战以后,加强了边防军事备御,并做了人事调整:贬谪范雍为安州知州,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分别主持泾原路和鄜延路;在中央罢免宰相张士逊,枢密使陈执中等,重新启用吕夷简①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为重振西北边防军威,在诸位边臣的主持下进行了军事弊病的改革,并展开了攻守之议,最终制定了主动进攻的军事决策,对好水川之战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军事决策为视角,一是考察好水川之战前边防军事弊病的改革与攻守之议;二是探讨好水川之战中边防层面的临敌决策及其存在的诸多问题;三是论述好水川之战后西北边防攻守理念的转变问题。希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①代表性的相关成果有:中国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刘庆、毛元佑:《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另有安北江:《宋夏好水川之战问题再探》,《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主要侧重于军事地理问题的探讨。,能够进一步揭示宋仁宗朝在对夏战争中军事决策的制定与执行之间的矛盾及诸多弊病,并对加深理解中央与缘边之间两个层面的互动关系有所助益。
一、好水川之战前边防军事弊病改革与攻守之议
宋朝在延州之战以后,在边防进行了积极的军事弊病的改革,包括军事部署的调整,军事运行弊病的改革,同时展开了攻守之策的议论,构成了战前军事决策的重要过程和必不可少的内容。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癸未,陕西安抚使韩琦上奏指出西北诸路的军事屯驻与人事安排等问题:
鄜州不能守,则延州城寨,非朝廷之有也。……臣虑出其不意,再来奔突,故御捍之备,宜以鄜延为先。……臣今为陛下计者,莫若差锐兵三五千,或于同州、河中府等处分减,进屯鄜州。选才望大臣一员,复本路经略之任,兼知鄜州,处置边事。令张亢就充本路钤辖,于鄜州驻扎。用朱观知环州,就差葛怀敏充环庆部署。如朝廷必以经略一司更不合置,即乞专于鄜州益兵,使葛怀敏知泾州,充替夏竦。……然后并兵入城,只留人员兵士三二十人,以为斥候。……愚短所见,愿早裁择。上皆纳之。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三月癸未,中华书局,2004年,第2995—2997页。
韩琦认为:首先应从同州、河中府等处分减兵卒屯驻鄜州,选有名望的臣僚一人担任经略安抚使兼知鄜州,令张亢为钤辖,以重兵驻扎鄜州,在同州、河中府可屯驻策应兵马;其次,环庆路最缺乏得力将帅,朱观可为环州知州,葛怀敏为环庆部署,或使葛怀敏代替夏竦为泾州知州;再次,朝廷还应大力招募才勇之士,差选弓箭手和边境巡逻之人,加强巡护边防。康定元年(1040年)七月癸亥,鄜延钤辖张亢也上疏指出了边防军队中存在的诸多弊病:一是边防统兵官有严重冗员问题,在军事决策会议上因意见不同,众说纷纭,使得事权不专,决策效率较低;二是泾原路兵力过于分散,不能集中力量阻挡劲敌入侵;三是诸路策应不力,朝廷应按照一定的编制与兵力,以旗帜为号加强应援;四是边防应加强练兵,提高军队战斗力;五是防止将士贪功轻进,开弓箭手晋升渠道,激励边民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七月癸亥,中华书局,2004年,第3025—3028页。。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癸巳,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为进一步提高边防军队的战斗力,又上奏朝廷将勇、懦之兵分队重组:
缘边部署、钤辖下指挥使臣,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知将之威惠,以是数至败衄。昨诸班中选武艺优者为寨主、监押,然拘于一城,未能各适其用。欲下陕西都部署司,分所试中人,鄜延路十五员,环庆、泾原、秦凤路各十员,为逐路教押军阵,以士卒所习精粗,重行赏罚。如此,则老懦者不能自容,勇壮者各思奋身,复免主将争占精兵,专为己卫也。又临敌取胜,必有奇兵,若并力出攻,则所向皆溃。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癸巳,中华书局,2004年,第3032—3033页。
即韩琦认为以往将勇、懦士兵混为一团的做法,极易导致战争失败,其旨在令边防诸路组建精兵,以便发挥精壮将士奋勇杀敌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避免勇者在作战之时被懦者所拖累。韩琦要求朝廷从士兵、厢兵、禁军之中选马上使刀、枪槊、铁鞭、铁简、棍棒勇力过人的士卒编为平羌指挥军,每指挥编制为五百人,各给予其壮马和丰厚的赏赐;西北四路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秦凤路,每路各置士兵和屯驻驻泊兵士一指挥;其中鄜延路驻扎在延州和鄜州,环庆路驻扎在环州和庆州,泾原路驻扎在泾州和镇戎军,秦凤路驻扎在秦州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癸巳,中华书局,2004年,第3032—3033页。。可谓对西北边防的军事部署重新做了规划和重组,增强了对夏的军事实力。范仲淹主要针对作战时的出兵机制,也积极提出了西北边防军事弊病改革的建议,认为以往每当遇敌,将官不问敌兵数量多少,皆按照官卑高下出兵迎战,多导致失败:“先是,诏分边兵,部署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有寇则官卑者先出。(范)仲淹曰:‘不量贼众而出战,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为分州兵为六将,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贼不敢犯,既而诸路皆取法焉。贼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盖指雍云。”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庚戌,中华书局,2004年,第3035—3036页。改革以后将每州士兵分归六将指挥,每将带领三千人,遇敌则根据其数量多少出兵作战,并推行到了边防诸路,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除对西北边防的军事部署及弊病做出调整与改革的同时,朝廷也展开了关于对西夏的攻守之议。“初,晁宗悫等至永兴议边事,夏竦等合奏:‘今兵与将尚未习练,但当持重自保,俟其侵轶,则乘便掩杀,大军盖未可轻举。’及刘承宗败,上复以手诏问师期,竦等乃画攻守二策,遣副使韩琦、判官尹洙驰驿至京师,求决于上。”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乙未,中华书局,2004年,第3060页。起初晁宗悫等人到永兴军商议边事时,夏竦以将士不曾训练为由,主张固守边防,若西夏入侵则乘机出兵掩杀。在刘承宗失败以后,宋仁宗下诏询问夏竦出师日期,夏竦等制定出攻守二策,遣韩琦、尹洙到京师与二府商议,令皇帝定夺。康定元年(1040年)十二月乙巳,“诏鄜延、泾原两路取正月上旬同进兵入讨西贼。上与两府大臣共议,始用韩琦等所画攻策也。枢密副使杜衍独以为侥幸出师,非万全计,争论久之,不听,遂求罢,亦不听”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巳,中华书局,2004年,第3062页。。韩琦等入朝与二府商议以后,宋仁宗决定采取其攻策,枢密副使杜衍反对本次军事决策,认为不宜“侥幸”出兵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一〇《杜衍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0191页。。吕夷简则表示赞同:“自刘平败覆以来,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韩尹健果如此,岂可沮之也,然吕不计事之可否,而但持此说,识者非之。”③[宋]田况撰:《儒林公议》卷上,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实际上吕夷简之所以同意本次军事决策主要是想要重振军队士气而已,并不在于其计策如何。进攻西夏的军事决策制定以后,为筹备军粮,康定元年(1040年)十二月丁未,“诏开封府、京东西、河东路括驴五万,以备西讨,从陕西经略司所上攻策也”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丁未,中华书局,2004年,第3070页。。括市五万头驴主要用来驮运粮草。据《东轩笔录》载:“韩公曰:‘今大兵入界,则倍道兼程矣。’(楚)执中曰:‘粮道岂能兼程耶?’韩公曰:‘吾已尽括关中之驴运粮,驴行速,可与兵相继也。万一深入,而粮食尽,自可杀驴而食矣。’执中曰:‘驴子大好酬奖。’韩公怒其无礼,遂不使之入幕。”⑤[宋]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43页。
在军事决策的执行上,泾原、鄜延两路并不能达成一致。陕西都转运使范仲淹言:“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西则邠州、凤翔为环、庆、仪、渭之声援,北则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东则陕府、华州据黄河、潼关之险,中则永兴为都会之府,各须屯兵三二万人。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复命五路修攻取之备,张其军声,分彼贼势,使弓马之劲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二三年闲,彼自困弱。待其众心离叛,自有闲隙,则行天讨。此朝廷之上策也。又闻边臣多请五路入讨,臣窃计之,恐未可以轻举也。”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五月甲戌,中华书局,2004年,第3012页。可见范仲淹主张严守西北边城,充实关内边备,据险而守。使西北五路虚张声势,敌来则坚壁清野,“未可出师”⑦[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九二《田况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9778页。,以此消耗西夏国力,待西夏疲敝之时,可以实行缓攻之策⑧刘庆、毛元佑:《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6页。“宋朝两路边帅韩琦、范仲淹在此问题上的主张是不一样的:韩琦主张集中兵力,深入西夏腹地,寻求敌人主力决战,以绝永久之患,范仲淹则要稳扎稳打,打算先巩固边界防线”,然后进取,两路边帅之间不能达成共识,已经为战争埋下了失败的隐患。。“朝廷既用韩琦等所画攻策,先戒师期”,而范仲淹又上奏言:“鄜延路已有会合次第,不患贼之先至也。贼界春暖,则马瘦人饥,其势易制。又可扰其耕种之务,纵出师无大获,亦不至有他虞”“鄜延路入界,比诸路最远。若先修复城寨,却是远图。请以二月半合兵万人,自永平寨进筑承平寨,俟承平寨毕功,又择利进筑,因以牵制元昊东界军马,使不得并力西御环庆、泾原之师,亦与三路俱出无异”“朝廷虽许仲淹存鄜延一路示招纳,仍诏仲淹与夏竦、韩琦等同谋,可以应机乘便,即不拘早晚出师。”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〇,庆历元年正月丁巳,中华书局,2004年,第3079—3081页。朝廷采取了韩琦等人的进攻之策,也同意了范仲淹保留鄜延路缓攻的意见,虽使其不拘于早晚出兵,但却令其与韩琦、夏竦共同谋议,以便随机应变。针对范仲淹缓攻的奏论,夏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戊辰,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言:“范仲淹前已相度泾原、环庆、麟府等路齐入贼界一二百里,四散攻击,乞朝廷发军须器械,以正月上旬至延州,又别立入界擒捉蕃汉赏条甚备;又近者朝廷取问不逼逐塞门贼马之因,仲淹亦奏称非是怯惧,候将来春暖大为攻取之计;又奏西界春暖马瘦人饥,易为诛讨,及可扰其耕种之务,与臣前所陈攻策并同,但时有先后尔。贼界已知所定进兵月日,岂得却退?”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〇,庆历元年正月戊辰,中华书局,2004年,第3084页。夏竦认为西夏已经得知宋朝进攻的时日,认为范仲淹的缓攻之计不可行。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辛巳,为进一步争取范仲淹协同出兵,夏竦又上奏言:
昨韩琦、尹洙赴阙,与两府大臣议用攻策,繇泾原、鄜延两路进讨。……今范仲淹却奏王师若自泾原镇戎入界,则臣令保安、金明并东路延州,环、庆等州整兵耀武,为入界之势,使绥、宥、银、夏一带贼兵不敢西去,自保鄜延一路。况已降下出师月日,而仲淹所议未同,臣寻令尹洙往延州与仲淹再议,而固执前奏,未肯出师。近投来人杜文广称贼界闻诸路入讨,只聚兵一路,以敌王师。今两路协力,分擘要害,尚虑诸将晚进,士卒骄怯,未能大挫黠虏。若只令泾原一路进兵,鄜延却以牵制为名,盘旋境上,委泾原之师以尝聚寇,正堕贼计。……乞早差近上臣僚监督鄜延一路进兵,同入贼界,免致落贼奸便。诏以竦奏示仲淹。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辛巳,中华书局,2004年,第3093—3094页。
韩琦、尹洙与两府大臣制定了主动进攻的军事决策,但是范仲淹一直坚持缓攻之计,不愿共同出兵,只愿在后方策应,所以夏竦上奏朝廷监督催促范仲淹进兵讨敌。李华瑞先生在《宋夏关系史》中认为夏竦与范仲淹皆主张采取守策,实际上此时夏竦也主张实行攻策④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8页。笔者前文已引[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乙未,中华书局,2004年,第3060页。“初,晁宗悫等至永兴议边事,夏竦等合奏:‘今兵与将尚未习练,但当持重自保,俟其侵轶,则乘便掩杀,大军盖未可轻举。’及刘承宗败,上复以手诏问师期,竦等乃画攻守二策,遣副使韩琦、判官尹洙驰驿至京师,求决于上。”后来夏竦又上奏朝廷催促范仲淹出师,都是主攻的体现,只是前后有一个从主守到主攻的变化过程。,仅范仲淹“不预此议”“固执不可”“终不从”⑤[宋]田况撰:《儒林公议》卷上,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庞籍虽不反对朝廷主动进攻的军事决策,但是其从军费开支的角度建议朝廷裁汰老弱,保留精锐,削减军费消耗。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甲申,陕西转运使庞籍言:“元昊父子,受国大恩,一朝背叛。今朝廷定议讨伐,以正逆顺,实合大义。然此时兴举,须为万全之策”;“臣窃度庙议,以大兵屯聚已久,上费国力,下困生民,欲决于攻取之计,其如将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为岁月持守之备,汰去冗兵,只留精锐在边,数少则费用日宽,兵精则足以御捍,贼地所产之物,严法以绝之,使不得与边人市易。既劫掠无所得,贷利无所通,其势必日蹙,如更益练将卒,俟其衅隙可乘,然后大举,庶几有万全之策也。惟圣心裁择。”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甲申,中华书局,2004年,第3094—3095页。田况则直接上疏反对朝廷所定进攻之策,并且尖锐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切中要害。如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丙戌,陕西签书经略安抚判官田况指出韩琦等人筹划的攻守二策,守策最为完备,但是朝廷却采取了其攻策。攻策不可用有七:一是将帅怯懦,缺乏训练,且对韩琦、尹洙的决策恐未敬服,战场进退之间必然误事,又鄜延路部署司葛怀敏等人索取甚多,不相协同;二是以往西夏常合兵而袭,边防却分兵抵御,所以致败,今西北举兵齐入必然成功的想法缺乏深思熟虑,若有不测,边防不守,后患无穷;三是今出师一旦失败,大国威严将被西夏轻视,又恐中西夏奸计;四是今兵虽多却不精,又庸将欲图赏邀奇功,无利可言;五是兴师动众,大张旗鼓,西夏得知后已经大为防备,并不能袭击措敌;六是元昊赏罚分明,无机可乘;七是鄜延路范仲淹不同意出师,泾原路孤军深入,元昊已有准备,正中其计。现在如果中途完全否决韩琦等人的进攻之策恐不妥当,如执意进攻,范仲淹又不协同,所以朝廷应召集两府大臣制定出新的折中的军事决策,令边臣严守边防,若遇西夏入侵则出兵讨伐,如果再出现作战怯懦的问题,当以军法处置。有探报说元昊已经加强了守备,所以不可轻易举兵,中西夏之计,这样可保有功无患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丙戌,中华书局,2004年,第3095—3098页;[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九二《田况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9778—9780页。。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言:“若陛下决知可攻,两府大臣主议不变,或能集事。今臣方归本司,而横议日腾,朝听已惑。攻刺之说,比已札下。朝廷举大事,主大谋,自当坚如金石,无有回易。……况鄜延路范仲淹意在招纳,更不出兵,虽具奏闻,乞依元策。假若朝廷强之使进,终是本非已谋,将佐闻之,必无锐志。……臣比来奉行成算,非是年壮气锐,虑不及远,幸而求胜,以误国家。诚以昊贼据数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万,余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陕西四路之兵,虽不为少,即缘屯列城寨,势分力弱。故贼始犯延安,生擒二将,屠掠无数者,盖刘平、石元孙聚一路之兵拒之,才及九千而已。……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闻臣僚坚执守议,以为必胜之术者,臣恐数失寨堡,边障日虚,士气日丧,贼乘此则有吞陕右之心。”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丙戌,中华书局,2004年,第3098—3099页。韩琦的奏疏首先要求朝廷坚持攻策不动摇,认为不必催促范仲淹,否则即使出兵也不是其本意,军队必无锐志;其次认为陕西屯二十万重兵,元昊才四五万,却只持守策,不敢进兵,容易导致边防日益虚弱,士气日趋低下的问题,是培养西夏吞并陕右野心的行为。仁宗曾言:“韩琦性直”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23页。,尹洙在与范仲淹商议出兵之事时,即已表现出韩琦并未有胜算的把握,只是凭一时意气采取攻策而已:
仁宗时,西戎方炽,韩魏公琦为经略招讨副使,欲五路进兵,以袭平夏,时范文正公仲淹守庆州,坚持不可。是时尹洙为秦州通判兼经略判官,一日将魏公命至庆州,约范公以进兵。范公曰:“我师新败,士卒气沮,当自谨守,以观其变,岂可轻兵深入耶?以今观之,但见败形,未见胜势也。”洙叹曰:“公于此乃不及韩公也,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败于度外’,今公乃区区过慎,此所以不及韩公也。”范公曰:“大军一动,万命所悬,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见其可。”洙议不合,遽还。魏公遂举兵入界,既而师次好水川,元昊设覆,全师陷没,大将任福死之。魏公遽还,至半涂,而亡卒之父兄妻子号于马首者几千人,皆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不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既而哀恸声震天地,魏公不胜悲愤,掩泣驻马,不能前者数刻。范公闻而叹曰:“当是时,难置胜败于度外也。”②[宋]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第82页。
尹洙所谓韩琦将胜败置之度外一事,虽是激劝范仲淹之语,但也体现出了本次军事决策有一定的冒险性质。而范仲淹在战前保持了一定的谨慎,不愿与韩琦一道出兵,不过这也正符合元昊之意:元昊一方面与范仲淹虚与委蛇以坚其不出兵之意,另一方面则迅速集中兵力进攻泾原路,韩琦则已是孤立之师③中国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92页。。
二、好水川之战的演进及其临敌决策
元昊通过延州之战试探了宋朝的军事实力,又俘虏边将刘平、石元孙,更加助长了其侵宋的野心:“贼新得志,其势必复来。”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壬子,中华书局,2004年,第3036页。如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甲子,“元昊陷塞门寨,执寨主、内殿承制高延德,监押、左侍禁王继元死之”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五月甲子,中华书局,2004年,第3011页。。五月乙亥,“延州言元昊陷安远寨”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五月乙亥,中华书局,2004年,第3013页。。九月丙寅,“西贼寇三川寨,镇戎军西路都巡检杨保吉死之”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九月丙寅,中华书局,2004年,第3042页。。可见元昊进攻塞门寨、安远寨、三川寨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宋军在后来的几次进攻战中占据了上风。康定元年(1040年)九月壬申,“环庆副都部署任福等攻西贼白豹城,克之”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九月壬申,中华书局,2004年,第3044页。。九月壬午,“鄜延部署葛怀敏出保安军北木场谷、珪年岭袭西贼,破之”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九月壬午,中华书局,2004年,第3045页。。十月乙酉,“鄜延钤辖朱观等袭西贼洪州界郭璧等十余寨,破之”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月乙酉,中华书局,2004年,第3051页。。十月辛卯,“环庆钤辖高继隆等出兵攻西贼经纳、旺穆等寨,破之”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月辛卯,中华书局,2004年,第3051页。。朝廷在与西夏的多次交战中逐渐由败转胜,与宋朝在西北边防的人事调整与军事经略分不开。宋朝为进一步遏制元昊的嚣张气势,重振西北边防军威。康定元年十二月,宋仁宗下诏问夏竦攻守之策,夏竦等筹划以后,“遣副使韩琦、判官尹洙驰驿至京师,求决于上”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乙未,中华书局,2004年,第3060页。。前文已述,经过与二府大臣共同商议,宋仁宗决定采取攻策。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乙酉,“泾原路走马承受崔宣言元昊遣人至边请和”,仁宗谓辅臣曰:“贼多诡计,欲懈我师尔,宜诏逐路部署司益严守备。”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乙酉,中华书局,2004年,第3095页。宋朝不接受元昊的求和,认为不可中其诡计,决定坚持主动进攻西夏的军事决策。而鄜延路范仲淹并不愿执行与泾原路合兵出师的军事决策,只愿作为泾原路的策应之师,实行缓攻之计,最终得到了朝廷的同意。
当宋朝中央在商讨军事决策之时,西北缘边接到元昊阅兵谋寇渭州的情报:“先是,朝廷欲发泾原、鄜延两路兵讨贼,议未决,诏环庆副部署任福乘驿诣泾原计事。会经略安抚使韩琦行边,趋泾州,而谍者言元昊阅兵折姜会,谋寇渭州。”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己丑,中华书局,2004年,第3100页。在宋朝中央制定军事决策之时,朝廷下诏令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参与经略安抚使韩琦主持的边防层面的军事决策会议。韩琦在巡边的过程中接到元昊在折楟会阅兵准备进攻渭州的情报以后,决定出兵讨敌。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己丑,“(韩)琦亟趋镇戎军,尽出其兵,又募敢勇凡万八千人,使(任)福将以击贼。泾原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泾州都监武英继之,行营都监王珪、参军事耿傅皆从。琦面授福等方略,令并兵自怀远城趋德胜寨至羊牧隆城,出贼之后;诸寨相距仅四十里,道近且易,刍粮足供,度势未可战,则据险设伏,待其归然后邀击之。福等就道,琦亦至城外重戒之”⑧[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己丑,中华书局,2004年,第3100页;[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13996—13997页;[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二五《任福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0506—10507页。。可见宋朝中央虽制定了主动进攻的军事决策,但是本次战争仍属于守御之战。韩琦在得知元昊谋寇渭州的情报以后,仓促赶往镇戎军,调遣镇戎军全部的兵力,又招募勇敢之士一万八千人,令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为统率,其余诸将皆出自泾原路,先锋为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又有钤辖朱观、泾州都监武英、行营都监王珪、参军事耿傅共同组成行军领导成员。韩琦临敌决策,制定了行军路线、军粮供给和战场计谋。当面对任福授予计策,采取合兵御敌的方略,从怀远城赶往德胜寨再到羊牧隆城,出元昊军队身后。行军途经各寨距离仅有四十里,军粮供给充足,令任福可根据战场形势,占据险要预设埋伏,等待元昊军队一出现,可出伏兵袭击,韩琦也在城外设重兵加强了戒备。任福出兵以后,具体的战场决策情况如下:
翌日,福自新壕外分轻骑数千趋怀远城、捺龙川遇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同巡检内侍刘肃,与贼兵一溜战于张家堡南,斩首数百。贼弃马羊橐驼佯北,怿引骑追之,福亦分兵自将踵其后。薄暮,福、怿合军屯好水川,朱观、武英为一军屯龙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约明日会兵,不使贼得逸去。逻者传贼兵少,故福等轻之。路益远,刍粮不继,人马已乏食三日。
福等不知贼之诱也,悉力逐之,癸巳,至龙竿城北,遇贼大军循川行,出六盘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结阵以抗官军。诸将乃知堕贼计,势不可留,因前接战。怿驰犯其锋,福阵未成列,贼纵铁骑冲突,自辰至午,阵动,众傅山,欲据胜地,贼发伏自山背下击,士卒多堕崖堑相覆压,怿、肃战死。贼分兵数千断官兵后,福力战,身被十余矢。有小校刘进者劝福自免,福曰:“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挥四刃铁简,挺身决斗,枪中左颊,绝其喉而死。福子怀亮亦死之。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己丑,中华书局,2004年,第3100—3101页。
任福率领的军队与西夏军首先交锋于张家堡南,西夏军假装败逃,宋军先锋桑怿率骑兵追击,任福也分兵紧追其后。到黄昏时分,为避免西夏军队逃跑,任福、桑怿合兵屯驻在好水川,朱观、武英的军队屯驻在龙落川,二军仅相距五里,等待第二天会兵击贼。可知任福等在张家堡南与西夏军交战以后,虽然乘胜追击西夏“诱饵”,但是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谨慎,在天色渐晚之时,并没有再继续向前追赶,而是在好水川、龙落川屯兵设伏,等待西夏军中其埋伏。但是不久任福接到了一个西夏故意制造出的虚假军事情报,情报为西夏本次兵马较少。任福等得到虚假的情报以后,急于立功,更加轻视敌人。然而任福等由于追敌过远,粮草不能供给,军队人马已经三天未曾进食。任福等人此时尚未发觉此前在张家堡之战中西夏的诱敌之计,也未能认识到本次军事情报的虚假与错误,于是放弃了其在好水川诱敌深入的计策,开始全力追击。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癸巳,任福等人率兵追赶到龙竿城北,在羊牧隆城相距五里处,与西夏大军主力相遇:“元昊自将精兵十万”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13997页。,此时宋军才知中计。宋军先锋桑怿先与夏军交战,而在任福的军队尚未来得及排兵布阵时,被西夏骑兵冲破。宋军想要占据山上高地,又被山后伏兵冲杀,桑怿和刘肃战死。任福的军队被西夏军断后,任福以及他的儿子任怀亮皆战死。韩琦派出的援兵,在任福战死以后也因寡不敌众相继战死,“唯(朱)观以余众千余人保民垣,四向纵射,会暮夜,贼引去。泾原部署王仲宝亦以兵来援,与观俱还民垣,距福败处才五里,然不相闻也”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己丑,中华书局,2004年,第3101页。。可见援军在军事情报的获取上也存在严重问题。
三、好水川之战后西北边防攻守理念的转变
宋朝在好水川之战前,本想通过主动进攻的军事决策,深入西夏兴师问罪,重立军威,不曾想西夏却先发制人,谋攻渭州。宋朝攻策未兴,守御再败,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成为宋夏战争以来“空前最大之惨败”②中国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91页。。好水川之战以后,宋朝中央与缘边制定了何种边防理念呢?笔者下文将着重探讨其攻守理念之转变。
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戊戌,好水川之战以后不久,“西贼再寇刘璠堡”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戊戌,中华书局,2004年,第3103页。。二月辛丑,“(尹)洙还至庆州”“贼侵刘璠堡未退,因遣权环庆路都监刘政将锐卒数千往援,未至,贼引去。夏竦寻劾奏洙擅发兵,降通判濠州”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辛丑,中华书局,2004年,第3104页。。受到好水川之败打击的宋廷开始变得谨慎,为避免贸然出兵引发更大的问题,尹洙因发兵救刘璠堡一事受到朝廷贬官的惩处。朝廷开始由韩琦等所主张的对西夏实行积极进攻的战略,转向范仲淹的缓攻之计:
任福等既败,朝议因欲悉罢诸路行营之号,明示招纳,使贼骄怠,仍密收兵深入讨击。诏范仲淹体量士气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驱策前去,乘机立功。仲淹言:“任福已下,勇于战斗,贼退便追,不依韩琦指踪,因致陷没。此皆边上有名之将,尚不能料贼,今之所选,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祸未可量。大凡胜则乘时鼓勇,败则望风丧气,不须体量,理之常也。”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丙辰,中华书局,2004年,第3110页。
宋廷在好水川之战失败以后,想要罢黜西北缘边诸路的行营之号,表面上对西夏实行招纳羁縻之政,使其放松对宋朝的警惕,暗自则招兵买马,令范仲淹主导西北边事,乘机立功,实际上想要实行的是范仲淹此前所主张的缓攻之策。根据当前的形势,范仲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对西北边防的经略理念开始由缓攻转变为保守。其缘由有三:一是任福等皆是边防名将,尚且不能度敌取胜,今日将官有所不及;二是如今军需粮草不济,兵少将寡,败中难以求胜;三是复仇不可仓促,更不可以怒出兵,贪图小利。范仲淹进而提出了具体的守御之策:第一,修延州南安几处废寨,安存熟户和弓箭手,俯视西夏巢穴,根据具体形势,敌大来则防守,小来则出击,有机可乘则进攻,就近扰之,出奇制胜;第二,持重练兵,在德靖寨西至庆州界和环州西至镇戎军界据险而守。朝廷采取了范仲淹的建议,在西北边防由积极进攻的理念转变为保守防御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丙辰,中华书局,2004年,第3110—3112页。。庆历元年(1041年)六月壬辰,“诏陕西诸路部署司,自今西贼犯塞,方得出兵掩击诸族,以牵其势,自余毋得擅行侵掠”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六月壬辰,中华书局,2004年,第3139页。。即朝廷下诏令约束了陕西诸路,规定仅在敌犯我时方可出兵讨击。庆历元年(1041年)六月丁酉,同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知永兴军陈执中指出:“臣昨与(夏)竦议,欲专以静胜敌,杜其蹊径,绝其资粮,益自训练军旅,浚理城池,安辑人民,减节经费,三二年间,可使穷虏自归。今复轻为举动,暴露师徒,但启戎心,实滋边患。”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六月丁酉,中华书局,2004年,第3139—3140页。可见陈执中与夏竦此时也主张静守边防,安民节费,反对轻举妄动。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也主张采取守势:“今须较四路之势,因其地形,益屯兵马,以待其来。”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六月己亥,中华书局,2004年,第3140页。亦有臣僚指出:“元昊不可击,独以兵守要害,捍侵掠,久当自服。”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八月辛卯,中华书局,2004年,第3165页。在宋朝理念转向保守之时,元昊发动了麟府丰之战。庆历元年(1041年)七月,“元昊寇麟、府州”⑥[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一《仁宗本纪三》,中华书局,1985年,第212页。,城中告急,不久丰州失陷。庆历元年(1041年)九月庚戌,朝廷任命“张亢为并代钤辖,专管勾麟府军马公事,代康德舆也”“时元昊已破丰州,引兵屯琉璃堡,纵骑钞麟、府间,二州闭壁不出。民乏水饮,黄金一两易水一杯。朝廷议弃河外,守保德军,以河为界,未果。因徙亢使经度之”;张亢乘敌军无备,“夜引兵袭击,大破之,斩首二百余级。敌弃堡遁去,乃筑宣威寨于步驼沟捍寇路”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九月庚戌,中华书局,2004年,第3172页。。钤辖张亢虽然最后击退西夏军,但是宋朝却丧失了丰州,损失惨重。此战以后,宋朝在西北继续致力于其保守的边防理念⑧刘庆、毛元佑:《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7页。“好水川之战失败后,宋朝完全丧失了进攻的勇气,改而采取守势。”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转变仍然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笔者在文中已有论述。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8页,指出:“经过康定元年,庆历元年连续两次大败,使得宋朝野上下开始比较客观地认识来自元昊的威胁和审视自己的弱点,故一度很不得势的主守反战的朝议逐渐占了上风。其后主守成为仁宗朝对夏的基本策略,这一策略的发展便为后来与西夏议和奠定了思想基础。”。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壬寅,知谏院张方平上奏道:“今边事之费,岁课千万,用兵以来,系累杀戮不啻十万人。故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戍为害,盖深念此也。愿陛下延召二府大臣,商愚计而施行之。上喜曰:‘是吾心也。’令方平以疏付中书,吕夷简读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庆历元年十月壬寅,中华书局,2004年,第3194页。宋朝为应对西夏边患,军费开支庞大,张方平上奏朝廷要求与西夏和平共处,避免征伐,减轻戍守之役,得到宋仁宗与二府大臣的一致认可②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页。“张方平的和戎之策不仅得到了宋最高统治者的认同,而且至此反战论由主守转向与西夏讲和,渐成为朝野人士较为一致的共识。”。范仲淹又上疏重申了其边防主张:“如贼不至大入,则各务静守,养勇持重,以待寇至。”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庆历元年十一月乙亥,中华书局,2004年,第3204页。
四、余论
宋朝在延州之战以后与好水川之战前,虽然在西北边防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在中央制定了主动进攻的军事决策,但是并未来得及执行。元昊一方面以求和掩人耳目;另一方面在宋朝中央攻守之议尚未结束之时,先发制人,主动进攻渭州,足以反映宋朝军事决策的效率与军事情报的保密性之低。虽然宋朝中央最终决定采取攻策,但是韩琦在缘边临敌发兵,实属仓促。一是镇戎军本身兵力有限,临时招募的勇敢士卒一万八千余人占据比率过高,缺乏训练,且“昊贼自领十余万众,我以三二万人当之,其势固难力制”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甲戌,中华书局,2004年,第3130—3131页;[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一二《任福》,中华书局,1989年,第227页。“二月,元昊寇渭州,福与诸将出兵合数万人御之。先战小利,乘胜直进,至三川口,忽遇夏兵,且二十万,官军大败。”;二是任福作为环庆路副都部署,临时被任命为统率泾原路镇戎军的兵马,并驾驭泾原路诸将,过于轻率:“方元昊倾国入寇,而福所统皆非素抚循之师,临敌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趋利,故至甚败”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己丑,中华书局,2004年,第3102页;[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二五《任福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0507页。;三是任福不能识破敌军诱敌深入之计,轻率追击,虽中途有持重之心,设伏待敌,但是又轻信虚假错误的军事情报,最终中计战死:“好水川之战,任福实为大将,而不能指麾统制以为己任,乃自率一队前当剧锋,矢尽势穷而后陷没,忠勇之节,虽可嗟闵,然论其才力,止一卒之用”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甲戌,中华书局,2004年,第3132页。;四是韩琦所派援军情报闭塞,与任福战败处相距仅五里而不知;五是在好水川之战演进的过程中,并未见到除泾原路以外的策应兵马,如鄜延路范仲淹在此前中央制定军事决策之时,虽不同意共同出兵深入讨敌,但是却愿作为泾原路的策应之师,行缓攻之计。而在本次战争中,未曾见到相关记载,可能并未接到泾原路求援的情报,如“始,朝廷既从陕西都部署司所上攻策,经略安抚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与范仲淹谋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听兵勿出。洙留延州几两旬,仲淹坚持不可。辛丑,洙还至庆州,乃知任福败绩”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戊戌,中华书局,2004年,第3104页。。尹洙与范仲淹同在延州商议攻策,当其回到庆州以后才知任福战败的消息,所以范仲淹在好水川之战期间并未得到有关求援的情报。
总之,在好水川之战中,宋朝中央制定的主动进攻的军事决策并未得到执行,好水川之战仍属于守御之战。在缘边,经略安抚使韩琦在战前的临敌决策过于仓促,“任福军败,琦即上章自劾”“会夏竦奏琦尝以檄戒福贪利轻进,于福衣带闲得其檄,上知福果违节度,取败罪不专在琦,手诏慰抚之。及是乃夺琦使权”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 庆历元年四月辛巳,中华书局,2004年,第3113页。。任福在战场上对韩琦所做军事决策的执行与持重二字相背离,“趋利以违节度”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二五《任福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0514页。,存在严重失误。在好水川之战以后,宋朝在西北边防由攻策转向保守的边防经略理念。在战争中,宋朝军事情报之所以存在严重问题,与其对间谍人员的赏赐有密切的关系:“自古用兵,未有不由间谍而能破敌者也。昊贼所用谍者,皆厚其赏赂,极其尊宠,故窥我机宜,动必得实。今边臣所遣刺事人,或临以官势,或量与茶彩,只于属户族帐内采道路之言,便为事实,贼情变诈,重成疑惑。今请有入贼界而刺得实者,以钱帛厚赏之。”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甲戌,中华书局,2004年,第3133页。军事情报是宋朝中央与缘边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与西夏相比,宋朝对间谍人员赏赐菲薄是其情报屡屡失误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为保证边防军事决策的效率与机密性,“贵不漏泄”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正月癸丑,中华书局,2004年,第3214页。。庆历二年(1042年)正月庚戌,“诏近分陕西缘边为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钤辖以上,许与都部署司同议军事,路分都监以下,并听都部署等节制,违者以军法论”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正月庚戌,中华书局,2004年,第3213页。。宋朝在该时期实行经略安抚使兼任都部署的统兵与军事决策制度,本次下诏明确了参与边防军事决策会议的人员,即路分钤辖以上可以参与边防的军事决策,路分都监及其以下听其节制,不可参与到边防层面的军事决策会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