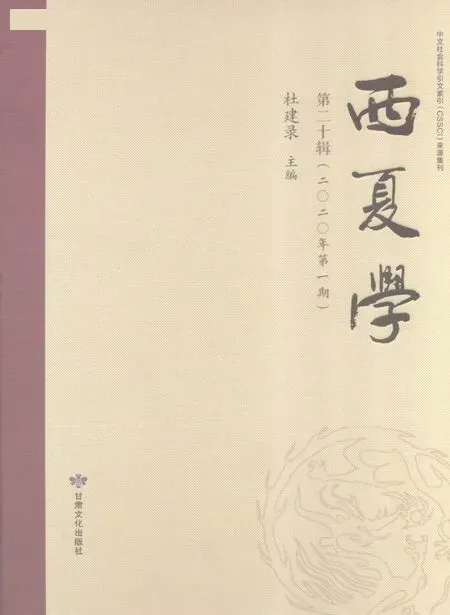喀罗川考辨
——西夏卓罗和南监军司境内地名新证
妥超群
一、引言
西夏立国初共设左右厢十二监军司,卓罗和南监军司属于其中比较大的一个监军司,位于夏、蕃、宋的交界地带。这一监军司的境域大致西起青海大通河,北达凉州沙漠,东以黄河为界,南抵兰州近北,地域十分辽阔。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先生在其《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一书中对卓罗和南监军司的地域范围、境内交通路线以及相关地名都做了详细的讨论,是这一问题研究的集大成者。然而,由于对境内喀罗川这一地名的审音有误,前田正名将喀罗川定为庄浪河的结论与兰州地区的地理实情以及史料均不符①[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532—544页。国内学者周宏伟先生也持喀罗川为庄浪河说,与此相关京玉关、巴咱尔宗、巴拶桥、通川堡、通湟砦等数个堡、砦位置的考定也出现了失误。周宏伟:《北宋河湟地区城堡寨关位置通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第173—199页。。追本溯源,喀罗川为庄浪河一说始自《光绪重修皋兰县志》,由于该志对史料中出现的“宗河”按湟水解读,将考定喀罗川的数个关键地名定在了湟水,致使喀罗川的位置考定出现了错误,境内与之相关的若干地名也出现了误考。前田正名之说现几成定论,这直接或间接地对邻近地区特别是宋代河湟地区的历史地名考定造成了混乱。笔者不揣简陋,就这一问题与学界共同商榷。
二、关于“喀罗川”的审音问题
喀罗川是西夏卓罗和南监军司境内的河谷,河谷内有喀罗城。在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宋本和旧本中,喀罗川也被记为“斫龙”“革罗”,四库全书本中,清人将其全部勘音转译为“喀罗”。中华书局校勘本又将“喀罗”改回“斫龙”“革罗”。如下:
《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四年(1081年)七月庚戌条:
苗履等言:“西蕃大首领经沁伊达木凌节赍阿理骨蕃书称,七月戊子,斫龙城(四库本:喀罗城)蕃家守把堡子南宗向下地名西啰谷,有夏国三头项人设伏,劫掠蕃兵。”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四,元丰四年九月丙午,中华书局,1990年,第7611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五年(1082年)四月丙寅条:
手诏李宪:“近闻夏人复遣间使许董毡斫龙(四库本:喀罗)以西地求平,及契丹亦继有使人到青唐,深虑为夏贼成和。”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五,元丰五年四月丙寅,中华书局,1990年,第7820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符二年(1099年)二月丙戌条转摘自《青唐录》:
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言,洮西沿边安抚司申,夏国衙头首领鄂特丹卓麻於革罗城(四库本:喀罗城)差蕃部尚锦等赍蕃字,及尚锦等分析鄂特丹卓麻元系邈川大首领温溪沁弟温阿旺格男,元名阿敏,走投夏国,有王子改名作丹卓麻,密令遣人赍送蕃字,欲归汉。诏熙河兰会路经略使孙路选兵将以讨荡招纳为名,至革罗以来,多方诱谕鄂特丹卓麻等,迎接归汉。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六,元符二年二月丙戌,中华书局,1993年,第12058页。
当前学界主要以中华书局校勘本“斫龙”为定勘。“罗”“龙”读音相近可以勘同。“喀”中古读音苦格切,陌韵溪母。“斫”中古读音之若切,乐韵昌母。溪母与昌母是不能进行对音的。这就出现了两种可能:一种是清人勘音有误,“斫龙”是正确读音;一种是宋人记音有误,“斫龙”是错误的记音,清人对此做了勘误。
《光绪重修皋兰县志》对此问题有过讨论:
案斫龙、喀罗皆音之转,续通鉴长编元丰五年夏人遣间使许董戬喀罗以西地求平,宋史吐蕃传作许割贿斫龙以西地是也,应与癿六岭相连。①[清]张国常:《光绪重修皋兰县志》,见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三),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68页。
此处提到的癿六岭,为宋夏界山,山界处有城、有川,皆名“斫龙”,清人通译为“喀罗”。“癿”具遮切,读若“伽”,与“喀”可以音转,但与“斫”不能音转。
清人撰《西夏书事》载:
重和元年(1118年)六月……乾顺见中国进筑不已,于癿六岭分界处筑割牛城,屯重兵守之,为东南捍蔽。童贯使灌由肤公城夜出兵袭据之。贯以闻,赐名“统安”。②[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78页。
由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五二〇卷后皆散佚不存于世,只记录至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查北宋成书的《东都事略》有“重和元年,贯出师收割牛城”③[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八《附录六》,见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二十五别史·东都事略》,齐鲁书社,2000年,第1109页。。宋代确有割牛城,为童贯所收。按西夏人在此屯重兵以及宋军对此城的重视,此城是宋夏交界处一重要大城。前引元丰四年(1081年)有喀罗城所管守巴堡子南宗,其实就是《宋史·地理志》记元符二年(1099年)置南宗堡。周宏伟先生考南宗堡地在永登县连城境内大通河边④周宏伟:《北宋河湟地区城堡寨关位置通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第173—199页。,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喀罗城下的属城已经至大通河沿岸,足见该城管辖面积很大是当地吐蕃部族之主城,也在癿六岭分界处。因此,喀罗城与重和元年西夏人占领的割牛城应该为一城。此城原属青唐蕃人,西夏人占据后称“割牛”。
显见,此城宋人记音中出现了两种,即“斫龙”与“革罗”,又有夏人“割牛”之转读、所在分界岭“癿六”,按各个名称之间的对音关系,此城名称的正确读法应该是“喀罗”。考虑到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宫中古籍善本丰富,边疆民族语译校便易,清人的转译应该是有一定依据的。
三、喀罗川位置之辨误
前田正名采信《光绪重修皋兰县志》的说法,认为兰州庄浪河口一带就是宋代的喀罗川,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喀罗川在宋代的错误记音“斫龙”与庄浪河产生的对音关系。《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持此结论①谭琪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中华地图出版社,1982年,秦凤路。。《续资治通鉴长编》四九一卷绍圣四年(1097年)九月壬申条中有关于喀罗川位置的关键史料,前田正名正是引用这条史料来支持其观点。
布(曾布)因极陈:“边事未可轻动……如卓罗去金城百二十里,欲溯黄河运粮至斫龙(四库本为喀罗),然后渡河讨定卓罗及该珠城一带部族,中间有黄河,两岸皆石崖,无车路处。苗履云不可开凿,而钟传遣张照踏逐,云可以簇钉椿橛牵舟,又云有车路可行……今道路险远如此,水路既不可行,陆运还有尔许车乘否?”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一,绍圣四年九月壬申,中华书局,1993年,第11659—11660页。
前田正名的引用与中华书局的校勘本一致,其引文中“喀罗”作“斫龙”,他只引用了前半段史料,对后半段史料没有提及③[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536页。。这段史料是曾布向宋哲宗建言在喀罗渡黄河进讨卓罗城与该珠城的计划,涉及了从喀罗前往卓罗城可能的路线选择。“卓罗”与“喀罗”(斫龙)出现在同一段文献中,完全是两个地名,不能等同视之;“喀罗”就在黄河岸边,“中间有黄河”显然是“喀罗”与“卓罗”的位置关系;“喀罗”至“卓罗”之间的水路是不通的,只能选择走陆路。因此两者的地理位置不可能是在一个河谷之内。细查史料,宋代兰州通往青海有水路与陆路两条道路。熙河转运使李复向宋徽宗的奏疏《乞于阿密鄂特置烽台》提供了自兰州往青海湟州的道路信息:
臣近巡历自兰州京玉关至通湟寨入湟州路经巴咱尔宗,其路极深峻窄险滑,阔不及二尺,陡临宗河。般贩斛斗客旅畏其难行,头畜脚乗尽由宗河北路过往。北路是夏国生界,三处有贼马来路,又近夏国斡珠尔城,沟谷屈曲贼马隐伏不测,出入抄掠前后被患已十余次。④[宋]李复:《潏水集》卷一《乞于阿密鄂特置烽台》,见《四库全书》第11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页。
斡珠尔城即该珠城异写。京玉关是兰州前往青海与河西的西部关口,也是重要的渡口,在宋代可与金城关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宋史·地理志》载:“京玉关,元符三年(1100年)赐名,本号把拶(读zan)桥,东至西关堡四十里。”⑤[元]脱脱:《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2166页。把拶桥、巴咱尔宗应该是京玉关一带之藏缅语地名。“宗”与藏语“rdzong”(读“宗”)可比定,意“城堡”,“巴咱尔宗”应该是吐蕃时代遗留下来的旧城堡,大概在京玉关以西不远。兰州市西关向西四十里为西固城,京玉关在此无疑。西固城以西为一险要之峡谷,黄河在此形成一个急弯,沿黄河过此峡谷后便直趋庄浪河与黄河交汇处河口镇,在河口可渡过黄河前往青海,即李复所行路线。这里出现的“宗河”不是湟水,而是宋代兰州至河口段黄河的叫法。《光绪重修皋兰县志》正是将宗河认作湟水,才将京玉关定在湟水入黄河处的小寺沟口(现名小茨沟),又按京玉关北30里又有癿六岭和癿六、喀罗的对音关系认定喀罗川就是庄浪河。其载:
案宋京玉关在县西小寺沟,自小寺渡河而北,上下数十里除八盘山其余山俱无名。而庄浪河口一带地,宋时为喀罗川,喀罗、癿六同母音近,此岭应在其处。①[清]张国常:《光绪重修皋兰县志》,见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三),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67页。
由于京玉关这一位置的西移,《兰州文史资料选辑》(兰州大事记、地名专辑)也将宋代西关堡西移了40里至西固城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兰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兰州大事记、地名专辑),1987年,第173页。。可见清代地志将京玉关的西移造成了这一带地名考定的混乱,即宋代兰州至湟水间多个城堡位置普遍西移了40里。即便如此,小茨沟距离兰州西固城大约要80里,这与京玉关与西关堡之间的40里也是严重不符。
为何此处宗河为黄河,《水经注》所记湟水之河道线路可以解答这一古代河道地理观。湟水在兰州西面入黄河前纳三水,为涧水、龙泉和逆水。这三水流经地名有令居县、永登亭、街亭、枝阳县、广武城等。三水中涧水最西,所经永登亭毫无疑问就是庄浪河谷永登附近,湟水又东流在枝阳县合逆水后汇入黄河。
逆水又东经枝阳县故城南,东南入于湟水。《地理志》曰:逆水出允吾东,至枝阳入湟。湟水又东流,注于金城河,即积石之黄河也。阚骃曰:河至金城县,谓之金城河,随地为名也。③[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9—40页。
因此,在《水经注》中庄浪河以东至兰州才被称之为黄河,而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湟水真正的入河口小茨沟以下约80里的河段在《水经注》中被称之为湟水。这一现象应该溯源至汉代旧河源说湟水为黄河正源一说,《水经注》将湟水入河位置定在了西固峡口位置而不是小茨沟,对兰州西固区以上80里黄河段名之湟水,兰州西固区以下河段“随地为名”才始名黄河、金城河。对于《水经注》在处理河湟水系中出现的这一失误,其成因比较复杂笔者将另结文详论。可以肯定的是此说影响深远,唐代中后期已经对河源有了清晰的认识,但还是在今西宁地区设置以“河源”命名的河源军。湟水藏语称之为“宗曲”,即宗河。宋朝占领兰州时间较短,加之对周围地理不清,毫无疑问因循旧说而称这一段黄河为宗河。
李复与曾布所言从兰州过京玉关、巴咱尔宗这条路线是极其难走的,贩运粮食的商贾都不愿走这条路,军队就更是困难重重,是为通青海之水路;宗河以北,即黄河以北是一条易行通畅的大道,是为通青海之陆路,地近西夏该珠城,在西夏境内。
从兰州黄河北岸通青海的陆路路线,清代学人陶保廉在光绪辛卯年(1891年)前往新疆路过兰州的记录可资援引:
金城关(过河)—十里店—石家湾(在此分路,经沙井驿、苦水西行138里至红城驿)—安宁堡北—沙沟—朱家井—白石头—俞家湾(计行71里)—小涝池—兰沟—原山庙—琵琶台—哈家寨(计行21里)—狄家铺—咸水河铺—张家庄—达家庄—观音寺—泉沟岭—徐家店—红城驿(计行52里)①[清]陶保廉撰,刘满点校:《辛卯侍行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9—250页。
陶保廉所记路线中的地名今天大部分尚存。其路线是在金城关渡河西行至安宁堡,在石家湾分路,向北经红城驿前往河西;在石家湾也可向西经沙井驿,然后翻越西固北部山脉进入庄浪河谷前往青海。宋代黄河北岸通青海陆路线路即后者,由此路可达庄浪河河口与通青海之水路线路会合,西夏该珠城就在这条道路不远处。
搞清了宋代兰州的交通路线,喀罗川口是庄浪河口之说就很难成立。宋军不可能舍近求远、择难舍易运粮前往庄浪河口去渡河。要讨伐黄河北岸地区西夏境内的卓罗城、该珠城,宋军完全在金城关或京玉关渡河即可。综合前论喀罗川一词的审音问题,《光绪重修皋兰县志》与前田正名将喀罗川定在庄浪河谷皆误。
四、喀罗川以及沿线的山、城位置
(一)喀罗川,元符二年(1099年),熙河兰会路经略使孙路向哲宗谏言,请在喀罗川口修桥建城。
熙河兰会路经略使孙路言:“兰州之西喀罗川口有古浮桥旧基,自喀罗川口北四十里至该珠城,又北至济桑约三百里间,有古城十余所,每城相去不过三四十里。自济桑以北则入甘、凉诸郡,即汉武帝断匈奴右臂之遗迹。乞於喀罗川口复修浮桥,於桥之北置七八百步一城,延袤该珠、喀罗,渐至济桑,以通甘、凉,隔绝西蕃、夏贼往来便道,乞措置施行。”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五,元符二年正月庚戌,中华书局,1993年,第12028页。
结合曾布在1097年在喀罗川口运粮渡河的谏言,宋朝迫切地要在喀罗川口建立渡口与要塞以打通兰州通往河西与青海的通道。由于喀罗川的重要性,崇宁三年(1104年),熙河兰会路经略使王厚又请求将金城关移至喀罗川口,哲宗不许。这说明宋朝对已经建立的金城关渡口不是很满意,亟需修建另一渡口即喀罗川渡口,其距兰州不会太远。对照元符三年(1100年)宋朝设置了京玉关这一事实,此处有把拶桥,喀罗川渡口应该在此处。
金城关,绍圣四年进筑,南距兰州约二里。崇宁三年,王厚乞移置斫龙谷口,不行。京玉关,元符三年赐名,本号把拶桥,东至西关堡四十里,西至通川堡四十里,南至临洮堡一百三十九里,北至癿六岭分界三十里。②[元]脱脱:《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2166页。
按京玉关、巴拶桥在兰州西固城,距离兰州西关四十里,黄河对岸应该是喀罗川口的位置。按地图索,此处为秦王川南端谷口沙井驿的位置,由此向西可达庄浪河谷,向北可趋甘凉,向东可抵金城关,向南与京玉关隔河相望。这一带也正是兰州黄河古渡之一的钟家河古渡位置所在。《光绪重修皋兰县志》所记兰州西段黄河渡口有六处,马滩渡在县西二十里,钟家河渡在县西四十里,以及新城渡、青石嘴渡、八盘渡、小寺沟渡皆为通青海之要津③[清]张国常:《光绪重修皋兰县志》,见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四),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3页。。其中青石嘴渡与八盘渡其实相距不远,分别在河口镇黄河南北两岸。宋代从京玉关、巴咱尔宗沿黄河水路正是在青石嘴渡或八盘渡渡河,然后翻越河口以西的八盘山进入湟水河谷,陆路则由钟家河渡口渡河,向西可达庄浪河河口与水路会合。
秦王川清代又谓晴望川、黑川,是兰州前往河西、宁夏的要道,为兰州北部通衢。此川道为北部毛毛山下泄洪水冲积形成的一开阔盆地,南端形成一较窄峡谷直抵黄河岸边钟家河渡口。《西夏书事》对西夏卓罗和南监军司的境域这样描述道:
右厢甘州路,以三万人备西蕃,有扑丁原庄浪族、乔家族诸路,以麻宗山、乳酪河
为界堠,内包斫龙川、採牟岭等地。①[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5页。
《宋史·地理志》有“临宗砦,崇宁三年赐名。南宗堡稍南一十五里乳骆河之西……北至界首抹牟岭七十里”②[元]脱脱:《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2168页。。“採牟岭”应该为“抹牟岭”之讹。抹牟岭即今毛毛山,与喀罗川皆在卓罗和南监军司境内,秦王川应该为西夏卓罗和南监军司的核心地带喀罗川无疑。
(二)癿六岭,秦王川与庄浪河谷之间是一条南北纵向50多公里的黄土梁峁丘陵带,为天祝县境内马牙雪山向东、向南之余脉,从北向南依次为青龙山、凤凰山、三条岭、大红山、大兰沟岭,南端为河口—西固北部黄河岸边山地③永登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永登县志》,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88页。。这一丘陵带普遍低矮,自秦王川越此丘陵带通往庄浪河谷的路线分别有上中下四条主要路线:上路为上川与庄浪河谷永登间路线;中路为中川与庄浪河谷大同镇之间路线;下路即哈家咀至庄浪河谷红城镇之间路线,清代陶保廉所行路线即此;下路最南端路线为从沙井驿至庄浪河谷河口镇,宋代兰州通青海陆路线路即此。《宋史·地理志》载:
通川堡,元符三年,自京玉关至啰矹抹通城中路镪厮狐川新筑堡,赐名,寻弃之。崇宁二年,再收复。东至京玉关四十里,西至通湟砦四十里,南至圆子堡约九里,北至癿六岭分界八十里。④[元]脱脱:《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2166页。
按前引“京玉关至癿六岭分界三十里”,此处通川堡至癿六岭分界80里,那么宋夏间北界在通川堡以北80里,南界在京玉关以北30里。通川堡在京玉关以西40里,按宋时路线向西40里只能是今河口镇位置,由此沿庄浪河往北80里是永登县大同镇,即北端癿六岭分界点;京玉关以北30里,即今西固城以北30里秦王川南端峡谷甘家滩,即南端癿六岭分界点。通川堡又谓“镪厮狐川新堡”,据此宋时庄浪河的真正名称是镪厮狐川,宋人在崇宁三年(1104年)重新收复了镪厮狐川新堡,此处至上游80里河谷为宋人地界,80里以上河谷为夏人地界。东南西北四点标定后,那么庄浪河与秦王川之间这条黄土梁峁丘陵带就是癿六岭。
(三)该珠城与卓罗城,前田正名定该珠城在庄浪河河口以北40里处,又认为卓罗城与卓罗和南监军司为一处,将其定在永登稍南,皆误。按前引“喀罗川口北四十里为该珠城”,此城位置已经十分明确,自沙井驿沿秦王川谷口上行40里至哈家咀处,陶保廉记作哈家寨,是兰州北部重要路口,即该珠城的位置。
前引卓罗城距离兰州120里。兰州至沙井驿40里,沙井驿至哈家咀40里,按陶保廉所记里程,哈家咀至红城驿稍南徐家店47里,合计127里,卓罗城位置可定为红城稍南。按前田正名所定卓罗城位置,永登稍南距离兰州超过200里,“卓罗”与“卓罗和南”一为地名一为军事机构名称,名称也不尽一致,前田正名将二名定为一处与地理实情不符,也失之草率。又按青藏高原立名规律,重要路口和河流交汇处皆以相关地名或河流之首字合读成一新地名。例如四川甘孜州康定城的藏语地名“打折多”若此,由打坡河与折多河之首字合读。“安多”即由阿庆冈山与多拉仁茂山(祁连山)合读。哈家咀是自秦王川至红城驿的重要路口,即宋代喀罗川与卓罗城之间的关口,“该珠”一名即由两地名之首字合念而成。
该珠城又“北至济桑约三百里间”有古城十余所。前田正名定济桑为汉代苍松县、唐代昌松县,西夏人转读作济桑,即今古浪县位置①[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538页。。从对音这一观点是可取的。按陶保廉所记里距,哈家咀至红城驿52里,再至平番县71里,再至岔口驿80里,再至乌鞘岭龙沟95里,再至古浪县45里,合计343里②[清]陶保廉撰,刘满点校:《辛卯侍行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0—251页。。沿庄浪河至济桑路线与“三百里”还是有一定差距。细读史料,济桑为西夏人占领,宋人修城不可能修至乌鞘岭以北的济桑城,“三百里”应该是指与济桑交界处。哈家咀至古浪还可向北穿越秦王川至上川镇,再向西北经天祝县松山镇至天祝县华藏寺与庄浪河路线汇合,由此向前至乌鞘岭山脚下为300里,此处为凉州与兰州之界山。按孙路向哲宗建议,自喀罗川口建城经该珠、喀罗延伸至济桑以通甘凉隔绝西蕃西夏之往来,是自哈家咀向北、纵贯秦王川至乌鞘岭修建一系列城堡,此举既可打通兰州至河西的通道,又可切断吐蕃与西夏之间的联系。秦王川是兰州前往河西、青海与宁夏的北部主要通道,如按前田正名先生的考定该珠、喀罗都在庄浪河谷,西夏人的卓罗和南监军司的背部就直接暴露在宋人的面前,宋人可从哈家咀长驱直入。依此可以看出西夏人的防线正是自南向北纵贯秦王川,而非庄浪河谷。
(四)喀罗城,西夏人占领此城后称割牛城,重和元年(1118年)童贯攻取此城后改名统安城。宣和元年(1119年)熙河经略使刘法统兵两万前往朔方,至统安城兵败,史料中有关于这座城的关键地理信息。
宣和元年,童贯复逼刘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万出,至统安城。遇夏国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骑为三阵,以当法前军,而别遣精骑登山出其后,大战移七时……自朝及暮,兵不食而马亦渴死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朱峗,守兵见,追之,坠崖折足,为一别瞻军斩首而去。①[元]脱脱:《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0—14021页。
刘法是从青海湟州出兵前往宁夏地区,青海与宁夏之间最近的道路就是经兰州以北、西夏卓罗和南监军司的地界。有研究认为统安城在青海海北州境内,前引统安城就在癿六岭宋夏分界处可证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盖朱峗即该珠城附近一山岬,刘法自统安城附近战场连夜逃向该珠城意图非常明确,即向南至兰州宋军营地,因此统安城在该珠城北70里之处。对照地图,今哈家咀以北70里处为秦王川秦川镇所在。秦川镇为自庄浪河中段前往宁夏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正处路口,其路线为从庄浪河大同镇向东穿越黄土丘陵带,即宋代癿六岭,向东行约20里便是秦川镇。此地是当地传统的中心城镇,喀罗城位置可定在此处。
(五)阿密鄂特城,《宋会要辑稿》中也记为鹅毛瓦都城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八之四五,中华书局,1957年,第7292页。。熙河转运使李复在《乞于阿密鄂特城置烽台》奏疏中,明确提到此城位置:
今京玉关东北约二十里有旧阿密鄂特城,地基正在两城中路,地势甚高,接连生界。③[宋]李复:《潏水集》卷一《乞于阿密鄂特置烽台》,见《四库全书》第11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页。
元符二年(1099年)九月,熙河兰会路经略使胡宗回奏:
臣近体问得兰州西关堡近西,地名把京玉相近,可以系桥通路,直入邈川,不惟路径平坦,兼道里甚近,可以互相照应,兼可以於宗河行船,漕运直入邈川。其宗河口东岸近北,旧有邈川管下鹅毛瓦都城,迺西蕃旧防守夏国该珠卓啰等城去处……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六,元符二年闰九月丙子,中华书局,1993年,第12272页。
此处把京玉应该为把珍旺之误,京玉关处有把拶桥,其西有把咱尔宗,把珍旺即京玉关藏缅语地名。京玉关在兰州西固城,东北方向即秦王川南端谷口。宗河口在黄河西固峡口,宋代从此处可行船至上游渡口。又查秦王川南端谷口明清时期又称李麻峪。《乾隆甘肃通志》:“李麻峪,在县西四十里,路通甘州。”⑤[清]许容:《乾隆甘肃通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510页。《永登县志》载:李麻沙沟,又名咸水河。始于天祝藏族自治县毛毛山南麓,经四泉、正路沙沟、秦王川,至安宁区于沙井驿西注入黄河,全长103.9公里⑥永登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永登县志》,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00页。。秦王川南端山谷也谓李麻沙沟,由沙井驿沿此沟北行10里便是今兰州高速西收费站,是前往庄浪河谷之传统路口,距离西固城约20里。这一位置再向北30里可达哈家咀即宋时该珠城。阿密鄂特城可定在今兰州高速西收费站附近。又按李麻河谷西20里有瓦砟沟,阿密鄂特又谓鹅毛瓦都,此城名称应该是两河谷地名之合念,“都”可与藏语“mdo”比定,为藏语路口、河口交汇处之常用地名。据此,宋时秦王川南端河谷应谓阿密河或鹅毛河,为南北纵贯喀罗川的河流,至明代讹为李麻河。
五、余论
相较唐代,宋代汉文地志对河湟地区的地名记音比较混乱,无论从音韵的准确性还是规范性都不如唐代,此为这一地区地名考证的难点。究其原因,宋朝实施“熙河开边”的政策后,于元丰四年(1081年)占领兰州,迟至绍圣四年(1097年)才设置金城关,元符三年(1100年)设置京玉关,对这一地区的真正控制还是比较晚的;加之同一地名既有吐蕃人的叫法,也有西夏人的转读,经略河湟的宋朝官吏中有相当数量的内地人和南方人,其对周边民族语言、地理不熟,这就更加造成地名记音的前后不一、一地异名的现象。就本文涉及地名来讲,这一特点是比较突出的。
补记:本文在前期调研中得到了永登学人西铁中学杨善德老师的大力协助,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