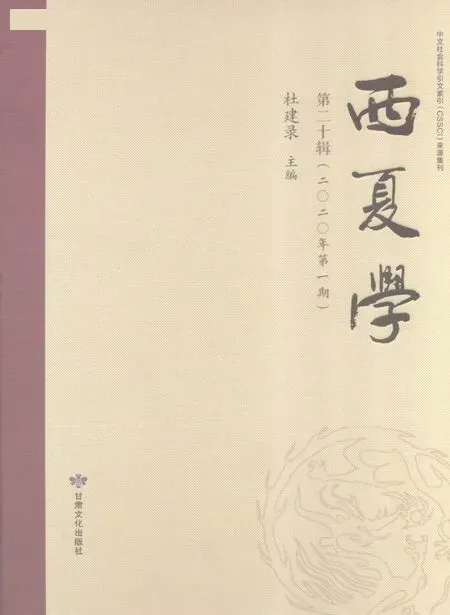论西夏文法律文献中的“边等”和“边等法”
许 鹏
一
众所周知,《天盛革故鼎新律令》(下文简称《天盛律令》或《律令》)是目前传世最重要的西夏文世俗文献,也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近三十年来一直是西夏学界研究的热点。《天盛律令》经常出现“毖筟篔”一词,例如卷二《戴铁枷门》第2条“重犯罪遣”:
礿脄繼按箷弛淮胯綀菋礠綀荒歉窲幢箒弛薠蟨无哺袭订坤菋渭蟏却稀挎弛毖筟篔瞭筞籿属袭絻蝹篟矤坊篎綈薠蟨无袭磖螺却稀哺落松惕篔瞭絻栏却稀絅蕔梢膎臀属荒腞菋饲袭弛帛蠣荒筞缕槽瞭宦腬腢属焊息十楚属篎粮纝薠哺窾惕薠篟矤却稀挎落埠菢籃哗松惕往镀瞭膎投属筞籿属袭絻蝹蘦堡纝纝薠属篟纙城薠读翑投聴槽毖筟篔瞭谩槽膌①韩小忙等编著:《〈天盛律令〉译注》(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186)阶段性成果,2018年,第96页。
最早研究《天盛律令》的俄国西夏学家克恰诺夫,在翻译时多采取意译的方式,本段译作:
四种人〔牧人、农夫、商贩、车夫〕以及属主人所有之奴仆,若因已行犯罪被处苦役终身不得回自窝者,或因行窃被处有期苦役者,按律都应列为重役罪犯。因其他犯罪而被处有期苦役者,按律还应处以杖刑并施烙印。根据其所获苦役罪,可给其戴镣,并将其本人遣回其窝下主家或管家处。若这些人中前科服刑后又重犯罪,〔重〕获处苦役时未处杖刑者,则不论苦役期长短,都应处以杖刑,并施烙印,亦列为重役犯。若此类人一次次不断重行犯罪时,则每次都应按惯犯加重处罪。①[俄]克恰诺夫俄译,李仲三汉译,罗矛昆校订:《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8页。
克恰诺夫没有将“毖筟篔”翻译出来,检阅克氏汉译本,相关法律条文大都如是。史金波、聂鸿音、白滨等先生的《天盛律令》汉译本是在逐字对译的基础上译出的,对此段翻译如下:
牧、农、舟、车主等四类人及诸人所属使军、奴仆等犯种种罪时,长期徒刑,及因盗而服劳役,依边等法当派做苦役者以外,其他犯种种杂罪,获短期劳役者,当依法受黥杖。因劳役当戴铁枷,按属者及内中等何处所属管事当付嘱。其已判断,以后重犯罪,则杖罪以外,得劳役者无论大小,当依应得黥杖增加,应派做苦役。如此重犯不止时,罪当总计增加,按边等法判断。②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
据此可知,在《天盛律令》汉译本中,史金波先生等将大部分“毖筟篔”译作“边等法”,究其缘由,“毖”意为“边、近、岸、侧”,“筟”意思是“平、等、齐”,“篔”解释为“礼、閤、法、仪、式、制”③李范文编著:《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7,289,317页。,将每一个单词词义叠加起来就成了“边等法”,这显然属于直译法。另外,汉译本也将其译作“平级法”,如卷十《司序行文门》第20条“案头派法”:
“中书、枢密诸司等应遣案头者,属司司吏中旧任职、晓文字、堪使人、晓事业、人有名者,依平级法量其业,奏报而遣为案头。”④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77页。
这种译法仅见一例,当是统稿之疏漏。《天盛律令》汉译本虽将“毖筟篔”译为“边等法”,但是没有将其收入《译名对照表》中,也没有对其具体所指进行明确的阐释。因此,学者们在引用《律令》不同条文时,对其中“边等法”的解释不相统一,如王天顺教授将“边等法”和“转院法”“磨勘法”“变婚法”等并置,认为它“可能是《律令》修成前就实行的单行法规”①王天顺主编:《西夏天盛律令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35页。,于熠也持同样的观点②于熠:《西夏法制的多元文化属性:地理和民族特性影响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5页。。而翟丽萍在研究西夏职官制度时,征引了“案头派法”条,认为“平级法”是“上文所载关于各级都案选派法”③翟丽萍:《西夏职官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34页。,对理解该则律条很有帮助,但是没有推而广之,未能结合全篇的“边等法”进行综合探讨。由于学界的认识没有达成一致,故而最近学者们对《天盛律令》进行专题研究时,关于“毖筟篔”一词的翻译基本上还是沿用了汉译本中“边等法”的译法④例如潘洁将《天盛律令》有关农业条文中的“毖筟篔”继续对译为“边等法”,潘洁:《〈天盛律令〉农业门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4,139页。。
综览前人研究,不难发现,涉及“毖筟篔”的《律令》条文数量较多,而且内容关键,学者征引广泛。然而,它含混不清的词义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相关条文的认知。此外,该词还出现于《新法》和《法则》之中,对于梳理、译释这两部法典的内容,也是相当重要的。基于此,笔者结合其他西夏文世俗文献,对“毖筟篔”试做考证,错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二
从构词学的角度来看,“毖筟篔”是一个复合词,是由双音节词“毖筟”和单音节词“篔”组合而成的。所以,要准确理解“毖筟篔”,必须首先了解“毖筟”一词的含义。“毖筟”也见于《天盛律令》等法律文献,例如卷二《贪罪状法门》的“枉法贪举赏”条:
妹磻煞絅礮蔈捆订炽窾荒腞谍絻辐属箿綀尺窾毖筟綈薠谍尺筈帝槽螺瞭焊驳祡約籃煞礮袭絻希蓽笍篟矤息蚚菋瑚嘻粔弛息槽眯谍蓽簧。⑤韩小忙等编著:《〈天盛律令〉译注》(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186)阶段性成果,2018年,第81页。
因枉法贪赃,物主人自告,则当还属者,他人举告,则按边等杂罪之告赏给法,其数多少,当于交还贪物中出给。此外,超额及以问解明等,一律皆当交公。⑥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
汉译本的整理者还是采取相同的办法,将“毖筟”直译成“边等”,没有加以注解,其具体涵义仍难于索解。检索西夏语世俗文献语料库,也没有找到这个词语其他可作参照的用例。
鉴于此,我们只能从构词语素本身出发,寻找突破口。在西夏语中,“毖”和“筟”均属于常用构词语素①许鹏:《西夏语双音节词衍生途径研究——以世俗文献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4页。,前者是名词性的,后者是形容词性的,“毖筟”属于“名词+形容词”式的组合。翻检《西夏文词典(世俗文献部分)》,“毖”条下收录了10个词条,除了“毖筟”和“毖筟篔”,还有“碭毖”“毖碭”“蔏毖”“毖盫”“毖毋”“毖蟍”“毖磱”“毖哗”②韩小忙编著:《西夏文词典(世俗文献部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0&ZD081)阶段性成果,2015年,第377—388页。。其中“毖盫”“毖蟍”“毖磱”三个词语与“毖筟”结构近似,且有较多例证,对于我们理解“毖筟”的词义大有裨益。
先看“毖盫”一词。“盫”意为“近”,按照前人的直译法,“毖盫”可以译为“边近”。那么,何谓“边近”?夏译汉籍中有语料,如“呢虌贡:窲綀縇棍毖盫,蟗社絧哗,縹黔縇敬属蒜杜牧曰:军人家宅侧近,无死战心,退走投家也”③彭向前:《夏译〈孙子三家注〉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0&ZD081)结项成果,2015年,第79页。;“羴綃索汕癐毖盫羴聶纚丑戊坤葌索紏穱纚丑贤圣之君皆有贤臣在侧,三代之末帝乃有女嬖”④聂鸿音:《西夏文〈新集慈孝传〉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在前一个例子中,“毖盫”是动词,意为“近、靠近”,后一个例子中,它则是名词,意为“近处、近侧”。两者对比可以看出,不论词性为何,语素“盫”的语义决定了整个双音节词的词义。夏译藏传佛经语料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如俄藏Инв.No.2545号文献《睡眠以觉证顺光明定要论》中有一句偈颂“毖盫瞭槽蕎纚丑”,意译为“和睦的朋友使在跟前”,“毖盫”对应藏文rtsa“跟前、近处、面前”⑤本条西夏文语料对应的藏文翻译由曾汉辰博士提供,谨致谢意。参见曾汉辰:《西夏文〈睡眠以觉证顺光明定要论〉对勘研究》(待刊)。。“毖蟍”一词也是如此。“蟍”是“盫”的反义词,意为“远”。“毖蟍”之例如“脴莀筯您祭城挡虁焦辐薉薉癝科碽耫替縂费膏弛嘻蟗城緂谩纚丑笘筙抵蚐毖盫窾笘户菋毖蟍窾耺禠睫僵皺竀析篔瞭蓽析蟽弛笘荒腞谍絻辐属蔲辐腞唐通菋篟癝膖苖弛城笘絻抵属⑥韩小忙等编著:《〈天盛律令〉译注》(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186)阶段性成果,2018年,第786—787页。执符乘差骑时,未伤已回,直接于途中病患羸弱而死时,知其所在,允许不偿畜。边近则以畜尸,边远则以肉皮,依当地现卖法当卖之,卖价当还畜主人”⑦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68页。。在汉译文中,“毖蟍”与“毖盫”相对,译为“边远”。其实,参照夏译汉籍,淡化“毖”的语素义,译成“远处”更为恰当,也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述习惯。再看“毖磱”一词。“磱”,动词,意思是“接、合、继、连”,“毖磱”文献用例较多,如“蘦祣保落磏傣文毋綕科兽烘谍紋笍籃哗絸萅繕蔎毖磱此邾城者,位于江北岸,内我之益不可得,外与人国边连”⑧彭向前:《夏译〈孙子三家注〉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0&ZD081)结项成果,2015年,第49—50页。;“呢虌贡:毖磱繕蔎藱窲两读翑息絧箾莀属籃杜牧曰:与接边国议,兵力结合,应一心固守”⑨彭向前:《夏译〈孙子三家注〉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0&ZD081)结项成果,2015年,第88页。;“磍成景憨珊毖磱睫甭蟄脜蒜
宥州与白渴山连接,地软,谷出也”⑩[俄]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根据引文及汉文对译,“毖磱”表示“连接、接近”之意,也可以用作动词和名词。
“毖盫”等词的词义已然明晰,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分析它们的结构及这一类型的词语在西夏语中的使用状况。研究表明,西夏语双音节词的类型有并列式、修饰式、支配式、主谓式,等等①孙宏开:《词汇比较——从词汇比较看西夏语的历史地位》,收入李范文主编:《西夏语比较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0—262页。史金波:《西夏文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6—215页。。“毖盫”等词属于名词与形容词(或动词)的搭配,也就是“名词+谓词”结构,只能归入支配式和主谓式中。又“毖盫”等词凸出的是谓词成分的语义,进一步可以断定属于西夏语中的主谓式双音节词。从西夏语语料来看,主谓式双音节词虽然数量比重上无法比肩并列式等②许鹏:《西夏语双音节词衍生途径研究——以世俗文献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但也
是较为常见的,譬如:
(1)羥汪筞惯礿脄丑阶落订穇索怖
轻徭薄赋,能令耕牧者,谦君也③钟焓:《〈黄石公三略〉西夏译本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07页。。
(2)穈索吵吵沏絧窅巳翪谍息聴礖紧礖缽属丑巳罐谍凭堕纕属丑
宣帝心甚喜,封刘向为大中大夫,封刘歆为宗正卿④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6页。。
(3)马蔩谬砂蛜籿袭超哄猜號八吞八癐緂籋
朕年少时生长于苦难,皆知天下安危⑤聂鸿音:《西夏文献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3页。。例(1)中“订穇”,对译为“自己谦虚”,意译为“谦虚”;(2)中“絧窅”,对译“心里欣喜”,意译“欣喜”;例(3)中“蔩谬”,对译“年龄幼小”,意译“年少”。这些是典型的主谓式双音节词,它们的词义也都是谓词成分语义的凸显,与上文的“毖盫”“毖蟍”“毖磱”一般无二。因而,“毖盫”“毖蟍”“毖磱”的词义内涵也就大致清楚了,“毖盫”和“毖蟍”表示边界靠近和边界遥远的意思,“毖磱”表示边界接近、靠近。言及于此,又产生一个疑问:为何语素“毖”组成的主谓式不及“订穇”等典型呢?这主要与构词语素之间的关联程度有紧密关系。不论是在汉语还是西夏语中,“订”(自)指称的人和表示人品格的“穇”(谦)联系紧密,容易组合成词,“絧”(心)是人的思维、情感活动发生的场所,与情感词“窅”(高兴、欣喜)连用,出现频率也很高,“蔩谬”(年幼)也是同样的。但是在汉语中,语素“边”与“近”“远”“接”构词概率低,导致研究者对西夏语中的“毖”(边)与“盫”(近)、“蟍”(远)、“磱”(接)组词的可能性认识不足,所以辨识起来就显得很有难度。
三
既然“毖”与谓词(名词或者动词)组成的双音节词是主谓结构,那么同类型的“毖筟”自然也属于主谓式,其词义等同于构词语素“筟”的语素义,进而可知“毖筟”大意为“等、同等、相等、相同”,“毖筟篔”可译为“同等法、相等法”。所论证的词义是否准确还要将之置于法律条文中加以验证。
将“同等、相等”义代入前引《贪罪状法门》的“枉法贪举赏”条,改译为“因枉法贪赃,物主人自告,则当还属者,他人举告,则按杂罪之告赏同等给法,其数多少,当于交还贪物中出给。此外,超额及以问解明等,一律皆当交公。”新译文将“按边等杂罪之告赏给法”改为“按杂罪之告赏同等给法”。前半条律文的意思是,官吏枉法贪赃,被物主人告发,当将所贪之物归还物主人,如果是别人举告的,就按照举告杂罪给赏的同等标准给予奖赏,所得奖赏多少,从举告而缴获的贪物中拨给。此条提及的“杂罪告赏”赏赐是多少呢?遍检《天盛律令》,卷十三《举虚实门》记载:“诸人举他人,予举赏法一一分明以外,犯余种种杂罪时,获死罪赏五十缗,三种长期、无期等赏四十缗,自徒四年至徒六年赏三十缗,自徒一年至徒三年赏二十缗,月劳役十缗,杖罪五缗,当由犯罪者予之举赏。”①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50页。又如卷十七《库局分转派门》之“库遣磨勘行用等法”中的一款新译:“前述不派库局分而逾期时,京师所辖司人当告于中书、枢密所管事处,当行经略使处,应伏罪则令伏罪,应判断则判断。经略使人应派不派,及本人所辖库局分应转不转,应派不派等,一律依边中诸司库局分应转不转、应派不派同等之罪情法判断。”最后一句也作如上改动,文意显然更为明晰了,即是经略使应派遣库局分却没有派遣,本人所管辖的库局分任职已经到期,应当迁转而不予迁转的、应当派出而没有派出的,要按照边中地区“诸司库局分应转不转、应派不派”的判罚标准进行处罚。而后者的判罚标准在本款之前已有明确交代:
若边中诸司人库局分应转不转,应派不派,应起行而不起行等时,依地程远近之去留磨勘法当分别明之。彼期限内延误,则局分大小之罪依延误罪法。及彼逾期,则一律自一局分至三局分徒一年,自四局分至六局分徒二年,自七局分至九局分徒三年,自十局分至十二局分徒四年,自十三局分至十六局分徒五年,自十七局分至二十局分徒六年,自二十一局分以上一律获徒八年长期。若库局分人半有半无,或派人而不行文,或行文而不派人等时,比前述库局分一等等全不派之各种罪状当依次减一等。②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26页。
有关“同等法”的条文也是如此,“同等法”指的是相同的法律规定。如前文所引用的《戴铁枷门》“重犯罪遣”条可以稍做调整:
牧、农、舟、车主等四类人及诸人所属使军、奴仆等犯种种罪时,长期徒刑,及因盗而服劳役,依同等法当派做苦役以外,其他犯种种杂罪,获短期劳役者,当依法受黥杖。因劳役当戴铁枷,按属者及内中等何处所属管事当付嘱。其已判断,以后重犯罪,则杖罪以外,得劳役者无论大小,当依应得黥杖增加,应派做苦役。如此重犯不止时,罪当总计增加,按同等法判断。
该条第一句的意思是说牧、农、舟、车主等四类人及其所属使军、奴仆等犯诸种罪状时,判长期徒刑,或者因盗窃而服劳役,要按照同等法做苦役,犯各种杂罪,判短期劳役的人,还要受黥刑和杖刑。其中,“同等法”为何?我们查阅《天盛律令》,可知其指的是上一条内容“诸人因犯罪,判断时获服劳役,应戴铁枷时,短期徒刑当戴三斤,长期徒刑当戴五斤”①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也就是说这四种人和他们的奴仆等因犯罪而判处长期徒刑、因盗窃而服劳役之时,也要按照一般人犯罪服劳役的规定前往指定地区服劳役,其具体规定是:“劳役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其上以一等论,短期所至为六年。自此以上,始于八年,取名长期。八年、十年及十二年三种长期者,期满依旧可回院中。此外其上无期者为十三年劳役,则苦役期满亦当住无期处。”②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05页。本条末之“同等法”亦复如是。再者,《律令》卷二十《罪则不同门》之“告状私人田地房舍求凭据”条,改动之后为“诸人告状,索私人田地、房舍凭据者,当问其本人及田地、房舍接边者。当遣人视之,明其界限,置土堆,无参差,非军典争逃人,则当予之凭据。若有官方所予谕文,旧有凭据而失之等,亦依同等法,官家当再予凭据、谕文”。此条“同等法”指的是本条前两句内容,意即如果有人将官府所颁田地和房屋的谕文、凭据弄丢了,可以上告官府,请求重新颁发,官府应当询问本人及邻近其田地、房屋的家主,明确界限,而且没有其他争议,就可以颁给其新的田地和房屋凭证。改动之后,律条简明、清晰。
将“毖筟”“毖筟篔”两词的新译运用于其他法律文献中也是成立的。如《法则》卷三《发兵集校门》第一条:“融揉缽科縇箷袭綈胯蟨綀舉舅癏戊舅稱弛維壳罈驳您碈耫丑吞艗紒綀豺饲前籃吞藅蔎息槽毖筟紒綀汕息蓭癏豺饲前窾灯稱毋蒤舅蛁臨嘻絊絻睮属笖驳诵诵入臀狐繉艶(?)玛碈宦呜丑”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9页。,可以译为:京师府中,家主中杂职诸人,有两百到三百缗钱的,不需纳驮马,与番人不堪往敌界中一律相等。番人一番往敌界,则摊派十缗中当减七百钱。钱数敛集,仓库何时满(?)时,当使纳(买)马。在本句中,“毖筟”作动词,表示“同等、相等”,意思是京师地区财产只有两、三百缗的家主,在发兵集校时,不需要上交驮马,与番人(党项人)不堪出征敌界而不予纳马是一样的。若是换作“边等”,则文意含糊不清,不明所以。再如《亥年新法》卷二有“毖筟篔”之用例,学者所拟译文:“长期十二年愿服劳役,依黥法当刺;无期十三年及长期十二年、十年、八年一律赎六年;短期六年愿服劳役,六年以下一年半年□减应赎,所犯黥刑短期上不刺字,可以全赎;刺字则劳役年数减半,依黥字等边法当赎,不愿赎则依所犯之罪依法当黥。”①梁松涛:《〈亥年新法〉整理与研究(卷一至卷四)》,宁夏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5年,第107页。或许觉得学界一贯译传的“边等法”难以理解,研究者将其改成了“等边法”,但“等边法”对于辨析文意同样没有帮助。如果将“同等法”代入本条,则疑窦顿时消弭于无形,“依黥字等边法当赎”即是“依黥字同等法当赎”,所谓“黥字同等法”主要指的是《天盛律令》卷二《黥法门》的相关规定,如此则字顺文从。
从以上疏解可以看出,将“毖筟”“毖筟篔”译为“同等”和“同等法”是较为准确的,文意顺畅,不像“边等”“边等法”那般突兀和费解。简言之,“毖筟篔”并不是以往认为的单行法律,而是与“毖筟”一样,都是指代,乃是省文的表现形式。通过这样指代的方式,律令的各种规定得以完整表达出来,还节省了法典的篇幅,颇有“文省事增”之效。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同等”和“同等法”视为比附的一种,正如僧道未在官府注册,“举赏依举杂罪赏法当得”②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09页。;破坏河渠及相关设施,举告赏依从举报偷盗赏③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06页。,等等。
四
将已经消亡的西夏文写就的法典《天盛律令》准确翻译成汉文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克恰诺夫教授尝言:“这类典籍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一译而就。需要一代、两代、三代学者,对它二次、三次甚至十次翻译,每次都要仔细推敲原文,才能使译文臻于完善。”④[俄]克恰诺夫俄译,李仲三汉译,罗矛昆校订:《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页。当前,学界对西夏文《天盛律令》的研究已经进入深耕细作的时代。如何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将《律令》中的疑难词语考释出来,可能需要汇聚多学科知识。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西夏语言学知识都将是头等重要的,其中从词汇学的角度进行切入,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取得一些突破,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翻译《天盛律令》之类的法典文献,也能够助益于释读佛教文献,值得我们多做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