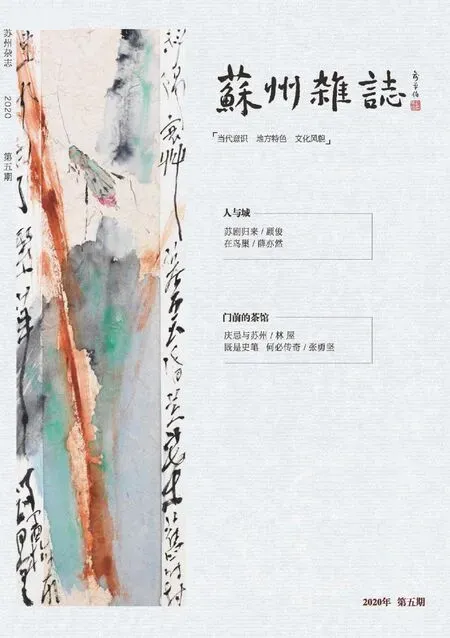追踪苏式汤面
蒋洪
坦白地讲,独立生活之前我早餐吃的基本都是自制腌菜和白米粥,没有馒头、面条或鸡蛋面饼。母亲是信用社的会计,父亲是乡里时常下乡蹲点的干部,记忆中最好吃的面是母亲在年度结算后带回的夜宵。印象深处有两三次是被母亲半夜喊起来喂我的,搪瓷杯里盖着厚厚一层勾了芡的清炒肉丝,肉丝下则是吸足了汤的面。背书包的岁月,午餐或晚餐大概率会吃到母亲煮的糊涂面。虽说是糊涂面,但未到筷子挑不起来的烂糊状。切面店买生湿面,用剩的生湿面在没有冰箱的年代只能盘卷在竹筛里晒干收贮,以备不时之需。锅里水沸后下面条,再沸下青菜,面汤煮得略有糊芡时,下一勺猪油,撒些胡椒粉,就是菜点合一的美味了。
可能是双职工带孩子无暇煮饭或是省得开油锅的缘故吧,糊涂面省菜省时,归根结底省钱。工作后实现了早餐的面条自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八都小镇并无面馆,早上自带搪瓷餐盆和筷子,去饮食店排队买阳春面吃。面汤其实就是酱油、猪油、盐、味精、葱花和开水,为何不吃浇头?财务不自由。等自己成了家,为省时妻子也煮震泽人称青菜一落面的糊涂面。至于吃糊涂面的好处,东坡先生的《养老篇》说得很明白:“烂煮面,软煮肉,少饮酒,独自宿。古人平日起居而摄养,今人待老而保生,盖无益。”养生非养老,好事要赶早。
南稻北麦的格局,大概在神农时代已经形成。“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白虎通·号》)良渚古城遗址20万斤水稻的仓储,实证了五千年前的史前社会稻作农业的发展成就,江南人稻饭鱼羹由来久矣。面食在江南登堂入室,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引发的三次北方人口向南大迁徙密切相关。特别在南宋高宗初年,江、浙、湖、湘、闽、广等地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南方“麦一斛至一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于是朝廷为解决口粮和照顾移民的饮食习惯,规定“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课麦之利,独归客户”。孝宗淳熙七年(1180):“复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劝民种麦,务要增广,自是每岁如之。”面食不但能疗饥,还丰富了吃食品种,有啥吃啥才会增加生存的概率,这是民以食为天境界的随遇而安。当下大苏州人口超千万,土著血脉日渐稀少,不断输入的中原及北方的饮食习俗被吴文化一方水土所包容、所融合,演化在姑苏的日常生活之中。
麦子磨成的粉称面粉,用面粉制成的食品为面食,早期面食统称为饼,先秦典籍《墨子·耕柱》的“见人之作饼”句,佐证当时北方饮食皆为面食。饼有多种,东汉刘熙《释名·释饮食》:“蒸饼、汤饼、蝎饼、髓饼、金饼、索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汤饼为汤煮且连汤一起吃的面食。西晋束晳《饼赋》:“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成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热汤最能御寒、发汗、运化精谷,此饼赋为苏式汤面之面汤须烫打下注脚。
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饼》则以成熟方式释名:“水瀹而食者皆为汤饼。今蝴蝶面、水滑面、托掌面、切面、挂面、馎饦、馄饨、合络、拨鱼、冷淘、温淘、秃秃麻失之类是也。水滑面、切面、挂面亦名索饼。笼蒸而食者为笼饼,亦曰炊饼。今毕罗、蒸饼、蒸卷、馒头、包子、兜子之类是也。炉熟而食者皆为胡饼。今烧饼、麻饼、薄脆、酥饼、髓饼、火烧之类是也。”瀹,煮也。索有搓、绞之意,如绳索。可以称作汤饼的东西较多,然汤饼中的索饼与当今的面条相差无几。清代成蓉镜在《释名疏证补》中论及:“索饼疑即水引饼。今江淮间谓之切面。”再看后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饼法第八十二有“水引、馎饦法”,所用面粉水要过细绢筛。吃之前需“以成调肉臛汁,待冷溲之”。想必是夏日妙品。
《齐民要术》记水引法:“挼如箸大,一尺一断,盘中盛水浸,宜以手临铛上,挼令薄如韭叶,逐沸煮。”挼为双手揉搓,逐沸煮为趁着水沸下锅煮。此水引法未记载煮至什么状态,会不会也像糊涂面一般?而馎饦之法为:“挼如大指许,二寸一断,着水盆中浸,宜以手向盆旁挼使极薄,皆急火逐沸熟煮。”从字句描述看,水引比馎饦长,馎饦比水引更薄而宽。汉以后“索饼”作为面食的记载已不多,南宋林洪《山家清供》记载的玉延索饼是用山药磨粉做的粉条。“水引”之名也没走进隋唐。“馎饦”之名自北魏始至元代,用料广泛,小麦粉、青稞麦粉、大麦粉、山芋等,亦有将羊肾生脂、鲜虾肉泥等与小麦粉拌和,形状也由最初的宽长片演变为宽而长、细而长、方叶形、厚片,“阔细任意”或“擀切成阔面”等。陕西十八怪之“面条像裤带”恐怕也是馎饦之隋唐遗风。
转眼到了南宋,江南浦江出现了“水滑面方”:“用十分白面,揉、搜成剂。一斤作十数块,放在水内,候其面性发得十分满足,逐块抽拽下汤煮熟,抽拽得阔薄乃好。”此“面性”乃是充分聚合筋力,无筋力之面经不起煮。苏式生活除了雅致,还有悠然。我信奉悠然得至味,不紧不慢手工上出的活最宜人。在面条的机械化生产时代,将面粉演变到面条的过程,也应该略微放慢脚步,不然容易吃到僵僵的“死面”。元明之际,平江(苏州)人韩奕著《易牙遗意》,汤饼类收录“燥子面”为浇头做法,“水滑面”浇头为“麻腻、杏仁腻、咸笋干、酱瓜、糟茄、姜、腌韭、黄瓜丝做齑头,或加煎肉尤妙”。与浦江《吴氏中馈录·水滑面方》无异。将芝麻、杏仁在石臼内捣烂到黏糊状,称麻腻或杏仁腻。齑头为雅称,俗呼臊子是也。另有“索粉”乃“每干粉一斤,用湿粉二两,打成厚浆……搓索下滚汤中,浮起便捞在冷水中,沥干,随意荤素浇供”。真希望能在炎炎夏日的中午,在听得到蝉鸣声、看得见荷花的凉亭或水榭中与三五好友分享美味的索粉。
元代时,出现了与水滑面同的“索面”以及“挂面”“红丝”“红丝面”“经带面”“炒鳝乳齑淘”“冷淘面法”等,其中红丝为羊血和白面,红丝面为白面中渗入虾茸、川椒汁,炒鳝乳齑淘是素浇冷拌面,冷淘面法记载于《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是冷拌面的各种冷浇头制法,喜欢吃面之人又要馋唾水嗒嗒滴了。
明代,江苏松江宋诩《宋氏养生部·面食制》记有鸡面、虾面、鸡子面、豆面、莱菔面、槐叶面、山药面、玲珑面,所记鸡、虾等并非面浇,而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将他物揉搓进面粉之中,以增加面条鲜香。眼下姑苏多食府会所私房菜,不知哪家曾仿古?
清代始,面的花样多了起来,汤煮也有了定式。清冲斋居士《越乡中馈录·下面》:“煮水极滚,将面抖开投入,加镬盖煮之,俟面浮水面,即熟矣。如面身燥硬,及碱少者,应多滚一二次,以面不白心为度。”不白心则断生,面馆二灶大师傅算准了那碗面刚刚端到客人面前断生,遇到技术差的师傅就只能吃夹生面了。汤煮有了标准,阳春面就不会变糊涂面了。
当下面馆很少自备轧面机,大多是怀揣配方找可靠切面房定制,轧面既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苏式汤面的机制面条,一般分粗细两种,传统的切面刀受钢轴强度和机械加工工艺的制约,面条直径一般在1.2至1.5毫米。随着机械加工技术的进步,新式面条直径可以降低为0.8至0.9毫米,甚至更细。听面馆业前辈讲以前面馆自己压面都在五遍以上最多九遍,为的就是反复压制的面条可在热汤中较长时间保持原貌而不会吸干汤水,所以苏式汤面趁热吃的道理,就是要达到面外挂汤而面条不糊。
融合了专业厨艺的民间面食,最终均将演化为各地特色美食,苏式汤面也不例外。民间开水冲猪油的阳春面,逐步衍化出红汤、白汤、原汤三大类苏式汤面。红汤之红绝大多数为提炼过的红焖肉卤汁,行内称“助汁”。一碗以酱油、猪油、盐、味精和开水冲就的民间阳春面汤,与用助汁的阳春面汤有着天地的差别。老字号面馆会加入自备的风味物质,比如爆鱼卤汁或者酱鸭卤汁等成为复合风味的助汁,在挑面前或挑面后再浇入额外的大骨鸡汤,就形成了面馆之间汤味各不相同的格局;也有用鱼骨、猪骨及酱油炖煮而炼成助汁,如以重油著称的奥灶面之红汤,以助汁加红油再冲入滚烫无盐味的好汤而成。
吃面人呼白汤,非汤白,而是汤清。白汤面的代表有枫镇大面和奥灶卤鸭面,枫镇大面的助汁由白焖肉卤汁加入鳝鱼清汤炼制,再加发酵的上好酒酿就成为独特的好汤头,哪怕就是冲开水下去,也是鲜得眉毛要飞。奥灶卤鸭面的助汁,则是炖煮卤鸭的浓缩卤汁。
原汤即烧煮食材的原卤汤汁,原汤面算是苏式汤面的特例。比如吴江震泽、桃源、盛泽等地的红烧羊肉面,面汤即为肉卤。其中已经传承了四代的盛泽雷顺兴面馆,创办时就以整只羊腿的“生笃羊肉”最为闻名,生笃羊肉面几乎除了三伏全年供应。在隆冬的日子里还有干切羊肉,佐酒或过桥作面浇两宜。比如从纯粹的喝汤时代走过来的藏书羊肉汤也兼营面条,奶白色的面条别有滋味,鱼头汤面同理。还有颇有吴越古风的炒浇面,浇头炒熟后加入断生的面条,注水煮开,怎一个鲜字了得。
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言,“古人有云:入广者,朝不可虚,暮不可实。然不独广,凡早皆忌空腹。”广,通“旷”,意为空阔之地。如此说来,早上吃一碗尚好的汤面,除了吴地皮包水的习俗意义还有养生功效。而对于吃客而言,在靠谱的面馆吃一碗头汤面,也是给自己的味蕾定味,味道对了整天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