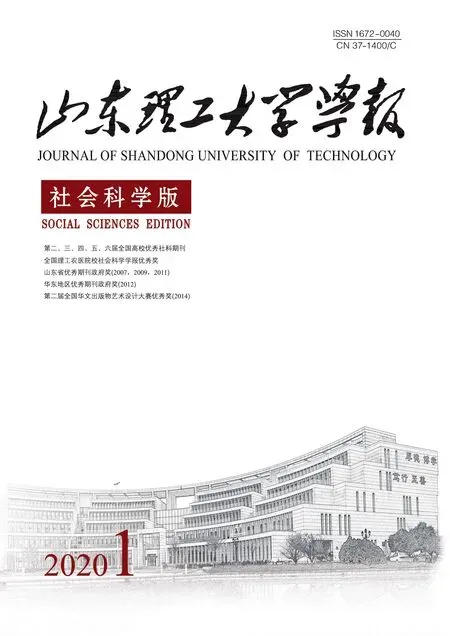近代墨学复兴之批评
沈 传 河
近代墨学是中国墨学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值得关注与研究。由于这一时期墨学研究日益兴盛,治墨学者众多,涉墨著述层出不穷,并于民国初年出现了墨学高潮,故学界一般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国墨学的复兴期。当代学界,对近代墨学已多有研究,多有评析,但总体上看尚不够深入,不够细致,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推进。笔者拟在这一方向上作一些相关探讨,尚期方家不吝指正。
一、近代墨学复兴的学术评析
(一)墨学与墨学研究不同
墨学和墨学研究显然不同,其实二者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墨学一般是指始于先秦的墨家的学术活动,其核心是墨家学说,代表人物是墨子,代表典籍是《墨子》。墨学,实即墨家之学,其研究主体一般是墨家的学者;而墨学研究则一般是指学界对墨家学术及其诸多具体方面的研究,其中有两个主要方面:对《墨子》文本的研究与校理、对墨子思想的研究与阐发。与墨学不同,墨学研究的研究主体一般是非墨家的学者。当然,实际上墨学与墨学研究是相互关联的,有时难于把它们截然分开。从逻辑上讲,应当是墨学的发生在先,墨学研究的发生在后,但实际上,墨学与墨学研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为墨学本身就是在与其他学派的辩难中产生的,当初其他学派对墨学的理解与批评构成了中国墨学研究的最初形态。举先秦的情况来说,从尹佚到墨子,再到墨家后学等,他们的学术研究即是先秦墨学,相应的史实构成了先秦墨学史;而从孟子、庄子(理论上可以上溯至更早),到荀子、韩非子,再到吕不韦等人,他们对墨家、墨学的研究与批评即是先秦墨学研究,相应的史实则构成了先秦墨学研究史。这两种学术活动各有脉络,区别十分明显。但到了秦汉时期,情况有了变化。专制政权的建立,使墨家不断遭受打击,墨家终于在西汉时期消亡。墨家的消亡,意味着墨学传承与发展的中断,中国墨学史自然也随之中断。中国墨学史何时能够得到接续,那要看中国的新墨家、新墨学何时能够出现。而墨学研究的情况则与之不同。墨家虽然消亡了,但墨家的典籍、学说及人们对墨家的相关记载却依然存在,人们对墨家、墨学的研究与述评依然在继续,绵延不断,直至今日。当然,其中是有兴衰起伏变化的。与之相应,中国的墨学研究史自然也就没有中断,一直延续至今。
事情本来很简单,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学界,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对这个问题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一般不把墨学与墨学研究加以相对严格的区分而分别治之。当代即使是专门研究中国墨学史的学者,一般亦是如此。在当下学界,人们对“墨学”“墨学研究”的使用,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和含混性,需要加以规范和厘清。主要情况有:其一,人们会在以下三种情况下都可能使用“墨学”一语:指称墨家之学;指称对墨家之学的研究,即墨学研究;兼而指称这二者。其二,“墨学研究”,不少时候会被省称为“墨学”。
(二)近代墨学复兴的学术评析
此处所言学术评析的基础即是,上文所讲的将墨学与墨学研究加以相对严格的区分并分别予以考察。
1.近代墨学复兴,复兴的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早有学者有所涉及,只是没有完全言明而已。兹略举两例:其一,马克锋:近代墨学“在经历了一段辉煌的时期后,并没有结出成熟的果实。不仅墨家之组织无人恢复,甚至连新墨学也没有出现”[1]。这里是讲,在近代墨学复兴中,新的墨家学派没有形成,“新墨学”也没有出现。其二,张永义:“严格地说,近代的墨学只是关于墨家的学问,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墨家理论的发挥或发展。”[2]这里强调的是,近代墨学复兴的只是“关于墨家的学问”,而“墨家理论”本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创新或发展。
将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与上文已有相关内容结合在一起去分析、考察,我们即可大致这样去立论:总体说来,近代墨学复兴,复兴的主要是墨学研究,而墨学本身,即墨家之学,并没有得到多少复兴或发展。当然,这样的立论需要去论证和阐释,以下试简要为之。
上文立论的前半部分,几乎不需要什么论证和阐释,因为近代时期,墨学研究大兴并推至高潮是学界公认的学术史的事实。此一时期,治墨大家辈出,相关著述不断涌现,成就巨大,水平卓越,并于民国初年出现了家传户诵、人人言墨的学术盛况。梁启超、栾调甫等人的相关著述中对这些情况均有所描述和论说,可资参考。如栾调甫对民国初二十年的墨学状况论述道:“独至晚近二十年中,家传户诵,几如往日之读经。而其抑扬儒墨之谈,亦尽破除圣门道统之见。……原此三端,遂以造成二十年来墨学春苗勃发之势。”[3]139-140
上文立论的后半部分,确实需要一些论证和阐释。近代墨学研究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掩杀了人们对此一时期墨学(墨家之学)兴衰的认识能力。在近代,墨学研究虽然兴盛了,但墨学(墨家之学)并没有随之兴盛起来,墨学(墨家之学)本身并没有获得多少复兴或发展。我们这样说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近代,身份明确的“新墨者”或“新墨家”并没有真正出现。这一时期,心仪墨学、推崇墨学者虽然不乏其人,如孙诒让、梁启超、谭嗣同、栾调甫等,但严格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算不上真正的“新墨者”或“新墨家”,最多只能算是“准新墨者”或“准新墨家”。其二,新的墨家学派显然没有形成和出现。既然“新墨者”或“新墨家”没有真正产生,新的墨家学派也就无从谈起。上文马克锋先生所言“墨家之组织无人恢复”,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考察墨学(墨家之学)复兴,新墨家学派的出现无疑应当被视作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其三,墨家学术的核心,墨家学说并没有获得什么创新和发展。这一点具有核心意义。因为一个学派的学术史,其实质是该学派学说的发展演变史。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一般是找不到属于墨家的新思想或新学说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墨学应当借鉴一下中国的儒学。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俱进,注意吸纳,不断有所突破与创新。
有必要作一些补充说明。在近代墨学复兴中,到底有没有墨学(墨家之学)复兴的成分?严格地说来,当然是有的。这主要表现在一部分人对墨家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予以接受和践行。这使得墨家消亡后以死的知识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墨家价值系统得以复活,对当时的个体在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墨学(墨家之学)复兴的实质性表现,当然应当予以肯定。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并不完全否认近代墨学(墨家之学)有所“真正复兴”。只是这种“真正复兴”的水平尚较低,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萌芽的状态。再者是,我们这里的分析与论述,无意去否定近代墨学研究兴盛的价值意义。相反,我们是肯定的。单就近代墨学(墨家之学)的复兴来说,近代墨学研究的兴盛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基本前提和基本路径,没有后者,前者便无从产生。当墨学研究者转化为墨者(墨家学者)的时候,新的墨学(墨家之学)之路就被开启了,墨学(墨家之学)复兴也就有了可能与希望。但遗憾的是,近代墨学研究的兴盛并没有带来近代墨学(墨家之学)的兴盛,而只是低水平的萌芽而已。其中因由应当是比较复杂的,有待进一步探究。
2.近代墨学复兴的水平
这个问题,上文其实已经有所述及,此处无需再展开论述,今仅就相关问题再加以必要的总结或补充。从上文可以看出,在把近代墨学区分为墨学研究和墨学(墨家之学)的前提下,近代墨学复兴,复兴的是什么?没有多少复兴的是什么?它们各自复兴的水平如何?这些问题都变得十分容易回答。近代墨学复兴,复兴的主要是墨学研究,即人们对古代墨家之学的研究,并且达到了很高的复兴水平;而其中墨学(墨家之学)本身并没有获得多少创新与发展,只是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萌芽状态。将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去看,虽然我们可以也应该肯定近代墨学确实复兴了,且成就斐然,但我们仍不能认为近代墨学复兴的总体水平很高或相当高。同样道理,我们在谈论近代墨学复兴时,还是要慎谈“全面复兴”或“完全复兴”为好。
二、相关思维方式的批评
近代墨学复兴,是中国文化于近代演进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中国文化所固有的一些思维方式自然会影响着这一复兴过程。其中诸多相关问题值得探究与反思。
(一)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批评
二元对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之一,它贯穿并体现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在近代墨学复兴的过程中,它体现得同样非常明显。
1.对儒、墨选用上的二元对立
出于与封建专制政体配套的需要,中国封建皇权势必要在众多学说中独尊一家,罢黜其他。中国皇权大多选择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正统与异端的二元对立也因此得以确立。这种独尊儒学的文化政策,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儒、墨之间原本的矛盾对立,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尊儒黜墨的文化结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深含其中。汉武帝以降,清中叶以前,这种尊儒黜墨的文化结构一向十分牢固。但清中叶以降,随着墨学的逐渐兴起,这一文化结构逐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愈演愈烈,终于在清末民初将这一传统的文化结构完全打碎,完全解构。
按道理,人类近代化的历程,在思想文化上,即意味着旧的封建文化专制的结束和新的多元并存文化格局的确立。但在中国,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和容易。虽然儒学不再被独尊,尊儒黜墨的文化结构亦随之坍塌,墨学也终于获得了解放和复兴,但人们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文化的脚步依然要在泥泞中挣扎。近代以前,人们的主流思路是尊儒黜墨,进入近代以后,主流思路逐渐演变为尊墨黜儒——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吴虞、傅斯年等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这一新的思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主流思路,虽然其思维内容刚好相反,但其思维方式本身却是完全一样的——在选用儒、墨上,二者均持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所以,从以前的尊儒黜墨,到近代的尊墨黜儒,看似是一种巨大的文化进步,其实不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期,历史性地终结了,但人们却又倾向于开启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墨术”的时代——正如郭沫若所言“在打倒孔家店之余,欲建立墨家店”[4]一样——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悲的吗?以墨代儒,罢黜他家,独尊墨学,其实只是文化专制在内容上的变化,作为形式的专制本身并没有变化。只要文化专制不能真正地终结,即使墨学能够登上官学的位置,其近现代意义上的创新与发展也不可能取得什么真正的成就。对于其他先秦子学,道理是一样的。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束缚。
因而,在近代墨学复兴中,人们应当放弃传统儒、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换用新的多元并存、多元并用的思维方式来对待儒、墨关系,对待整个学术文化。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真正确立新的文化民主制。也只有这样,墨学、儒学及其他先秦子学,才能真正获得其近现代意义上的创新与发展。在这一思路上,韩愈“儒墨相用”说的价值意义将大大突显出来。
2.对墨学评价推崇上的偏激化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思维容易走向偏执化、过激化乃至极端化等。中国人在评价对待墨学上,这一思维特点表现得亦十分突出。即使到了文化渐趋进步的近代,情况亦不免如此。
以一种偏激或极端的态度评价对待墨学,先秦时就已经开始。第一个开其端者可能就是孟子。孟子继承孔子的学说,以“正说”自居,视杨、墨为“禽兽”,视其学说为异端邪说,采取全部否定、全部辟除的激烈态度——这就是所谓的“孟子辟杨墨”——这显然是一种最极端的学术否定。虽然如此,但在秦汉以降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孟子对杨、墨的这种评判却成为学界主流评判杨、墨的标准。进入近代,儒衰墨兴,尊墨黜儒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与此同时,学界主流对儒、墨两家的评价也都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对于儒学,以前是尊崇有加,现在则是极力批判;而对于墨学,则刚好相反。近代对于墨学的评价推崇,总体上具有鲜明的偏激化倾向——时人执著于墨学,评价过甚,推崇过甚,出现了一些偏执、过激乃至走向极端的现象。
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不少人把墨学看成了振弊救世、救亡图存的不二法宝或灵丹妙药。如梁启超、严复、觉佛(高增)、许啸天等人,无不在某种程度上持有这种思想倾向。显然,这种思想倾向有失理智,过分夸大了墨学的治世功用,神化了墨学。其二,在宗教意义上推崇墨学,将其宗教化,甚至有人主张以墨教代替儒教来治国救世。这方面主要有梁启超、严复、易白沙等人。不顾墨学不是宗教的事实,而一味地在宗教意义上阐释墨学,推崇墨学,神化墨学,显然是更加主观化、偏激化的做法。而在国家政治的意义上提倡墨教,乃至欲立其为国教,这更是需要批评乃至批判的,因为它已经违背了人类文化近代化历程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政教分离。其三,新的政治力量,有人在国家政治的意义上对墨学推崇过分,有以墨代儒,建立新的官学的趋势。这里所说的新的政治力量,主要是指近代新兴的资产阶级。这方面的主要人物有梁启超、孙中山、易白沙和《民报》同人等。这方面的思想取向显然也是值得分析与批评的。近代新的政治力量,对政教分离、政学分离应当有着明确的思想认识,在推崇墨学上当适可而止,方不失应有的政治理性。
近代中国对墨学过高地评价,过激地推崇,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墨学的工具价值存有不切实际的过度渴求。因而,从墨学的方面说,近代中国对墨学的过高评价、过激推崇,除了有利于利用墨学外,对墨学本身的创新发展并无益处。甚至是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因为在这种过高评价、过激推崇的时代话语中,墨学很容易被凝固化、完美化乃至神圣化,而这些倾向对于一个学说的创新与发展是非常不利、非常有害的。
(二)线性思维方式的批评
线性思维方式,一般是指以单一化、片面化、机械化等为基本特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广泛存在,对近代墨学复兴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执一”的个体思想取向
“执一”的概念早在孟子时已经产生,孟子用之批评杨、墨等人在学术上执于一端,失其全面。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学是儒学,学术的主体是经学。在尊儒读经的时代,学界个体的思想取向自然多被框束在儒学上,执一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选择。但这种情况到了近代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儒学衰退,墨代儒兴,崇墨黜儒一时成为主流风气,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执一于儒学的传统做法,改而选择执一于墨学。这一时期“吾墨”“吾墨子”“我子墨子”等一类称呼的出现,即是一个明证。由从儒到从墨,貌似近代个体的思想选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实并不尽然。虽然“执一”这种思维方式的内容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作为形式的这种“执一”的思维方式本身却并没有什么改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按道理,人类近代化历程的到来,即意味着传统文化专制的结束,意味着多元并存文化格局的确立,从而也就意味着个体在自己的思想选择上获得了自由,可以多元兼取,融构自我。但是很显然,中国近代的相关状况并非如此令人满意。人们虽然有了一些自由,可以弃儒择墨,有了新的思想取向,但是文化发展的惯性似乎倾向于将人们继续框束在“执一”的线性思维方式之中,虽然这个时候不再是传统的执一于儒,而是新的执一于墨。只要这种“执一”的线性思维方式没有发生变化,即使墨学能够成为学界主流,甚至被奉为官学,其近现代意义上的突破与创新也是不可期待的。
近代中国,按理说应是一个对话、融构与新建的时代,但这种传统“执一”的线性思维方式,却极大地限制束缚了这一时代应有的学术文化趋向。按照人类近代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近代中国人应当放弃这种个体思想取向上的“执一”思维,而换用一种新的多元兼取的立体思维方式来选择确定自己的思想取向,成就自我——这才是更加现实、更加可取的做法,这也正是个体发展、学术创新的根本动力之所在。如果中国近代学术文化能够在这样的思路下展开,墨学定会能够在较为多元、较为丰富的层面上与他者发生对话,融构自我,从而获得墨学本身的创新与发展。如果是这样,在近代中国,新墨学的出现,新墨者的出现,就都将是可以期待的。
2.“尊一”的官方思想取向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专制,就其思维方式而言,恰是典型的线性思维方式:“尊一黜百”。从秦朝下迄清代,中国皇权多数选择了“独尊儒术”,亦有少数选择其他的例子。绵延不断的文化专制,不断地在强化着这种“尊一黜百”的思维方式,以致形成了强大的思维惯性,让近代中国在文化体制转型上变得难乎其难。
人类文化的近代发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是发现并确立了政教分离或政学分离的原则。这一思想对于近代中国学人来说,应当是并不陌生的,但他们似乎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还有,这一思想的一个直接推论,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更为重要,但他们似乎并没有发现,或者是即使发现了,却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关推理的过程及其直接推论是这样的:既然应当政教分离或政学分离,原本的国教或官学就应当回归到民间文化的状态中去,同时新的国教或官学也就不应当再产生设立。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看的话,近代中国,在国家政治的意义上,不管是“独尊儒术”还是“独尊墨术”,不管是推崇儒教还是推崇墨教,其实都是不对的。近代以来,儒学渐衰,墨学渐兴,在一些新的政治力量那里,墨学被推崇至高,明显出现了欲以墨代儒,建立新的官学或国教的趋势。这种现象显然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是需要批判和反思的。这样说来,近代中国在国家政治的意义上对墨学所作的过分推崇和神化,不应当被看作是墨学的荣耀。
历史的发展表明,人类注定是要走出中世纪的,而人类走出中世纪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政教分离或政学分离,传统意义上的国教或官学阙如——这一位置其实让位给了宪法。在近现代文化视野中,政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臣民思想观念的掌控者,而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仅仅是为公民服务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近代墨学无疑应当顺应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不应逆这一趋势而动;也只有这样,墨学才能获得真正的、持续的复兴与发展,达到其服务于社会人生的目的。对于儒学、道家、法家等传统学说,道理同样如此。也就是说,在近现代文化民主制的体制之下,包括墨学、儒学在内的诸多传统学说都必须回归民间,走民间学术发展的道路,这才是正途。
(三)“述而不作”与创造性思维的出现
1.从“述而不作”的视角来看近代墨学
“述而不作”是孔子的学术信条——孔子有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5]这一简短的表述,却为我们提供了两个相对又相关的学术批评的视角:“述”(阐释)与“作”(创新)。我们不妨用之于对中国墨学的审视。当然,这种审视是基于墨学(墨家之学)的本位立场来进行的。统观中国的墨学整体,亦即广义的墨学,包括墨家之学与墨学研究,显然“述”的部分是其主体部分,而“作”的部分是其非主体部分。当然,这里是就其学术存量的多少而非其学术价值的大小而言。墨学之“作”,即墨家之学,存量较少,仅集中于先秦时期而已。墨子是最主要的创作者,从墨子到墨家后学,创新的轨迹均清晰可寻。相形之下,墨学之“述”,即对墨学(墨家之学)的研究,则源远流长,存量很大,尤以清中叶以降为重。大凡学界对墨家之学的称引、批评、校勘、训释、考证、阐释等,我们均可以归之于墨学之“述”。
再来审视一下近代墨学。按“述而不作”所提供的两个基本视角去审视中国近代墨学,得出的结论是,它基本上就是“述而不作”。在中国近代,新墨者没有真正地出现,墨家理论基本上没有什么突破与创新,新的墨家著述亦基本上没有出现,也就是说,墨学之“作”,在近代中国基本上是缺失的。但相形之下,墨学之“述”在近代中国却十分发达,成就空前,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所谓的墨学复兴。近代的墨学之“述”,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去看:其一,沿袭传统的朴学方法,继续对《墨子》及相关问题进行校勘、训释、考证等,代表人物及著述是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其二,引入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亦广泛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墨学,研究墨子,重点在于阐发墨子的思想学说,探究墨家的名辩逻辑,代表人物及著述则是梁启超、胡适及其相关著述。总之,近代墨学的基本情况就是:“述”之者多,且足够多;但“作”之者少,且非常少。
2.近代墨学(墨家之学)的创新
上文已经说过,墨家之学在中国近代的创新是很少的,这应当说是近代墨学复兴中最大的遗憾。
按道理,墨家之学在近代急需对话与融构的学术背景下,是应该有所创新和发展的。之所以没有,原因固然是比较复杂的,但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应当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墨家之学确实有其伟大的一面,包含着一些超越其时、可归于近现代的文化因素,近代中国人对此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与阐发,这自然是值得肯定和嘉许的。但墨家之学终究是古代的学说,与中国近代相差尚远,它要想适应近代中国并进而有所创新与发展,应当说还有一些路程需要去走——在人类近现代的文化视野下,积极与时代对话,与自我对话,力求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从而创造出新的墨学形态,这种取向应当说是有可能的,是有希望的。就笔者个人的理解,在近现代文化视野下,墨家之学至少还是有一些创新基点的,可以加以阐发和新构,兹略举一例。墨家的“兼爱”,原本就兼有“爱己”与“爱他”两层意思,如墨子就此曾言:“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6]不仅如此,还可以看出,墨子在言说兼爱时,倾向于立于“爱己”的立场,强调“爱他”的目的在于“爱己”。但遗憾的是,在墨家实践及后世墨学研究者那里,“爱己”与“爱他”的关系往往被割裂开了,“爱己”被掩没在对“爱他”过分或极度的推崇与追求中,这是十分值得深思的。到了近现代,人们有理由去发掘和阐扬兼爱中的“爱己”思想,这也是从墨家之学中“拯救个体”并导向个人主义的重要途径。
客观地说来,墨学之学于近代并非全无突破与创新,一些突破与创新的萌芽应当说还是有的。笔者认为,易白沙的《广尚同》即可以算作是其中一例。墨子对尚同制度的设计大致是这样的:里长上同于乡长,乡长上同于诸侯,诸侯上同于天子,天子上同于天。这种制度,总体来说应当视其为一种专制制度,其中所蕴含和强调的是“下必须服从于上”的专制思想。但易白沙在其《广尚同》一文中却对其作出了新的阐释,借以表达了自己的民主思想,这种创新是值得关注的。其创新的关键是用“同于仁”将原本尚同的思路作了转向,转向了“同于民”。他说:“天子不可为同之标准,故必同于天;然天者郁苍苍而不言者也,故必同于仁;然仁之范围,又至大且博、浩无涯漠者也,故必同于民。天以见仁,仁以托民,然后尚同之真谛,如日月之昭天。”[7]这样,总体上就改变了尚同的取向,由原来的“上同于君”变成了现在的“下同于民”——这也正是易白沙所要表达和强调的思想主旨。显然,这一思想主旨与墨子原本的思想主旨是有很大差别的。文中易白沙认为,这些新的尚同思想是墨子原本就具有的,应当说这是不符合学术事实的,实际上是他在托墨子以自述新说——当然,就其思想实质而言,这种新说是属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体系的。
三、近代墨学价值的发掘与使用
近代墨学的复兴,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界,而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总体来说,近代中国与墨学相关的事情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研究墨学、发展墨学、倡导使用墨学。近代中国对于墨学的研究很多,成就很大,而对于墨学本身的创新与发展却很少,成绩微弱,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那么近代中国对于墨学的倡导使用情况如何呢?最简括的回答是:热。近代中国人热情、亢奋乃至不无狂热地倡导墨学,推崇墨学,以致许多场合人们都可以看到墨学登场言说的身影。也正是这种对于墨学异乎寻常的倡导与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近代墨学一度兴盛的表象。
(一)墨学的两种价值: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
任何人或事物存在的价值意义都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对于他者而言的价值意义,一是对于其自身而言的价值意义,前者一般可称之为工具价值,而后者一般可称之为目的价值。例如一位工人,他对于工厂生产而言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就是其工具价值;而他对于自身而言,本身即是目的,本身就具有价值意义,这就是其目的价值。理论上讲,任何人或事物都是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统一。中国的墨学(墨家之学)也应当是这两种价值——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统一。一方面,墨学本来就是应世运而生,为治世而来,作为先秦产生的一套治世理论,一种治世工具,自然具有突出的治世工具价值。当然,墨学的工具价值肯定不会限于此一端,例如墨学还可以用于个人修身,用于反对儒学,用作墨学研究的对象等,这些都体现了墨学所具有的不同的工具价值。另一方面,墨学作为应世运而生的一种学说,本身就具有存在的充分理由,本身对于自身及其创新发展就是具有价值意义的,这也就是墨学对于自身而言所具有的目的价值。这种辨析告诉我们,后世人们在研究墨学、倡导墨学、使用墨学时,既要注重墨学的工具价值,又要注重墨学的目的价值,并将二者适当地统一起来。
出于对世俗功利的重视和追求,人们往往更加注重人或事物的工具价值,而有意或无意忽视其目的价值。在近代墨学复兴的过程中,人们在对待墨学的问题上,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并且这一问题还相当突出,值得分析和探究。
(二)重视对墨学工具价值的发掘与使用
墨学在清代的兴起,原本就源于人们对墨学之于经学工具价值的发现与使用——再加之其他子学,即学界常言的“以子证经”。近人支伟成即言:“殆清儒理董经史,引据尚古,子书既多出先秦,不得不以馀力旁治之;久乃愈觉其弥可珍贵,竟跻之群经之列,遍为之注。”[8]其中所说的“子书”,自然包括《墨子》。墨学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中逐渐复兴并走向独立的。
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变迁日趋剧烈,文化思潮亦随之急剧变化,在此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墨学不断受到重视和推崇,其工具价值不断地被发现、发掘和使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选择墨学作为对冲西学的工具,或者是作为理解、接受乃至宣扬西学的媒介或工具。这两种目的取向,在“西学墨源”说流行的过程中均有突出的表现,“激进的思想家声称‘西学墨源’是为了替西学的传播张目,因为中国人笃信古已有之的教训,极端的保守分子爱说‘西学墨源’则是为了寻求对抗西学的工具”[9]186。虽然他们的目的取向不同,但他们都持工具目的性则是显然的。其二,将墨学视为振弊救世、救亡图存的工具或法宝,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崇和倡导,甚至有人欲将墨学抬升至国教的位置上。近代中国对墨学的价值推崇和利用,无疑以这方面最为突出。这一价值取向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那里表现得均十分明显,“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以墨家的平等意识、人格理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作为自己变革社会、拯救人类的信念源泉和人生楷模”[1]。这种对墨学工具价值的使用,虽然能够带来很大的社会政治功效,但显然亦有其偏颇之处。如栾调甫对之批评道:“今则曰惟墨学可以救中国……此学者本其殷切用世之心以治《墨子》,而墨子之学所以不能蕴发无余者一也。”[3]145-146其三,在新文化运动中,把墨学作为反对儒学,倡导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工具。这种选择当然是有理由的,儒、墨向来对立,而墨学又包含着一些与科学、民主、博爱、平等等近现代文化观念相通或相似的文化因素,因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倍受启蒙者的青睐和推重,如陈独秀、吴虞、鲁迅、钱玄同、傅斯年等,皆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里,笔者想顺便指出的是,就人类文化近现代发展的历史趋势而言,真正能够代表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向的思想学说,应当是王学左派,而不是墨家学派,选择墨家学派来代替王学左派,应当说是近代中国文化演进中的一大历史误会。其四,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把墨学作为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或工具。作为西学,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时,需要中国本土资源作出接引和呼应,不少人此时选择了墨学。墨学中的讲究兼爱、重视劳作、倡导节俭、反对掠取等思想,确实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理论貌似有相符之处,故能引起时人对墨学的相关探究与使用。梁启超、吴虞、蔡和森等人于这一方面皆有所述论。这一做法虽然多是借用和比附,但客观上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解、接受与传播。
墨学原本就是一种理论工具,修身工具,乃至治世工具,对墨学的工具化使用应当说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没有理由反对这一点。但问题的关键是,当人们过于热衷于对墨学的工具化使用,极力发掘其工具价值时,客观上就影响、削弱了人们对墨学本身问题的思考和探究,而只有这些对墨学本身问题的思考和探究,才可能导向人们对墨学目的价值的发掘与使用。
(三)忽视对墨学目的价值的发掘与使用
墨学不光是工具,也是目的,关于墨学本身的问题也是问题,也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探究。但在近代墨学复兴的热潮中,学界于这方面做得显然是非常欠缺的,人们忽视了对墨学本身问题的关注与探究,忽视了对墨学目的价值的发掘与使用。这里所谓的墨学的目的价值,其实是指墨学本身——实际亦即古代墨家之学的历史遗存——对于近代墨家之学的存在与发展是具有价值意义的。
关于墨学本身的问题,主要存在以下方面:其一,如何获得和坚持墨学的本位立场来进行相关评判?近代学界对此显然缺少思考,能够真正获得并长久坚持墨学本位立场的学者似乎确实很少。其二,如何对历史上的墨学作出是非优劣等方面的评析与评价?这方面的实际情况是,近代墨学“研究者多注重揭示和发挥墨学中的积极内容,至于墨学本身的内在限制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9]206。而对墨学本身缺点与不足的思考与探究,才是创新墨学、发展墨学的现实起点。其三,立足于当下时代,应建构什么样的新的墨者人格?近代学界于这一方面显然也是乏善可陈,这也是近代中国没有真正出现新墨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四,如何创新发展墨学,形成新的墨家学说,建立起新的墨家组织?其中创立新的墨家学说的问题,在诸多关于墨学本身的问题中具有核心意义。在这一方面近代学界显然也是几乎没有什么创建。
既然近代学界对于墨学本身的一些问题关注较少,探究较少,那么他们对于墨学目的价值的发掘与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无从谈起,因为只有在对墨学本身的一些问题作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中,墨学对于自身的目的价值才可能得到实际的发掘与使用。这实际上是讲墨学对于自身的对话、使用与创新,这同样是墨学整体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