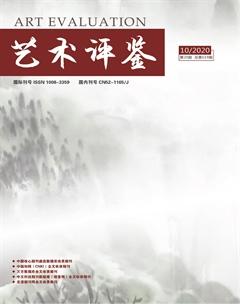《词谑》中的曲学思想初探
王凯
摘要:嘉靖一朝承前启后,相比明代前期,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社会风气的迁移自然使得戏曲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念有了较大不同。《词谑》的完成时间大约是在隆庆时期,但它的作者却是完整的经历了嘉靖一朝的明中叶戏曲大家李开先,他对于民间俗曲的喜爱和金元“本色”观念的推崇,不论是对当时还是万历之后的戏曲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李开先 曲学思想 明代戏曲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20-0004-03
纵观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程,戏曲的发展经历了一段先抑后扬的过程,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以及政治风气的流动从外部给戏曲发展带来了诸多影响。明初的高压政策留给戏曲行业发展的空间有限,出身农民起义的朱元璋非常注重从元亡的教训中吸取经验,以儒家正统思想标榜的朱明政权在立国之始就实行了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元明人多恒歌酣舞,不事生产,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歌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明太祖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出发,主张禁戏,又从“劝忠劝善”的角度推崇《琵琶记》,看似矛盾的行为实则反映了戏曲只是作为一种教化民众的工具存在于明王朝的顶层规划中。如果按照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的观点,将明代文学的划分以嘉靖元年(1522)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作为元代文学的馀波和明代中后期文学突变的准备,可视作中国中古文学的最后阶段;嘉靖以后,文学变革犹如狂飙突至,迅猛异常,中国文学正式步入近古的新时代”。可见明代戏曲在嘉靖一朝长达45年的时间中,不论是曲学思想还是从事创作的社会环境都已经较之前有了巨大变化,并且对后世,特别是万历以后明传奇创作的黄金时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探究这一时期曲学思想的变化对整个明代戏曲的梳理有着特殊的意义。李开先的一生经历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四朝,为官十二载却在壮年之时罢官回乡,此后闲居山东章丘,寄情于词曲,倒也怡然自得。其主要戏曲活动大都集中在嘉靖一朝,所涉包括散曲、院本、杂剧等等,范围甚广,是明中叶戏曲大家之一。
关于《词谑》的版本及作者,学界此前多有争论,但就目前所见材料来看,《词谑》作者应确为李开先。作为一部明代戏曲选本,《词谑》选录了大量的元代散曲文学作品,是明中期复古思潮的重要体现。《词谑》一书约略成于隆庆二年(1568),是李开先晚年着手从事的一部戏曲理论之作,虽未全部完成,然就其所处的时代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亦具有很高的价值。
一、《词谑》编撰的时代背景
嘉靖以武宗堂弟的身份入继大统,登基之始就引发了一次改变明朝政坛格局的“大礼仪”事件,前前后后震荡近20年。当时距离朱元璋建国已经过去了154年,距离明亡还有122年的历程,正好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裂变时期。政治上,“大礼仪”事件的结束是皇权对以内阁为首的士大夫话语权的一次胜利,但其后的演变却逐渐成为内阁与士大夫群体的分离。后期的嘉靖越发痴迷于修道事玄,常年居于西苑之中,大小事务皆由内阁首辅而定,依靠迎合皇帝喜好入列内阁渐渐成为常例,这自然演变成了朝臣之间互相倾轧,党争不断的局面。应该说为官十二载的经历让李开先看懂了官场的明暗规则,可即便他小心翼翼却仍不免受到牵连,成为党争下的牺牲品。
世风的变化具体包括经济活动、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内容。我们先从这三方面逐一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明清以来,国家赋税仰仗东南地区,虽然嘉靖一朝面临着南倭北寇的威胁,但经济总体态势仍旧保持着一个向上的局面,特别是江南地区,社会变迁的速度较之前与其他地区有了明显的加快,富商大贾也不再受到行政权利的打压。至于日常生活更是不分等级,“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宫衙然,园囿僭拟公猴。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普通百姓的住宅就已经豪奢若此,更不必论富商大贾以及士大夫之家。虽然在明初之时对于房屋建制有过明确的规定,但历经100多年的发展已经名存实亡,世风奢靡,僭越已成常态。人际交往更是利字当先,明前期的文人尚能坐而论道,以文会友,到了嘉靖时期,士人交往无外乎房屋田产,经济的繁荣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不僅仅体现在衣食住行上,在戏曲文学等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即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上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与建国之初官方所秉持的儒家正统思想相背离,无论是这一时期的剧本创作还是曲学思想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二、明前期的曲学思想
关于明前期的界定,学界有多种划分,这里以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中的观点为依据,即将嘉靖之前的时期统称为明前期,具体时间为公元1368—1522年。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艺术思想与生俱来的特质,具有儒家正统教育背景的士大夫们不仅是具有政坛话语权的主体,在文学创作领域,即便是一向被视作“小道”“末技”的戏曲,也占据着绝对的主导。“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促使着他们将人伦道德、礼仪教化视作戏曲天然必须具备的原始命题。及至朱家王朝立国,文化专制主义盛行,自上而下的推动更是使得教化论思想彻底成为了主导。高明《琵琶记》肇其端,邱濬《五伦全备记》、邵灿《香囊记》继其后,皆可被视作符合这一思想的代表作品。邱濬被明孝宗赐为“理学名臣”,一生受程朱理学影响颇深,这种只知宣扬封建伦理,毋论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将戏曲的教化思想推向了极致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除了文人创作之外,朝廷先后设教坊司、钟鼓司,从官方层面完全控制了杂剧的编演,同时一些受封亲王或为了躲避政治打击,或为了歌功颂德,也参与到创作之中,以这两部分群体为代表的作家构成了明前期戏剧作家的主体。他们代表了上层阶级的利益诉求,掌握着解释封建伦理道德的话语权,阶级地位使他们不可能深入民间深刻感受百姓疾苦,自然也就失去了戏剧创作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同时统治者对元代以来的民间创作群体进行打压,元明易代,杂剧衰微,南戏复兴尚未被传奇取代之时,自元以来形成的戏曲繁荣期进入了短暂的沉寂。
三、《词谑》中包含的曲学思想
《词谑》分词谑、词套、词乐、词尾四个部分。李开先性情洒脱,“词谑”部分中所录的35则趣闻轶事多为嬉笑滑稽之作,如王舜耕骂驴:“在家不吃竹,出家却吃竹。急欲趁程途,锥戮不动…将欲割了两耳,教人骂你是‘秃驴;割了下唇,你又‘般若、般若的;恨将起来,和上唇都割了”。王舜耕明为骂驴,实则暗讽和尚,滑稽调笑,读罢令人捧腹。类似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李开先搜集了大量前人曲作的同时,再于文末之处提出自己的见解,虽只言片语却不乏真知灼见。“词套”部分所录为李开先搜集整理的元明间散曲;“词乐”部分为当时著名的演唱艺人;“词尾”部分则是自己创作的见解和曲作收录。
(一)对戏曲语言的要求
明中期以后,世风迁移,戏曲创作的群体更加多元,类似李开先这般的失意士人开始醉心于戏曲创作,罢仕回乡固然断了李开先的仕途,却使他有机会潜心词曲,不为声名所累。与前代作家如朱权、邱濬相比,他尤为注重民间词曲的情真意切和率真奔放,也许与他罢官多年,与社会底层接触较多有关。李开先曾经提出“真诗只在民间”的主张,对于被视作“俚俗”的民间俗曲大加赞赏。徐渭曾言,“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记》延续了已经发展到极致的教化思想,同时在形式上堆砌辞藻之典雅工丽,这种风格甚至在汤显祖早期作品中都能看到。但李开先却大异其趣,一反当时剧坛这种形式主义的倾向,他重视俗曲,以“俗”为美,看重的正是其语言质朴和直抒胸臆。如《词谑》中收录的咏疟疾:
【叨叨令】有咏疟疾者,颇尽其情态:“热时节热的在蒸笼里坐,冷时节冷的在冰凌上卧,颤时节颤的牙关错,疼时节疼的天灵破。兀的不害杀人也么哥,害杀人也么哥,寒来暑往都经过”。
此处,只言片语,用词俚俗,但将疟疾发作时的特点描述的真可谓淋漓尽致,读罢,都能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生命力。无刻意雕琢之痕迹,无卖弄文采之嫌疑,浑然天成。由此可见李开先对于民间词曲的推崇不仅在于其“形”,更在于其“质”。他在《市井艳词又序》中提出“学文、学词者,初则恐其不劲、不文,久则恐其不软、不俗”,学习诗文创作,将通俗化看作是最终追求。戏曲不是晦涩难懂的伦理说教,束之于高阁,而是通俗易懂的真情流露,传唱于民间,李开先的曲学思想很明显已经具有了“主情论”的某些特质,推崇词曲语言的俚俗化倾向,为明朝的传奇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对戏曲创作标准的要求
在李开先之前,明代文壇上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倡导“文笔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之风,要求振新文坛,但只是模拟古人的做法而不重视思想内容的表达,必然会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
李开先与前七子中的康海、王九思交往甚密,康、王二位最以戏曲见长,《词谑》中亦多次提及王九思其人。李开先推崇金元本色,肯定了元曲的文学之地位,与前七子在文学上的观点似有相近之处,显然是受到了时代风气的影响。就像盛唐是诗歌不可跨越的巅峰,金元杂剧也是戏曲史上只可仰望的高山。但与那种寻求刻意模仿甚至是剽窃的极端论者不同,李开先并没有陷入复古的泥沼里动弹不得,《词谑》中词套部分收录了约48套散曲,其中多为元人所做,在他看来,今人的作品“有燎花气味”,全不似元人作品情意动人。他敏锐的感觉到元杂剧的兴盛在于其精神气质,敢于发出“不平”之音,这在他的传奇作品《宝剑记》中有所反映,借林冲被奸臣陷害逼逃梁山,最后清除奸佞,匡扶朝廷的故事表达了对朝廷权臣当道的不满,冲破了长期以来教化论思想的桎梏。李开先认为戏曲创作的标准应以元人为样,但他对元曲的推崇不是连篇累牍的模仿,而是对其审美价值的肯定,戏曲创作不是只有骈俪的辞藻和枯燥的说教,而是内在情感的表达,以及社会现实和人间至情的表达。
(三)李开先的“宗元”观念
明代戏曲的“宗元”观念强化了元代戏曲的“经典”意味,元代戏曲的经典化,使其部分内容相应地拥有了“经典”的文化影响力。戏曲“宗元”观念,挟带了传统“宗经”思想的文化威势,移用了其价值论证逻辑,为明代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之繁荣创造了合适的舆论环境。罢仕归乡后的李开先是较早推崇戏曲宗元观念且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词谑》中我们也能找到很多佐证,词套部分收录有套曲、散曲等,其中元人作品约有25部之多;其次他推崇元代散曲作家张小山是因为他讲究用韵,“小山青劲,瘦至骨立,而立血肉销化俱尽,乃孙悟空炼成万转金铁躯矣”。张小山的作品力求脱离散曲白描而雅正,讲究音韵,词套收录有两篇张小山所做的套曲,如“长天落彩霞,远水明金镜。花如人面红,山似佛头青”这样对仗工整、词句优美的句子,也可以看出李开先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于音韵的要求。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明初期高压禁戏政策的影响下,戏曲创作唯有以教化论思想为主导,过分追求语言的绚丽而忽视内容的做法自然失去了杂剧生长的土壤,在成化、弘治年间,戏曲创作一度陷入了消沉。嘉靖之后社会风气迁移,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以及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大夫开始倾心于词曲,在对比了明初寂寥的曲坛之后,元杂剧往日的繁荣呼唤着时人以古为尚,但复古的气息很容易便成了对古人的模仿抄袭,因此,急需新的戏曲理论来主导下一个时期的创作。李开先的《词谑》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虽不是一部绝对意义上的理论之作,但从中亦可窥见嘉靖一朝曲学思想的沿变。
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词谑》中包含的曲学思想,首先民间俗曲展现出了强大的表现力,其质朴的语言和充沛的感情引得时人侧目。其次李开先以元曲重新定义了戏曲的审美标准,以元人为师是对教化论思想的公开反叛,在他的时代,文辞斐然却内容空洞的戏曲失去了生命力。在他之后的汤显祖已经树起了“主情论”的大旗,情与理的矛盾已然是下一个时代争论的焦点,嘉靖一朝曲学思想的沿变为后世的传奇繁荣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二,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2.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明代文学·绪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牛建强.嘉靖年间世风之迁移[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29-32.
[4]顾起元.建业风俗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169-170.
[5]李开先.词谑(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73.
[6]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43.
[7]李开先词谑(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80.
[8]张小芳.宗元观念与明代戏曲理论之建构[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3).
[9]李开先.词谑(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