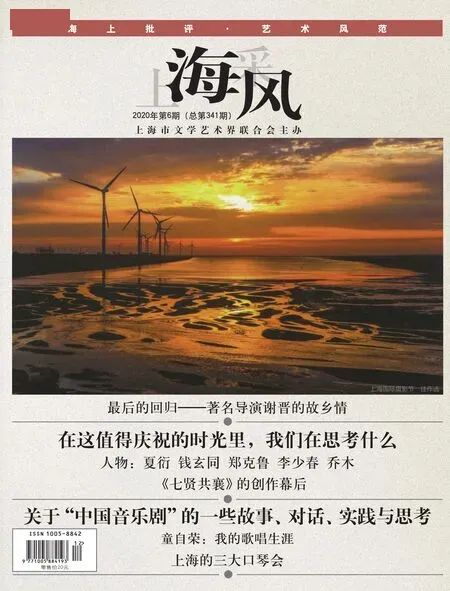最后的回归
——著名导演谢晋的故乡情
■ 许朋乐

2008年10月18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然而,它在我的记忆中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那年四月,年届而立的女儿准备披婚纱了,打算把婚礼订在10月18日,她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求之不得,二话没说,全力支持!于是筹办婚礼成了我们家的大事,女儿总体安排调度,大家分头落实。尽管女儿和我都不喜张扬,更不愿铺张,但环环节节,零零碎碎,要全部搞定,也不是简单的事。谁料,正当我们满怀喜悦积极筹办,许多事已经基本落实的时候,女儿突然变卦,想把婚礼改在10月26日,问我同意不同意。我一听,有点不乐意,我问她,10月18和10月26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么一改,会产生好些麻烦。再说18,要发,多吉利!女儿笑笑,没说什么,只是强调26日是星期天,大家参加婚礼更方便。既然如此,我也就顺水推舟,尊重女儿的选择,毕竟这是她的终身大事。凑巧的是,几天后,我接到一位老同事的请柬,打开一看,哦,他儿子10月18日举办婚礼,盛情邀请我们务必参加,那一刻我为女儿改动婚期独自鼓了掌。
10月18日那天上午,我和爱人正商量着怎么去参加同事儿子婚礼,送什么礼物,穿什么衣服,突然,手机响了,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在电话中告诉我,谢晋导演去世了。那低沉的声音像引爆了一颗炸弹,轰地一下,我懵了。我不信也不敢信:前些日子还遇到过谢晋,他虽然脸色有点憔悴,但身板依然硬朗、声音还很洪亮,怎么可能毫无征兆地离我们而去?我追问了一句“怎么可能?”仲伦压抑着情绪,尽量平静地告诉我,谢导去上虞参加母校春晖中学的校庆,突发疾病,意外地去世了。倏然间,我想到了谢衍,谢晋最喜爱的长子,难道是他的病故将谢导彻底击倒了?没容我多想,仲伦要我立即赶到瑞金医院,市委宣传部王部长找我。
我心急火燎地赶到瑞金医院,王部长以极快的语速给我交代了任务。他说,谢导是独自一人去上虞参加春晖中学校庆的,他突然去世,什么情况,什么原因,上海没有一个人知道。你马上去上虞,把谢导去世前前后后的来龙去脉摸清楚。快去快回!他还告诉我,谢晋的夫人徐大雯前几天刚装上起搏器,怕她一下子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我们给她的信息是谢晋身体不适被送进了医院,同时以需要给她做再次检查把她安置在瑞金医院,以防突发情况。王部长让我去病房和大雯老师见个面,告诉她我马上就去上虞。心急如焚的大雯老师听说我去上虞,竟然执意要我带上她。我只能安慰她,让她相信我一到上虞就会尽快给她准信。
离开瑞金医院,我和集团办公室主任汤新华坐车向上虞疾驰而去。一路上我心情沉重,望着车外掠过的一幢幢民宅,我想起了谢导的家乡上虞谢塘,想起了修葺一新的谢晋故居,那长满茸茸绿草的小院子,那卧坐在墙角的盛满雨水的四只大缸,那土头土脑的农家灶台,那安放着谢晋曾经使用过的老式家具的厅房——这种简朴温馨、隐含着浓浓人情和烟火味的氛围,曾经熏陶了谢导的童年,沐浴了他的青春,给他植入了对故乡深深的热爱和眷恋。我又想起他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就像风筝,飞得再高再远,下面总有一根线紧紧地牵着。这根线的一头就是故乡。”我还想起两次和谢晋一起回他家乡的情景,一次是纪念他从艺50周年,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从杭州到绍兴,再到上虞,最后抵达谢塘。徐桑楚、汪洋两位上影北影的老厂长,著名作家李凖、黄宗江来了,和他合作过的编剧、摄影、演员几乎都来了,他一手栽培的斯琴高娃、刘晓庆、姜文、徐松子也来了。那天,故居被挤得满满的,每一个角落都沉浸在欢乐和喜悦中。脸上写满为家乡骄傲的谢晋,神采飞扬,笑声朗朗,他让我明白爱家乡应该是爱祖国的前奏,家国情怀是血肉相连的。
还有一次是上海影协和浙江影协举办谢导的研讨会,我们又专程拜谒了谢导的故居,我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寻觅谢导的足迹和踪影,嗅着空气中飘逸的炊烟的味道,我仿佛看到谢晋一家正围坐土灶前,品着女儿红,吃着霉千张——我感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厚重的文化,家庭传承的血脉,在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中会有永不消逝的投影。是啊,故乡、故居承载了谢晋留下的美好记忆,也给热爱谢导的人带来不尽的遐想。我不知道还有哪位名人大家,能像谢晋那样,客居外乡,却每年春节携家带眷,回到故乡,回到老屋,吃柴火烧的大灶饭,喝大缸里存蓄的天落水,电影和故乡是谢导一生不能分割的伴侣。
汽车风驰电掣,我的思绪也在记忆的高速路上奔驰,美好的记忆从心底牵出丝丝悲怆和惋惜,难道正是他对家乡始终如一的真情挚爱,让家乡把维系他的那跟风筝线收回、游子重回故里?也许是谢导把生命的最后一次约会留给了故乡。
近乡情更怯,到了上虞,我感到沉重的双脚几乎挪不开步子,我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揪心的一幕。上虞市的领导热情接待了我们,他们已经根据上海方面事先提出的要求,在上虞人民医院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安排了我们想见的从上海到上虞陪伴或接触过谢导的人。此时正逢午餐时间,我们婉言谢绝了市领导邀我们去饭店用餐的请求,坚持在会议室吃盒饭,边吃边了解情况,争取尽快将实地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反馈到上海。
整个会议室,气氛凝重,每一个与会人员的脸上都挂着悲痛,都有点懵。谢晋的离世太突然、太出人意料了,对每一位在座的人都是不小的打击,给这座城市笼罩了悲痛的气氛。我们之间的交谈从谢晋离家上车开始,两位到谢导家接他上车的交大毕业的上虞籍年轻人讲述了简单的经过。这次上海回上虞参加春晖中学70年校庆的人比较多,组织方特意安排了一辆大巴接送,平时回家乡都坐小车并由家人或驾驶员全程陪护的谢导也独自和大伙一起坐大巴了。我考虑到谢衍去世不久,痛苦了几个月的谢晋几乎足不出户,很想知道这次外出他的精神状态。两位交大生直言,那天他很兴奋,一上车就和大家打招呼,在大家自报家门时,他还用家乡话说了一句“谢家塘的谢晋,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那腔调那神色,流露出一丝诙谐,赢得全车人笑声连连。

位于浙江绍兴上虞谢塘镇的谢晋故居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顺着时间和谢晋活动的轨迹,我们提问,当事人解答,一步一步深入了解真情。从到宾馆的时间,谁接待的,住哪一间房,他干了些什么,到晚餐何时开始,哪些人和他一桌,喝了什么酒,一共喝了多少瓶,谢导喝了多少……几乎滴水不漏。谈到喝酒,同桌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一桌七个人只喝了一瓶瓷瓶装的花雕,谢导喝了其中的五分之三。一瓶才一斤,五分之三也就五六两,对于爱喝酒的谢晋来说真是“湿湿嘴”,我心中有点疑惑。
说实话,听到谢导去世的噩耗时,我的第一反应这一定是一次意外,或许和酒有关,或许与摔跤有关。谢晋好酒而且酒量很大,艺术界无人不晓。据说,他年轻时一次能喝两瓶茅台酒。他出外景必带酒,全是好酒,他喜欢用酒提神解乏。一次喝完酒后,他曾经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喝酒也能强身健体,你跑四百米,心跳120,我喝半斤白酒,心跳也能达到120,殊途同归,都能锻炼心肌。不过不能醉,一醉就伤身体了。“七人一瓶,还是黄酒?”我心中的疑惑没有解除,我仔细问了同桌的人,他们一口咬定就是一瓶。那么吃完晚饭、喝了酒,谢导又做了什么呢?一位负责接待陪伴谢导的年轻人告诉我,他们只在宾馆里散了一会步,七点多,谢晋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回房间之后,谢晋的所有活动无人知晓,成了一段“黑片”。好歹宾馆老总根据监控提供了两个镜头,一是回房不久,谢晋曾打开门,朝走廊两头望了一眼,估计是有事要找服务员。还有一个镜头是九点钟光景,一位服务员路过谢晋房间时,发现他的房门没关,灯还亮着,人却睡着了,就帮他熄了灯关了门。第二天早餐时,谢导迟迟没有下来,就让服务员去请他。服务员反复摁铃敲门都没有反应,便打开了房门,谢导平静地躺在床上毫无声息,服务员大声唤了几声,谢导纹丝不动。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立即惊动了宾馆、医院、公安和上虞市的领导。第一时间赶来的医生实施了抢救,但谢晋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医学无力回天。
我问在座的那位负责抢救的医生:你能告诉我谢导去世的原因吗?医生有点紧张,或许他害怕承担什么责任,笼统地说了一句:突发性疾病。什么病?你是专家,你得根据你的判断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又追了一句。医生垂下头,思考了一会,说:心源性猝死。至于离世的时间,我也让他根据推断给了明确的答复。接着,公安的同志报告了现场的勘查情况以及他们所作的死亡证明。至此,谢晋猝然离世的来龙去脉似乎已经清楚了。我提出了我们的请求,希望在座的市领导能组织有关人员,根据会议记录形成一份书面文件并附上有关单位的鉴定材料,盖上政府的公章,由我们带回上海,市领导慨然允诺。
这时,夜幕已经降临,窗外灯火阑珊,瑟瑟的秋风吹着落叶,发出沙沙的声音,秋虫低吟浅鸣,渲染了秋天的萧瑟。我遥望天边那颗闪亮的星星,倏然间被一块硕大云彩吞噬,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谢晋。一股想见他的激情油然而生,我必须见他一面,我要彻底打消我曾经有过的疑虑,我要和他作最后的告别。我当即向上虞的领导提出了我的请求,他们没有拒绝,立即着手安排,并陪护我们一同前往。
因为一直在等上海方面的意见,谢导的遗体没有放进医院太平间,而是安置在僻静处的一间普通的屋子里。我和汤主任在手电灯光的指引下,沿着黑黢黢狭窄的小夹弄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小屋前。路上医院领导不住地打招呼,说来了上百名记者,走大路会被他们拦住。我想这么大的事,嗅觉灵敏的记者自然不会放过。小屋的门打开了,我突然紧张了起来,心怦怦直跳,我不是怕,而是恐惧,恐惧谢导怎么会睡在这里?一间阴森森的简屋,一盏昏黄的小灯,一台陈旧的哼哼唧唧的窗式空调,一张极其普通的小床上,躺着我们敬重的电影大师,这画面则能不叫人恐怖?我突然大叫一声“谢导啊,我来看你了”,一个箭步就跨到了谢导的身边。我借着微弱的灯光仔细辨认着,谢导的神态是安详的,但脸色泛青,微微开启的嘴唇青得发紫。我凑近他的脸闻了闻,没有一点儿酒味,至此“七人一瓶酒”的说辞尘埃落定。但是我还有一个担心,谢导一向走路比较急,喜欢往前冲,会不会摔过跤?我揭开了盖在谢导身上的被子,将他的身体两侧都看了,除了肤色没有任何异常。也许与谢晋太熟了,父辈的感觉很快淡化了我的恐惧,替代恐惧的是一种不安和急切。十月的江南,风吹在身上有一丝凉意,但关着门窗,室内的温度还是蛮高的,虽然有窗式空调,床下还放了冰块,但我总觉得时间久了,谢导的身体受不了。我突然萌生了要将谢导带回上海的主意。但是我清楚,根据我国一些法律条款,遗体是不允许移动的。我想真的要这么做,一是上海的有关领导要同意,并火速落实他的安放之处;二是上虞要支持,要派车派人协助。我立即旁敲侧击地对上虞的领导说:谢晋是上虞人,也是上海人,更是全国人民关注并敬重的大师级艺术家,因此他的后事处理应该不是上虞能一力承担的。上虞领导似乎对此早有思考,不住地点头。
离开小屋后,不远处传来一阵阵嚷嚷声,像有人吵架似的。上虞同志告诉我,现在记者越来越多,都聚在医院办公室门口,嚷嚷着要了解谢导离世的真相。医院负责接待的同志在最终结论未确定前不敢随便说,记者自然不依,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大。我想看个究竟,径直走到记者边上,没想到刚露面就被来自上海的几位曾经打过交道的记者发现了,他们立即涌了上来,向我抛出各种各样的问号。我平静了一会,对他们说:谢导不幸去世,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新闻?告诉你们,这里有的只是悲伤!说完转身走了。
这种场面让我越发觉得,带走谢导,宜早不宜迟。我拉着几位上虞的领导简单商量了一下,让他们准备一辆救护车安放谢晋,给人一种抢救病人的感觉,这样过高速公路收费站不会有什么麻烦。我们坐车开道。上虞的同志提出他们要专程护送谢导回上海,安排一辆科斯塔断后。初步商定后,我们各自向领导汇报,征求意见。上海的领导听我汇报后,认为这样处理非常好,对后续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叮嘱我路上要注意安全,并答应立即请有关委办在龙华殡仪馆落实安放地点。上虞的主要领导也同意这样做,不过在谢导离开前,他们市里领导想一起和老人家告别一下。我想,家乡人有这样的要求,理所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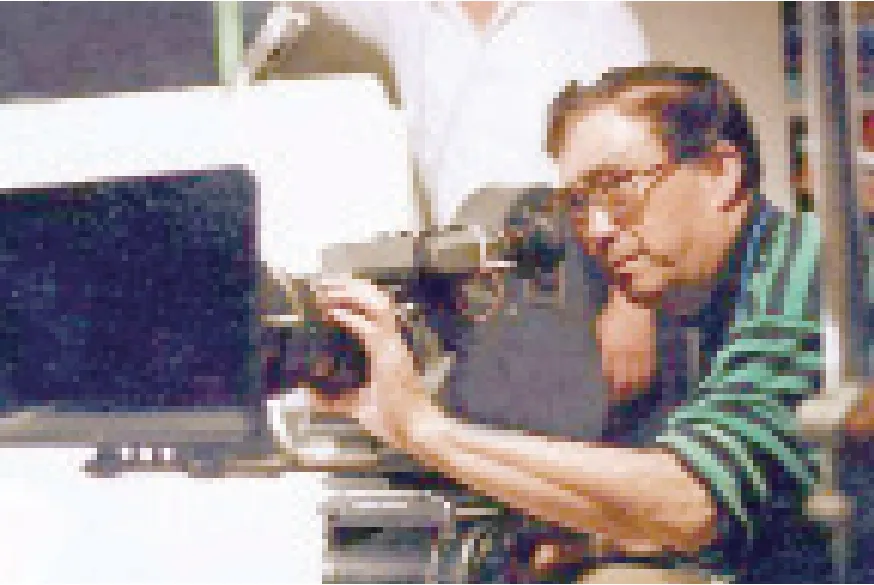
晚上七点,一切安排就绪,为躲开记者的耳目,我们的车缓缓开到高速路口静静等候着。片刻,一辆没有闪灯的救护车也悄悄到了。再过一会,坐着十几位上虞同志的科斯塔也到了。于是,三辆车按照事先商定的顺序出发了。那一天路上特别顺,车很少,是否为谢导让道了?几乎没有减速的机会,只用了两个小时一刻就顺利抵达上海龙华殡仪馆。我想,也许是谢导归心似箭,他知道家人在等他,同事朋友在等他,热爱他的无数上海观众在等他……
谢导被安放在已经准备好的灵堂,在鲜花的簇拥下安静地沉入他永不破碎的梦想。他的妻子徐大雯被搀扶着,颤颤巍巍扑向他,一声声悲泣,如一首爱的挽歌,震颤着我的心。我转过身,一行憋了很久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接下去几天,我一刻不停地参加谢晋追悼会的筹备工作,把对他的爱戴和崇拜留在了他的灵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