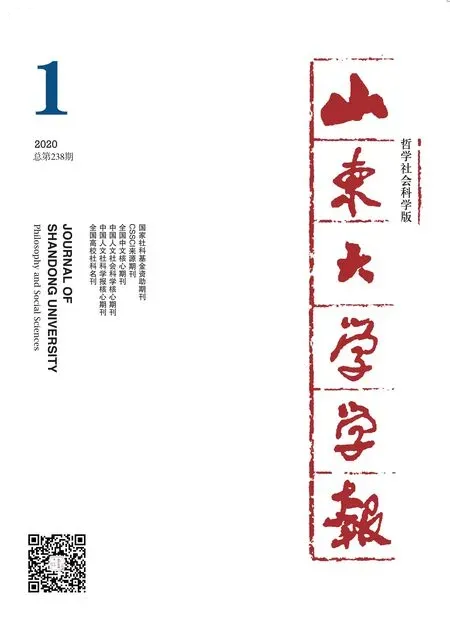西医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的亲和性研究
马来平
如果说,在明末清初第一次西学东渐中由于中国改历的迫切需要,天文历法和数学的东传成为当时的重中之重的话,那么19世纪中叶之后,由于新教传教士奉行藉医传教方针并且把行医当作服务于殖民势力在华谋取利益的重要工具,西医东渐便上升为第二次西学东渐的重头戏了。19世纪中叶之后的西医东渐过程中,各种医学思潮纷争不断、高潮迭起,令人惊心动魄。于是,关于西医东渐,人们对西医与中医的冲突津津乐道,而对于西医与中医及其背后的科学与儒学的亲和性却往往熟视无睹。为此,本文拟着重就西医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的亲和性予以初步探讨。
一、几个基本认识问题
研究西医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亲和性,需要首先明确几个相关的基本认识问题。
(一)中医是儒学在医学领域的特殊存在形式
从最直接的意义上看,西医东渐是中、西两种医学互动的过程。
就西医而言,西医不仅是各门自然科学在医学领域的具体应用,也是以人的身体、生理、心理和疾病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所以西医不仅是技术,而且也是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
就中医而言,它大致包括医理、诊疗和药物三部分。医理是基础,它支配着诊疗和药物。如何诊疗、用什么药、如何用药,统统依据医理。通常认为,中医医理的核心观念是阴阳五行学说和元气说。阴阳五行学说和元气说的早期形成蕴含着先秦诸子百家尤其是道家和阴阳家的贡献。将阴阳五行学说和元气说系统引进医学的是形成于汉代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1)关于今本《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学界意见分歧,迄无定论。本文从医史专家廖育群的考证意见。。该书以阴阳五行学说和元气说为纲阐述生命的形成、疾病的发生和辨证施治的原则。而在汉代,不仅儒学已经取得独尊地位,而且,阴阳五行学说和元气说也已是儒学的基本理论了。 《汉书·艺文志》强调儒家自始就与阴阳理论有不解之缘。它为“儒家”所下的定义中第一句就是:“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著名中国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则指出:“由于从董仲舒开始,阴阳五行学说已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组成部分,所以儒和医之间的联系也建立起来了。后世有不少医家都认为,作为医,如果不懂得儒家那一番道理,就只能是个庸医。这种情况也表明,中国的医学,乃是儒家哲学为父,医家经验为母的产儿。”(2)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11页。其实,不仅如此。中医和儒学在许多基本理论方面是一脉相通的。例如,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中医则把“仁”作为行医的前提和出发点,故而李时珍《本草纲目》重刻本说:“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3)李时珍著,刘恒如、刘山水校注:《本草纲目》《重刻本草纲目序》,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3页。;儒家以“天人合一”作为自己的宇宙观,而中医以“天人合一”作为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主张“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4)《黄帝内经·灵枢》,卷十一,《刺节真邪第七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395页。;儒家重“礼”,强调伦理角色和社会次序,而中医以“君臣佐使”为用药原则,借助对社会次序的认识来描述脏腑功能;儒家崇尚“中和”思想和“执用两中”“执中权变”的中庸之道,而中医力主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重要标志,治疗当遵循“阴阳和合,阴平阳秘”,追求“致中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情况表明,儒家的一整套基本理论和价值观念渗透进中医,成为中医之魂。因此,可以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中医既是医学,也是儒学在医学领域里的特殊存在形式,抑或说,中医乃是医学领域的儒学。
强调中医是儒家思想在医学领域里的特殊存在形式,是否意味着贬低道家对中医的贡献?不是的。当我们论及道家对中医贡献的时候,需要明确:首先,道家在先秦中医形成期的贡献十分突出,但汉代以后,儒家对中医的贡献就逐渐领先了。其次,道家对中医的贡献,集中体现在阴阳气化、精气观和矛盾转化的思维方式等方面。第三,强调儒家对中医的贡献并不意味着对道家贡献的否定,而且,儒、道两家对中医的贡献常常胶着在一起、难分难解。尤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道释相互融合的趋势压倒相互排斥趋势,乃至一度出现了三教合一现象。
既然中医和西医分别以儒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甚或分别是儒学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或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那么,中医与西医的关系从属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并且是后者的特殊表现形式,则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科学与儒学关系在西医东渐中的重要地位
在西医东渐中,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1.西医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是中、西两种文化互动的重心
从根本上说,西医东渐是中、西两种文化冲撞和融合的互动过程,其中心乃是科学与儒学的关系。
就西方文化而言,自近代科学革命开始,包括西医在内的科技文化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羽翼丰满的科技文化逐渐在器物、制度和价值等不同的层面对社会各建制或各领域发挥引领和一定的支配作用。由于近代科技革命发生在西方,所以,科学技术曾一度集中反映了西方文化追求真理的价值观、尊重客观规律的宇宙观和严密的逻辑思维方式等,成为西方文化的精华和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才全面成为世界性的了。西医东渐时期,正是科学技术由西方地域性文化开始走向世界性文化的时期。当时,西医和整个西方文化一起传入中国。19世纪中叶以后,西医不仅是西方科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担当着西方科技东渐的开路先锋角色。加之西医以人的生命这种最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门类中最复杂、最高级,并具有综合运用各门自然科学成果的特点,所以,可以认为,西医东渐时期,西医是整个西方科学乃至西方文化的杰出代表。
就中国文化而言,尽管20世纪初,儒学受到全面否定和激烈批判,黯然走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神坛,但是,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地位并未真正被撼动。在中国,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争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西学东渐时期,中西两种文化在医学领域的关系,主要是儒学和西方文化的互动关系。而后者则主要发生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儒学在医学领域特殊存在形式的中医与西医及西方科学的关系,二是作为西医东渐文化环境的儒学整体与西医及西方科学的关系。
总之,正是由于西医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异质的文化,而且是整个西方科学乃至西方文化的杰出代表,所以,西医一旦进入中国,便立即受到了来自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强力作用,上演了一幕幕中西医之争的大戏,从而使得西学东渐时期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成为中、西两种文化互动的重心。
2. 西医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是各种医学思潮论争的根本点
在一定意义上,西医东渐是一场医学思想的斗争或革命。
西医传入中国后,从诊所到医院,从传教士办医院到国人办医院,从医院量的扩张到医院人才、器械、设施和管理等方面质的提高,以及利用开办医校、吸引留学生、迻译出版医学书刊和建立西药房、药厂等途径,西医在体制上迅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尤为重要的是,西医建立在精密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它在许多疾病的治疗上,尽展医理清晰、诊断准确、医疗过程透明、疗效立竿见影等风范。这给作为千年古医的中医造成了泰山压顶之势,随之,中医由一家独大降为西医的配角,甚至数度发生了生存危机。在这个过程中,相继促生了中国医学界形形色色的医学思潮。这些思潮,尤其“废止中医论”“保存中医论”“中西医汇通论”和“中医科学化论”等有代表性的若干思潮的论争,无不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为根本点:“废止中医论”割断了中医与科学的联系,认为中医与科学是完全对立的,是伪科学;“保存中医论”主张中医是与现代科学技术性质不同的“另一种科学”,它与现代科学技术“道并行而不相悖”,甚至既相容又可以互补;“中西医汇通论”认为中医与科学技术存在局部可通约关系,可以有选择地用科学技术完善和补充自己;“中医科学化论”认为中医与科学技术是完全可以通约的,中医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断用现代科学技术解释、完善和发展自己。总之,各种医学思潮的论争最终都汇聚于:如何看待中医的科学性?中医和科学的基本关系是对立的,还是相容的?若基本关系是相容的,那么,二者是否存在可通约性?中医为什么能够在中国传统科学中独立存在下来?中医的发展是回到中医经典,还是主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提升自己?如何看待中医在与西医觌面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局限性?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从现象上看各种思潮的论争的根本点是中医与科学的关系,但由于中医是儒学在医学领域里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所以,各种思潮的论争的根本点乃在于科学与儒学的关系。
(三)西医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内容
较之西方科学其他学科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西医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内容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
1.多样性。除了直接的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以外,西医东渐中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尚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西医与中医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两者分别奠立在科学与儒学的基础上,二者的关系既是东西方两种医学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科学与儒学关系。(2)科学与中医的关系。实际上是以中医为中介的科学与儒学关系。(3)西医与儒学的关系。实际上是以西医为中介的科学与儒学关系。其中,对于西医东渐中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说来,分别作为科学与儒学具体存在形式的西医与中医间的关系最直接、最重要。上述情况在其他学科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中极为少见。形式影响内容,它决定了西医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内容必定是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
2.儒学形式双重性的长期存在。和西方古代科学包容于哲学相类似,中国古代科学整体上主要隶属于儒学,所以,在西医以外的其他学科东渐的过程中,都曾一度存在儒学形式的双重性情况。所谓儒学形式的双重性是指,西学东渐过程中,在科学领域,儒学有两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一种是以直接形式存在的儒学;一种是以间接形式存在的儒学即以古代科学形式存在的儒学。由于在西方科学的冲击下,中国古代科学的其他学科相继汇入世界科学的主潮流,只有中医顽强地独立存在下来,所以,儒学形式的双重性,唯独在西医东渐领域中一直保留下来了。这一现象不仅提供了关于儒学与科学具有相容性的新证据;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关于考察科学技术与中医这类民族性或地方性知识关系的一种新视角。
二、西医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具有根本上的亲和性
整体上看,西医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在发生一定冲撞的同时,呈现出根本上的亲和性。具体表现如下:
(一)面对西医和科学技术的冲击,中医不断做出重大调整
西医东渐中西医和科学技术对中医产生了一定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指西医东渐过程中,一方面,中医曾遭受来自民国政府的一次次施压和公开取缔;另一方面,在西医势力渐趋扩大的形势下,以西医界人士为主的一部分人一次次兴起攻讦中医的浪潮,以致引发近现代史上的数次中医存废之争。这种作用一直贯穿西医东渐的始终,不过,在西医和科学技术的冲击和引导下,中医不断做出了重大调整,使得中医焕发青春、如虎添翼,从而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中医的调整贯穿于西医东渐的始终,并使中医主要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深刻变化:
1.中医学术内容上的变化。中医依据科学技术摈弃了大量猜测和臆说,纠正了延续多年的大量错误和偏见,不少经验认识和做法得到了现代医学理论的解释和验证,使得中医医术更加规范,从而更具科学性和严谨性。例如,区分了经络与血管、知道了心脏会跳动、尿液不是从肠子进入膀胱的、人吸入的空气不是在五脏之间周游一圈而是进入肺;接受了许多西医病名,将中医的诸如气虚、血虚、痰湿、气郁等病名改称为“证”;中医依据科学技术改进了病因、病机学。如,认识到“外邪”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细菌、病毒、支原体等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以及中毒、中暑等理化因素,“情志致病”亦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神经或体液异常、内分泌紊乱和免疫功能低下等。此外,在中医诊断中,其诊断方式转变为采用四诊法的同时也适当运用现代仪器进行检查;药物方面较为重视药物构成成分的配置和中药剂型的改革等。
2.中医人才教育方式的变化。尽管中国古代也出现过诸如唐代“太医署”之类的小规模的医学学校教育,但是,中国古代中医人才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父传子、师授徒。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医人才教育的方式由父传子、师授徒的传统方式全面转向了现代院校教育方式。这种变化引发了双重效应:一方面,提高了培养人才的效率,实现了人才教育的体制化和规范化等;另一方面,学生在校大部分时间是课堂学习,导致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的结合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中医感悟性、体验性等缄默知识的传授,中医经典的学习和研究有所削弱等。迄今,关于院校教育应当适应中医特点,以师为主、把师傅带徒弟的个性化授业方式适当引入学校教育的呼声不绝于耳。
3.中医学术研究方式的变化。过去,中医的学术研究全神贯注于中医经典的注疏、考据和药方的积累与编辑等方式。西医东渐以来,中医除了继续开展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外,已经开始利用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广泛和深入的中医药基础研究,以及临床研究和药物研究等。例如,西医东渐以来,我国在藏象肾脾研究、证候研究、经络研究、针刺镇痛和针刺麻醉研究,以及中医学术标准的规范化建设等医学基础研究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我国,中医的许多学术研究越来越成为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中医界对于这种学术研究方式的变化一直存在不同声音,认为中医的实验室研究是西医的做法,对中医是一种异化。一部分人认为,中医学术研究唯一的正途是回到研读中医经典的轨道上来。
4.中医学术交流方式的变化。宋代政府曾设立过“校正医书局”,专事搜集、整理和刊印历代重要医籍,明代也成立过“一体堂宅仁医会”的民间医学团体(46人),但要么昙花一现,要么规模有限。整体而言,中医传统的学术交流不那么开展。著书立论,把自己从医的心得,以及搜集和研制的药方公诸于世,被称赞为“不藏私”,是“立论以济天下后世”(明代名医吴有性语),这大概是古代医界学术交流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一般情况下,医生们处于“进与病谋,退与心谋”(清代名医吴鞠通语)的相对封闭状态。西医东渐以来,中医学术交流已经实现了成立社团、创办期刊、举行学术会议等现代化方式。这一转变,活跃了学术氛围,提高了交流效率,有效促进了中医的进步。当然,对中医学术交流方式的这一变化,中医界也有异议。异议者认为,中医学术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对中医经典参悟的深浅,与他人交流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西医和科学技术促进中医所发生的变化,绝不限于以上所述。诸如医生职业化、医院及其管理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等均属此范畴。西医和科学技术对中医的冲击固然是双方冲突的直接表现,但同时应该看到,冲击和中医的调整密不可分,冲击最终导致了中医的调整,而中医调整的实质是,中医和儒学在强大的压力下向科学技术的一种靠拢,是中医科学性的增强,以及儒学和科学技术接榫的过程。因此可以认为,西医和科学技术对中医的作用表明,科学与儒学是具有根本上的亲和性的。
(二)儒学和中医对西医持欢迎态度并对其发挥一定的建构作用
西医东渐中儒学和中医对西医的作用主要是一种“选择”的作用。所谓“选择”主要是指:以儒学化了的人为中介,即儒学思想首先内化为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乃至生命观、身体观、生理观、疾病观等,然后,通过人对西医和科学技术所表现出来的迎拒作用。从西医东渐的历史实践看,充任当时儒学对西医和科学技术作用中介的,不仅仅包括社会上层人士,而且也包括社会基层的老百姓。而“选择”则表现为许多种形式。其中,主要分为排斥、欢迎和建构三种形式。其中,欢迎是建构的前提,而建构则是欢迎的深化。
诚然,儒学对西医产生过一定的排斥。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新教传教士借助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并且以行医作为传教和西方殖民势力经济活动先导的历史阶段,与基督教胶着在一起的西医所遭遇到的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排斥情况更是司空见惯。从西医剖腹和截肢等外科手术长期不被接受,到误传西医“剜眼剖心”“盗尸炼银”“拐卖幼童”“蒸食小儿”等,把西医妖魔化;从教会医院与民众之间层出不穷的医患冲突事件,一直到西医的生理观、身体观、疾病观与儒家传统观念的深层冲突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这种排斥贯穿于西医东渐全过程,但总的看,随着西医东渐的深入,儒学对于西医的排斥呈弱化趋势,而欢迎则长期占据主流。
1.关于欢迎。西医东渐过程中,从整体和主流上看,儒学对于西医是持欢迎态度的。鉴于西医对于儒学的冲击和影响直至清末才格外明显起来,所以这里将主要聚焦于清末民初主要儒家流派对西医的态度。清末民初,最有代表性的儒家流派是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国粹派”,以及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早期现代新儒家。下面,将扼要考察一下上述流派对西医的态度。
晚清今文经学继承和发展了汉代今文经学的变异、进化思想,主张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依据《春秋公羊传》所说的“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三阶段,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新的三阶段论。例如,晚清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提出的三阶段论即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康氏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一直处于“据乱世”,实行君主统治。应当通过变法,将社会推进到“升平世”,实行君主立宪。将来再将社会推进到“太平世”,实现民主共和,康氏以此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合理性。晚清今文经学所主张的社会历史进化论不仅直接依据了达尔文进化论,而且与西方科学求变、求新和求真的科学精神是一致的。所以,它对中医和西方自然科学持欢迎态度。例如,康有为热情赞扬西医。《日本书目志》(1898年)是康有为为国人介绍西学的一份详备的书目表,当时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在这份长达15卷的书目中,生理学和医学雄踞篇首。皆因康氏认为“大治在于医,故以冠诸篇焉”(5)康有为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8页。。书目表每卷卷后均有作者“序”。在这些“序”中,康有为热情赞扬西方的解剖学、妇产学和生理学。他说:“近泰西解剖之学至精微,贤列氏其冠冕矣”(6)康有为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268页。;“若产婆学,尤关生理之本,泰西皆有学人专门考求。而吾中人弃于一愚妪之手,草菅人命数千年”(7)康有为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278页。;“如生理之学,近取诸身,人皆有之,凡学者所宜,尽人明之。吾《素问》少发其源,泰西近畅其流,鳖杰儿氏、兰氏、歇尔蔓氏,大唱元风,兰氏阐析尤精矣”(8)康有为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267页。。他还自学西医,“创试西药,如方为之”,治好了自己的病。
清末“国粹派”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派别。古文经学是其主要思想资源之一,宗旨乃是,保存国学,重铸国魂,反对欧化。基本主张有四:一是用国粹激发和增进爱国热忱;二是颂扬“国学”,批判“君学”,反对帝制;三是从“国学”中寻找变革政体、实行民主共和的根据;四是在效法西方各个中国政治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复兴中国文化。尽管“国粹派”在如何保存国粹和如何处理保存国粹与中国文化实现近代化的关系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它反对一味醉心欧化,主张中西文化互补和会通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所以,它对西医和西方自然科学整体上是持欢迎态度的。例如,“国粹派”骁将、古文经学殿军章太炎出身中医门第,精通中医医理,却不讳中医之短,不妒西医之长。他说:“脏腑血脉之形,昔人尝解剖而不能得其实,此当以西医为审……脏腑锢病,则西医逾于中医,以其察识明白,非若中医之悬揣也。”(9)章太炎:《论中医剥复案与吴检斋书》,《华国月刊》1926年第三期,第三册。他认为,较之中医,“西医则有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助其药学;理学家发明探热针X光显微镜,助其诊断;电学机械家助其治疗。此中西医一进一退之关键在焉。”(10)陈仁存:《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存仁医学丛刊》(香港)第二卷(1953年)。
早期现代新儒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全面否定和批判儒学的刺激下而走上历史舞台的。在“五四”激进派看来,儒教是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儒学“仁义道德”吃人、儒学与民主和科学完全对立,因此他们激烈抨击儒学,主张在中国彻底根除儒学。这种偏激态度刺激了以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为首的一批儒者。这批儒者针对“五四”激进派将中西等同于新旧、新旧等同于是非的独断文化观,基于文化的根本精神,将中西两种文化归结为不同民族生活样法和意欲方向的不同,进而揭露了西方文化的弊端、展示了中国文化的优长。他们认定,西方文化的路向已经走到了尽头,未来将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他们的核心理念是,中国应当增强文化自信,充分认识到儒学并不比西方文化逊色,相反,却拥有西方文化不可企及的许多优长之处。中国不仅不应当根除儒学,相反要爱护、光大和发展之。儒学具有与科学和民主等现代化要素一致的深厚潜质,也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所以,儒学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在现代化中发挥引领作用是早期现代新儒家提出并成为后来各时期现代新儒家的中心议题。既然如此,早期现代新儒家对西医和西方自然科学持欢迎态度则是不言而喻的了。例如,梁漱溟终生研究儒学和传统文化,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其“中西文化比较”思想享誉海内外。它基于中西医比较,对西医赞誉有加。他说,中西文化“两方比较,处处是科学与手艺对待。即如讲到医药,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1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4页。他认为西医追求客观共认的确实知识,中医习用猜测、崇尚天才,“这种一定要求一个客观共认的确实知识的,便是科学的精神;这种完全蔑视客观准程规矩,而专要崇尚天才的,便是艺术精神。”(1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55页。他还认为:“西医是解剖开脑袋肠子得到病灶所在而后说的,他的方法他的来历,就在检察实验。中医中风伤寒的活,窥其意,大约就是为风所中,为寒所伤之谓。但他操何方法由何来历而知其是为风所中、为寒所伤呢?因从外表望着像是如此。这种方法加以恶谥就是‘猜想’,美其名也可叫‘直观’。这种要去检查实验的,便是科学的方法。这种只是猜想直观的,且就叫它做玄学的方法。”(1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57页。且不说梁漱溟对中医的看法是否准确,单就他对西医是否持有肯定和赞扬的态度说,则是一清二楚的。
儒学对西医整体上的欢迎态度,既充分显示了儒学对科学技术具有亲和性的内在基质,也充分显示了儒学对异质文化海纳百川的博大气度。
2.关于建构。建构有多种表现形式:
(1)西医的主动适应。西医东渐初期,在儒学和中医的作用下,西医对中医做出了种种适应性努力,或者说中医对西医发挥了某种形塑作用。如传教士行医时,为了适应病人不了解西医而相信和依赖中医的心理,往往要学习一点中医;在西医诊断中加进了中医把脉问诊的步骤;有的传教士在自己所办的诊所里,聘请中医坐诊,用以招徕病人、配合和补充西医;英国传教士、医学硕士合信(Benjamin Hobson)主张中西医应该沟通,在临床上中西药并用,甚至说:“药剂以中土所产为主,有必须备用而中土所无者间用番药。”(14)转引自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上海:学苑出版社, 2012年,第 58页。
(2)中西医汇通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影响西医发展。西医东渐过程中,在西医和西方科学技术的冲击下,中医界一部分人做了大量中西医会通和中西医结合的工作,以致形成了颇有影响的中西医汇通派。这些工作有不少是把西医经过改造纳入中医,其实质就是对西医的建构。此外,中国知识分子在研究或参与翻译西医著作的过程中,往往掺入儒学意识,从儒学和中医的角度理解和解释西医,从而使得传入中国的西医较之其本来面目表现出一定的变异。这也是对西医的建构。
(3)中医和儒学的现代科技价值对西医产生了巨大诱惑力和挑战性。西医东渐对于中医和儒学,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机遇的突出表现是,正是由于西医东渐,彰显了中医和儒学的现代科技价值。和中国传统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中医与科学的关系表现出了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这种关系的深度与广度无与伦比。中医比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任何学科都更加鲜明、更加集中地表征着儒学。二是中医集中放大了儒学所具有的整体性、关联性和有机性等特点。关于后者,无独有偶,恰恰是西医以其往往治标有余而治本不足和防不胜防的药物副作用等许多缺陷,也同样集中放大了科学技术所具有的分析性、机械性和还原论的弱点。于是在西医东渐中,当中医遇上西医,这两种放大共同造成了一种效应:彰显了中医和儒学的现代科技价值,即彰显了中医和儒学对于西医和现代科技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不少人认为中医和儒学的补偏救弊作用只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甚至更晚一些才显现出来。其实,早在西医东渐时期就已经十分明显了。面对具有关注病灶、细菌、细胞病变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等特点的西医,中医以其“重在治人”、“治未病”、辨证论治,以及重视人体器官的有机关联、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和情志保持平衡等特点,在预防疾病、治疗顽症和慢性病、克服药物副作用等方面,显示出了突出的优点。其实,中医相对于西医的优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学对现代科学补偏救弊的作用即儒学现代科技价值之所在。在现代,尽管西医和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但由于人体生命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具有自组织性、自稳态性和开放性,而且人的各种疾病还具有随机性、偶然性等不确定性。所以,西医在许多疾病面前无能为力。如何从中医和儒学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乃是关乎西医甚至整个现代科技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时代性课题。
在中医和儒学对于西医“选择”作用的几种表现形式中,欢迎既然占据主导地位,那么,科学与儒学之间具有根本上的亲和性,则是不言而喻的。而建构作用看起来是儒学和中医通过沟通中西医和缩小中西医差异而实现对西医的改造和同化,其实,与此同时也为西医和科学技术改造和同化中医搭建了桥梁。甚至由于科学技术和西医的日新月异和高速发展,西医和科学技术对西医的改造和同化反倒占了上风。换言之,中医界所做的中西医会通工作,在中医和儒学对西医的改造和同化方面举步维艰,而在客观上却大大加速了西医和科学技术对中医的改造和同化进程。当然,无论是谁改造、同化谁,既然是改造和同化,就意味着双方的一种认同和接近。简言之,就是一种亲和性。
总之,西医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是具有根本上的亲和性的。
三、西医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具有根本上亲和性的内在根据
为什么西医东渐中,科学与儒学会具有根本上的亲和性呢?
(一)“知医为孝”
从儒学的角度说,医学一向为儒家所重视。在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知识系统中,医学属于“子”类。这是因为“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15)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69页。。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具有贯彻儒学基本理念的工具价值。
众所周知,儒家学说的中心内容是一种伦理道德体系。其中,“孝”具有基础性地位。用《孝经》的话说即是“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16)胡平生译注:《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页。。原因是,“孝”制约着其它伦理关系,甚至关乎政治。“孝”是“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17)胡平生译注:《孝经》,广至德章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0页。,就是说,“孝”不仅是孝敬父母,事实上,它可以外推至尊敬兄长、顺从长官、忠于皇帝等。所以,《孝经》强调,以“孝”化民,便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18)胡平生译注:《孝经》,《孝治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页。基于此,儒家极为重视“孝”,认为“孝”是大经大法,是人人应遵守的天经地义的纲纪:“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19)胡平生译注:《孝经》,《三才章第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页。汉代以后,统治者大都提倡以“孝”治天下。
于是,如何践行“孝”成为一大问题。原则上说,践行“孝”的途径有多种。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途径就是“知医”。为此,医学界逐渐形成了“知医为孝”说。早在魏晋时期,名医皇甫谧就说过:“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20)皇甫谧:《甲乙经》,序。引自叶怡庭:《历代医学名著序集评释》,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213页。到了宋明时期,理学家更是力推“知医为孝”说。程颢说:“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21)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28页。程颐认为,人子事亲学医,“最是大事。……今人视父母疾,乃一任医者之手,岂不害事?必须识医药之道理,别病是如何,药当如何,故可任医者也。”(22)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5页。
“知医为孝”说的道理并不深奥,为此,该学说在古今儒士中影响很大。儒士们高度认同并自觉践行该学说。例如,被誉为金元医学四大家的张从正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23)张子和著,邓铁涛等整理:《儒门事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13页。明代儒医、“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创办者徐春甫说:“父母至亲者,有疾而委之他人,俾他人之无亲者,反操父母之生死,一有谬误,则终身不復。平日以仁推于人者,独不能以仁推于父母乎?”(24)徐春甫辑,崔中平等主校:《古今医统大全》(上册),《医儒一事》,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第209页。许多儒士也正是在“知医为孝”说的鼓舞下投身医学的。如明代名医王肯堂自述从医经过:“嘉靖丙寅,母病阽危,常润名医。延致殆遍,言人人殊,罕得要领,心甚陋之,于是锐志学医。”(25)王肯堂:《证治准绳》(上册),《自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年,第1页。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的吴瑭回忆说:“瑭十九岁时,父病年余,至于不起。瑭愧恨难名,哀痛欲绝。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遂购方书,伏读于苫块之余。”(26)吴瑭著,南京中医药大学温病教研室整理:《温病条辨》,《自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其实,在儒家看来,医不仅能为“孝”服务,也能进一步为“仁”服务。其一,医服务于“孝”,就是服务于“仁”的根本。这是因为“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27)《论语》,《学而》。。其二,医有助于实现“仁”的目标。“仁”即“爱人”,“仁”的目标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28)《孟子》,《尽心章句上》。。治病救人就是施仁爱于民,“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29)张仲景:《伤寒论·序》,参见叶怡庭:《历代医学名著序集评释》,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142页。,于是“仁”的目标得以实现。其三,医是“仁”的践行。医的职业道德要求,医生的天职是治病。医生要处处为病人着想,视人之疾,犹己一体,不计报酬,不辞劳苦,尽心治病;而且,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具有至上性和排他性。在医生面前,病人仅仅是病人,病人的一切社会属性全都遁去。不论贵贱、穷富、亲疏和长幼,均须一视同仁。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医为仁术”“医儒相通”。
既然儒学这么看重医,又这么需要医,而且西医这么有疗效、中西医在职业道德上又这么如出一辙,那么,西医东渐中,儒学和中医对于西医持欢迎态度,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双方均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地方性
从医学的角度说,西医和中医双方都既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也具有一定的地方性。
1.西医和中医都具有一定科学性。西医已然成为自然科学的分支之一,其科学性自不待言,关键是,中医是否具有科学性呢?西医东渐中,在中医的科学性问题上,中医界和思想文化界基于为中医辩护的立场,所提出的较为集中的一种意见是:中医正确与否不能以科学为标准,中医是与现代科学不同的“另一种科学”。例如,民国著名中医理论家恽铁樵认为:“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30)恽铁樵:《对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医界春秋》1933年,总第81期。理由是:“鄙意以为科学是进步的,昨日之是,今日已非,故不能谓现在之科学即是真是。”(31)恽铁樵:《对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医界春秋》1933年,总第81期。就是说,在恽氏看来,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不断纠错、不断自我扬弃的历史,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科学尽管面目不同,但同样都是科学,因而科学是多元的。既然如此,中医为什么不能称为科学呢?这种观点的要害是混淆了科学知识和非科学知识的界限。的确,科学是带有一定假说性质、具有一定社会建构性的。但是,科学追求真理的终极目标决定了,科学的发展既是不断纠错的历史,更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尽管追求绝对真理的过程是无止境的,但是,基于经验事实的理论抽象、具有可检验性而又和已有科学知识相一致的知识,是与错误知识或无法判定其真假的知识有天壤之别的。客观真理性和普遍性是科学知识的本质属性,是科学知识与一切非科学知识相区别的分水岭。因此,科学归根结缔是一元的,和科学平起平坐的所谓“第二种科学”是不存在的。
当然,认定中医不是“第二种科学”,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刀切断中医与科学的联系。
首先,从根本上说中医在认识论上是主张反映论的,它的理论深深扎根于人体器官、人体组织的形态和功能的客观基础之上。不少人认为,中医不讲解剖,中医理论根本没有生理解剖学的基础。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中医经典著作中并不乏解剖学的内容。例如《黄帝内经》早就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32)《黄帝内经·灵枢》,卷三,《经水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995页。说的是,人活着时,可从体表进行触摸和测量;人死后,可通过解剖进行观察和测量。不仅可测知内脏质地的软硬,还可以用尺子、竹签和器皿测量“腑”库的大小、容纳水谷的数量、脉管的长短、 血液的粘稠度和人死后血液的浓缩程度等。其解剖之细和范围之广,令人叹为观止。再如,《灵枢·肠胃》载:“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所记食道长度基本正确;《灵枢·肠胃》又载:小肠“长三丈二尺”、回肠“长二丈一尺”、广肠“长二尺八寸”,大肠与小肠总长为56.8尺。古今长度有别,但大小肠之间的比例与现代解剖学所得大小肠之间1∶37的比例大体一致。《灵枢·海论》说:“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腑)。”把脑髓的上界定在颅骨的最高点,下界定在风府穴的水平线,相当于枕骨大孔的水平线。这与现代解剖学的划分完全一致。《难经·四十二难》说:“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大肠重二斤十二两,长二丈一尺。广四寸,径一寸,当脐右回十六曲,盛谷一斗,水七升半”。《灵枢·平人绝谷篇》说:“小肠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受谷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或许上述解剖数据依然粗疏或欠精确,但中医重视解剖,努力将医学理论建立在人体生理解剖之上的旨意是一清二楚的。
其次,中医具有西医无可替代的许多合理性。其根本的合理性是,相对于西医“看人为各部机关所合成,故其治病几与修理机器相近”,而中医“即在其彻头彻尾为一生命观念,与西医恰好是两套。”(3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8页。具体说即是:其一,中医注重人体器官之间以及器官与人体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其二,中医注重人体及其器官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有机联系;其三,在中医医理的指导下,经过数千年无数医家的反复试验和大胆探索,中医积累了无数行之有效的药方;此外,还有魅力无穷的经络理论和针灸方法;等等。这些合理性不仅对于中医形成特色和提高疗效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整个现代医学的未来发展,可资借鉴和利用的潜力十分巨大。因此,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爱护中医、发展中医;同时应当坚信,凡是中医有合理性的地方,大都是合乎科学的地方,即便一时不能说明其科学原理,随着科学的发展,将来迟早会得到越来越充分的说明的。
应当指出,中医的科学化意味着中医逐步汇入世界科学主潮流,是中医对壮大世界科学作出了贡献,而不是中医变成西医。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于西方,在科学诞生初期,称之为“西方科学”理所当然。但是,随着现代科学事业的全球化和科学知识的去地方性,自然科学已逐步变为世界性的了。与此相关联,现代医学也已逐步具有普世性,而非单单是西方的了。所以,“西医”称谓不过约定俗成,仅具象征意义,中医的科学化绝不等于中医的西化,而是中医的现代化。
2.西医和中医都具有一定的地方性。在一定意义上,西医和中医既是科学和儒学的关系,也是科学医和民族医的关系。如果说,民族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地方性知识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西医和中医的关系则是普遍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关系。
中医的地方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医是儒学在医学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本身,就是中医地方性的突出表现。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医并非完全的地方性知识,它包含着大量的科学性成分,是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混合物。长期以来,中医主要以地方性知识的面目示人,而西医东渐以来,中医以各种方式摄入了大量科学知识,它所固有的科学成分得以极大地扩张,而且从此以后,其科学成分的扩张趋势从来没有停止过。
其实,西医也不是完全的普遍性知识。它也包含一定的地方性,而且,西医所包含的地方性知识成分之重,出乎人的意料之外。这是因为,西医所依托的科学知识也是有地方性的,其具体表现如下:首先从起源上看,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是西方希腊理性传统、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的兴起等众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曾一度作为西方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杰出代表。尽管近代科学革命完成后,科学走向世界,逐渐实现了普世化,但胶着于科学之中的西方文化遗迹,即西方文化所赋予科学的地方性遗迹也还是难以消弭殆尽的。其次,更重要的是从实践角度看,科学是一种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正是在这种实践活动中,科学知识的生成、传播、辩护和应用,统统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和它欲反映的事物的本来面目有某种偏离,从而使得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定的地方性。既然科学知识带具有一定的地方性,那么,以科学为基础的西医也必定具有一定的地方性。
总之,尽管西医和中医各自所包含科学成分的多寡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双方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混合物,二者性质相近又有一定的互补性,所以具有充分的亲和性,则是理所当然的了。
——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