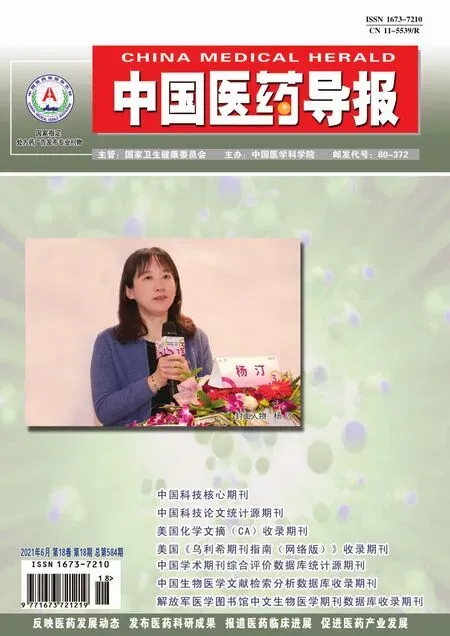《黄帝内经》治未病之“微病”探讨
康鹏飞 秦明臻 孟 佳 沈一凡 李 冰 秦建国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北京 100078;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
[关键字]微病;治未病;黄帝内经;气血
“治未病”这一概念来自于《黄帝内经》,是指采用预防或医治手段,防止疾病发生、发展的措施,包含未病先防、防微杜渐、防止传变、病后防复等几项[1-2]。但关于治未病的相关文献中,详于对预防的讨论,而对防微杜渐的相关概念及“微病”的论治和辨识少有单独论述,而随着治未病思想的流传和当今社会对亚健康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3-4],在治未病的基础上对轻浅疾病的防治应重点强调,所以本文试挖掘《黄帝内经素问校注》[5]、《灵枢经校注》[6]原文探究其根,以彰其义。
1 上工当治微病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见微得过,用之不殆。”[5]73对患者身体极小病变的观测,辨别病情轻重并掌握疾病整体趋势,以便对疾病从源头截流,这是医者处理疾病正确的观念。而且从《素问·灵兰秘典论》:“至道在微。”[5]95也可以看出诊治微病在疾病预防及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
但是微病症状表现隐蔽,经常难以直接诊断,易被忽略,如“若有若无”[6]14、“极微极精”[5]135等,从对“微”的描述可知,微病初生以无形之变为主,因其身未大伤,以及受邪不重,此时患者症状变化轻微,在外的症状或体征并不明显,或不自知。
所以对于这种状态疾病的辨别和传变趋势的把握,更需要医者拥有高超的诊治能力,因此不仅是预防,而能够及时识别并消灭疾病于萌芽状态者,应有上工之能,即《素问·八正神明论》中所说:“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5]264因此正需医师着眼于细微处,及早发现萌芽状态的疾病,不可养病。
所以,治未病时不仅要强调预防疾病,还要在病情轻浅、微萌阶段能够敏锐的发现疾病,积极消灭异样于初生之时。
2 微病含义和分类
2.1 微病含义
2.1.1 正瑕病浅 对于微病的描述,可以从《素问·调经论》篇中一窥端倪[7],此篇谈论脏腑精气和邪气盛衰的补泄治疗方法时,论及五脏病各有虚实,在五脏病外有“血气未并,五脏安定”[5]525这类表述,而对此类疾病的具体治疗,黄帝多次询问:“刺微奈何?”[5]526故遵经之意将此病命之为微病。
对此《类经》[8]400解释道:“并,偏聚也……今血气未并,邪犹不深,故五脏安定。”认为气血虽伤,但尚且通调,未与邪合,五脏本身未受侵扰,所以气血虽乱但未及五脏,仅是浅表受邪,故在脏腑虚实的论治之外有此论述。同理 《素问·逆调论》:“络脉之病人也微。”[5]322虽有异样但正亏不甚,发病仅在浅表位置,故病不重。
2.1.2 正风邪微 微病除了人体自身正气的表现,受邪亦轻。如“气相得则微”[5]593、“所胜则微”[5]103,反常气候、非时令之气侵袭人体,按照和时令的五行生克关系,时令胜邪气或彼此相生者,淫邪不重,所以感病轻浅为病微。或仅四时之气为殃,如“正邪之中人也,微”[6]14,“正风者,其中人也浅”[6]262等,《黄帝内经太素》[9]认为这是四时正常之气,乘人体之虚入内而成淫邪,故邪不胜,病亦微。
2.1.3 微病之外 在《黄帝内经》中将疾病的病因一般分为外感和内伤,如《素问·调经论》中论述风雨、寒暑等外感为阳,情志、饮食、起居等内伤为阴[5]532,阴阳所病均已归虚实,如外感邪气入内已深,“输于大经脉”[5]533者,气血与邪气并,则成已病;“血气以并,病行以成”[5]535,如有因情志过激、饮食失节等引起的内伤,虽然有些症状表现轻微,但实则内伤已成,故依《黄帝内经》不归微病。也可说明微病虽属外感,但病位极浅,未乱脏腑大经,尽在浅表,不归虚实。
所以说,外来之邪柔弱及人体浅表层的气血失和,二者共同作用下引起的病位浅且病势轻的一类疾病,即为微病。
2.2 微病分类和症状
人有经络筋骨、四肢百骸等,但均以五脏为核心,以经络联系全身,统一为五脏系统,邪气依附于不同位置而各有损伤也各依其名[10],即“气合而有形,得脏而有名”[5]524。
2.2.1 微病分类 对于微病的分类命名也是同理,和五脏相应,以神和心、气与肺、血及肝、肉同脾、骨和肾分别匹配,依据五脏特点,分别表现于皮毛、肌肉、筋脉、骨节等部位,诸微病的症状各有不同,表现为“洒淅起于毫毛”“皮肤微病”“经有留血”“肌肉蠕动”“骨节有动”等[5]525-530。
因此按照五脏的特点把微病分为五类,并依《黄帝内经》命名为“神之微”“白气微泄”“留血”“微风”“骨节动”[5]525-530。
2.2.2 微病症状表现 五种微病的具体表现如上文所述,但描述较为简略,因此参考其他篇章总结如下:
“神之微”应为患者体表感觉的异常为主。首先,原文描述为“洒淅起于毫毛,未入于经络也”,“洒淅”说明了邪气性质,“未入于经络”则限定了病位,即表皮的恶寒。其次,同段落前文论述心病时主要为神志变化,再参考《灵枢·五邪》:“邪在心……喜悲。”[6]102可知心“神”病以神智感觉异常为主,再结合“神之微”的微病命名进一步推测,“神之微”不仅有恶寒,应是表皮的感觉异常,具体症状表现需结合邪气性质及患者生理状态判断,如《灵枢·百病始生》“毛发立则淅然”[6]226,二者所论相应,恶寒之外,皮肤感觉异常互证,或《素问·痹论》“皮肤不营,故为不仁”[5]400,可能表现为皮肤毫毛的麻木不仁等感觉异常。
“白气微泄”应为患者皮肤腠理的开合失常。首先,结合“皮肤微病”的病理表现可知病位,《黄帝内经太素》认为“泄者,肺气泄也”[9],气持续地小幅度逸散,尤其治疗时说:“精气自伏,邪气散乱。”病理情况下精气不伏有张扬外散之势,所以“白气微泄”主要是指皮肤腠理失于收敛而正气外散,且随腠理开闭失司,邪气也可入内。其次,气泄也可见于《素问·举痛论》“炅则气泄”[5]358,大热则皮毛汗孔开,皮肤腠理“气泄”,汗出不止,所以“微泄”亦为汗出,再与《灵枢·五邪》:“邪在肺……汗出”[6]101相互参考可证,如此“白气微泄”为邪气在肺的初始状态,主要表现为皮肤的微汗出。
“留血”者,其意较明,络脉堵塞而未及经脉是其关键,而且与《灵枢·五邪》:“邪在肝……恶血在内。”[6]101比较可发现,“留血”或“恶血”随病轻重而有内外不同。其次,根据“视其血络”,可说明“留血”位置极其浅,且能够从外部直接诊察。因此全身浅表络脉气血因邪而瘀阻者,皆可归于“留血”。
“微风”“骨节动”较易理解,为邪居肌肉组织、骨节。总结《灵枢·五邪》中脾肾病的论述为“病肌肉痛”“病骨痛”[6]102,脾肾病的病情较重,病位入深,微病与此一脉相承,故可知邪轻者主要表现为肌肉蠕动痉急和骨节异动等。
2.3 微病转归
虽然微病各方面的变化较小,待真气恢复或可自愈,即《灵枢·刺节真邪论》所记载:“合而自去。”[6]262,但不辨而养病,也容易传变加重。
微病着身可层层转进,邪气从皮毛而至络,络聚入经,再入脏腑,最终隐忍以成痼疾,即《素问·缪刺论》[5]358所论,外感疾病虽由外邪入侵而成,若随其病位入深,病情亦逐步加重。
或由微邪局部聚集而为重,如《灵枢·玉版》所说:“夫痈疽之生……积微之所生也。”[6]133病患微小,但邪未能及时去除,积累为患,继而酿毒成脓,痈疽若成,则脓血内伤不断,治疗也会事倍功半。
所以在疾病完全成形才去采取措施的只能是“愚者”所为,而圣人大医在病邪积累之初,损伤形体之前,就会对其加以阻挠。
3 治疗原则
对于微病的调理,《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微者调之。”[5]779的原则,若邪气亢盛,病重疾危,须用重剂强夺胜利之机;而对于邪浅病微者,通过各种手段辅助调理气血,使经络通畅,阴阳自和,顺之驱逐微邪而愈,即能止于萌芽之间。
因此治疗微病,应以调畅气血、通络驱邪为原则。
4 微病治法
治疗微病各有其法,总结《素问·调经论》可知,治疗微病时使用了按摩、针刺放血、情志引导疗法[5]525-530,《灵枢·禁服》也有类似记载:“所谓经治者,饮药,亦用灸刺;脉急则引;脉大以弱,则欲安静。”[6]116根据前文论述可知,“经治”是指病初中经络,尚未波及脏腑,对不盛不虚状态下疾病的治疗,即对于微病的治疗,其中提到了药食、针灸、导引、情志调理等多种疗法。《金匮要略》[11]也可以辅证:“适中经络,未流传藏府,……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
所以治疗微病时,可以通过药食调理、情志调节、针刺艾灸、导引按摩等方法,用以疏通经络,理气驱邪,根据脏腑、病邪特点等,适当选取,配合使用。
4.1 药食调理
关于药食调治疾病,《素问·五常致大论》 中有记录:“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5]663使用毒性较大的药物攻伐主邪,治疗疾病主症,针对余邪兼症则选取不同级别的药各以治疗,针对微邪、余邪可用水谷果蔬等,养身而不为过,也能使正气充足。
4.1.1 食疗力薄 治疗微病须用无毒之药或用偏性较大的食物进行调治,谷肉果菜之类性平无过,可以养身健体,但食疗终究效力浅薄,全力亦难以驱邪。因此微病为患仍需治疗和养身相结合,使用药物或偏性较大的食物攻其微邪,之后用平性水谷强健身体,即《灵枢·大惑论》:“诛其小过,后调其气。”[6]290
4.1.2 药剂力偏 虽然说药物治病效果拔群,但过犹不及。微邪伤身,正亏不甚,不耐大毒,切不可强以大毒之药攻微病,否则药物强损病邪,也会使内部空虚,反而助病邪入内,甚则危害性命,出现《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论述的情况:“哀其太半而止,过者死。”[5]721
4.1.3 汤液治疗 在《素问·汤液醪醴论》篇中有论及“汤液醪醴”“必齐毒药攻其中”等[5]133,“齐”与毒药并称,其意与剂互通[12],同理文中汤液和醪醴并用,二者之意相似,其中醪醴二字《说文解字》[13]解释道“醪:汁滓酒也”“醴:酒一宿孰也”,所以说醪醴即浊酒,而且通过“以为备耳”[5]133,可以推测出汤液是一种经过加工后的液体,可长久储存,性弱于醪醴,《类经》认为汤液在此类似于清酒[8]317-318,326,故暂归为谷酒或清酒。
治疗微病时,既要避免矫枉过正又不至力有所不逮,因此各取长而折中,所以汤液谷酒为先,以熟谷之性补养五脏,借汤液气悍之性以驱邪,病可顺势而除。
关于清酒治疗微病,《素问·玉版论》有曰:“其色见浅者,汤液主治”[5]140对于色见浅者,《素问·汤液醪醴论》[5]133也有类似的表述,并以“中古”之人为例,与上古之人比较,其道德未全备,情志不坚则气血易被邪扰动,而形体气血略有不足,但与后世之人比较可知,病后受邪不重,可知中古之人正瑕邪浅,可归为微病,尊此以汤液谷酒疗微病。
《黄帝内经》认为以稻米为酒并使用稻杆加工者为佳,岐伯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5]132-133《黄帝内经集注》解释道:“盖谓中谷之液,可以灌养四脏故也。”[14]稻米为首选者,以取稻米之性连通脾胃,借中焦运化水谷补养五脏之意,以一谷应五脏,使五脏和调,五种微病皆可治疗。但醪醴汤液非享乐之用,仅在被邪气所伤后,以能及时得治,即“邪气时至,服之万全”[5]133。
总结可知,以药食防治微病,应针对微病邪微病浅这一特性,不可以强用猛药,过则伤身不已;谷肉果菜可扶养人体正气,但驱邪力犹不及,对此《黄帝内经》中以酒液醪醴为例,当以五谷所酿为先,俱占养护、驱邪之意,所以对微病的治疗当优先选取稻米所酿,但饮之有度,不可肆意。
4.2 情志调理
4.2.1 神志内收 通过情志调理也可消除微病,《素问·调经论》中在治疗白气微泄时,通过针刺辅以引导情志,使患者精神专注守一,以平稳气血,收敛神气,即“精气自伏,邪气散乱”[5]527,邪散则微病可祛。同样《灵枢·本藏》 也总结到:“志意和则精神专直……五脏不受邪矣。”[6]109精神专一,同时要避免情绪随外物波动,使情志安定精气内聚,从而强健五脏,使内不受侵犯。故神情专注,于内可护真气,于外可辅助驱邪气。
4.2.2 神志宁静 对于微病的治疗需要患者保持神情宁静。《灵枢·禁服》记载:“脉大以弱,则欲安静,用力无劳也。”[6]116其中脉象表现出大而弱者,《类经》[8]636认为是营气阴血不足的表现。所以在气血不足时更要保持神志安宁、情绪稳定。《黄帝内经注证发微》[15]也解释道:“虽有用力,不至大劳也。”精神宁静,即便是虚人费力劳作,也不至于积劳成患。对此《医宗金鉴》[16]指出“心静则藏神”,认为神情安定,是以情志安定统御气血,气血调和而平稳,神气内敛,脏有神养,纵使微病本有气血不足的表现,因正气内收,体内的精血充沛,也不致病重而为患作劳。
4.2.3 勇气内盛 还可激发其勇气,强其心志,达到驱散邪气的目的。《素问·经脉别论》说:“勇者气行则已。”[5]217志勇则心志坚定,可统御气血,使气血遵神识而畅,即便有气血紊乱病邪留止,正气也可驱逐邪气,即“正风者……不能胜真气,故自去”[6]262。而人之勇气可借酒增强,如《灵枢·论勇》说饮酒后:“当是之时,固比于勇士。”[6]186借用酒之悍气,增人勇志,使精神坚守而神有所增强,神旺以生气,则正气恢复强盛,又可顺酒势以驱邪。但如前文所述,酒应留作备用,不可贪多,免生弊端。
而且在现代临床研究中也有大量实验可以证明情志安定、心理健康可以对微病进行有效干预,对诸多疾病的治疗方案中已经有情志疗法的提出,如心血管疾病、妇科疾病、精神疾病等[17-19],并认为情志疗法对疾病的预防、防微杜渐、调养康复等各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充分体现了情志调理的作用。
因此保持精神专注于内可护养五脏;淡泊情志,不受外物的诱惑,内在气血不受扰动,可以阻止邪气入内,防病发展;勇气内盛,神识坚定,使邪无处遁形,则邪气驱散。
4.3 针刺调理
4.3.1 对症治疗 《黄帝内经》对微病针刺调理叙述较多,详细针刺方法《素问·调经论》[5]524-530有讨论:
治疗微病在心者,通过长时间的按摩,再加上入针刺浅,可通利气血,促使气血流通,气血和则神气可复;病属肺系者,需要长时间的按摩,再使用针刺轻度惊吓患者,从而使患者精气内聚,达到情志疗法的效果,邪气无法安于体内,再加上针刺按摩,则使邪气从皮肤腠理外泄而去。
肝系受到微邪侵袭时,治疗需要顺从肝藏血主疏泄的生理特点,刺瘀放血,疏浚经脉即可。
微病属脾系者,因脾主肉,而卫气流行于脉外肌肉间,所以针刺不可刺伤经络、血脉,仅落针于气分,刺激兴奋卫气即可刺激肌肉。
肾系受微邪,邪伤骨节局部,需针对邪气留居之所,局部治疗即可。
因此,按照五脏的特性,着眼于通畅气血,针对五种微病,心者使神气恢复,肺者使邪从腠理而散,肝者流通血脉,脾者促气旺卫外,肾者使骨节邪气不留。
4.3.2 针刺原穴 针刺还可以直接刺激原穴,强化五脏六腑之气,强化内在,《素问·刺法论》中对此有详尽的论述,总结可知脏腑神气失常则易受外邪侵袭,可先循脏腑之经络而刺其原穴[5]830-831,强化五脏六腑的气血,顾护脏腑,提示阻止疾病入内。
在临床上,常有微病针刺调理,如针灸医治中青年疲劳型患者,经过临床施治后,可以明显起到改善相关症状的作用[20],提示通过使用针刺疗法,可以疏通经脉、协调气血,从而消除微病,改善亚健康状态[21]。
综上得知,针刺治疗微病主要是通过针刺或按摩,刺激经络驱邪外出,调理原穴,和调气血,补足正气,驱邪和养正配合从而治疗微病。
4.4 按摩导引
4.4.1 按摩疗法 《黄帝内经》原文中没有单独说明调整微病的按摩方法,常合于其他疗法,在《素问·调经论》对心肺微邪的治疗里面,按摩和针刺并用,均以长时间的按摩为起始,充分表明了按摩对于微病治疗的意义。
顺通经络,如《素问·血气形志》所说:“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5]247通过推按经脉筋肉,有针对的疏通经络,并辅助以外用药酒,促进气血顺通,使瘀滞顺气血周流而消散。
通过局部按摩,温阳散瘀止痛。《素问·举痛论》云:“小络急引故痛,按之则血气散。”[5]358因寒凝而络脉不舒,血气凝聚不通,通过局部按摩之后血气瘀滞散开则痛止,按之则气血通达,经络气顺得以温养,能够补气于不足之处,也是行气活血的意思,仍以气血通畅为主。
所以通过循按经络或局部按摩,或以治肌肤不仁、疼痛,皆着眼于经脉[22],运活气血以散邪疗微病。
4.4.2 导引吐纳疗法 患者进行自我导引吐纳,可防治微病,参考《素问·移精变气论》可知古人在通过导引动作以增强阳气,驱除寒气,充盈气血,即“动作以避寒”[5]127。
关于吐纳呼吸,《素问·上古天真论》:“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5]12通过呼吸吐纳精气,主动控制体内气机的运行,使其升降出入循规守己;调整身体的姿势动作使肌肉统一,活筋骨利关节,使气运行通畅,配合二者情志调理,达到由内及外、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协调统一。
因此导引吐纳可使身心俱调,则气血流畅,用于预防辅助治疗微病。而后世对此颇有发挥,通过八段锦、五禽戏等[23-24]导引调整气血,预防疾病,如柯小剑等[25]对早期颈肩综合征患者进行研究,经过八段锦功法练习后,发现功法锻炼对颈肩综合征的防治具有积极作用。而张海波等[26]通过探究《诸病源候论》编创了一套锻炼功法,通过练习,使肺卫功能复健,用于治疗或预防感冒,在导引吐纳的练习后,情志安定,气血流畅,可以达到身心俱调,进而防治微病。
因此进行一些按摩或功法导引等,或让医师对患者进行调整操作,或通过患者自我导引呼吸,可以提升正气,运活气血,助邪外出,阻止微病的进展。
5 总结
因此,在治未病中防微杜渐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而且能对轻浅疾病的诊断治疗也是上工所必需。微病可以按照五脏生理特点或联系分为五类,只是症状的表现较轻,病位较浅,却可以发展为重病,所以不可不重视,更要及时调理,治疗时按照五脏的特性,调理皮毛、骨节、肌肤等,可通过药食调养、针灸、导引按摩、情志疗法等手段进行施治,适事为度,总之使经脉畅达,气血充盛,从而身强体健,远离疾病,得以保身长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