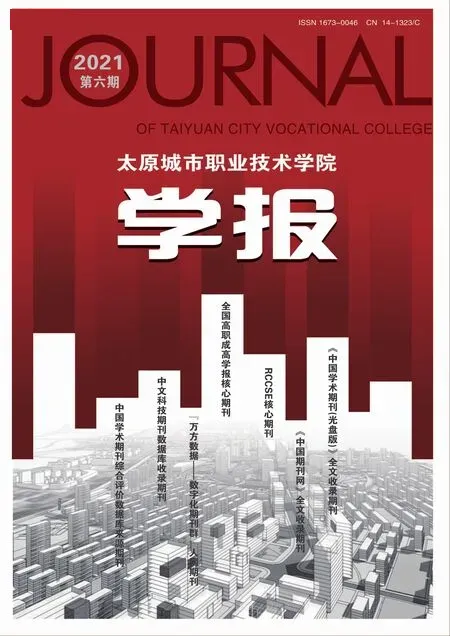“三区”计划在地方社会的实践、问题与反思
——以桂林L县为例
■罗既白
(桂林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社会工作是以科学方法助人的专业和职业,在参与社会治理中获得了长足发展,其中尤以民政领域社会工作发展最为显著。截至2018年底,各地在城乡社区、相关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机构共开发设置了38.3万个社工专业岗位,成立社会工作服务机构9793家,社会工作事业投入经费达61.12亿元,全国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专业资质人员共439266人[1]。国家在2012年出台了《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专项计划实施方案》(简称“三区”计划),预期在2012年至2020年,每年引导100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三区”工作或提供服务,每年支持“三区”培养50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完善社会工作制度,提高社会工作服务水平,逐步实现社会工作服务均等化。然而在经济落后、社会问题复杂、接纳程度不高的地方社会实施“三区”计划,面临着“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本土情境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张力”[2]的适应性问题。广西L县实施“三区”计划已有多年,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社会工作机构孵化、社会工作项目开发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及时总结实践经验,有助于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功能。
一、“三区”计划在地方社会的实践成效
L县位于广西东北部、桂林市西北部,属国定贫困县,下辖“六镇四乡”,共有119个行政村,1469个村民小组。现有人口18.6万人,农业人口15.03万人,少数民族人口12.76万人,苗、瑶、侗、壮、汉等民族聚居。在广西民政厅、L县民政局的支持下,“三区”计划于2013年正式启动。针对社会工作发育程度较低、项目人力资源及经费有限、地方社会对社会工作认知不足的现状,项目以点带面逐步推进:嵌入当地民政系统、社区,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开展服务,使特殊群体受益,进而提升当地对社会工作的认识,引导民政系统开发社会工作项目,孵化社会工作机构,鼓励民政系统、社区工作人员考取职业资质证书,向专业社工转变。
(一)基本服务架构形成
一是形成了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社工以社区高龄、病残、失独、“三无”、空巢等特殊老人为服务对象,搭建了社区助老服务平台,运用社区工作方法,开展了防走失手环进社区、发放紧急与常用电话卡、制作温馨提示牌等生活支持服务,建立了一支志愿服务队伍,开展社区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并对社区老人进行不定期走访;运用小组工作方法,对社区特殊老人开展健康教育、手工、绘画等形式各异的活动充实晚年生活;运用个案工作方法,开展经济帮扶、精神慰藉、关系调解等服务。二是形成了院舍社会工作服务。运用小组和个案工作方法,针对院舍老人开展精神慰藉、娱乐康复、健康养生系列服务,针对养老护理员开展了能力提升、职业减压服务。此外,根据老人和院方需求,帮助社会福利院建立老人健康档案,设计规章制度。三是形成了民政社会工作服务。社工搭建民政局联络站,面向低保群体开展低保核查,面向民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开展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培训等服务。“三区”计划在城北社区、社会福利院、县民政局搭建服务平台,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形成了社会工作基本服务架构。
(二)地方政府对社会工作接纳度的提升
地方政府对社会工作接纳度的提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县民政局开始了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服务的探索。在各县区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的背景下,社工积极与县民政局协调,查找政策依据,开展前期调研,完成实施方案,明确采购流程。在“三区”计划开展的第三年,县民政局安排专项资金,向社会工作机构采购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项目。运作成熟后,县民政局又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的调查工作纳入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范围,极大推动了该县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二是注重孵化本土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县民政局和社工的推动下,成功孵化了2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并开始承接当地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项目及社会救助服务项目。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社会工作机构均实现了从无到有,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大步迈进,印证了政府对社会工作接纳程度不断提升。
(三)社会工作职业意识得到唤醒
县民政系统、社区接触社工的时候,均把社工视为志愿者,或等同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等基层服务项目人员,对社工的角色、职业理念、工作内容、工作方法的认知存在偏差。随着社会工作方法、社会工作内容的不断呈现,《民政事业单位社会工作岗位设置》《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政策的出台,以及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培训的开展,使民政系统、社区工作人员加深了对社会工作职业的认识,逐渐意识到他们目前从事的工作是现实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产生了一定的职业认同。“三区”计划开展以来,L县通过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的人数不多,但每年社会福利院、婚姻登记处、乡镇民政办、社区等部门都能够保持一定比例的报名人员,一来是希望获得中级职称评聘,二来是希望与医生、会计、教师一样获得职业的认同。
二、“三区”计划在地方社会面临的问题
(一)社工团队稳定性不足
有学者认为,薪酬体系不完善、职业前景不明朗、社会评价不积极等是影响社工人才流失的主要因素[3]。从职业薪酬来看,相比广西民政厅购买的其他社会工作项目,“三区”计划的项目经费仅为15万元,但仍然须派遣4名社工到受援地开展工作。另外,每年的项目购买至下年的项目启动间隔了4个月的空档期,导致社工的基本收入不仅微薄,且无法保障。社工嵌入民政系统和社区中,与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相比,薪酬收入落差较大,不平衡心理加剧。从职业前景看,“三区”计划实施方案中社工的升学、就业等政策保障难以实现,如“社工报考社会工作硕士、博士同等情况优先录取”,由什么单位落实升学政策?再如“自愿留在当地工作的社工,由当地解决配偶和子女的安置入学问题”,留在当地什么单位工作,报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有无相应优惠政策,什么单位负责解决配偶和子女的安置入学问题?这些都没有明晰责任主体,具体政策含糊不清,导致社工的职业发展前景渺茫。从工作环境来看,L县地处山区,是国定贫困县,同时又是民族地区,相比城市地区,工作环境较为艰苦,需要克服语言不通、地理环境恶劣、气候潮湿、饮食不适等诸多难题,而良好的工作关系需要社工长期驻扎才能够实现,很多社工难以接受这样的工作环境。在社会评价方面,社工的身份不被理解,很多服务对象、工作伙伴、家庭成员都“好言相劝”,建议社工向体制内转行,在这样的评价环境下工作,影响了社工的专业情怀,打击了他们的职业自信。2013年项目启动至今,社工流失率居高不下,一些拥有了工作经验,与当地建立起良好工作关系的社工纷纷转行,影响了“三区”计划项目团队的稳定性。
(二)项目持续程度不够
社会工作服务的成效不像医疗服务,需要一定的过程才能够看到成效。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购买周期均为1年,期间需要开展项目评估,以及下一期服务项目采购。“三区”计划前一期服务结束到后一期服务的启动时间间隔较长,而承接“三区”计划的社会工作机构资金来源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自身无法垫付资本维系项目运作,在空档期只能采取关闭社会工作服务平台、中断社会工作服务、将社工撤离受援地等措施确保机构运营不受亏损。在此期间,社工无法观察到服务对象和当地环境的变化,无法直接开展服务,与工作伙伴、服务对象建立起来的良好工作关系冷却,对于项目成果的维系极为不利。此外,由于项目的经费已经完结,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只有安排“三区”计划的社工参与到其他地区的项目中去,一些社工觉得收入不稳定,也难以适应在不同地区项目之间的奔波,就此离开团队。
(三)与其他单位的合作有待加强
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经济相对落后,缺乏规模较大的企业单位,但是机关行政单位数量不少。与其他单位合作主要在两个方面存在不足:一是在工作层面的合作有待加强。社区是政策落实的最后环节,社工在社区开展工作时,发现其他单位的工作与社会工作服务内容有契合之处,如社区的宣传教育,但是社工并没有很好地将社会工作方法与其他单位的业务相结合,导致一些工作重复开展。在社会福利院服务点,社工过于注重开展微观层面的院舍服务,缺乏与企业单位互动,从宏观层面连接资源的能力有限。二是在开发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合作上有待加强。“三区”计划开展至今,仅在民政系统开发了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其他领域开发不够。据广西境内开发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可知,司法系统、妇联、团委、老龄委、残联等均有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先例,社工可依据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政策,密切与相关部门的联系,开发社区矫正、儿童保护、青少年成长、社区助老、残疾人融合等领域的服务项目,形成影响力,进而推动全县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
(四)易被行政工作干预
“三区”计划采用嵌入民政系统及社区的方式推进项目,一方面虽然较好解决了办公场地问题和社工身份“合法化”问题,但另一方面,社工被视为民政系统和社区中一员,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行政性工作。如第二次地名普查期间,社工被安排地名核校工作,工作内容多为文字校对、信息录入、地名释义等,与社会工作专业毫不相干,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影响了项目的推进。再如对低保家庭的入户调查中,社工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与服务对象建立起良好工作关系,而行政人员则认为了解概况即可,尽可能短时间内完成调查。另外,在项目的实施方案上,社会工作机构希望将几个服务点做成精品,而地方政府则希望工作全面铺开,形成面上的影响力。社会工作机构为建立与项目购买方长期合作的关系,势必会接受地方政府的规训,社会工作的服务理念、职业操守、工作方法、理论技巧可能会遭到削弱,社工有异化为行政工作人员的风险。
三、“三区”计划适应地方社会的反思
(一)社会工作机构与地方政府需互构信任关系
在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社会福利院、救助管理站、共青团、残联、妇联、社区居委会等虽无社会工作之名,却存在着社会工作之实,地方政府对外来的“三区”计划较为陌生,不知将其以何种形式嵌入到社会福利框架中。在观望状态下,地方政府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于行政工作的“助手”,“做一些锦上添花之事”,这显然不能完全体现社会工作的专业目标。社会工作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需要构建信任关系,达到地方政府能准确引导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社会工作机构又能为地方政府排忧解难的理想状态。第一是陌生阶段,这一阶段地方政府对社会工作的认识不明晰,运用行政手段过多干预社会工作项目,社工机械使用专业工作方法,身份角色混乱,工作开展较为困难。第二是磨合阶段,地方政府对社会工作的认识逐步加深,大体清楚社会工作能够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能够推行一定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孵化一定的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机构在地方实践上积攒了一定经验,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能够为地方政府建言献策。第三是互信阶段,地方政府清晰认识社会工作的整体架构,能够根据社会治理的需要精准设计长期稳定的社会工作项目。社会工作机构能够按照专业思路设计方案和开展工作,社会工作方法逐步本土化和专业化,社会工作职业能够得到利益相关方的认同。
(二)注重提炼社会工作地方实践经验
西方社会工作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发展而成,建立符合地方社会实际情况、能为大众接受、能切实发挥助人成效的本土化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中的应有之义。卫小将认为,社会工作的深度本土化要“跳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模式的束缚,摆脱追随欧美社会工作亦步亦趋的发展态势。但这并非完全摒弃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而是要将社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本土实践中来,真正立足于受众的实际需求”[4]。“三区”计划过分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夸大社会工作的功能,不但不能得到地方政府和服务对象的认可,反而束缚了社工的手脚,增加了开展工作的难度。社工应该摆脱框架的“束缚”,深度嵌入到服务点中,注重对服务对象的调查,了解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立足于服务点的现实情况,大胆实践和总结,形成扎根于地方实践的理论和经验,为社会工作深度本土化提供现实依据。
(三)加强政策的支持和引导
社会工作的发展很大程度需要政策的支持。政策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优化,一是优化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政策,在服务周期上,延长至2-3年,克服因项目持续性不足带来的人才流失、成果倒退、关系冷却、机构运营困境等问题。在项目规模上,项目购买经费向其他项目看齐,确保社工的人头费用在5万元/人的标准。在项目拓展上,可以整合团委、残联、妇联等部门的小规模经费开发多种子项目,以维系项目断档期间机构的正常运作,保证社工的收入,减少社工的跨区域流动。二是优化社会工作人才保障政策。在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即使存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其薪资收入、职业前景、社会地位均缺乏吸引力,存在招人难和留人难问题。“三区”计划人才保障政策可以借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等基层服务项目的做法,制定参与“三区”计划的毕业生参加当地公务员、事业单位考试的优惠政策,明确认证部门,限定最低服务年限,以此吸引广大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参与“三区”计划,不仅能为当地输送社会工作人才,还能破解“三区”计划招人难和留人难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