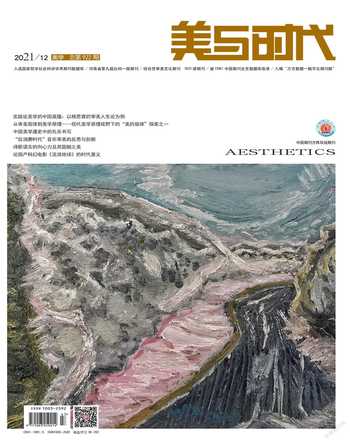基于庄子哲学审美体验思想的景观审美体验新释义
刘翠翠 李宇宏
摘 要:庄子哲学审美体验思想可以概括为以“目视、眼观、耳闻”观照世间万物的感官之审美体验、以“神遇、神行”感“天地之美”的心神之审美体验及以“共感、物化”体“逍遥之道”的生命之审美体验三层级递进式审美体验路径。结合庄子哲学审美体验思想体系,可以探讨景观之感官、心神及生命审美体验新释义。
关键词:庄子哲学;感官体验;心神体验;生命体验;景观审美体验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21YSKY08)研究成果。
古今中外不同的哲学家、美学家赋予了审美体验不同的内涵,如刘勰的“心與物的感应”、胡塞尔的“审美现象学”、康德的“瞬间精神活动”、马斯洛“高峰体验”、孔子“游于艺”、王阳明“格物致知”、王夫之的审美“现量”、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等。对庄子而言,“道”是人深层生命意识的体现,是人内在世界透升而上的宇宙精神,是人生所达到的最高心灵境界[1]18。庄子哲学审美体验思想是从外在感官的审美观照透升为内化心神的审美感悟,最终达到生命体道的审美境界,是超越时空、现实局限对审美意象的生命本真自由情感的深层体验。庄子哲学审美体验思想涵盖的三层级递进式审美体验方式对景观审美体验的当代释义具有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一、庄子哲学的审美体验思想
(一)感官的审美体验——以“目视、眼观、耳闻”观照世间万物
“目视、眼观、耳闻”是庄子哲学审美活动中观照万物的初级感官审美方式。外篇《山木》中的“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茂盛”“见美丑二妾”“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人间世》中的“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见大木焉,有异”;杂篇《则阳》中的“观于大山,木石同坛”;内篇《齐物论》中的“闻人籁,而未闻地籁,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皆是以“目视、眼观、耳闻”等初级感官体验的方式观照万物所形成的审美经验。庄子对大自然物象美景的细致描摹,诸如天地四海、日月山川、禽兽草木、河谷深潭、风雨雷霆、山林湖泽、激流瀑布等,亦借助人类感官以呈现自然壮阔的外在景象,内篇《逍遥游》开篇便展示出浩瀚辽阔的自然场景。此外,对外在世界形态、色彩、声音之美等感官审美体验,因人类感官视角的不同存在差异与变化。《秋水》中,庄子将大自然的壮美描摹得波澜壮阔,借河伯与海若(北海神)之问答,以“物观、俗观、差观、功观”等多种观摩视角道出了不同观照视域所形成的感官审美体验之间的差别与变幻。
庄子虽以为感官可目睹北冥之鲲,耳听人籁地籁之声,可感大自然鲲鹏之大、秋毫之末、学鸠朝菌之小,却从认识论角度认知到人类感官审美的局限性。杂篇《庚桑楚》中,庄子以南荣与庚桑子之对话举例“目之与形、耳之与形、心之与形”,来表述人类感官外形的审美满足易使人依赖于外物之形,以致“心为物役”[2]。因此,庄子哲学审美体验不可仅止于最初的五官感受,应突破感官思维、时空限制,由感官内化为心神感悟,以虚静澄明之心凝神观照,由外及内进入心神审美体验境界。
(二)心神的审美体验——以“神遇、神行”感“天地之美”
庄子哲学的心神审美体验是超越形体外感审美,内化透升为精神心灵体验的高级审美方式。庄子以“天地者,形之大者也”(《则阳》)描绘天地外物形之大始于感官知觉;又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秋水》)强调感知“天地至大之域”需要超越耳闻目视等感观局限,上升为由心体悟、由精神体验才可领略大美。内篇《天道》云:“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以形色名声为足得彼之情。”庄子以为外在形色名声虽可由感官所得,但却与万物的实情(本源)离之甚远。只有在精神上超越于物的形体感知,超越时空、地域、历史的界限,才能全神贯注于心神之融通,以“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知北游》),探究天地之本源,通达万物之原理。内篇《养生主》云:“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以“神遇、神行”的心神体验方式超越耳目感官,以己“心”己“神”感悟审美对象的“心、神”,使二者在心灵精神上沟通、契合,以达到对天地万物内在本质的把握[3],全凭心领神会由耳目之观达心灵精神之“徇耳目内通”(《人间世》)之“心斋境界”。
在庄子看来,以“神遇、神行”方式体验“天地之美”的本质源于顺应自然、遵循天性。外篇《刻意》云:“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外篇《天道》云:“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本,万物之本也。……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只有虚静恬淡、朴素无为的精神状态才可深刻体验到天地之美的本源,且这种精神体验本身已具备美之特征,远超于形体美之上[4]。外篇《在宥》云:“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顺任自然无为,万物便自生自化。忽略掉形体所限,摈弃感官所得,完整融入环境而至无我之心神境界。如此,对审美主体自身提出的方法论释义亦同于庄子《齐物论》中“吾丧我”所释,以忘物、忘名、忘情、忘己,把各种外在的成心、成见通过类似胡塞尔现象学“悬置”的方法达到物我两忘的“无”之境,从而容纳万物[5],方能“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天下》)。
(三)生命的审美体验——以“共感、物化”体“逍遥之道”
庄子哲学的生命审美体验是由外在的知觉审美透升为内化的心神体验后最终达到生命得道的神秘高峰体验方式。庄子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释义物我“共感”审美活动是在心神虚静的无为状态下产生内在生命的跃越,并借《齐物论》中“庄周梦胡蝶”寓言释义“物化”之“天地万物生态演化”内涵。“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周与胡蝶物我不分、主客为一、冥同物我的自由融通境界,是人内在生命与宇宙外在精神的亲和圆融,使生命本身产生永恒的超越与共生。于是可“旁日月,挟宇宙”(《齐物论》)、“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在宥》)、“登天游雾,挠挑无极”(《大宗师》)、“以登云天,立乎北极”,使“道”的生命世界本真之境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体验在“物化”的生命境界中得以呈现。《秋水》文末借庄、惠游于濠梁之上谈鱼之乐,以从容不迫、怡然自得的游鱼之乐为己之乐的物我“共感”体验,将人类情感“物化”在游鱼身上,以游鱼之生命存在为我之生命存在,自由徜徉于游鱼的精神感知世界,进入物我神合、物我共通的浑然境界,以体悟其“与物同游,不分彼此”生命得道之境。
由此可见,庄子哲学生命悟“道”的审美体验使审美主体运用一种独特的感知能力和运思方式,即直觉体悟的方法,参与整个人格力量,注入全部生命意识,不受理解力与想象力的局限与诱惑,无功利无目的,超越物象[1]19。心神体悟始于虚静澄觉,经过“神遇、神行”“共感、物化”等悟道历程,渐入创造性的空灵与跃越状态;“物化”入万物之中,“逍遥”于天地之间,“畅游”于自由辽阔的宇宙时空,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超然生命自由逍遥的境界。庄子哲学“逍遥之道”的审美“高峰体验”,以整体论的态度和思想方法,倾向终极整体生命之状态,倾向囊括宇宙全体,以“关怀”态度去感知生命本源,洞观自然本身的存在。有如《在宥》云:“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夜。”《齐物论》云:“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云:“乘天地之气,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应帝王》云:“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庄子追求的悠然自得、尽情遨游的逍遥状态,作为人类理想存在层级的构境高点,真正抵达道之理想生命审美体验的终点和目标。其超越时间束缚与生死界限,游乎太虚之境,体察宇宙之浩瀚,体悟生命之道的高远,解脱精神桎梏通往逍遥生存之境。
二、庄子哲学审美体验路径启示下景观审美体验新释义
(一)景观的感官审美体验释义
庄子哲学以“目视、眼观、耳闻”等方式观照世间万物的感官审美体验,与景观空间感官审美体验有着相似释义。景观空间场所作为宇宙自然环境中的客观物质存在,其审美体验是以景观审美及使用主体——人对景观物质空间的感官审美感知为起始。庄子外篇《达生》云:“凡有貌声色者,皆物也。”《知北游》云:“万物以形相生。”景观物质空间中具体存在物的形状、色彩、大小、材质、韵律、声音、气味、肌理等形貌声色特征,亦以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方式直接被人感知体验。不同地理地貌、功能属性、规模尺度、场景特征的景观物质空间产生的感官审美体验也存在差异与变化。乡野景观以农田林地、聚居村落、田园风光、清新空气、空旷原野、田间小径等乡野风景为审美体验特征;城市景观则以高楼林立、路网交错、城市公园、街区广场、游乐设施、園林绿化等城市风貌为审美感知对象。基于审美对象的景观功能性差异,景观审美体验具有特殊的功能性倾向及角色化定义,如校园景观审美体验、儿童娱乐景观审美体验、医养医疗景观审美体验、乡村郊野景观审美体验、公园城市景观审美体验等多种功能类型。同质于庄子对人类感官审美局限的认识论判断,景观物质空间的感官审美体验因其被动式审美接受方式存在局限性,对景观物之存在实体的直观体验过程往往极其短暂。景观物之感官审美体验功能性实现初始,无形之中已由感官内化为精神感悟,由外及内进入庄子所述的心神审美体验阶段。
(二)景观的心神审美体验释义
庄子哲学心神的审美体验赋予了景观审美体验新的启发性释义。景观精神审美感悟中的感官知觉已不仅仅是感官对景观之物的初始体验,而是融入自然观念、历史人文、宗教民俗、社会伦理、艺术情怀等非物质元素,将景观空间赋予性格特征和精神归属。人作为最直接的景观审美主体,凭借自身以往人生阅历、审美经验,超越时空、地域等外在因素限制,在静思冥想精神状态之中,忘却自我与外物的存在关系,唤起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留恋与驻足。景观作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感知纽带,使情感意象、历史情境在心神体验域中不断展现,实现景观主体的内心世界与景观外物“物我两忘”“物我同构”的共融合一。庄子内篇《人间世》中言:“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以凝寂清虚的心境应待宇宙万物,以心灵情感的联动感悟自然精神的存在,从而实现以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神遇、神行”心神体验方式,激发人的心灵直觉体验与景观空间的精神互动。诸如闻名遐迩的日本枯山水景观,作为禅宗景观以静观为功能特征,由细心耙制的白砂、造型常绿孤植、浓缩山石石组及荫蔽绿苔铺地等自然元素构成幽玄静谧素朴的景观意境,以写意象征手法再现海洋、山川、岛屿等自然生命之美。人在对枯山水景的凝神观照与冥思遐想中,通过对山、水、石、砂等自然之物的格物致知,实现内在精神与景观自然意境的“心物同一”,达到物我两忘“无”之境域。
(三)景观的生命审美体验释义
景观的生命审美体验与庄子哲学生命审美体验在审美生存境域中有着本源性契合。庄子生命逍遥之道与景观生态美学蕴含共通的生态美学观念,既追寻“大”之生命体无限力度之美,又描述小大不一之生命形态共同构成的生态秩序之美[6]。庄子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本为一体,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本质在于“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治”(《大宗师》),安时处顺[5]205,推崇自然万物平等的生存权利和生命本真,尊重自然万物及其自然演化方式。而如何善待天地自然万物,恰当处理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关系亦是景观之生命审美本源所在。工业文明的全球性发展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带来的人与自然万物二元对立、人与自然关系对象化及人与自然整体性生存危机。回归庄子审美哲学中人的逍遥生存本源状态,也是景观实现美好生活的诗意本真,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解决当下人类生存困境,满足人类与生俱来“归乡”情思,改变将世间万物对象化的审美生存境遇的根源。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意的栖居”的哲学诠释,即“近乎本源的栖居乃是原始的栖居,人类此在的诗意与自由共存在这片大地上,仰望贯通天地与大地之间,天空下、大地上的万物在其中作为不可知者得以庇护”[7],道出了对我们所生存环境超越物质与功能层面的的深层生命体验与感悟。以庄子哲学“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审美体验展现人与自然生命、天地之美相融合的心神状态,改变工业文明以来损害自然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进而从更高层次把握自然万物生态演化之美。在此基础上保护好山川河流、森林草原、湖泊沼泽等天然景观,注重景观场所历史延续、地域文化、自然肌理等第二自然的更新协调,充分发现和认识景观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审美生存本源特色,充分展现和感知景观空间场所精神。通过审美体验延续增强景观空间的生命与活力,将有限的现实生存世界转化为理想的审美生存境界,将生命审美体验延伸至浩瀚无穷的宇宙和似水流年的时间情愫之外,超拔于时间和万物的流变而居于永恒存在之中。
三、结语
庄子的哲学审美体验思想理论蕴涵超卓的美学精髓与生存智慧,其由“目视、眼观、耳闻”观照世间万物初层级的感官审美体验上升至以“神遇、神行”感“天地之美”中层级的心神审美体验,最终实现以“共感、物化”体“逍遥之道”生命审美体验的审美体验过程,与景观的感官、精神及生命审美体验过程存在相似性、启发性及本源性释义路径。庄子哲学审美体验超越耳目感官直觉与心神审美愉悦,体验虚静空明的深层生命境界,透升而上的宇宙意识与深层生命情怀,对景观生态可持续、诗意栖居美学理念及美好生活方式的构建具有启迪意义及哲学价值。
参考文献:
[1]朱良志.庄子的悟“道”与审美体验[J].齐鲁学刊,1988(4):18-23+78.
[2]涂波.《庄子》审美体验论新解[J].人文杂志,1999(6):96-100.
[3]吴建民.庄子的审美体验理论系统[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63-65.
[4]方勇,译注.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19.
[5]郭继民.庄子哲学的后现代解读[M].成都:巴蜀书社,2013:95.
[6]方勇.庄子生态思想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7.
[7]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谈诗意地栖居[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刘翠翠,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风景园林工程师。研究方向:美学,园林景观规划设计。
通讯作者:李宇宏,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公共环境行为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