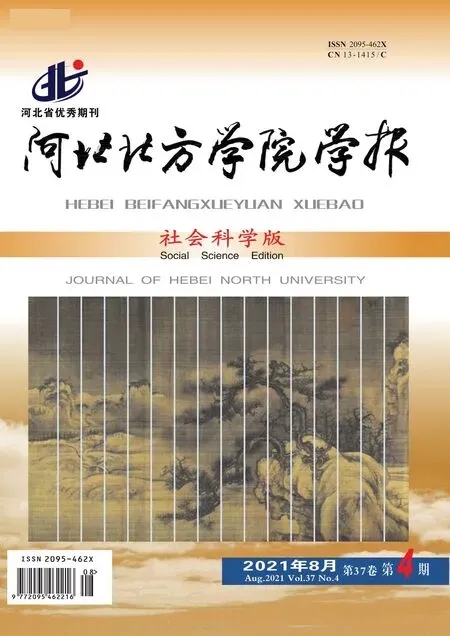“非理性”的迷狂:余华对酒神精神的张力书写
——以《现实一种》为例
董 亭 亭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酒神精神在尼采的哲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核心内涵是要求人以狂欢化的方式摆脱世俗伦理的枷锁,放纵本能欲望,进而肯定生命,回归永恒生命的怀抱。尼采对酒神精神的强调丰富了西方“非理性”哲学思想内涵。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马原、洪峰和余华等作家打破传统的常规叙事,转向注重文本的形式与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向传统宣战”的先锋姿态。余华在《现实一种》中赋予人物冲破传统伦理束缚的欲望冲动,体现出酒神精神的“非理性”特征。但在“非理性”的深层内涵上,余华的《现实一种》与酒神精神在欲望及生命本能方面又存在明显张力。通过文本细读,从余华所处文化语境和他独特的成长经历出发,厘清他对酒神精神张力书写的原因,可为现代人思考生命情感与欲望本能的关系带来重要的启悟。
一、颠覆伦理的“非理性”狂欢
近代西方推崇理性,强调知识,力求以科学的眼光审视世间万物。直到叔本华提出“唯意志论”的哲学思想,才扭转了理性居于社会中心的局面。叔本华将人对外部社会的关注转向人的内心世界,强调个人意志,对理性进行批判。尼采对叔本华的理性批判加以创造性继承,倡导打破传统秩序的酒神精神。他认为酒神代表的是打破秩序的癫狂及纵情生命的本能,具有“非理性”的本质特征。余华在《现实一种》中通过狂欢化的叙事方式,表现了伦理失序的文本内容。这与酒神精神突破传统以及张扬欲望本能的特征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契合。
(一)伦理失序的文本内容
余华在《现实一种》中秉承着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意识。他打破了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无节制地释放原欲,通过人物的非理性报复与残杀赤裸裸地展示了人性中最阴暗、最粗鄙且最远离理性的一面,将人的“良知”和“理性”虚无化。
《史记》载曰:“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1]传统的家庭秩序讲求母慈子孝、夫妇和谐以及兄弟友爱。余华却坚持颠覆常理,“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现实一种》……那时期作品体现我有关世界结构的重要标志,便是对常理的破坏。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却无法出现”[2]172-173。余华在《现实一种》中对传统仁爱家庭秩序进行了全面解构。首先,母不慈与子不孝成为家庭常态。祖母异常自私,只关心自己枯槁的身体,甚至看到孙儿被摔死都无动于衷。而儿子儿媳对母亲的痛苦呻吟也置之不理。其次,传统的夫妇和谐的理想状态不复存在。当山峰得知儿子意外去世后,将怒火发泄到妻子身上,“山峰屈起膝盖顶住她的腹部,让她贴到墙上,然后抓住她的头发,狠命地往墙上撞了三下”[3]12,体现了他对妻子的残暴无情。最后,兄弟间感情的凉薄随处可见。山岗和山峰两兄弟虽一起就餐,但并无过多交流,甚至在上班时“两兄弟走在一起,就跟不认识似的”[3]3。此外,仅4岁的皮皮在余华的笔下也失去了孩童的天真无邪。他“伸手去卡堂弟的喉管,当他松开时,那如愿以偿的哭声又响了起来。他就这样不断地去卡堂弟的喉管又不断地松开,他一次次地享受着那爆破式的哭声”[3]5。由此可见,家中长幼都无视道德伦理,在非理性精神的驱动下成为施暴者与受暴者。余华撕掉人性的伪善面纱,将人物的施暴本能无限延展,以冷漠的笔触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丑陋。
(二)狂欢化的叙事方式
尼采认为,酒神精神“是狂欢精神的化身,是一种超然理智之外的冲动力”[4]。余华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一改常规叙事方式,以“零度”的叙事视角审视现实,重构内心精神世界的真实。“当我不再相信有关现实生活的常识时,这种怀疑便导致我对另一部分现实的重视,从而直接诱发了有关混乱和暴力的极端化想法。”[2]68因此,他在《现实一种》中的情节设置和意象选择均呈现出与酒神精神相对应的暴力狂欢色彩。
情节设置上,余华打破了现实理性和常规逻辑,用荒诞化的写作手法表现被破坏的常理。首先,余华将祭祀酒神的全民狂欢引入到故事情节中,巧妙地将暴力场面移置于大庭广众之下,使全民有机会参与这场暴力的狂欢。场外所有的看客在山岗被执行枪决时发出了洪亮笑声,他们伴着笑声观看这场死亡的盛宴。其次,余华抛弃了理性逻辑,以文本的内在复仇逻辑推进故事发展。在正常情况下,大脑作为人的意识器官,一旦遭到损伤,必会影响逻辑思维。然而,余华却设置了被子弹打掉一半脑袋的山岗还可以意识清醒地跑回家并与妻子进行正常交流的荒诞情节。最后,余华笔下的解剖情节也可看作是医生施暴的狂欢。从医学伦理角度讲,解剖行为具备一定的合法性,但医生在荒诞化的肢解中成为了尸体的施暴者,他们“像提溜麻袋一样提着山岗进屋了”[3]48,“山岗的皮肤被她(女医生)像捡破烂似地一块块捡了起来”[3]50,这都与传统医生解剖尸体时所持的庄严肃穆态度形成了强烈反差。
意象选择上,余华在《现实一种》中破天荒地将带有酒神精神色彩的“血”意象与带有日神精神色彩的“阳光”意象有机融合于文本中。尼采认为,日神精神是“在无意志静观达到的对个体化世界的辩护”[5]62,而酒神精神则是“隐藏在个体化原理背后的全能意志,是在一切现象之彼岸的历万劫而长存的永恒生命”[5]63。生命在日神精神的观照下最终要回到酒神精神本身,即回归到无理性状态。因此,《现实一种》中的“阳光”与“血”之间的博弈,具有酒神精神色彩的“血”意象始终占上风。“阳光”不仅起到衬托作用,更加剧了“血”意象的视觉冲击力。如山峰妻子“发现血迹在阳光下显得特别鲜艳,而且仿佛还在流动”[3]27,山峰“看到两摊血相隔不远,都在阳光下闪闪烁烁”[3]36,明晃晃的光亮与鲜红的血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血”在“阳光”的照耀下更加触目惊心,由此衬托出人物无理性残杀的冷酷与绝情。
二、欲望与生命的张力书写
余华在《现实一种》中所呈现的伦理失序的文本内容和狂欢化的叙事方式与尼采的“非理性”酒神精神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契合。但两者对欲望与生命的态度又呈现出明显的区别,即尼采主张放纵人类的原始爱欲,推崇生命的强力意志,肯定人在战胜痛苦后所获得的一种生命的狂欢。而余华则挖掘出人性丑陋的一面,将人的欲望本能指向暴力,死亡成为了人的最终归宿。因此,他在《现实一种》中呈现的是亲人间的暴力残杀和死亡悲剧。
(一)原始爱欲与暴力残杀
酒神精神表现出对人原欲的一种追溯与推崇。尼采认为,“生命本身是非道德的,万物都属于永恒生成着的自然之‘全’,无善恶可言。基督教对生命作伦理评价,视生命本能为罪恶,其结果是造成普遍的罪恶感和自我压抑”[5]6。他摒弃了“善恶”的生命伦理道德观念,解放人的原始生命欲望,表现出对现实理性社会的反叛。人在酒神精神的感召下,受压抑的欲望有了宣泄的可能。如在希腊酒神祭典上,男女可以无视一切神律条约与日常禁忌,狂饮纵欲,载歌载舞。人的原始冲动和感性欲望在此过程中得以彻底解放,从而使人焕发出勃勃生机。因此,原始欲望的狂欢可看作是酒神精神肯定生命的外在表现形式。
余华意在反思人的暴力欲望在现代社会肆意放纵所酿成的悲剧后果。他重在表现人的暴力本能,“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2]167。因此,他在《现实一种》中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亲人间各种残杀的场面。4岁的皮皮像抱着“一团肉”一样抱着堂弟,因过于沉重便松开了手。余华用“肉”来形容活脱脱的生命,表现了皮皮麻木的精神状态。此外,成人之间的残杀更加血腥。山峰得知皮皮摔死儿子后,将哥哥山岗打得不成人形。哥哥山岗目睹皮皮被山峰一脚踢死后,将山峰绑在树上,使他在狂笑中结束生命。山峰妻子直至看到山岗强壮的身躯被全部肢解才罢休。骨肉在残杀中获得短暂的快感,愤怒的情绪得以宣泄,内心的暴力欲望也得以满足。
尼采从精神层面打消了男女之间的情爱欲望禁锢,使个体生命的情欲自由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对本能欲望的满足和救赎。然而,余华却将欲望本能指向了暴力与残杀。在《现实一种》中,亲人间的报复直接作用于身体,表现出了对生命的极大摧残。余华正是用暴力嘲弄文明和秩序的方式引导读者领悟生命的意义,进而启迪读者对人性的形而上的思考。
(二)生命狂欢与死亡悲剧
余华对死亡的书写与酒神精神呈现的强意志在生命的悲剧本质层面达成了共识,即两者都认为痛苦是人生常态,但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又不尽相同。尼采“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5]6。尼采虽意识到个体生命的死亡,但他从“永恒轮回”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体生命的死亡只是永恒生命的阶段性过程,且从整体人类发展历程看,生命仍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具有先锋意识的余华也表现出对生命的思考,但他放弃了生命是“永恒轮回”的观点,对死亡进行了大肆书写。
在《现实一种》中,余华将常态或非常态的死亡不动声色地表现出来。首先,老太太的死亡是一种生命的常态死亡。老太太在餐桌前向儿女倾诉听到自己“骨头正一根根断了”,但未有人理睬;一家人都熟知老太太咳嗽后要将痰吐到手心里,观察“痰里是否有血迹”的恶心行为;皮皮觉得“近来祖母打出来的嗝越来越臭了”,于是跑开了。老太太的枯槁身体触动着一家人的感官,但未有人提出医治的建议,最终任由这病躯悲哀死去,由此表现了一家人对待生命的冷漠以及老太太生命逐渐走向死亡的悲哀。其次,除老太太的常态死亡外,其他人的死亡均是一种非常态的死亡。新生儿被4岁的皮皮无意摔死,皮皮被叔叔山峰踢死,而山峰被哥哥山岗折磨致死,最终山岗又被残忍解剖。这一系列的非常态死亡表现出作者对强健生命的漠视,从而营造了强烈的暴力悲剧效果。余华笔下的人物都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亲人之间展开了无情的残杀。当然,这些人的生命在复仇后也走向了终结。
尼采在对待生命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他承认生命中苦痛的存在,但重在强调人要以超人意志战胜苦痛,从而享受生命带给人的欢乐。而余华却搁置了生命的美好,在《现实一种》中将亲人之间的暴力残杀呈现在读者面前,一个个强健的生命在非理性情绪的支配下走向了死亡。可见,余华对生命的书写与尼采的酒神精神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三、社会思潮与成长经历的影响
余华在《现实一种》中的暴力书写与酒神的“非理性”特征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契合,但在人物的欲望与生命表现上,他对酒神精神的书写又呈现出一定的张力。这既是因余华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重要影响,也与其自身独特的成长经历和孤僻性情有关。
(一)现代社会思潮的冲击
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在对“理性”的反叛中应运而生。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日益深入,“理性主义”显露出弊端。现代文明虽改善了人的生活,但却损害了人的创造性,使人成为理性和知识的奴隶,即“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6]。在此社会背景下,“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兴起。以叔本华为首的哲学家宣扬人的意识本能、意志、欲望与情感,认为非理性才是人的本质。处于这一思潮中的尼采主张颠覆传统,强调人的生命情感,肯定了宣扬人爱欲本能的酒神精神。这种“非理性”哲学思潮对后来的整个欧洲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在文学领域,象征派诗歌、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以及新小说等文学流派都带有“非理性”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解放了人的思想。1983年,在周扬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后,全中国掀起了对“人道主义”的广泛讨论。学术界凭借非理性主义高扬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主体性精神。这一时期的作家也发现人根本无法以理性来阐释神秘复杂的主观世界,致使传统的以理性为中心的价值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崩溃甚至瓦解。因此,西方现代主义的“非理性”哲学思想在中国有了生发的文化土壤。洪峰、残雪、苏童和余华等先锋作家颇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他们热衷于元叙事和叙事迷宫等叙事策略,追求荒诞和意识流的叙事手法。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精神内容层面实现了突破。如洪治纲所言,“真正的先锋,除了在形式与传统文学存在着各种差异之外,更重要的是作家在精神本源上对人类生活的历史、文化、生命及其自然有着更为深远的体认”[7]。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恪守传统伦理的“礼”与压抑欲望本能的“善”一直被视为正统思想,而破坏伦理传统与释放本能欲望的“恶”总是受到压制。然而,在“非理性”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先锋派作家对长期受压抑的本能欲望和复杂人性展开重点叙事。
在众多先锋派作家中,余华对传统伦理的反叛与人的暴力本能欲望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坦言,“我感到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世界并非总在常理推断之中”[8]。他在《现实一种》中打破了传统母慈子孝、夫妻和谐以及兄弟友爱的家庭秩序,以狂欢化的形式表现了亲情的冷漠与人性的自私。此外,余华将由暴力残杀所酿成的悲剧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使人重新思索生命的意义。因此,余华在社会文化语境及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解构中国传统文学“礼”与“善”的精神内涵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主张颠覆传统的酒神精神。
(二)成长经历与孤僻性情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余华接受了西方“非理性”的哲学思想,并结合本土文化语境对传统文学中的性善论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反叛,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酒神精神相契合。但他在欲望本能与生命态度上同酒神精神存在明显的不同,这与其独特的成长经历和孤僻悲观的性格有关。
人的成长经历会对性格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余华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父亲是外科医生,母亲是护士,由于医院事务繁多,一家人聚少离多。余华虽有哥哥陪伴,但哥哥在余华的记忆中并不美好:“两个人打架,一打架我就吃亏,吃了亏就哭,我长时间地哭,等着我父母回来,让他们惩罚我哥哥。”[2]59可见,在童年时期,家人未能给余华无微不至的呵护和爱,使他缺失对温馨家庭的亲身感受。在动荡的“文革”中,余华目睹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批判文章以及自己尊敬的师长被红卫兵惨无人道地当街批斗,耳边屡屡听闻知识分子不堪人格受侮辱上吊自杀的消息,这一充满暴力与死亡的记忆给余华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与迷惘,身边人道德的堕落和人性的沦丧使他对非理性的人性之恶的体察尤为深刻。之后,余华在卫生院5年的工作经历更加深了他对生命与死亡的感知。孤独寂寞的童年生活、血腥暴力的“文革”记忆以及苦闷无趣的从医经历使余华形成了孤僻悲观的性格,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一方面,在人的本能欲望选择上,余华成长在孤独冷清的家庭氛围中,缺失对“爱”的情感体验,加上“文革”的所见所感,使他对人的暴力欲望产生疯狂的迷恋。因此,他在《现实一种》中着重表现“血”意象,并呈现了暴力美学的意象群,如“毒打”“狠揍”“舔血”“飞起一脚”“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狗舔山峰的脚”以及“分尸”等血腥意象在文中随处可见。另一方面,余华在成长经历中所形成的悲观性格决定了他无法调动起如酒神精神般的高昂生命基调。他在孤独的童年经历中认识到生命的荒诞无常,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对生命的失望及对死亡的热忱。如在《现实一种》中他着重强调了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被皮皮摔死、皮皮被叔叔山峰一脚踢死、山峰被哥哥山岗折磨致死以及山岗被医生残忍解剖的血腥情节。
西方现代主义社会思潮对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马原、洪峰和余华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家开始重视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形式的学习,并在作品中以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展现出新奇的艺术风格。余华在创作中还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非理性”特征,对酒神精神进行了张力书写。因此,以“非理性”特征为出发点,探讨余华在《现实一种》对尼采酒神精神在颠覆传统伦理层面的契合以及在表现生命欲望时呈现的张力特征,启发读者对先锋作品进行创造性解读,进而能够为现代人思考生命情感与欲望本能之间的关系带来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