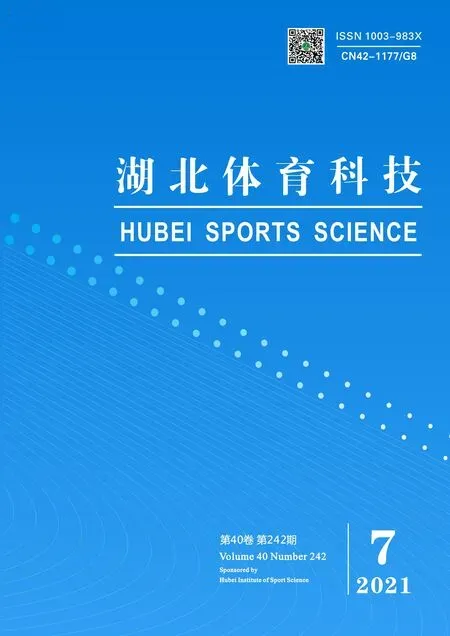土家族仪式体育“撒叶儿嗬”的人类学阐释
——基于鄂西长阳县的田野个案
刘 广
(中南民族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鄂西南山区,是集老、少、山、穷、库一体的特殊县份。世居于此的土家族在历史的演进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土家族文化,丧葬仪式是土家民族文化的表达形式,对土家人民具有独特的文化和社会意义。撒叶儿嗬是长阳土家族人民丧葬仪式中的祭祀歌舞,是丧葬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撒叶儿嗬作为民间丧葬仪式的祭祀歌舞,是土家族颇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1]。从隋唐时期开始,便有“父母初丧,击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的文化传统。撒叶儿嗬主要分布于清江流域,在长阳县、五峰县和巴东县等地广为流传,其中以长阳县资丘镇的撒叶儿嗬为主要代表。本研究选取长阳县作为田野调查点具有个案的典型意义。
“北跳丧,南摆手”就是对土家族丧葬祭祀较为常用的表述,北跳丧是指清江流域土家族的“撒叶儿嗬”,南摆手是指酉水流域土家族的摆手祭祀仪式。同为土家族,在丧葬仪式上的差异显示出同一民族不同族群的标识,也展现出丧葬和祭祀等仪式对土家人民的重要意义。正如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所言,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2]。撒叶儿嗬成为土家丧葬的仪式符号,牵动着土家人民生与死的集体记忆,象征着土家族的生死观、孝义观和民族价值观,并随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着自我重构与现代建构,被赋予时代性色彩的符号象征意义。
对于世界上多数族群和集体而言,仪式活动有着特定的符号和象征的意义与价值。正如彭兆荣提出,仪式“上至宇宙观的认知,下至具体的实践行为”[3]。仪式是人的社会活动,通常以身体实践的操演,传递、表达出特定的意义和象征。撒叶儿嗬是长阳地区土家族的丧葬仪式,同时也是独具特色的体育活动。正如刘俊梅等提出:“跳丧”(指跳撒叶儿嗬)是土家族的丧仪民俗,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体育[4]。2006年撒叶儿嗬以民族舞蹈条目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至今,跳撒叶儿嗬也已逐渐脱离丧葬仪式的传统,进行自身的现代化转型,成为全民健身的依托形式,成为长阳地区“广场舞”的理想运动项目。可以认为,仪式体育撒叶儿嗬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进行着自身价值的重构和意义的延伸,已经超脱于作为丧葬仪式的社会认知,并日显多元化。
1 历史的记忆:土家族撒叶儿嗬的溯源与承载寄托
1.1 结构性失忆:撒叶儿嗬的溯源
结构性失忆,简言之是族群记忆理性的传承选择,对族群的历史选择性记忆,共同忘却历史中的某些事项。对撒叶儿嗬起源的族群记忆历经结构性失忆,对于其来源及历史的发展没有普遍认同的观点。当前,学界一般认为土家族撒叶儿嗬主要有两种起源的观点,分别是起源于古代巴人的战舞和传统的祭祀仪式。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倒戈,故世称之,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在这段文献记录中可以看出,文献中记载巴人战事前要起歌和舞,在战争结束之后也会歌舞祭奠亡灵,文献所记载的“歌舞”就是早期的撒叶儿嗬。据当地文化保护部门同志ZYH谈道:
我们研究的历史渊源就是土家族,撒叶儿嗬最早的巴人舞王发阵的时候……巴人配合武王去讨伐纣王的时候,军前舞就是男人出去打仗,就是跳撒叶儿嗬战死之后,为了纪念亡人跳的一种舞蹈。
与此同时,据《云南志》记载:“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初丧,鼙鼓以为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盘瓠白虎之勇也”[5]。这段文献大概是说古代巴人祭祖的时,通过击鼓纪念先祖,同时伴之以歌,合众而跳。从文献上看这段描述与现代的撒叶儿嗬的表达形式比较接近,尤其是“鼓、歌、跳”等关键性表述与当代撒叶儿嗬如出一辙,也可以认为是现代意义的撒叶儿嗬。然而,撒叶儿嗬究竟来源于何种典故,现在已经无从可考,只能从古代文献的一角寻求历史所封存的描述。但从文献记录的历史来看,撒叶儿嗬传承的时间已有千年之久。据清朝《巴东县志》载:“旧俗,殁之日,其家置酒食,邀亲友,鸣金伐鼓,歌舞达旦,或一夕或三五夕”,同治《长阳县志》记载:“临葬夜,诸客群挤丧次,擂大鼓唱曲,或一唱众和,或问答古今,皆稗官演义语,谓之‘打丧鼓’,唱‘丧歌’”。从这段文献年代可以看出,撒叶儿嗬作为丧葬仪式在长阳和巴东等地经久不息未曾间断。在这长时间持续性的文化浸染中,撒叶儿嗬对地方族群产生特有的小传统意蕴,并通过族群集体记忆与结构性失忆曲折传递至今。
1.2 集体记忆:撒叶儿嗬的承载寄托
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组织或群体(如家庭、家族、国家、民族,或一个公司、机关)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并指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6]集体记忆依托于文化的媒介而存在,如实质文物、雕塑、传说、仪式或集体行为,依此得以存留、寄托、强化和再生产。承载着集体记忆的事项通常是与当地族群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所或器物、仪式或集体行为。撒叶儿嗬在历史的代际传承中,接续承载着集体记忆的土家族群体情感和价值观。在田野调查中,笔者了解到,跳撒叶儿嗬对当地的群众而言具有特殊的社会作用。据撒叶儿嗬省级非遗传承人TXL谈道:
这个(撒叶儿嗬)也是我们长阳土家族的传统嘛,大家也都差不多会。跳撒叶儿嗬嘛,我是从小就学着跳,也喜欢去跳,小时候人家家里老人哒(指去世),我们就喜欢去凑这个热闹,慢慢地次数多了也就会跳了,那个时候跳撒叶儿嗬都是在死了人以后办丧事跳的。我们有传统就是说“生者不记死者仇”,就不管你之前的关系怎么样……或是说两家有冲突嘛,在你人去世了之后,大家还是到你灵堂前热闹一下嘛,这个时候两家人的关系也就自然好了嘛。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存在的意义就是他的功能。杨庆堃从功能主义出发,认为丧葬仪式强化家族血缘联系,突出亡者对后人的重要性,有助于维持群体凝聚力、宗族传统信仰、促进家族团结等情感[7]。丧葬仪式中撒叶儿嗬的存在,也有着其特殊的功能与作用。分析上述信息报道人所述,可以认为,集体的概念在当地土家族社会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族群的概念通过参加到丧葬仪式当中跳撒叶儿嗬得以强化,撒叶儿嗬同时也是个人与社会集体连接的纽带。通过跳撒叶儿嗬形成的集体记忆,促使族群意识的形成和强化,演化成为民族(族群)的集体认同。此外,在这样特殊的文化语境下,跳撒叶儿嗬还具有缓和社会矛盾和化解民间纠纷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儒家的大传统语境中人际关系整体表现为以和为贵,在长阳土家族地区这个小传统语境中是“生者不记死者仇”,社会的和谐文化的赓续在此协调统一。撒叶儿嗬承载的不仅仅是生与死的丧葬观念,还有民族与社会情感和价值观,以及包含文化符号系列的表达。
2 复合的价值:撒叶儿嗬的符号象征
仪式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一直是人类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它不仅体现了族群的信仰、价值观、历史、文化等,而且还以有形的仪式、仪式行为、仪式器具等实践着自己的信仰、价值观,谱写着族群的历史和文化[8]。作为丧葬仪式组成部分的撒叶儿嗬,最为突出且直观的符号象征就是土家族人民生死情感和精神。据调研,当地传统的观念认为,跳撒叶儿嗬只能是在丧葬仪式中进行,在长阳资丘的一些村寨中,人们闻讯有老人去世,便自发组织前往吊唁,有俗语称“人死众家丧,一打丧鼓二帮忙”,当天吃过晚饭之后,鼓师敲响鼓点,同时歌师开唱:“打起丧鼓唱起歌,大伙儿来跳撒叶儿嗬”,随即在场的成年男性应道“撒叶儿嗬也”,便开始跳起撒叶儿嗬。撒叶儿嗬从文化的整体上看,集合于唱功、鼓点、动作,展现出歌、乐、舞三者和谐一体,通过文化的整体表达,展现出撒叶儿嗬的特殊符号象征。
撒叶儿嗬是关乎生命的游戏,是在庄重肃穆的丧葬仪式现场进行的轻快且狂欢的集体情感表达的游戏,这种游戏是身体实践与民间仪式的双重组成。正如学者王光进指出,游戏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其中不但残存有人类历史的初始景象,而且也绵延着人类对教育、伦理、礼仪、社会规则、美学和哲学等诸多方面的实践和思考[9]。撒叶儿嗬作为土家族的传统丧葬仪式,大开大合的动作结构表达和传递着土家族人对于生命与亡灵的身体语言,通过身体的操演释放精神的内在。正是因为撒叶儿嗬具有游戏性的轻快和狂欢色彩,成为热场的重要方式,土家人在此刻就是有热闹和狂欢。正如撒叶儿嗬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家属ZAG所言,
我从小时候开始记事就看他们跳这个撒野儿嗬,看到大人们跳这个,感觉蛮过瘾……一般的像这个谁家(老人)了,这个鼓一敲,会跳的,不会跳的,都涌来了,会跳的就上堂跳了,挺热闹的,他都想去搞一搞嘛,现在小孩子搞不好就在里面混一下嘛……现在就是像居委会啊,下班的晚上都没事的时候,都去那个广场,就去搞一下,很多人都在那里跳,很多人觉得蛮过瘾,就来学一下。既锻炼身体,又觉得这个东西蛮过瘾。
瞿明安在《象征人类学理论》中指出,象征是人类文化的一种信息传递方式,他依据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和约定俗成的习惯,以某些客观存在或想象中的外在事物以及其他可感知到的东西,来反映特定社会人们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抽象概念及各种社会文化现象[10]。笔者认为,撒叶儿嗬的符号意义在社会层面表现为孝子身份的建构与社会阶层的隐喻。在孝子身份的建构层面,笔者在长阳当地的调研中得知,超过60岁的老人正常去世是走“顺头路”,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丧事应该当作喜事办,称之为“白喜事”。土家族的传统“父母亡,鼓报丧,众必跳,歌必狂”,老人的孩子为老人家风光地办一场丧葬仪式,跳一场热闹的撒叶儿嗬。
据撒叶儿嗬省级非遗传承人LXC介绍道:你比如说,哪家老人哒,我们跳撒叶儿嗬和吹打乐的一起去撒,我们一去就是吹的,唱的,跳的十几个人,晚上其他人都回去了,就只有我们这十几个人,(从晚上)一直给他弄到天亮。这样的话,(孝家)既使自己做到了孝道,又使自己有了面子,这是我们的风俗习惯必须得尽孝。
撒叶儿嗬在丧葬仪式中越是热闹,越是说明后人的孝道做得好,此社会传统极为受土家人民推崇,这符合土家族族群对孝子的身份认知。在中国儒家的孝文化大传统之下,土家人民也渴望拥有孝子的身份建构,在这样积极的社会内生驱动之下,同时促进了撒叶儿嗬的发展和普及。在社会阶层的隐喻层面,当前,长阳的撒叶儿嗬成立相关的文化艺术团,专门接取丧葬的服务事宜,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
据撒叶儿嗬省级非遗传承人LXC谈道:严格来说,过去的撒叶儿嗬……俗话说,白事众家丧,大家来帮忙。就是说,家里老了人,周围的人都来帮忙,就以撒叶儿嗬的形式陪老人走完最后一程,原来是一跳一通夜,就吃点饭,抽点烟,陪着老人过完最后一夜之后,明天把他送上山,就以这样的形式持续了二十多年。到现在,没有什么别的事儿,亲戚朋友也不会聚在一起,所以最近几年(跳撒叶儿嗬)才会给一点报酬,因为熬夜通宵也比较累,就给点报酬相对补偿一下。
一场浩大的丧葬仪式撒叶儿嗬,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员,其中会产生不菲的花费。据当地政府部门同志TZD提到,在我们调研的前几天,当地的社会精英举行了一个较为盛大的葬礼,到场和跳撒叶儿嗬的人数过百人,堪称规模盛大。据称丧家仅邀请跳撒叶儿嗬的艺术团的费用就过万元。一场体面的丧葬仪式所花费的财富较高,需要有一定社会资本的家庭才能承担举行体面热闹的丧葬仪式的高昂的消费,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撒叶儿嗬的举行规模就代表着丧家的社会财富和地位,成为社会阶层的隐喻。
土家族丧葬仪式撒叶儿嗬有多元复合的符号象征,上述议论重点是撒叶儿嗬的文化符号性上观,其文化符号性作的复合价值进行较为深入地阐述。此外,还有文化事项性上观,困于文章篇幅的原因,没有进行细致的描述和分析,笔者对其具体的文化事项性不在此突出论述,有待后继的追踪研究与思考。
3 破后而立:撒叶儿嗬的文化变迁
3.1 从传统到破灭:撒叶儿嗬的断代发展
长阳地区土家族丧葬仪式跳撒叶儿嗬的历史悠久,跳撒叶儿嗬也是土家传统的民俗传统活动。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时代中,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丧葬仪式中跳撒叶儿嗬(跳丧)是“文化的陋习”而强制禁止举办。
据吹打乐省级非遗传承人BJQ谈道:他这个,原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年纪的六十岁以上的,就有个过程(经历),他是那个时候的“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就不允许,这个有破四旧啊都不许搞,那个时候我们读小学,在学校里不允许跳撒叶儿嗬这些东西,但是基本上那个时候,几乎就是要失传的感觉嗒。
政权强制进入文化领域,社会形成普遍的约制,文化的变迁加速进行,文化的流失使其传统的符号象征解构,产生系列由文化产生的社会问题,社会亟待寻求新的象征寄托填补文化的失位。在政权的强势干预中,撒叶儿嗬虽然被“消灭”,但其身体的集体记忆仍然存活于土家人的生产生活当中,待到时机成熟,身体的集体记忆迅速恢复,并在族群中出现“抢救性”重构社会与文化,重拾符号和象征意义。
3.2 不破不立:撒叶儿嗬的文化变迁
在长阳县土家族的区域性社会中,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加速,在其文化层面将产生因变,表现为土家族民族文化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土家族文化符号的撒叶儿嗬也随之流变,基本表现为,撒叶儿嗬超越其传统的丧葬仪式,在其辐射对象和操演场域等方面延伸开来。
3.2.1 撒叶儿嗬辐射对象的变迁
传统观念认为跳撒叶儿嗬不允许女人和小孩跳,就连男性要跳撒叶儿嗬都必须等到结婚且有自己的子嗣之后才能跳。对此有解释认为,传统的撒叶儿嗬被认为是军前舞,如前所述《华阳国志·巴志》中的文献记载,撒叶儿嗬具有纪念战死亡灵的特殊意义。同时,由于参加战争的士兵都是男性,跳撒叶儿嗬具有歌颂男性英勇无畏的意义,如果女性和小孩也来跳撒叶儿嗬,那就意味着男性战亡,只由得女人和小孩参加战争。这个解释认为,之所以女性和小孩不能跳撒叶儿嗬是为了保护他们。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通信的普及,撒叶儿嗬的辐射对象发生较大的变化。
据吹打乐省级非遗传承人BJQ谈道:现在来说,现在发展了,从小孩到老人,男的女的都跳。但是以前女的不能打丧鼓,不能跳撒叶儿嗬,这个原来是说的“女人跳丧,家破人亡”。过去说滴哈,但是现在已经基本上开放了,认为女同志也可以跳,普遍的也有蛮多女同志也会跳。这个在(葬礼中)就是基本上,蛮多地方你不出钱,就是和原来不需要出钱也可以跳丧到大半夜,也可以。
撒叶儿嗬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家属ZAG也有谈道:就我们过去我们婆婆讲啊,就是这个女的不跳丧,男的不送竹篱(生孩子),就是说别人生小孩,都是女的去,男的就一边儿去,额,就有这种说法,我们只是听说,把这个传递下去,一直有这个说法。
撒叶儿嗬省级非遗传承人LXC谈道:其实现在跳撒叶儿嗬的大部分群体都是女同志,因为女同志到五六十岁都在带孙子孙女,在城里陪着孙子孙女上学,闲着没有事儿就都想学。现在农村里也差不多是这个状况,因为现在吃穿都不愁了,所以说在家做点儿杂事儿带下孙子孙女,就会没有什么事儿做,找点事情消磨时间。
丧葬仪式撒叶儿嗬实现从“女人跳丧,家破人亡”的辐射对象限制到全面放开,是传统文化的重大转型。但是从撒叶儿嗬的辐射对象的变迁中也带来一系列的论战,主要焦点在于传统的惯习与当代的变迁之间的矛盾,最终问题是传统文化的限制是否应该放开,政府的态度和应对之策等问题。
3.2.2 撒叶儿嗬操演场域的延伸
康纳顿指出,操演是人们对一些固定言说、姿势、手势和动作的掌握,它可以帮助人们简化人际沟通的繁琐程序,维持仪式中的秩序[11]。长阳土家族丧葬仪式中的操演有着固定的场域,作为丧葬仪式的撒叶儿嗬,从古至今其操演场域都是在灵堂之中。撒叶儿嗬有一个禁忌,小孩或青年人因意外而身亡均不会举行该仪式,因为夭折的小孩被土家人称为“化孙子”,认为是不吉利的,因此不跳丧、不闹夜。除开丧葬仪式现场,其余任何地方都不能进行撒叶儿嗬以及施展相关的身体动作、唱词、鼓点等。撒叶儿嗬在承载多年关乎“死亡”的集体记忆之后记忆形成定势,传统的观念就会认为,撒叶儿嗬就象征着死亡,死亡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甚至可以说,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死亡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撒叶儿嗬的操演场域有着严苛的要求和束缚。
据信息报道人BJQ谈道:他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传统),就是死了人之后,丧葬才能跳,这是一种特殊环境。他是我们这个现在,因为(我)是这个传承的,然后怕这个(撒叶儿嗬失传)。现在这个年纪轻(的人)就讲,这个年轻的没得事都不得学。在前些年代从小就学的,但是呢,在人家屋跟前都不能喊丧鼓调子,那就是兴旧的(传统),他就是(具有)特定的(含义),只能是死了人才能跳,平时不能跳。现在不一样,但是呢,现在还是要死了人才能跳,但是传承只能说是这个学校的啊,或者是另外的场地来学习,但是平常是不能跳的。
信息报道人BJQ作为省级非遗文化传承人,从其文化精英的社会角色出发,对撒叶儿嗬的场域延伸认为似乎是无奈的文化调适,是面临传承断代之后的理性选择。将撒叶儿嗬作为文化符号加以保护传承和发展,撒叶儿嗬的操演场域必然延伸,面向学校、舞台、社区,逐渐社会化、世俗化,逐渐突出其身体操演的体育健身属性,弱化或选择性遗忘关乎丧葬仪式的构成。
4 多元互构:撒叶儿嗬传承发展的基本模式
无论撒叶儿嗬在当代衍伸出的情境如何多元,“丧葬仪式”仍是其原生情境;无论撒叶儿嗬的传承主体身份如何混杂,“跳丧的实践者”仍是其核心身份[12]。撒叶儿嗬的发展现状基本表现为以民族文化为中心,赓续传统丧葬仪式的核心身份,适当放宽原有的约制,面向更为广阔的群体,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传承发展与保护,维系其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在此理念和框架下,撒叶儿嗬的当代发展传承与保护工作发展态势向好,据当代非遗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道,现在的撒叶儿嗬已经发展到由“输血”到“造血”的境地。撒叶儿嗬在长阳的区域性社会中形成保护与传承的共同理念,社会合力助力撒叶儿嗬的传承与发展,与此同时,撒叶儿嗬发挥出文化产业的价值,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造福于当地百姓。探析撒叶儿嗬的当代发展的基本模式对于重新审视文化符号转型与变迁、民族文化调适与再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同时对于国内外同类的文化变迁相关问题提供实践经验参考。
4.1 撒叶儿嗬的学校传承
当前,政府与社会将撒叶儿嗬作为民族舞蹈引进中小学校园内,通过大课间活动、体育课堂、学生兴趣班等方式在学校传习和演练。在长阳县资丘镇对撒叶儿嗬的学校传承尤为重视,由于资丘具有跳撒叶儿嗬较好的社会群众基础,社会倾向重点关注对撒叶儿嗬的传承和保护的工作。学校教育是发展文化传承最好的方式之一,撒叶儿嗬作为民族文化符号进校园是践行“校本课程”的成果,撒叶儿嗬的文化传承人通过政府与学校的对接,临聘到学校教学撒叶儿嗬。一般认为,对学生施加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也是让学生接受传统的优质文化影响,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依托,可以认为,学校传承是撒叶儿嗬最好的平台。
据信息报道人BJQ谈道:在传承方式主要是以学校的,这个为基础撒。从小学、中学的,都一代代的一届一届的儿们(小孩子)都会跳,就不存在说是失传了。但是我们这个年纪比较大些的都会跳,但是让这个小学的从三年级就开始学,但是有个打鼓的儿们,他是从一年级就开始教他,他一年级会跳,会打鼓。但是跳撒叶儿嗬的打鼓的是师傅,他必须要会,要懂节奏,起指挥作用,要醒得(清楚)蛮多歌子,那是师傅。跳的(人),稍微差点都不要紧,但是跳当然要学会。那个小学三年级的儿们现在打的很好,他现在就声音比较小,这个没得那么大,但是他的鼓点都非常好。
学生学习撒叶儿嗬相对于成年人而言会更易上手,能记住撒叶儿嗬的身体动作、唱词等,也能更好地把握鼓点节奏。正如信息报道人BJQ谈到的那位三年级的学生,笔者在资丘调研中看见那名学生的确动作和节奏把握恰当,学习能力向好,跳撒叶儿嗬的水平较高。以体育人类学的身体动作分析法[13]看,小孩子跳撒叶儿嗬比一般的成年人稍快一些,且跳撒叶儿嗬有一定的运动量,较为适合学校体育教学。基于以上,撒叶儿嗬的学校传承在长阳的延伸,是较为合理且有效的传统文化与学校教育的衔接,达到撒叶儿嗬代际传承的重要作用。
4.2 撒叶儿嗬的社会(社区)传承
前已论述,撒叶儿嗬随着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辐射面向转移,超越其原有的丧葬仪式场域,面向更为广阔的群众,且作为民族舞蹈成为社会所重新建构的文化符号。当前撒叶儿嗬以民族舞蹈出发,作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健身方式,获得国家体育总局、宜昌市人民政府等机构认定全面健身场所,并获得文化和旅游部举办的群英奖。撒叶儿嗬以重新定义的“民族舞蹈”身份标识成为广场舞、健身操等活动的项目选择,并举办文化节,进行撒叶儿嗬“舞蹈”的竞技比赛,撒叶儿嗬的社会(社区)传承发展态势向好。
信息报道人ZAG谈道:不管是哪个,只要你喜欢这个东西,喜欢的、不会的,都可以教嘛,现场教,但是一般的他也愿意,再就是说只要你们爱好的过来、我们马上就教一下、跳一下。我们这个是搞传承嘛,愿意学你就来。我们在晚上那个村委会里面有场地,大家就一起来跳(撒叶儿嗬)嘛,男男女女都要来,经常都有四五十个人在那里,人多的时候(场地)都站不下。
撒叶儿嗬有着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各家各户来到村委会、广场等场地,这撒叶儿嗬作为传统文化,其社会(社区)传承是不收费的,人们乐意于参与到集群中去,这或许也是在闲余的时光之中获得参与感的需要,也是个体与社会整合的需要,人们参与到撒叶儿嗬不仅仅是学习动作和唱词,更多的是文化的交流,社会网络关系的密切。这在自发的追求带动之下,撒叶儿嗬的社会(社区)传承以自然的方式进行着,不用政府或企业的价值引领或是利益的驱动。
4.3 撒叶儿嗬的家庭(家族)传承
家庭这个自然形成的生活环境,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影响,往往比任何人为形成的环境中所受到的影响要深刻得多,形成的习惯也稳固得多。人们是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中接受影响和教育[14]。撒叶儿嗬的家庭(家族)传承呈现极为自然的发展态势,在家族丧葬的仪式中,孩子们自发地就随着大人们一起跳动。这在过去尽管是不被允许的,但跳撒叶儿嗬对他们而言似乎是仅限于成人的特权,孩子想挑战权威就要通过跳啥撒叶儿嗬以身体的方式表达这种示威,在其个体的认知中这似乎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现在的长阳土家丧葬仪式中孩子也成为重要的参与对象,他们不会像传统中那样是撒叶儿嗬为成人的特权,而是重在参与仪式的过程。
据信息报道人ZAG谈道:我从小就随着父亲的爱好也喜欢这个事儿……从小时候记事就看他们跳这个撒野儿嗬,感觉蛮过瘾,但是自己亲身跳是在参加工作后,就是别人死了人之后举办这个丧事活动,滥竽充数就混一混。
信息报道人BJQ也谈道:但是也是从小在我在学校,小时候对这个(跳撒叶儿嗬)有特殊的爱好,别人跳撒叶儿嗬,我就想学然后就跟着学,但是撒叶儿嗬没得师傅,但是嘞,叫歌、鼓手,叫歌的要有师傅,你要有歌词、要懂。再就是吹打乐要有师傅,这就是小时候有一种特殊的爱好。
在家庭(家族)之中,传承民族文化符号似乎是自然天成的事情,作为丧葬仪式的撒叶儿嗬亦是具有自然传承的特点。通过传统文化的教化,灌输人们一种符合人性的伦理、价值,让人们寻找到生活的依据,培养一种健康的人格[15]。促进孩童对民族(族群)的认同,提升民族凝聚力。
应当指出,撒叶儿嗬的传承基本模式不是呈现相互割裂的态势,而是传承极具生活化,场域也是不定的,在田间地头,在农闲时余。家庭(家族)传承撒叶儿嗬的场域还有延伸至社区之中。
正如信息报道人TXL谈道:我们一起学的时候,一起有六七个孩子,他就在那个粮站那里,因为房子比较大,按农村话来说,就是“新净居”。我们是死人之后才跳撒叶儿嗬,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比死人开放些,我们就是那个粮站跳。就是那时候又没得鼓,我们就用那个盆子翻起过来,跟着那个节奏跳,就这样就学会了。
撒叶儿嗬的传习场域是为多元,各类不同传承基本模式形成有机的整体,共同传承和保护了撒叶儿嗬的赓续发展。纵观撒叶儿嗬的当代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学校教育、社会(社区)教育、家庭(家族)教育3种模式共同合力的结果,在撒叶儿嗬的文化变迁与转型中对撒叶儿嗬进行文化的重组,这是族群社会的理性选择,也是在政府的积极倡导之下进行的牵头转型,这也使得撒叶儿嗬较为成功地完成当代的文化变迁,适应于时代的主流价值。
5 困境与博弈:撒叶儿嗬的归向探讨
前已述及,作为丧葬仪式的撒叶儿嗬,其文化变迁的程度和水平较之传统有较大变化,在这变化之中引发了关于撒叶儿嗬变迁的诸多争论。其中不同的主体之间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和考量,主要有政府与民间对撒叶儿嗬社会认知建构的博弈、政府与文化精英关于撒叶儿嗬的博弈、文化精英与撒叶儿嗬演绎场域延伸间的博弈等重要的争论。
政府与民间对撒叶儿嗬社会认知建构的博弈,其主要焦点为撒叶儿嗬文化方向,是否去除撒叶儿嗬丧葬仪式化和是否歌舞艺术化撒叶儿嗬。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同一问题的不同发展方向,政府和民间都不绝对排斥文化的变迁,在整体上对于撒叶儿嗬的当代发展都做出各自突出的贡献,但在这根本的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撒叶儿嗬的发展方向在一定意义上与社会认知建构具有等同性,所以政府与民间对撒叶儿嗬社会认知建构之间的博弈问题就在于其根本发展方向上的争论。
政府与文化精英关于撒叶儿嗬的博弈,主要聚焦在撒叶儿嗬文化精英的利益分配之中。土家族丧葬仪式撒叶儿嗬的文化精英基本可以界定为各级各类的非遗传承人,他们通过撒叶儿嗬在顶层与政府相接,在民间与群众相连,在长阳的区域性社会中被赋予以特殊的社会角色,似乎成为政府与民间二元结构中的结构洞。可以看到文化精英在传承和发展撒叶儿嗬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也为撒叶儿嗬的传播付出不少辛劳,正如LXC提到,之所以搞这个撒叶儿嗬的传承,主要的原因还是想要传承土家民族的文化,让这个撒叶儿嗬也能发扬光大。ZAG提出,自己从事这个传承工作没有固定的工资,多数时候都是搞“奉献”,希望自己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能有经济利益的补给。政府每年都会给相应非遗传承人以补助金,由政府牵头的非遗进校园等活动也会为非遗传承人提供相应的酬劳,但文化精英的价值诉求似乎不能得到满足,在这之中政府与文化精英的博弈焦点就利益分配问题之中。
文化精英与撒叶儿嗬演绎场域延伸间的博弈,主要原因是文化精英对本民族文化和历史相关知识了解和掌握较多,具有较高的本民族文化自信,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的思路偏重于保守,老沉持重。当前长阳部分文化精英对撒叶儿嗬的当代发展比较认可,但是在部分文化的变迁问题上有着自己的思考。长阳撒叶儿嗬国家级非遗传承人QFC老先生在早期就一直反对撒叶儿嗬演绎的场域延伸至广场,曾多次前往公共广场劝返前来跳撒叶儿嗬健身舞蹈的民众,以撒叶儿嗬的“传统”“祖宗”“丧葬”“死亡”等符号为名进行宣传和教育,但是收效甚微。民家自发组织的习练撒叶儿嗬不是将其作为丧葬仪式,更重要的考量是继续自我的体育健身,以及密切社会网络关系。撒叶儿嗬的场域延伸在文化精英与民间的博弈也折射出来相关的问题值得思考,各自所站立的立场和观点不同,对于同一问题也就有着不同的态度。
在争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博弈的主体呈现政府、文化精英、民间三足鼎立的局面,各执一词对撒叶儿嗬提出己方的观点。在这3个不同主体之间似乎缺少一种对话机制,使得多方主体都处于信息失位状态,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重要问题。如此,便使得社会对撒叶儿嗬变迁、发展与传承缺失共识性观点,阻碍撒叶儿嗬的整体化发展,对撒叶儿嗬归向产生严重且深远的影响。
6 结语
对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而言,本真性与变异性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论题。笔者认为,对于作为仪式体育的撒叶儿嗬而言,整体思路为赓续传统丧葬仪式撒叶儿嗬的符号象征,重视族群社会对撒叶儿嗬的集体记忆,全力将传统的丧葬仪式撒叶儿嗬文化以文字、图画、影视、博物馆等方式保存,坚持撒叶儿嗬传承发展的代际真实性,重视撒叶儿嗬的体育健身属性。同时,搭建政府-社会精英-民间代表沟通和交流的机制,形成社会合力共同促进撒叶儿嗬的传承与发展。此外,可以尝试将撒叶儿嗬嵌入旅游产业,延伸撒叶儿嗬文化符号产业链,文化创意形成旅游产品,发展民族文化旅游。
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布朗指出,当一个群体失去其成员时,葬礼所起的重新整合的作用:超越其外在表现,此仪式是为活人做的,而不是为死者做的[16]。长阳土家族撒叶儿嗬所承载的符号象征早已超越其丧葬仪式的意义,并随着文化变迁更显价值的多元化。撒叶儿嗬从丧葬仪式到民族歌舞的当代转型是顺应非遗文化传承的选择,曾历经转型期的社会阵痛。撒叶儿嗬的当代传承取得阶段性成果,其传承模式可以进行复制和再现,对同属性的文化符号传承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撒叶儿嗬文化变迁呈现本真性与变异性共存、博弈与调试并行的发展态势。撒叶儿嗬嵌入旅游发展既能达到保护民族文化,又能传承民族文化,同时收获民族文化产业的红利。仪式体育有着超越于身体实践的物化价值,其文化和社会的属性重于体育健体功能。
———评《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