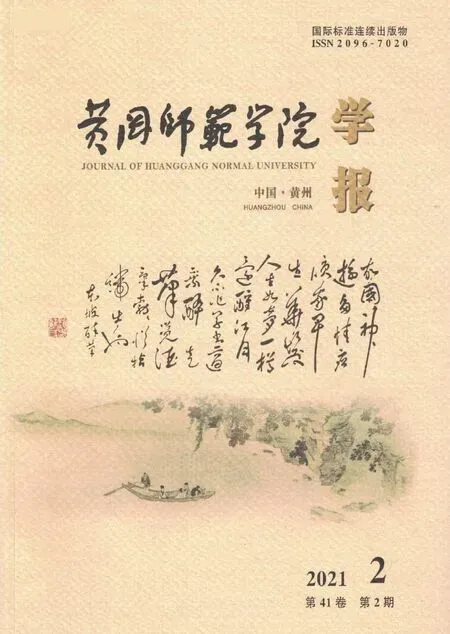李贽之死新探
——以黄麻士绅纠葛为中心的讨论
董恩林,吴 帆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献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李贽的人物事迹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关于李贽之死,学界多归咎为其狂狷的思想不为封建统治者所容。近年来,有学者将李贽所遭的暴力行为与政治集团的利益斗争联系起来,如姜进认为晚明意识形态控制相当宽松,因此地方政治实际上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1]。目前学界讨论的焦点多集中于李贽在京城被捕入狱一案,而在此之前,李贽在黄安、麻城地区已经与地方势力发生了长时间的摩擦。有学者指出16世纪末麻城所具有轰动性的社会现象主要体现在耿氏、周氏及梅氏三个家族集团身上[2]90,因此本文主要通过梳理李贽与以这三个家族为代表的黄麻士绅的交往及冲突情况,试图探析李贽在黄安、麻城期间遭受攻击的过程,并进一步揭示李贽被害致死的深层原因。
一、与耿氏的结缘与破裂
隆庆六年,李贽在南京任官,与正游历至此的耿定理结缘,二人虽是初次见面,但在思想上却非常契合,交谈甚欢。万历五年,李贽赴云南姚安任职途中路过黄安,专程拜访正居家守丧的耿定向、耿定理兄弟,这次愉快的交谈让李贽产生“弃官留住之意”,[3]817但最终在耿氏兄弟的劝说下,李贽仅将女儿及女婿庄纯夫安置于耿氏的五柳别墅中,并约定“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3]817随后李贽便携其妻入滇赴任。这一时期,与李贽往来的黄麻士绅主要是黄安耿氏兄弟,双方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彼此予以学者的尊重。
明中后期,讲学之风盛行,而黄州地区则“缙绅世家以书院为中心,形成地方政治学术的士大夫集团”。[4]162书院的兴起,进一步带来当地的讲学兴盛及学术争锋。万历九年,李贽离滇赴楚到达黄安,此时黄麻一带已经成为鄂东学术的中心,而这个学术中心正是以黄安耿氏及麻城周氏两个士绅家族为核心。在目前可考的六所明代黄安书院中,耿氏家族便占了三所,分别是天台书院、天窝书院和钓台书院,而周氏在麻城也建有辅仁书院。李贽来到黄安后,侨寓于耿氏修建的天窝书院,担负着教育耿家子弟的工作,同时也著书问学,与当地学者交流学术。
在学术思想上,李贽虽与耿定理有许多契合之处,但与耿定向始终存在分歧。万历十一年,邓豁渠作品《南询录》在黄安一带流行传抄,耿定向的门生吴心学因抄录该书而被耿定向严厉指责“彼邓老以残忍秽丑之行,为诐淫邪循之语,犹录而玩之,此则窃疑兄之胡涂耳。”[5]668这位耿定向所批判的异人邓豁渠,同样是耿定理的挚友,亦曾寄食于耿氏家中。耿定向对邓豁渠的批判,正是在影射当时正寓居于耿氏家中的李贽。对此,李贽亦做出了回应,极力称赞邓豁渠的言行。耿李二人虽然没有产生直接争执,但是在思想上的分歧已经逐步公开化。
万历十二年七月,耿定理病故,此时耿定向已离乡赴京就任,耿定力亦赴蜀中官任。耿定向原本对李贽的言行就略有微词,如今更是不放心李贽继续为耿氏子弟讲学,就连耿定向的门生也曾责怪李贽“楚倥放肆无忌惮,皆尔教之”[3]195,将耿定理不羁的言谈怪罪于李贽。因耿氏家中已有耿定理终生不仕的先例,这让耿定向对耿氏子弟的前途感到忧虑,而在这之前,耿定向的独子耿汝愚同样表现出无意仕途的想法。“万历壬午,江陵势倾一时。楚闱中因得各树其所私,监临为恭简公所取,士欲得克明甚亟。克明知其意,因避不入。后其弟怘举于乡,人颇以高克明,克明不以屑意也。”[6]646除了耿汝愚这种无意举子业的表现让耿定向担忧,耿汝愚年近四十还未得子,使得耿定向更加认为是李贽“不以嗣续为重”[3]191的思想影响了耿汝愚,并且把这种不满情绪迁怒于李贽,指责李贽“作此等榜样,宁不杀人子弟耶?”[5]661自此,耿李之间的私人关系逐步破裂。万历十三年春,李贽离开黄安,迁居麻城周思久的女婿曾中野家中。
李贽在黄安的这段时间,在学术思想上始终与耿定向有分歧,这种分歧原本可以看成是士人间的学术争锋,最初并未影响他们的私人关系。然而,李贽不仅是与耿氏兄弟交流学术的门客,更是耿氏子弟的家庭教师,这层关系使得双方之间存在切身的利益关系。耿氏家族主要依靠耿定向的个人功名而崛起,为了确保家族的繁荣能够持续,耿定向希望耿氏子弟继续走上科考举业之路。当耿定向认为李贽的言行将成为家族发展的潜在威胁时,出于对家族利益的考虑,这种学术争论便逐渐成为私人间的不满。
二、从学术争辩到人身攻击
万历十三年春,李贽寓居麻城曾中野家中,此时县中已经有人以李贽“弃人伦”为由攻击他学佛之事。同年,周思敬捐建维摩庵,不久李贽便迁居该地,而此时正是李贽思想从与世无争向狂狷转变的关键时期,他与耿定向之间的论战也日益激化,逐渐超出辩学的范围。耿定向再次借批评邓豁渠来暗讽李贽,李贽反击“人有谓邓和尚未尝害得县中一人,害县中人者彼也。今彼回矣,试虚心一看,一时前呼后拥,填门塞路,趋走奉承,称说老师不离口者,果皆邓和尚所教坏之人乎?”[3]489李贽言辞激烈,直指耿定向才是那位“害县”的元凶,并且嘲讽县中奉承耿定向的趋炎附势之人,不仅公开讽刺耿定向,还借机批判他的门徒友人们,对耿氏集团的形象造成严重打击。由于耿定向在黄麻地区名望颇高,因此与其辩学的李贽便逐渐成为当地士绅们攻击的对象。时麻城有位老嫠妇,孤寡无聊,受人欺吓,常往维摩庵送茶馈果。而李贽到了麻城之后,曾自言“然后游戏三昧,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间”[3]460,因此这位嫠妇到维摩庵诚笃供佛一事不免引起当地士绅的闲言碎语。当李贽率僧众到嫠妇家中询问缘由,此举却被谣传成“率众僧入一嫠妇之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薄之羞”[3]467。耿定向素来对李贽恣情纵欲的行为十分不满,于是在万历十六年春曾借此攻击李贽,并称李贽此举“士绅多憾之”[3]467,李贽再次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
然而,李贽并没有因流传的舆论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万历十六年夏,李贽在维摩庵落发,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一番波澜,“此中士绅闻卓吾薙发,或束名教,骇而异之者。”[5]662李贽的好友邓应祈、祝世禄等曾极力劝阻,周思久得知此事还致信耿定力,请他劝其兄耿定向切勿攻击李贽落发之举。从周思久的态度可以看到,当时耿李二人的矛盾已经相当激烈,李贽的举动为他招惹了许多麻烦,其中包括来自耿定向的攻击。或许是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李贽在这年秋天再次迁居,离开了地处闹市的维摩庵,搬到了距离县东三十里的龙潭芝佛院。芝佛院同是周氏兄弟的资产,在耿李争论激烈之际,周氏兄弟为李贽提供了物质保障,也成为李贽最大的保护来源。
然而,随着李贽与耿定向争论的升级,他与周思久也逐渐交恶,幸得二人好友及门生屡次在双方之间调和。万历十七年,周思久的门生杨起元致信其师 “二老皆人龙也……一切葛藤,从今已断,更不提起”[7]676,试图调解李贽与周思久之间的矛盾。万历十八年春,周思久的女婿曾中野从中斡旋,说服李贽试图与周思久和解,李贽承诺“自今已矣,不复与柳老为怨矣。”[3]277由于此时李贽与周氏家族有着更为密切的利益挂钩,且周思久在思想上二人并非无法调和,因此很快和好如初。后来周思久病重时,还曾向他人叹“朋友之义,以相规为正,余以为乐,卓吾以为苦耶。”[8]218这是在回应李贽正在刊行的《焚书》,《焚书》有一别录名为《老苦》,书中收录了大量与耿定向等人的辩学书信。与耿定向的争论使李贽受到了许多来自耿定向追随者的攻击,因此他视之为“苦”。而作为中间人的周思久则直言这只是朋友间的相互规劝,应以为“乐”,不断从中调停耿、李两位好友的冲突。
《焚书》刊行后在当时士大夫中影响颇大,不仅祝世禄、袁宏道等好友对此书称赞备至,汤显祖闻知此书后还曾向友人求书一览。与此同时,耿定向告老抵乡,看到李贽公开刊行的《焚书》十分愤怒,直言该书是李贽对自己的诽谤。这是因为李贽在《焚书》一书中所讨论的内容,已经超出了辩学的范围,涉及对耿定向私人家事的讥讽,对耿定向的形象造成了打击。随后,耿定向作《求儆书》予以回击,其门生蔡毅中作序梓之,公开攻击李贽。同时,许多黄麻士绅迎合风声,“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9]705,意图将李贽逐出麻城以正风化。另外,地方官员也参与到了此事,“黄郡太守及兵宪王君亟榜逐之,谓黄有左道诬民惑世,捕曹吏载贽急。”[10]4505此处所指“黄郡太守”,应为此时的黄州知府瞿汝稷。耿定向曾是瞿汝稷之父瞿景淳的门生,而瞿汝稷同样是位传统的程朱理学学者,“最不喜温陵人李贽,以为得罪名教”[11]80“痛疾狂禅,于颜山农、李卓吾之徒,昌言击排,不少假易”[12]1604,对李贽其人及学说十分排斥。而文中所说的“兵宪王君”,应指此时的湖广佥事王道增。据记载,王道增“转湖广佥事,闽人李贽以儒起家,二千石,削发留须,肆意隐怪,横诋孔孟,缙绅靡然惑之,道增独逐之出境”[13]2468“左迁楚佥事,恶李贽游部中,以檄逐捕”[14]178,这里所记逐境之事,指的便是此时李贽在地方官员驱逐之下入湖南衡州一事。可见,《焚书》的刊行使耿定向与李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黄麻士绅联合地方官员对李贽的攻击逐渐升级,从舆论攻击上升到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欲将李贽驱逐出境。
由于在耿李之争中李贽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因而逐渐产生和解的想法。万历十九年春,李贽得知耿定力将回黄安的消息,便致信周思敬,透露自己欲与耿定向和解的心意。耿定向对此仅回应“谤者自悔愧,书来”[15]53,认为李贽是对他的诽谤行为感到惭愧而前来求和,态度十分冷淡。同年五月,李贽与袁宏道等人同游武昌黄鹤矶,再次因“左道惑众”被逐。对此,李贽致信周思敬“弟反覆思之,平生实未曾会得一人,不知所惑何人也。”[3]288在与杨定先的信中同样提及“侗老原是长者,但未免偏听。故一切饮食耿氏之门者,不欲侗老与我如初,犹朝夕在武昌倡为无根言语,本欲甚我之过,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终始为此辈败坏,须速达此意于古愚兄弟。不然或生他变,而令侗老坐受主使之名,为耿氏累甚不少也。”[3]338李贽认为,是耿定向的门生从中挑拨他与耿定向的关系,而耿定向之所以对他进行攻击,也是因为偏听了这些话。这场事故是包括耿定向门生在内的诸多黄麻士绅及官员对李贽进行驱逐的延续,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耿定向是这场事故的幕后指使,尽管以现有的文献来看,李贽及二人的亲密朋友都没有提到耿定向直接参与到这场冲突中。然而,以耿定向在黄麻一带的名望来看,已在无形中对李贽施压。这年秋,蔡毅中书《焚书辨》、耿定向书《求儆书后》再次攻击李贽。
万历二十年夏,耿定向的三弟耿定力返乡,李贽在致周思敬的信中表示“令师想必因其弟高迁抵家,又因克念自省回去,大有醒悟,不复与我计较矣。我于初八夜,梦见与侗老聚,颜甚欢悦。我亦全然忘记近事,只觉如初时一般,谈说终日……我想日月定有复圆之日,圆日即不见有蚀时迹矣。果如此,即老汉有福,大是幸事,自当复回龙湖,约兄至天台无疑也。”[3]363虽李贽最后因事未能回到龙湖,但能够看出他欲与耿定向和解的强烈意愿。直到万历二十一年李贽自武昌回到麻城,在沈鈇的调解下,前往黄安与耿定向重叙旧情,“于是,耿、李再晤黄安,相报大哭,各扣首百拜,叙旧雅,欢洽数日而别。”[10]4506尽管这次和解并没有解决他们在学术思想上的矛盾,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二人很少发生如此前般激烈的争论。即便期间耿定向曾著《学彖》《冯道论》等文对李贽的思想进行批判,但言辞并不似先前般充满攻击性,也没有因此引起一场新的冲突。
三、冲突缘由的转变
李贽与耿定向交恶的同时,正与麻城另一家族七里岗梅氏关系日益密切。梅氏族中的核心族人梅国桢是黄麻地方中具有佛教倾向士绅的代表,自早前(万历十六年)与李贽相识之后,梅氏家庭成员与李贽之间便经常互动。万历二十一年,梅氏所建的绣佛寺落成后,梅国桢的二女善因、三女澹然等人开始正式向李贽请教佛法。李贽这一做法,再次被地方士绅指责为伤风败俗的行为。与此同时,李贽在芝佛院新添了佛殿,建藏骨塔,并拟再添新阁以作藏书。李贽在麻城的从游者甚众,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士绅们恶其簧鼓末学、乱麻城风气,因此欲以芝佛院没有请旨敕建为借口,扬言拆毁李贽所居的芝佛院。这一借口被李贽当场拆穿,“今贵县说喈者不见舍半文,而暗属上司令其拆毁,是何贤不肖之相去远乎……若供佛之所亦必请旨,不系请旨则必拆毁,则必先起柳塘于九原而罪之”[16]80。此寺院归周思久所有,尽管周思久此时已病逝,但周氏家族中与李贽交好的周思敬等人还在世,凭借周氏在县中的名望,足以确保李贽此时在芝佛院的人身安全。
万历二十三年初,耿定向的门生史旌贤因调任湖广佥事,专程到黄安拜访其师。途经麻城时,史旌贤问县官道“李卓吾去否?此人大坏风化。若不去,当以法治之”[16]56,扬言要惩治李贽。由于史旌贤与耿定向的关系亲密,有人便谣传此次史旌贤驱逐李贽之事与耿定向有关。尽管李贽敏锐地指出这是一场冯亭之计,但这样一种以官方身份对李贽进行驱逐的行为,使得麻城再次掀起一股攻击李贽的风潮。时麻城一位孀居老妇毛钰龙信奉佛法,周宏禴曾为其写序,有“有大士过化秽土,高谈最上乘法门,风动男女,谕意夫人,冀得半面以为重。夫人不许,又欲索片札往返酬答,亦不许”之言[17]331。这些内容被不怀好意的士绅曲解,甚至直言周宏禴所言“大士”正是李贽。谈迁指出“李贽倡龙潭庵,高谈佛乘,风动四方,钰龙独不往。欲索寸札酬答,亦不许”[18]283,后世钱谦益、陈梦雷等士人均持此观点。细探此事发生时,谈迁等人尚幼,因此他们的记载极大可能来自后世的坊间传闻,然而在当时与李贽交好的文人们,对此事均无提及。同邑文人丘坦与毛钰龙两家有姻亲关系,且丘坦与李贽也常有往来,而在丘坦为毛钰龙所撰的序文中只字未提李贽[17]271。另外,当事人周宏禴在听闻此事之后,亦回应李贽“龙湖伽蓝可表。他先与耿有隙之时,京中人为耿一边者我百计调护卓老,为卓老一边者我百计调护侗老,为他费了多少心力,今日乃遭此。随他打我骂我,我只受而不报”[16]56,极力为自己辩解。倘若此事与李贽确无关,当地士绅们为何选择毛钰龙作为攻击李贽的借口呢?毛钰龙是毛凤韶之女,刘守蒙之妻,无论是本家五脑山毛氏,还是夫家锁口河刘氏,都是当地最有势力的家族之一。而这个事件中涉及的另一位人物周宏禴,同样来自麻城大族新店周氏。由于毛氏、刘氏及周氏三家大族的影响力,这件事很快就在坊间的流传起来。这则传闻无疑将李贽与麻城最具势力的几大家族对立起来,意图使李贽在麻城的处境更为艰难,并借机以大坏风化为由驱逐李贽。
面对史旌贤发起的攻击,耿汝念曾多次致信邀请李贽赴黄安回避,此时耿定向致仕家居,对于耿汝念相邀李贽的行为并没有公开反对,自然是默许的。对于耿氏的邀请,李贽均以避嫌拒之,“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16]65同时,李贽也取消了原本前往山西的计划,决定“理又当守候史道严法,以听处分矣”[16]74,对史旌贤等地方官提出挑战。直到是年冬,李贽才到黄安与病重的耿定向相聚。期间,李贽至耿定理墓前悼念,著《耿楚倥先生传》。尽管此前二人也有和解的迹象,但此次耿定向能放下心中的私怨让李贽悼念耿定理,这一举动本身具有不一般的意义,以至于周思敬在得知二人冰释前嫌后不觉泪下“两先生大而化矣,乃适以今日至,岂非余更生辰耶,抑楚倥先生复作也!”[3]823
李贽与耿定向的和解并没有缓解他与耿氏门生的紧张关系,万历二十四年耿定向病逝之后,李贽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在耿定向去世之前,李贽便选择离开麻城,到山西沁水等地,但黄麻士绅并没有因此放弃对李贽的攻击,甚至扬言要杀李贽,幸得焦竑出面调停,李贽才没有生命危险。焦竑虽不是黄麻巨族,但因其与耿定向的亲密关系,且已取得较高功名,在耿氏门生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除了焦竑外,刘东星、马经纶、顾养谦等名宦友人也曾对李贽提供保护,使他尚且能够安心著述。直到万历二十八年夏秋间,李贽接到梅澹然劝回龙湖的来信,重回麻城。
重回芝佛院不久,李贽再次遭到地方士绅的攻击。士绅们称李贽为蛊惑人心的“说法教主”,扬言要将他递送回籍。是年冬,地方士绅捏造李贽与梅澹然“僧尼宣淫”的谣言,梅澹然遭诽谤而死。同时,与李贽曾有过节的冯应京时任湖广佥事,并且做了“毁龙湖寺,置诸从游者法”[10]4506的决定,芝佛院被烧,李贽的藏骨塔被拆,甚至还牵连到李贽的从游者。关于这个事件的经过,同邑士绅刘侗记载“有与中丞构者,幻语又闻当事,又逐之,至火其居”[19]226,明确指出与梅国桢有隙之人是这个事件的幕后主使。随后,李贽离开麻城,辗转河南黄蘖山、通州等地。直到万历三十年,京官张问达以李贽的著作 “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及李贽在麻城期间“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拉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20]6918等举止为由,对李贽进行弹劾,并逮捕入狱,不久李贽在狱中自刎。李贽在京城的遭遇,实质上是与黄麻士绅冲突的延续。正如好友马经纶指出“盖此事起于麻城士夫相倾,借僧尼宣淫应名目,以丑诋衡湘家声,因以败坏衡湘之官,如斯而已”[19]84,他认为对李贽的指控实际上是黄麻士绅诋毁梅国桢的阴谋,与刘侗对芝佛院被烧一事的看法一致。李贽去世后,有关他的诋毁并没有减少,黄麻士绅间对李贽之死也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四、梅氏与耿氏、周氏之间的纠葛
有学者曾指出“明代中后期麻城(包括黄安)地方事务即由耿、梅、周三家把持”[21],这三个家族中,耿氏与梅氏分别是黄安、麻城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士绅家族,且都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家族仕途的巅峰时代,因而此时也是双方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嘉靖四十二年,在耿定向等人长期向各级官员游说的努力下,户部最终批准设立黄安县,割麻城等地益之。此后黄安、麻城互为邻邑,士绅大族间因利益冲突争论不休。喻仪曾直言“黄安之粮,一半麻城所割也。黄安向荷哀矜,全赐改析;麻城差繁役重,十倍黄安,苦乐未均,万民嗟怨。”[22]58梅国楼亦叹“每一传呼,必立收受,头会箕敛,倍于常额。”[22]58可见,黄安县的设立,直接加重了麻城县的差役,损害了包括梅氏在内的麻城邑人的利益。而作为倡议设新邑的主导者,耿氏家族通过广泛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使得耿氏在黄安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新邑设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耿定向与梅国桢不仅在家族利益上彼此冲突,二人的私交也存在矛盾。据梅国桢好友南师仲记载,梅国桢任固安知县期间,其母在梅国楼家中病重,梅国桢闻知此事立刻从固安索骑驰赴。途中,“及春明门,遇回乡司寇耿天台、司隶刘司云,戒公且止,‘外吏非觐期,例不得潜入禁门。’公流涕,答曰‘吾方寸已乱,何例之云,为亲触禁,死非所恨’。”[23]235耿定向是一位传统的道学家,恪守孝道,而在梅国桢母亲病重之际,耿定向竟阻止梅国桢前去照顾,显然与他所坚守的儒家伦理有悖,有故意刁难之意。不仅如此,二人在思想上也存在差异。相比起耿定向对李贽思想的强烈批判,梅国桢十分欣赏李贽,曾在阅《焚书》后大叹“如此老者,若与之有隙,只宜捧之莲花座上,朝夕率大众礼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声价也。”[3]347此处所指与李贽有隙的人,即包括李贽争论的对象耿定向。梅国桢借此信,暗讽耿定向恶意诋毁李贽的行为,只会让李贽反增身价。另外,在梅国桢致周思久的信中直言“闻楚侗先生瞑眩之论,真有味乎?”[23]155“若下愚终不可移,清议终不可逭,不肖非朝市之鄙夫,而山泽之癯耳。宁复与有道者相接哉?”[23]155言辞激烈,对周思久、耿定向的态度并不友善。同样,耿定向亦曾在多封信件中都透露出对梅国桢之师刘师召的批评,并就对梅澹然等人与李贽学佛之事进行攻击。
周氏兄弟在麻城行政区划调整后,地产分布黄安、麻城两地,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周氏兄弟热衷于地方文化建设,设书院、建佛寺,为当地士人提供文化交流场所,因而与黄麻文人都维持较好人际关系。其中,周氏兄弟与耿氏家族交往最为频繁,耿氏三兄弟皆为周思敬儿女之托,周思敬又是耿定向的门生,双方既有姻亲关系,又有师承关系,因此两家关系十分亲密。思想上,周氏兄弟的观点介于耿李之间,因此在耿李争论激烈之际,常从中调和。周氏与梅氏虽然交友圈有部分交集,但双方则很少有书信往来,双方关系也较为僵硬,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来自梅氏。
梅氏虽是当地最负盛名的家族之一,在当地却树敌颇多。首先,梅氏代表成员梅国桢在生活上狂放不羁,曾先后与大地主万兆、士人吴可通、李梦麟等发生私人纠纷,引起地方士绅不满。其次,乡里无赖士绅如黄建衷,曾因觊觎梅国桢之女梅澹然才色设局,不料被梅氏识破而未得逞,“羞赧不敢言,为乡里所诮”[24]499,从此与梅氏结下矛盾,伺机报复。再者,梅氏族中多位女性成员向李贽求佛问学,而这一行为不断遭到道学家们非议,置梅氏于流言之下。关于梅氏在地方上的人际交往,从梅氏与锁口河刘氏的姻亲关系变化也可窥探一二。锁口河刘氏同样是麻城最具势力的家族之一,早前与梅氏交好,互为姻亲,梅国桢的两位夫人都来自刘氏,而刘氏族中刘承棨、刘承绪等人也娶梅氏女。而好景不长,或因刘氏家中变故,或因梅氏遭人非议,梅澹然与刘承禧、梅之焕与刘氏女的婚约相继取消。不难推断,这一时期梅国桢在麻城地区同样遭到许多来自当地士绅的诋毁和攻击,甚至有学者认为,《金瓶梅》一书谐音“今评梅”,就是为了诋毁梅国桢而作[25]。对此,梅国桢也叹息“髫龀之童,皆能操权诈以侮人。以凌驾为节概,以诋毁为才辩,相见煦若春风,而中多荆棘”[23]105,严厉指责麻城相互诋毁的地方风气。
五、结语
基于黄麻士绅间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重新梳理李贽与黄麻士绅交往及冲突的过程,按照时间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隆庆六年至万历十二年,李贽结识耿氏兄弟,姚安任满后来到黄安,以耿氏家庭教师及门客的身份寓居在耿氏天窝书院,交友论道。这一时期,与耿定向在学术上的分歧日益显著,耿定向出于对家族利益的考虑,与李贽的私交关系逐渐破裂。第二阶段为万历十三年至万历二十一年,李贽与耿定向之间的争辩迅速激化,并且逐渐脱离了辩学的范围,耿氏的追随者对李贽人身自由造成了威胁。第三阶段为万历二十一年至万历三十年,耿定向与李贽关系逐渐缓和,但来自耿氏追随者的攻击仍未间断。而在耿定向与周氏兄弟相继去世后,李贽失去了曾经强有力的保护人。与此同时,李贽因梅国桢卷入当地士绅纠纷而遭到牵连,最终惹上杀身之祸。
不可否认李贽因其不合礼法的思想及行为遭到统治阶级的不满,但倘若完全是因其异端思想而遭受攻击,那么李贽在辗转山西、南京等地时,同样会有当地士绅对其发起攻击。然而,尽管李贽在济宁客居刘东星家中时曾受到谢肇淛等文人的文字批斗,但并没有受到威胁或驱赶。即便是在南京这种声利之场,李贽虽不得屡易住所,但依旧能从事讲学。实际上,绝大部分针对李贽的攻击都来自于黄麻士绅,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耿定向及其追随者。李贽与耿定向之间的争论是他招致攻击的最初原因,耿定向因其名宦硕儒的身份,在黄麻地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二人论战开始后,与之争论的李贽便成为众矢之的。虽然耿定向在私人情感上与李贽有隙,但他的追随者对李贽抱有更大的敌意。他们的目的除了捍卫自身信奉的价值观外,还为了维护耿定向的声誉,这或出于对是师长的尊敬,或出于对权势的奉承。当耿李二人的争论逐渐脱离学术争锋的意味时,耿氏门生就对李贽发起人身攻击,试图驱逐出境。但同时,也正因为耿定向的声望,使得耿定向在世时李贽尚且是安全的。实际上耿氏族中子弟并没有对李贽实施攻击,即便是二人论战激烈之时,耿氏子弟如耿定力、耿汝愚等人仍旧与李贽交善,甚至处处提供便利,给予保护。
另一方面是梅国桢的政敌。李贽作为流寓客子,在黄麻时期的保护来源全来自于与士绅大族的人际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李贽曾多次凭借与周氏兄弟关系免受更大的攻击。耿氏与周氏兄弟去世之后,梅国桢作为与李贽交好的麻城巨族,替代耿氏、周氏成为李贽主要的保护来源。李贽在大同期间,梅国桢作为当地官员,尚且有能力为其提供庇护。然而,梅国桢在黄麻一带树敌众多,因此当李贽回到麻城时,这层关系不仅无法保护李贽,反而还成为他被攻击的理由,使他卷入了更为复杂的地方斗争当中。可以说,在耿李之争告一段落之后,针对李贽的攻击大部分是因梅国桢个人而起。值得注意的是,在打击李贽的梅国桢政敌中,有部分同时还是耿定向的坚定追随者。正因为这种双重身份,使得后期李贽受到的攻击更加猛烈,而这个过程中不断有其他道学家加入这个队伍,最终导致李贽被捕入狱的悲剧。
李贽虽自刎于京城狱中,但实际上他的悲剧在寓居黄麻期间便已埋下了伏笔。李贽从一开始来到黄麻地区,便相继与当地最具权势的士绅家族耿氏、周氏、梅氏打交道。这种人际关系给李贽提供了学术及生活上的便利,但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士绅斗争中。李贽狂狷的思想及怪诞的行为,使李贽所受的攻击更具合理性,也更容易让旁人忽略其背后还有黄麻士绅间的冲突及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