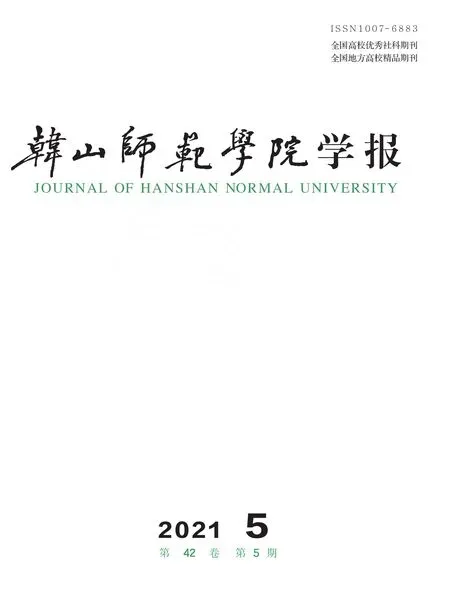《洗冤集录》蕴含的法律思想与现代启示
林 希
(中共南平市建阳区委党校,福建 南平 354200)
《洗冤集录》之所以能传承至今,不仅在于其法医学上的“术”,更在于其体现出来的法律思想上的“道”。李勤通、周东平认为,《洗冤集录》反映了宋慈重视生命、追求个案正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意义。[1]郑传芳指出,宋慈“洗冤”的公平正义理念、严谨求真的检验态度和善于学习借鉴的开拓精神,是我们要进一步坚持和弘扬的宝贵财富。[2]
宋慈,字惠父,汉族,生于1186年,福建省建阳人。1226年出任江西信丰县主薄,正式走上仕途。此后担任信丰主簿、长汀知县等官职,最高的职务为阁直学士、广州知州与广东经略安抚使。[3]最重要的是,宋慈四任提点刑狱官,担任过江西、广西、湖南和广东提点刑狱,办案和司法检验经验十分丰富。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他认为会出现冤假错案的原因是同仁们缺乏案件检验和审理经验,被下属蒙蔽。因此,宋慈在通读前人书籍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办案经验,终于在1247年写成《洗冤集录》一书,给同仁们参考,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法医学专著。
《洗冤集录》共分为五卷五十三条,它记载了宋代有关尸检的法律规定,以及毒死、病死、火烧致死等各种尸伤的检验鉴定方法。这是中国古代审理案件的必备书目,还被翻译到世界各地,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法医学专著,在中国乃至世界法医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洗冤集录》蕴含的法律思想
后世学者多从法医学和法医技术的角度对《洗冤集录》进行评价,却忽视了其重要的“内核”——宋慈洗冤泽物的法律思想。笔者认为,《洗冤集录》蕴含的法律思想包括以下几点:
(一)“慎刑恤狱”的法律思想
“慎刑”是中华法系的一种主流思想,宋朝历代的统治者大都是这一思想的贯彻者,以民为本,以宽仁之心为政,审慎刑狱。朱熹也提倡“慎刑”,他强调:“狱讼……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恐有误也。”[4]作为南宋的司法官员和朱熹的再传弟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宋慈克尽职守,身体力行。
《洗冤集录》蕴含的“慎刑恤狱”思想,具体表现在“恤民”“慎刑”“恤狱”三个方面:
1.“以民为本”的“恤民”思想
宋慈在《洗冤集录》的“恤民”思想,具体表现为提倡检验时不要无辜扰民。
首先,宋慈反对验尸前派人“打前站”的行为。他认为“打前站”的下属和随从先于检验官到达现场,会借机索贿受贿,敲诈勒索,徇私枉法,甚至有的会收钱虚假检验,改变案件事实。
其次,宋慈坚持验尸时要约束下属“不得少离官员”。宋慈认为,随行人员一旦离开官员,就可能会有不法活动。即使是晚上投宿,随行人员也必须立下保证,保证不骚民。
第三,宋慈对干证人的范围做出了限制。宋代案件发生后,官府有拘捕干证人(与罪犯相干的证人)到官府调查的合法程序,但实践中干证人往往被入狱,遭受折磨,除非花钱消灾。所以,宋慈严格限制干证人范围,要求初、复验完毕后,责令尸体的血亲、邻人等无辜有关人士看守尸首,避免吏役为谋取好处故意扩大干证人范围。
南宋时官吏在调查案件时骚扰乡民很普遍,老百姓对狱事往往避而远之。宋慈设计这些程序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官府办案时骚扰乡民,体现了宋慈“以民为本”的“恤民”思想。
2.“慎之又慎”的“慎刑”思想
在《洗冤集录》序言里,宋慈就说:“狱事……莫重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他强调认真、严谨检验,并把检验取证上升到死生出入的高度。因此,他“独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5]1对于存在疑点的案子,反复推敲,只要知道有不属实处,就会坚决发回,重新查验,以免产生冤假错案,让死者不得安宁。
宋慈一再强调不可扰民,唯独“有大段疑难”的情况例外。他要求检验官“广布耳目”,不能偏听偏信,要“反复审问”,将证词结合起来,看能否互相佐证。如果证词相互矛盾,令证人“各供一款”,与行凶人证词比对,达到“参会归一”的程度才能结案。
由此可知,宋慈是如何的“慎之又慎”。
3.“疑罪从无”的“恤狱”思想
在《洗冤集录》序言中,宋慈强调:“疑信未决,必反复深思。”[5]3据刘克庄的《宋经略墓志铭》记载,宋慈提点广东刑狱时,发现狱中存在许多疑难积案,于是“下条约,立期程”,重新审理。短短八个月,他就处理了两百多起死刑案件。[6]其他找不到犯罪证据的案件,宋慈选择“疑罪从无”。
南宋时,大部分官员的处理方式是“疑罪从轻”,即推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但可以从轻或以赎金的方式判刑。在宋慈看来,“疑罪从轻”仍然是推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这样,一方面对无法定罪的犯罪嫌疑人予以定罪,只是量刑上采取从宽政策;另一方面,对“疑罪”犯罪嫌疑人采用赎金的处罚做法,对没有钱赎的老百姓来说毫无意义。因此,司法官仍然坚持“疑罪从有”的潜规则,冤假错案就会继续存在,这也是造成大量疑难案件的原因。只有贯彻“疑罪从无”原则,才能杜绝上述弊端。因此,宋慈在处理“疑罪”时,援引“罪疑从轻”例文,对案件不予处理。这就是宋慈在短短的八个月时间里处理了两百多件死刑案件的重要原因。
(二)“礼法并用”的法律思想
“礼法并用”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法律思想,《唐律疏议》开篇更是认为法律只是治理手段,德礼才是根本。《洗冤集录》也体现了这个法律思想:重视官吏职业道德、刑罚与体恤相结合、维护封建宗法制度。
1.重视官吏职业道德
《洗冤集录》第一卷就明确列出了《宋刑统》等法律规定中有关检验制度、司法官员责任、违法行为处罚的各项规定,这些大多涉及司法官员的职业道德建设,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宋慈反对检验官“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5]2的行为,要求司法官员要亲临验尸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样才能准确判断案件的事实。他反复强调检验“贵在精专,不可失误”,认为“临时审察,切勿轻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5]34
2.刑罚与体恤相结合、宽严相济的法律思想
《洗冤集录》的卷一对《宋刑统》里有关检验制度条文进行了收录,明确了检验官员的法律责任。其中有一条针对初、复检的规定:“诸尸应验而不验;(初覆同)或受差过两时不发;(遇夜不计,下条准此)……各以违制论。”[5]4尸体应当检验却未检验的,或者受到差遣超过两小时不出发的(遇到夜间不算,下条同样如此)……按“违制罪”处罚。
从这条看出,对检验官责任的追究,采用的是刑罚与体恤相结合、宽严并施的原则。宽的方面包括检验时间的考虑,如果晚上报案的,不到现场不追究。严的方面,其余时间内应检验不检验的,接到报案2小时以上无反应的,或不现场检查检验等等,都要按“违制罪”处罚。
3.维护封建宗法制度
“礼”最重要的就是“亲亲、尊尊”原则,体现在伦理上就是“忠”和“孝”。南宋的司法检验制度也体现了统治者对宗法伦理的维护。
在中国传统社会,按照孝道观念,大多老百姓不能接受自己亲属的尸体被检验,一般不愿意接受官府的检查,而尸检又是重要的程序,所以《洗冤集录》中记录了有关免验的规定:“同居缌麻以上亲,或异居大功以上亲至死所,而愿免者,听。”[5]11病死死者是否需要检验,由他们的亲属来判断,这体现了维护宗法等级原则的精神。
包括《洗冤集录》在内,中国的各种涉及勘验的著作,进行尸检时大都停留在身体表面,而不像西医那样采用解剖的方法。除了因为当时医疗水平和技术的局限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思想对检验官的束缚,这也是“礼”文化影响的结果。
(三)重视客观证据的法律思想
1.重视检验证据
使用刑讯的方式求取口供是传统中国司法搜证的重要手段,宋慈却认为言辞证据不可轻易相信。他认为“告状,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5]54他不轻易相信口供。那么,他认为什么证据可信呢?当然是尸体检验获得的证据。
虽然《宋刑统》规定了血亲申请可免验的原则,但宋慈认为,利益动人心,血亲可能被收买,不能因为血亲的一纸免验申请就听信免验,还要客观的检验证据。“凡血属入状乞免检,多是暗受凶身买和,套和公吏入状,检官切不可信凭。”[5]22这是典型的物证的证明力大于言辞证据的表现。毕竟物证是客观的,口供可能更主观。
尸体是最重要的证据。即使凶手被抓,但尸体没有找到,或者尸体已被发现,但不能确定是受害人本人的,也不能直接定罪。《洗冤集录》第二卷有这样一个案例:少年被歹徒杀害,尸体被扔进河里。很久后,歹徒被抓住,对此供认不讳。官府根据供述发现了少年的尸体,但尸体已被水流侵蚀成了无法辨认的骨架。在南宋有犯罪嫌疑人口供就可以定罪了,但是宋慈认为还不可以,可能存在巧合。最后,根据少年亲属所说被害人“龟胸而矮小”的特点,确认尸体确系少年无疑,官府才对歹徒定罪量刑。[5]49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宋慈对证据的客观性和唯一性的重视。
2.注重程序正义的法律思想
宋慈重视检验的程序性。在《洗冤集录》中,他详细记录了《宋刑统》等法律里规定的司法检验程序条文,要求检验官员严格遵守。此外,他还要求检验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
首先,检验官吏的回避。《洗冤集录》记载:“诸检……差无亲嫌干碍之人。”但凡检验,需要差官的,应当差遣同案件没有亲故嫌怨关系的人,防止他们因为亲故嫌怨关系弄虚作假。
其次,接见人员的回避。“不可接见在近官员、秀才、术人、僧道……”官员、秀才大多在当地有一定的权力或者势力,术人、僧道更是活跃,其中不少靠招摇撞骗为生。不接见这些人,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被骗,先入为主;另一方面也是担心这些人参与案件,招惹是非。
再次,留宿回避。检验官遇到需要过夜的情况时,“须问其家是与不是凶身血属亲戚”,如果不是,才可以在那里休息,这样可以避嫌。否则,可能会出现凶手家属请托或者随行人员受贿的情况。
此外,检验记录保密。《洗冤集录》记载:“漏露所验事状者,各杖一百。”[5]20检验记录是案件审理的关键,不能泄露,否则会出现串供的可能,增加判案的难度。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不能泄露给行人,进行初检和复检的官员之间也不能见面和泄露检验记录。
二、《洗冤集录》法律思想的进步性
(一)“慎刑恤狱”思想有助于减少严刑峻法思想的消极影响
严刑峻法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酷刑”。先秦前实行的奴隶制“五刑”,除“大辟”外都是残酷的肉刑。汉朝“缇萦上书”后,中国逐渐开始废除肉刑,最终形成了由笞、杖、徒、流、死构成的封建制“五刑”,中国刑罚又向文明迈进了一步。但北宋中后期却开始出现了“重法”倾向。由于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频发,自仁宗时期开始,朝廷就在一些“贼盗”严重的地区实行重法审判。此后,“重法”地越来越大,南宋时期“重法”甚至成为了常态化的法律。[7]
更重要的是,“重法”地的“贼盗”首恶者会被实行特别严酷的刑罚。这些都是非常残忍的刑罚,其中有不少因为太过残酷早已被前代废止的刑罚,包括但不限于磔刑、醢刑、活钉、夷族和凌迟。比如醢刑,把人剁成肉酱,只在商朝纣王时期采用过;磔刑,分裂犯人肢体,杀人示众,汉景帝后已不再使用;凌迟,将罪犯千刀万剐;活钉,将人活活钉死,北宋独创。由此可以看出,宋朝时期严刑酷法的严重程度。而宋慈在《洗冤集录》中体现出来的“慎刑恤狱,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像一道温暖的光芒,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两宋时期严刑峻法思想的消极作用。
(二)重视客观证据思想直接否定了“罪从供定”的法律思想
“罪从供定”思想是指根据口供定罪,只要有被告的口供,就可以定罪。“无供不能定案”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诉讼证明思想之一。[8]因此,司法官们会各显神通,用各种手段获得口供定案,比如西周时就出现了“五听”断案的方法。但更多的官员会选择刑讯逼供来获取口供。一是因为古代技术手段不足,常常出现疑难悬案;二是有些司法官断案能力不足,只能选择刑讯逼供。
由于刑讯逼供易产生冤假错案,中国历代统治者会对刑讯逼供进行法律限制。比如宋代,法律规定了严格的刑讯逼供程序,违者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南宋这种情况更明显,宋慈的老师真德秀就说过:“今之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关节用刑”。[9]这是“罪从供定”思想导致的,违法刑讯已成为直接影响南宋司法公正的社会顽疾之一。
在《洗冤集录》中,宋慈表现出不信任口供的态度,认为尸体检验更为重要,这是对中国古代“罪从供定”原则的直接否定,不再把口供视为刑事诉讼的首要证据。他要求司法官员按证据办案,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先进的证据理念,对后世司法官刑讯逼供的情况有着较大的遏制作用。
(三)重程序思想改善了中国古代片面追求实体正义的公正观
自汉代董仲舒提倡“春秋决狱”开始,儒家思想慢慢成为了审判的指导思想。儒家对“和”的追求,让司法官们认为:比起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更重要;甚至为了实体正义,可以忽略程序正义。此外,古代老百姓对事物单纯的善与恶、好与坏的价值评价也会影响司法官们的审判原则。老百姓认为:即使程序正确,但判决不合正义观念的,绝对是枉法裁判。[10]因此,追求实质正义更有利于司法官们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所以,中国历代司法官们大都更重视实体正义。
但宋慈不同,他非常重视程序公正。他在《洗冤集录》开篇就列出法定的各种检验程序,还设计了一整套检验程序,要求司法官严格遵循。宋慈反对对实体公正的片面追求,这在当时乃至后世都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法律理念。他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影响到后世,改善了中国古代片面追求实体正义的公正观。
三、《洗冤集录》的现代启示
(一)“司法为民”的司法理念
宋慈始终秉持着“以民为本”的理念。在检验中,他反对滋扰乡众;在断案中,他坚持“民命为重”。宋慈的这种司法理念和司法实践,实际上就是解决人民群众合理合法的诉求,依法惩治各种刑事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符合现代的“司法为民”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
(二)“不敢萌一毫慢易心”的职业道德
南宋时期,吏治腐败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这样一个官场环境下,宋慈作为朝廷官吏,仍然坚持着清正廉洁、高尚正直的官德。他号“自牧”,用以时刻警醒自己:身居高位,不忘谨慎。他廉洁自守,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对随从和下属也要求严格。他一生四任“提刑官”,没有成为一位只会用刑、拍惊堂木的官老爷,而是不停走访,倾听民声,平反冤狱。他深知,断案要“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他的以人为本、廉洁自律的司法精神,赢得了当时人们和后人的尊重。这种“不敢萌一毫慢易心”的职业道德,对于加强我国公务员的教育,树立公务员的官德,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三)重证据的“疑罪从无”司法理念
在“屈打成招”“疑罪从有”为常态的中国古代,宋慈无充分客观证据不结案的“疑罪从无”思想简直是一股清流。[11]直至现代,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才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原则。然而,近二十年来,在“严打”“稳定压倒一切”的影响下,“疑罪从有”和“疑罪从轻”仍有存在,比如“余样林杀妻案”“呼格吉勒图杀人案”“张高平叔侄强奸案”“陈满放火案”等案件。
在千年前的南宋,宋慈打破了唐朝和宋初“重口供、轻证据”的格局,以尊重生命、求真务实的态度,反对刑讯逼供,主张案件必须要通过客观的司法检验获得充分、真实的客观证据后才能审判,坚持“疑罪从无”的理念,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现代社会规定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指导”司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四)注重程序正义的司法理念
宋慈十分注重检验官的职业操守,坚持“雪狱禁暴”,反对审理时一味的”大刑伺候”,在《洗冤集录》多处阐述了司法检验中的纪律与规矩,一再强调“回避”的法律要求,这是一种尊重和重视程序正义的理念,体现了现代社会“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司法公正观。
宋慈作为世界法医学鼻祖、中国古代司法文明的丰碑,自南宋以来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崇拜。他在《洗冤集录》中所体现的法律精神逐渐成为激励人们追求公平正义、探索法治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继承和弘扬宋慈精神,在当前不仅具有法制建设的意义,而且具有发扬地方文化和官德文化等的多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