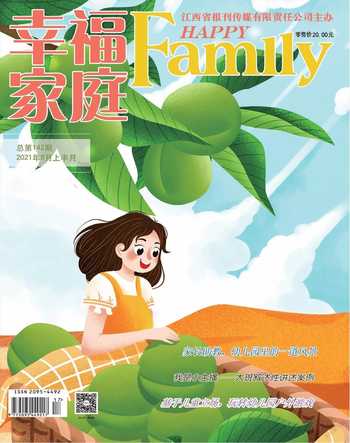美学微探《马缨花》,做“对”文本解读
周佳
本文从美学角度解读季羡林的《马缨花》,并从解“其人其文”“其时其境”“其真其妙”三個维度阐释正确解读的注意点。
《马缨花》是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本色天然,秀色内含”的散文,以“朴”与“真”的笔调,借马缨花为媒介,追忆过往岁月,并通过抒发对“光”与“影”中马缨花的不同情感,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珍惜。
13年前,“我爱上了马缨花,把它当成了知心朋友”。十三年后,“我从此爱上了这光中的马缨花”。是什么导致作者对同一事物的情感发生了转变呢?笔者借审美学的观点,以文本为依托进行探讨。
审美感受是人对美的事物的关照,即被审美对象可感的外在形式吸引,凝神关照而不旁骛他涉,进而触发情感。13年前与后的马缨花——审美的客观对象,是否发生了变化?13年前,“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一团团的红雾”。美艳动人,芳香醉人,充满着生命的活力。13年后,依然是“绿云红雾飘满北京,给首都增添了绚丽与芬芳”。色未变,香未改,审美对象依旧抱有美的特质。
物未变而情已改,何以?美固然不依赖于个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但一个审美对象之所以能引发人们的美感,并不仅仅由于其某些自然属性,而是透过审美对象的可感形态,看到审美者的本质力量,关照于个人的审美素养、审美心境及人生经验。正如月之阴晴圆缺,常常成为人们悲欢离合的象征,这是因为人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了月的身上,不过是在欣赏“自我”,欣赏一个“客观化的自我”罢了。国画大师齐白石在概括自己丰富的审美实践经验时曾说:“庐山亦是寻常态,意造从心百怪来。”大概就是这层意思吧。
那么,13年前作者为何爱上马缨花,观赏者在欣赏一个怎样的“自我”呢?“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我就觉得很不寻常,甚至有感激的心情了。”这句话或许可以告诉我们答案。作者强调“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时候”,作者曾说那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京城一片黑暗”。从发表时间推算,文中所写的“十三年前”大约在新中国诞生前,当时社会经济全面瘫痪,社会一片混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47年,作者从德国留学归来,在北大任教,寄居在一个很深的院子里(据考证这里曾囚禁过很多忧国忧民的志士,明朝时期是东厂所在地),这是一个很深的大院子,三面走廊,天井里遮瞒了树枝,充满着阴森凄苦的气氛。作者在文中写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一点活气。寂寞像毒蛇似地偷偷地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此时此刻,充满生机的马缨花盛放在“古墓”之上,盛放在孤独寂寞的作者的世界里,它已不仅只是美丽的皮囊,更是诱发作者联想和情绪反应的触发点。作者将自己渴望朋友、互相慰藉的情志转移到了马缨花身上,与它心物两契,生成了情感上的共鸣,这便是马利坦所谓的“隐约的意识”,也就如西方美学所说的审美移情。于是,作者“爱上了”马缨花,把它当作陪伴自己的知己伙伴。正如《囚绿记》的作者陆蠡,他为何囚“绿”,为何在心爱的“绿”渐渐娇弱枯萎时仍然不肯释放,原因在于“绿囚”与自己的命运、气节相似,留在身边聊以慰藉。
十三年后,“马缨花依旧笑春风”,然而作者却隐隐约约感到与记忆中的那些有所不同。客观对象依旧没变,改变的是观赏者的心境。作者曾写道:“1949年迎来了解放。当时我同北大绝大多数的教授一样,眼前一下子充满了光明,心情振奋,无与伦比。我觉得,如果把自己的一生分为两段或者两部分的话,现在是新的一段的开始。”怀着这样的心境,满怀豪情壮志的作者再见马缨花,便觉得它“仿佛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在深夜中,也觉得它们生机勃勃,同灯光竞赛,同明月争辉——“是更可爱的光中的马缨花”。
说到“更可爱”,自然有对比,没那么可爱的自然是给予自己安慰的记忆中的马缨花。于是,作者扩大回忆范围,发现同记忆中的马缨花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黄昏,就是夜雨,否则就是迷离凄苦的梦境……从来没有见过哪怕是一点点阳光。作者想起了与客观对象相联系的东西,想起了当时社会的混乱,想起了自己的孤独与困境。拴上了这些“影子”,美好的马缨花也就不那么至善至美了,自然不那么喜爱了。正是这些“影子”,让当年的作者爱上了司空见惯的马缨花,而如今恰恰成了“嫌弃”它的罪魁祸首!
看来,主体对某一事物或迎或拒,采取正面肯定或负面否定的情感态度,还要取决于事物是否契合主体需求——“欣赏的不是物,而是一个客观化的自我”。
文本解读是解读主体调动创造性,再创和建构文本的过程。正如伊塞尔所说:“文本的规定性严格制约着接受活动。”这种“解读创造”必然受到解读对象即文本的制约。解读的翅膀不可任意飞越文本所不能及的界域,否则将导致解读的谬误。因此,正确解读文本,即通过文本的整体感知,跨越时代的隔阂,达到读者与作者心理上的同质性。
李白与杜甫,一绮丽飘逸,一沉着典雅;巴尔扎克与雨果,一形象真切,一淋漓酣畅……每位优秀作家的作品,都贯穿着相对稳定的、鲜明清晰的个性,形成了一定的文风。了解作家的文风,对其作品产生全面整体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解读某一具体文本,才能更好地抓住文本的价值所在,把握其最广泛的普遍价值和区别于同类作品的独特性。因此,解读文本必须站在一定的高度,站在孤立单一的文本之上,解读作者 “其人其文”。
在内容上,季羡林先生的很多散文都表达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强调抒发真性情,抒发深沉的乡土情感和赤诚的爱国心;在形式上,则更多地表现出语朴情醇的艺术风格,尤其注重运用意象的选择与意境的构造。《马缨花》一文则借“马缨花”这一意象,表现了作者在“暗无天日”社会的愁苦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珍惜,语言平实质朴而内含秀色。
解决了作者“写了什么”,就要探讨作者“为什么写”的问题。这与作者写作时或文本涉及时期的环境、心境有关。任何一个文本传递给读者的信息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是作者思想的全部,也不可能是对社会现实的整体反应。脱离时代背景的解读,难免会造成对文本理解的不当或偏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正确的文本解读离不开对写作背景的了解,以历史观的角度关照时代文化,开展“由标即本”的解读。如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待《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她“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出场方式是热情、爽快的直接体现,却无法理解贾母为何称她“泼皮破落户”。但回到以“三从四德”作为女性美德的时代文化背景中,她则不符合“服从柔顺”标准,是当时社会的“另类”。
《马缨花》这篇散文主要涉及两个时间,即1962年——文章写作和发表的时间;13年前——作者寄居在那大院子的时间,推算大致为1949年前夕。解读作者在13年前后对马缨花产生的不同情感,必须了解这两个时期作者的处境和社会背景。查阅相关资料,在《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中,作者提及了这两个时期:新中国诞生前夕,作者回到一片黑暗的祖国,自己钟爱的项目又缺乏资料;新中国诞生后至1965年,作者悠闲自在,是新中国诞生后心理负担最轻的一段时间。不同的社会环境带给了作者不同的心境,自然反应于客观对象的情感也会有所不同。在《马缨花》中,全文贯穿了作者抒情的句子,如“我是不是有孤寂之感呢?应该是有的”“我爱上了马缨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我也爱藏在我心中的这一个光与影的对比”。这些直抒胸臆的句子能很好地帮助我们解读作者的情感。
接受主义美学认为,文本解读是意义再创和开放性的动态建构活动,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随时空的推移、时代情境的变化而发展。解读者的文化积淀、背景知识、阅读经验、人生体悟都会使文本解读着眼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风景。解读文本要发挥读者主体的艺术创造性,建立自觉的期待视野。如戴望舒的《雨巷》,有人认为其抒发了诗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所感到的迷茫与惆怅;也有人认为其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在追求的过程中诗人情绪的微妙变化。
文学是人类心智的产物。文学作品尤其是以抒情为主的散文,往往蕴含着作者的心理倾向。笔者将《马缨花》这篇散文置于审美学的角度,探讨个体对事物情感变化的触发点和心理缘由。如上文所言,美感是对人本质力量的自我关照,季羡林先生对马缨花情感变化的实质也是如此:爱它,因為它给自己带来了安慰,因为需要它;不那么爱了,因为这时候的作者需要能更加满足自我情感的对象。
文本解读正日益由“作家—作品”的二维理解转变为“作家—文本—读者”的三维立体视角,读者、时代、心境、情绪等多种因素导致不同个体的解读差异性加大。但无论开放性、再创性有多大多新,都不能缺失对文本的正确解读这一前提。
(作者单位:江苏省太仓市高新区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