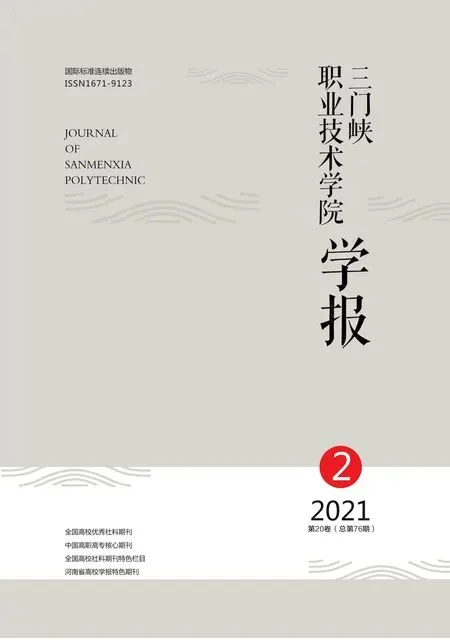乾嘉之际黄河岁修帮价筹款问题探究
——以摊捐养廉银为例
◎张 通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河政是清代之要政,基于保民护漕的需求,清入关伊始就开始重视并尝试治理明末因时局动荡而失修的黄河。清代的治河策略有诸多承续明朝之举,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束水攻沙”之策,东出豫西山地之后的黄河河道,在堤坝的束缚下,一线而行。受东亚季风气候的影响,黄河流域降水年际变化与年内变化均较大,夏半年的降水集中,黄河每年均需经历汛期水位上涨之考验。在地上河发育的黄河下游河道,河堤修守至关重要,故有“河防”之称。河堤的建造与修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清廷对于堤坝的修护也非常重视。黄河大汛之时,集中人夫抢险修堵,防止险工漫溢决口,这是黄河治理最关键之时。相对于大汛防堵,岁修是一项虽不起眼但相当重要的黄河修守工作。自顺治朝河工初创之后,岁修就成为黄河两岸堤坝重要的日常的维护工作,清人对岁修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河工修防事宜,首重岁修,次则抢修”[1],直至清末,黄河岁修制度历经沿革而始终未废,足见其在黄河修守中的基础性与重要性。
河堤的修护,需要治河之料物,石块、砖块、土、秸料、麻料、柳枝、芦苇等软硬材料需准备妥当,备于河堤之上,这样才能在黄河大汛之前,将堤坝薄弱处择要修补坚实,同时不至于在面对桃、伏、秋三汛突发涨水情况时无计可施。故有“堤工全恃修防,而修防专资物料,是物料为河工第一要务”[2]之说。采办物料是有清一代黄河岁修之基础而关键的任务,每年需定时定量采办料物运送存贮于河堤。在传统时期,这是一项并不简单的任务,物料之采买、运送、交料、存贮均需要统筹办理,尤其是在料物采买和运送均要用白银解决的背景下,黄河岁修便尤为依赖稳定充裕经费的支撑。在清朝“量入为出”的财政收支思想和实践下,河工岁修用银也逐渐形成一套定额用银管理制度。这种定额的规定,在面对河堤规模逐渐扩大,料物价格不断上涨等情况时,经常会面临令河务人员苦恼的经费短缺问题。为维持定额的管理办法,清廷在岁修例价不敷之时便通过各种临时途径筹集资金作为例价之外的帮价补贴岁修办料之用,清代前中期可见的帮价银经费来源有不同区域地粮内摊征、各级官员养廉银扣抵、发商生息、河工捐等。上述不同类型的筹款办法及其实际运作与效果,也对清代治河工程的筹办及黄河治理效果产生直接影响。
清代河工经费问题在学界受到一贯关注,从河工经费概述到具体各时段河工用银规模均有相关探讨。在此基础上,近年关于清代不同时期河工用银制度运作的探究深化了对清代河政问题的认识,基于档案材料的挖掘,清代东河帮价摊捐养廉的问题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学界已经注意到清前中期河工用银定额化的趋势及乾嘉之际维护定额之努力的失败①上述综述涉及研究分别如下:岑仲勉.黄河变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杨国顺.略谈明清两代治河[J].人民黄河,1981(1):64-67;陈桦.清代的河工与财政[J].清史研究,2005(3):33-42;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水利史研究文集[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6;裴丹青.清代河工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6;潘威.清代前期黄河额征河银空间形态特征的初步研究:以乾隆五十七年的山东为例[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4):5-12;潘威.河务初创:清顺治时期黄河“岁修”的建立与执行[J].史林,2019(3):77-87+219;潘威,张丽洁.晚清财政转型下的河务运作:以河银制度为中心[J].安徽史学,2020(3):52-60;潘威,张丽洁,张通.清代黄河河工银制度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通过对河工帮价摊捐养廉银相关问题的探究,可对清代河工用银管理及实践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清代黄河岁修办料帮价银的产生与筹款途径
埽工是清代河工中护岸捍水一个主要方法,“岸系积土而成,溜逼堤根,时虞汕刷,于是就堤下埽,以御水势”[3]。无论黄河日常岁修还是堵口大工,都需要埽工护堤御水。埽工以其材料不同,可以分为竹楗、柳埽、石埽、秸埽、砖埽、灰埽等类型,作为日常御水护岸的岁修工程,黄河河工最常用的是秸埽,其具体做法为“椿绳联结柴薪而成”[3],豫东两省地多务农,所出产的秸料是制作秸埽的主要材料。“河工料物以秸柴为大宗,向例于秋令新料登场之后即约计明年岁抢修应需料数,预为发银购办,勒限年前全数到工。先由该管道员验报,河臣再行复验,方准春修动用”[4]。
豫省河工需用岁修秸料,在顺治朝为分买物料派运②顺治十一年户部给事中苏文枢题陈中州苦累三事……至分买料物而借名多派运。。至康熙末,依然是分买派运的办法采办料物,“河南河工需草束甚多,俱派各县办运,每草一斤开销正项一厘,再各县采买价值以及运送脚费大约秫秸谷草一斤需费三四厘不等。合计每县一年办草数次,每次不下30万斤,除正项外,每运约赔五六百金,统计一年约赔数千斤”[1]。因正项开支少而办料需费多,此时的派买之法给各县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又因此时办料总数尚无定额,易滋生累民之弊①康熙五十九年复准嗣后一应购买物料严饬河务官协同地方官亲身赴买,仍取具地方官并无累民等弊印结送部。如被累之百姓具呈出首许该地方官详报总河督抚据实题参。。雍正十年(1732)议定河工采买秸料,每垛重五万斤,每斤价银九毫,岁需之数由沿河州县按地亩多寡领价派买,听民自行交工[5]。由于雍正年间实行火耗归公,地方无款摊赔运脚之费,只能让百姓自行运料交工,虽曰“稍借民力”,其实还是压缩正项开支的例价办料经费,将治河的经济负担部分转嫁于沿河各州县。
至乾隆前中期,已有料头专门包办民间运料之事,无时无力亲自运料之民人被迫出数倍之高价完成摊派的运料任务,沿河32州县之民以办料为累。乾隆三十年(1765),河南巡抚阿思哈在实地访查洞悉民情后,尝试“于秋成后物料价平之时查明不能自运之户,选委佐杂干员领银就近采买代办运交工”[1]。试行有效后,阿思哈奏请豫省河工岁料采办改之前的沿河州县按照闾阎地亩多寡派买为官为代办,在减轻民间载运料物苦累的同时,采购转运料物这一活动也开始与定时定量购买、雇佣民夫等经济活动密切联系。治河秸料由民运改为官办伊始,负责采办的官员发现,原来规定的额定九毫例价,仅为采买秸料之价,并不包含雇夫运送的运脚费。于是在官办料物开始的乾隆三十年(1765),阿思哈奏请“每斤加运脚一厘,计加银50两,合每垛例帮价共银95两,由司库拨给,委员采办以免民间购运,例价作正项报销,帮价于沿河三十二厅州县按粮摊征还款”[6]。官为代办需要清廷投入更多的经费,这在乾隆中期国库充裕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但不可忽视的是,官方负责采办料物这一活动,过程相当复杂,需要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道路有远近、工用有多寡、车运有忙隙、天时有阴晴……新料尚未收获,价值增昂……八月以后新料渐集,价亦稍减”[6],采办秸料受到转运距离、料物价格等方面的影响,经费投入的波动性明显增加,这一实情不仅为河工经费的估报奏销带来各种不便,也为之后办料例价不敷埋下了伏笔。早在官为办料之前的乾隆四年(1739),就有因“(秸料作物)岁欠昂贵,每束(十斤)增银五厘”[1]的前例,之后更是常被河臣引例奏请临时增银办料[1]。乾隆三十年(1765)前按地亩派买时稳定的例价就能解决的河工岁料问题,因官方介入增加,买料与输送一系列过程均需经费投入,在面对各种复杂因素时,例价之外的帮价对于黄河岁修办料越来越重要。
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后,“险工较多,用料日繁,帮价递增”[4],沿河州县需要摊征的帮价银也愈益增多,渐至不能支付,拖欠问题开始出现。沿黄运之州县本就属易受水灾影响之地,正项钱粮在灾荒之时尚多蠲缓,岁料帮价摊征之项更是无法保证[6]。乾隆四十三年(1778)河南巡抚毕沅奏请将河工帮价积欠银两,连同之后岁需帮价银,在豫省“通省摊征,众力所出无多,日久相安,工无缺乏”[6],这个建议获准,然甫经推行却逢乾隆五十年(1785)收成歉薄,又遇五十二年(1787)睢州漫口,大工需加价银近130万两在全省摊征[7],前后积累,需摊征之项繁多。因“当时既未严定章程,将催征不力之员照正项钱粮之例参处,州县未免忽视而逐年积累,辗转加增”[7]。帮价银摊征无着,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理库项,因摊征帮价未能年清年款,经“大学士和珅议令裁革,只准照例价仍交沿河州县购办”[6],岁修办料只剩45两例价,实属不敷。经河南抚臣藩司共同商议,每年岁料以5000垛为率,每垛加增帮价银25两,帮价银共需125000两。
二、河工帮价摊征养廉银的出现与推广
关于豫省河工帮价所需125000两白银的来源,乾隆五十七年(1792)穆和兰奏请将之作为定额经费从地粮正项内开销,但这个比较合理的建议并没有被清廷采纳[4],仅九毫之例价不足办料,“若交民间办运既滋派累之端,若另州县贴赔又必致亏挪之弊,公同筹议,唯有仿照抢险料物捐廉加价成案详明在于通省知县以上各官养廉内公摊帮贴,约计每年办秸五六千垛,需帮贴银十四五万两不等”[8]。摊捐养廉银由此成为豫省筹集河工岁料帮价之法。嘉庆四年(1799),河南布政使吴璥署理东河总督,甫上任秘加体访,认识到“若非请增运费,非贻误工需即暗增亏累,所关匪细”[8],于是再次奏请将十四五万两之帮价银于豫省每年三百余万两地丁银外加以摊征,但这个建议被户部议驳,吴璥本人也被交部严加议处。
与豫省紧邻的山东省,在黄河岁修料物采办方面,有诸多相似的处理办法,“每年于秋汛后就各该处工段形势缓急由司道会议应办垛数,筹定例帮二价发交厅员采办”[9]。最迟在嘉庆初年,例价之外每年都需要一定数量的帮价津贴银,“自嘉庆六年起至九年止,每年动支津贴银15500至18000及22600余两不等”[9]。与豫省存在的岁修规定例价额度无法囊括每年办料实际所需,以及帮价经费无法列入正项奏销的问题相似,山东例价之外的帮价银始终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东省每岁必须之项如黄河岁料帮价及捐办军需津贴战船并归还睢工帮价等款,每岁约需银二万四五千两,无款可动,均应另筹”[10]。而另筹的一个主要办法,与豫省相同,也是摊捐官员养廉银[10]。
东省除应办黄河岁料,还需维护境内南北贯通的运河之畅通。运河在山东省内绵长1200余里,“中有济宁、汶上、临清三处塘河因承汶泗诸河山泉之水,携沙而来,水去沙停,日积月淤,是以每年一小挑,间年一大挑”[11]。在乾隆初年已形成岁挑成规,每年在漕船往返回空过竣后,委员查看运河受淤之厚薄定土方之多寡,确定所需人夫之多少。“大挑之年例用募夫银17000余两,小挑之年用银2800余两,合计两年用银20000两零”[12]。现实情况是,应挑河段渐多,经常需要在额定数量外添募人夫,故这笔定额的大挑小挑例用募夫银经常不敷支用。“历年挑工岁料等款并无定数,按款动用每多短绌,即于司库闲款内借支”[13]。嘉庆四年(1799)山东巡抚陈大文因东省岁挑运河例价不敷,奏请津贴,每年“二三万两,准其一半在耗羡项下动用其余一半抚藩臬司道员所得养廉名下坐扣归款”[14]。在巡抚两司五道三成养廉外,每年动支耗羡银15000两[10],以此凑还借垫司库款项。然而运河岁挑例价和津贴之外,还是经常会超出规定之数,自嘉庆六年(1801)至十年(1805),运河历年挑工超过额定数量的借垫银已积累了44000余两[13]。
豫、东二省所在的东河区域为清代河工要地,除常例黄运岁修物料经费需要筹集,还需要承担黄河泛滥而致的另案大工经费带来的压力。虽然清朝有规定:“历次办理堵筑漫口大工需用料物繁多,向系循照成案于例价之外定有加价,例价销六赔四,加价归于通省州县分年摊征。”[5]然而一旦黄河决口,黄水肆虐,灾民呼号,作为救灾之策,蠲免钱粮是救灾的一个重要措施,增加民众负担的摊征之策往往是迫不得已才会使用的办法。同时作为对黄河漫溢决口相关各级官员的惩罚,黄河另案大工数量巨大的夫工办料帮价银之一部分也需要在其养廉银内扣抵。嘉庆五年(1800),山东巡抚惠龄奏请“将府州县三成养廉扣还曹工帮价”[10]。嘉庆十年(1805),山东仍在归还协济睢工(嘉庆四年)帮价银①嘉庆十年,归还协济睢工帮价银一万二千六百余两均于司库闲款内借支。,这笔经费需要在司库闲款内借支,最终还是以扣捐养廉银的方式填补。嘉庆十五年(1815)吉纶奏请将曹工帮价银于豫省展征十年还款[15],这个试图将超出规定奏销额度的治河经费在河南全省摊征的建议,被嘉庆皇帝认为是对灾民巧取横征,吉纶因此被申斥,所请不准行,只能继续用官员捐廉的临时办法来解决。
河工办料例价不敷的问题,虽然最先出现在豫、东两省,但并非东河独有的问题,这一情况在清代中期的南河同样存在。嘉庆五年(1800)南河邵家坝堵口,南河总督吴璥奏陈增加办料帮价:“现在办理绍工采办料物最为紧要,不得不议加帮价以期妥速集事,而所帮之价既断无报销正项钱粮之理,江省又不可创起摊征之例,唯有仿照豫、东两省各官捐廉成案事尚可行。”[16]而南河另案大工的帮价银同样无法在正项开销,只能仿照东河摊捐官员养廉银作为经费来源。
三、摊征养廉解决河工帮价需求之弊端与影响
养廉银制度在雍正时期逐渐推广后,各省存公耗羡银逐渐演化为“以备公用”①养廉之设,自各省耗羡存公,以备公用,即其赢余,定为各官养廉。的地方公共事务经费,除了发放官员养廉,还用于弥补地方亏空[17]。豫、东两省河工帮价需银无法从正项中开销,只能动用官员养廉银和存公耗羡银。但是黄河横跨多省,岁办河工需求繁多,仅河南省岁修帮价银125000两这个数额,已占豫省道府厅州县养廉银的七成以上,再加上豫省其他的一些杂项公共开支亦需摊捐养廉银,远超过了较为普遍认可的养廉摊征三成之数,这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依靠养廉银作为办公经费的地方衙门事务②臣等核计道府厅州县养廉以125000两之数摊扣岁料帮价已在七成以上,再加摊赔军需核减三成是养廉业经全数坐扣,无银可领,此外尚有弥补从前亏缺及应摊杂项银两,实不胜其赔累,其河工丞倅养廉本少自扣缴七成帮价每年所领仅止一百数十两,办公亦属竭蹙。。
豫、东两省的官员养廉银,大部分都用来填补河工帮价的需求,以至于嘉庆十六年(1811)河南因藩库垫款过多,“奏请将州县养廉办公银两解司支发抵扣”[15]。直接将州县养廉银解交司库的做法通常在临时需要大量扣抵官员养廉银的情况下出现,但对此时的豫省而言已属常态。就在同年,山东巡抚同兴也奏请“将东省州县佐贰等官廉俸等项仍解司收放,备扣垫款”[15]。
河督与豫省抚臣皆意识到河工帮价摊扣过多养廉银的弊端,“州县欲其廉隅自失禁绝亏挪,河厅欲其实力急公不致浮冒,均须免其扣廉,俾公用有资始足杜籍口而收实效”[18]。山东巡抚惠龄也因东省捐廉过多而担忧“不肖州县藉称办公不敷致有扰及闾阎之弊”[10]。
以官员养廉银抵扣河工帮价,不仅影响地方办公,易滋浮冒,更关键的是地方养廉银有限,无法覆盖不断加增的河工帮价支出。豫省河工岁料帮价所需,“自嘉庆七年(1802)起至二十二年(1817)止,各官捐解帮价除已完外,尚积欠银80000余两”[5],经费不敷,河工又不能骤停,只能设法挪借。“按款动用每多短绌即于司库闲款内借支”[13],借垫愈积愈多,无款归还,成为一个困扰地方财政的难题。“国家经费有常,年复一年借垫愈多,无项归款究属悬宕,终非通盘筹计核实办公之道,必须筹出款项以备补苴方有裨益”[13]。经费短缺势必影响到治河料物的采办,“采办料物,水土之工物料最难。虽上有经划之总理,下有谙练之属员与子来之兵役,而所需不给,以至万夫束手以待,其误事非浅鲜也”[19]。
自河工帮价产生之后,始终无法在正项钱粮内奏销,各种临时经费筹措办法虽然不动用“皇粮国税”,但因为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易产生各种弊端。“若令地方官捐廉办理既恐藉端科派,若令民闲协济又恐扰累闾阎”[15](卷169),固定区域地粮内摊征又经常会面临拖欠问题,摊捐官员养廉银同样不是经久之计。黄河岁修和运河岁挑均为东河每年例行之工,除非找到一个稳定的经费来源,否则不仅无法填补黄河岁修帮价的亏空,给地方财政造成持续压力,也对黄河治理中最为重要的日常修护不利。
四、小结
清代摊捐官员养廉银作为水利事业经费,不仅存在于东河与南河河工,在江南海塘与地方水利中均非罕见。官员养廉银作为地方存公耗羡银的一项重要开支,在地方事务无款可筹时,成为补贴地方必办事务如水利、官学、灾赈的经费来源。但如黄河河工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岁修采办需要稳定持续经费投入,虽每年需费相对于地方正项收入而言数额并不多,但积年累月总数并不少,同时另案大工之办料经费更是数额惊人,仅办料帮价经费需求而言,非一省一地之存公耗羡银可以支撑。
清代河政腐败的问题,是受学界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①贾国静.河堤上的腐败:乾嘉年间河务“全员贪污”[J].中国人大,2016(21):54-55;金诗灿.清代河防腐败问题及其治理研究[J].史志学刊,2019(3):4-9.,河政腐败这个表面现象背后,是河工用银供给体系制度设计存在的问题。治河工程中至为关键的秸料采办,并没有持续稳定的经费供给。正项开支的例价之外,帮价银经常无款可筹,官员屡次请求摊征而不被允许,“向来办理报销时,因将例外支销之款于工段丈尺内通融开报,以免部驳”[15],通过虚报工程量来保证基本的岁修办料经费,这套潜规则也成为冒河政腐败之滥觞。“工员捏报浮开,官吏勾串司书,通同舞弊”[15]亦是屡禁不绝,这也正是清代河政腐败的深层原因。
由于自然方面黄河含沙量大,长时段“束水攻沙”之策导致下游地上河发育,河口淤垫,水文情况日益复杂,河工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同时粮价、钱价增昂等经济方面因素都是造成清代河工办料用银不断上涨的原因。面对不断上涨的河工岁修经费,清廷也认识到“工程物料必应实用实销方可以杜工员侵冒之弊,而价值必有确据可查,钱粮方不致虚靡”[6]。但清廷并没有从财政层面为河工用银开辟一条持续的经费供给渠道,而是加大对治河官吏之监督,“随时查访”“严惩一二以儆其余”[15],“随时秘访严查,倘有不肖官吏多征重征等弊,一经查出或经告发,即当按律严参究办”[6]。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于黄河治理无益。嘉庆皇帝甚至希望通过令州县“一月内按日查报”[6]秸料时价的办法来掌握河工办料所需经费额度,这一操作起来纷繁倍难的想法当然无法付诸实践。在嘉庆初年,山东省开始用发商生息的办法解决帮价银需求,豫省也紧随其后奏请照例筹款发商生息,然而这依然是一种临时性的经费筹措办法。清前中期以来一直维持的定额河工用银管理体系,因定额不敷支用,又缺乏协济经费的渠道,故在具体河工运作中出现诸多问题,这也影响了清代黄河的实际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