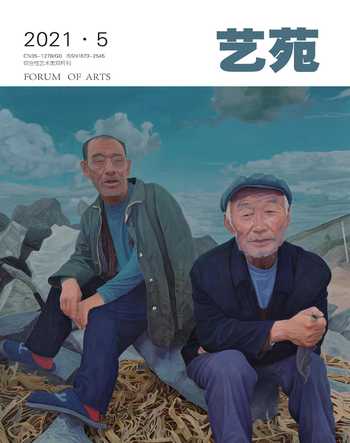从鲍德里亚的艺术思想看沉浸式艺术展
陈思函
摘 要: 随着5G通讯和全息投影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沉浸式艺术展览成为技术介入艺术创造的积极尝试。作为现当代艺术在消费社会下的呈现形式之一的沉浸式艺术展,鲍德里亚的艺术观点为理解其本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消费社会中,沉浸式艺术展成为艺术符号化的典型表现,是虚拟技术构建的拟真世界。技术改变了艺术的呈现形式与呈现内容,人们的审美方式、审美过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消费社会中,艺术价值的消失并不代表艺术的终结,而要在接受艺术平庸的过程中让平庸成为美感。
关键词:沉浸式艺术展;鲍德里亚;艺术终结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计算机技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一个由代码构成的数字世界,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被数字化、信息化。数字技术改变了艺术的表现形式与传播方式,使艺术与科技的跨界融合成为现实,虚拟化、数字化、多样化的艺术表达成为新的艺术潮流。沉浸式艺术展凭借着高专注性、高互动性、高愉悦感等特征成为近年来新媒体艺术中的“爆款”形式,其极高的商业潜力与“网红”效应吸引着众多知名度极高的艺术机构争相引入,也引发了对沉浸式艺术展极强的数字化效果下审美丧失与商业性增强的质疑与担忧。
鲍德里亚作为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之一,在他的《象征交换与死亡》《消费社会》等著作中对于消费时代下尤其是计算机符码参与的艺术发展进行了深刻分析,提出了关于“超真实”“拟真”“艺术终结”的观点。在“智能+”时代,随着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成熟与应用,以VR、全息投影等技术为特点的新媒体艺术正带领人类由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迈入鲍德里亚提出的“拟真时代”。由此,鲍德里亚的艺术思想尤其是他对“拟真”时代的分析对于反思当代媒体环境以及新媒体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与借鉴意义。本文基于鲍德里亚的艺术思想尤其是“艺术终结论”相关理论,分析5G与人工智能时代下沉浸式艺术展览的内涵,思考艺术展览从“距离式”到“沉浸式”所蕴含的审美转向,目的在于回答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下沉浸式艺术展览中艺术可能面临的“艺术终结”问题。
一、内涵分析:沉浸式艺术建构了艺术符号化下的超真实图景
(一)艺术符号化的极致呈现
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被符号价值所取代,同样,艺术的生产也成为了符号的运作过程。消费社会的符号化理论是鲍德里亚思想的重要基础。他认为,物质生产的空前丰富使人类社会进入到消费时代,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再是人们消费的第一目的,符号区分基础上的个性化才是主要目的。商品作为符号被消费,符号支配了人的消费目的与消费动机。在消费社会中,艺术的符号化与消费符号化同时出现。鲍德里亚承接了本雅明的观点,认为在大批量机械复制的背景下,艺术作品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孤本,艺术的“灵韵”消失了,艺术品的倍增和扩张使艺术成为与日常生活用品同质的商品,也就是消费符号,艺术的符号化由此产生。消费者在进行艺术消费或在参观艺术展览时,购买的也是艺术品背后的符号价值。消费社会中的艺术品与消费品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符号系统中的差异游戏,是符号系统中存在差异的一个个符号。这种符号价值是展示观众消费能力、阶级水平的符号价值,是展示观众审美趣味的符号价值。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鲍德里亚也举出了艺术家签名的例子来佐证艺术的符号化。消费社会中,艺术家签名的地位被格外凸显,签名不再是客观的、单纯的对艺术家身份的确认,而是成为了艺术家画作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签名甚至等同于艺术品。“在现代作品中,所签的名字总是与画作的内容浑然一体,他成为了一个构成要素,人们甚至可以设想一幅画作,它就在它的签名之中发现了自身,并消解了自身,只剩下了签名。”[1]94艺术家的签名成为确认艺术品差异性的重要符号来源,是符号价值最集中的体现。
沉浸式艺术展览通过精美的视觉图像构建了艺术消费领域的独特符号,充满视觉冲击力的图像成为了艺术符号化的极致呈现。通过声光电、VR技术等的配合,沉浸式艺术为参观者打造了一场绚烂、多元的观展体验,这种独特性与审美体验成为沉浸式展览的重要符号价值。以日本东京Team Lab艺术团队的作品为例,该团队致力于通过数字艺术融合艺术、科学、技术、设计和自然界,致力于打造富有科技感与艺术感的沉浸式展陈方式,其作品是沉浸式艺术展览探索的标杆。这类艺术展览的一大重要特征是在极富辨识度的视觉效果的基础之上鼓励观众拍照并分享至社交网络。Team Lab的系列沉浸式艺术展在国外图片社交网站Instagram上引起巨大反响,展览引入国内后与时尚社区平台“小红书”进行合作推广,据2021年10月检索数据,目前在小红书社区已经累积了超过1万篇世界各地Team Lab展览的看展笔记。在这样的观展氛围下,以Team Lab为代表的沉浸式艺术展览的符号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沉浸式艺术展览通过强烈的视觉效果甚至是预设拍照“模板”吸引观众进行拍照,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参与到沉浸式艺术所预设的符号体系内,符号价值得以生成;其二,沉浸式艺术展览富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增强了展览的辨识度与可传播性,彰显出沉浸式艺术展览独特的“文化资本”价值,激发了展览的“网红”效应,符号价值通过社交媒体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增强。在沉浸式艺术展览中,艺术的内涵退居在绚丽的光影之后,呈现着明显缺位状态。观众拍照打卡并将照片上传至社交网络的过程显示出了沉浸式艺术展览区别于其他展览的最大不同:绚丽的光影以及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图像成为沉浸式艺术的符号价值,观众沉溺于展览的视觉效果之中,艺术作品不需要对现实进行指涉,而是进行自我生产。
(二)拟真模式下的超真实图景
“拟真”阶段下,数字组建了存在的现场,虚拟优于现实而存在,社会呈现超现实的图景。承接对于符号的把握,鲍德里亚提出了“拟像”的概念用以表现失去了使用价值的空洞的“图像”符号。随着生产力以及价值规律的变化,拟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称为“仿造”,指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前的时期停留在初级仿造阶段的生产,依赖价值的自然规律;第二阶段称为“生产”,指工业革命时期生产无差别的生活日用品,依赖商品的价值规律;第三阶段也是目前所处的受符码支配的阶段,称为“拟真”,依赖价值的结构规律。[2]14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符号还能对应着某个现实,但是在拟真阶段,大众传媒、计算机、全息成像等高科技模擬手段大量生成拟 像、符号、符码,是对真实世界的极度逼真的模拟,符号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并脱离真实而存在,大量的符号在符号体系中自我生产真实,鲍德里亚把此时的现实称为“超真实”。[3]79
沉浸式艺术的“超真实”本质上是由数字化的虚拟技术构成的拟真世界,艺术不再反映现实,而是试图以模式化的操作取代现实。沉浸式艺术体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对于现实的模仿,而是在现实生活之外用符号构建出一个全新的“真实”世界。[4]29沉浸式艺术通过利用声光电等技术条件调动人的“五感”,并制造较为昏暗的环境而长时间吸引参与者的注意力,排除其它干扰。[5]47在这样的环境中,观众无法明确眼前呈现出的生动景观是真实还是虚幻,真实和虚假之间的界限不再明晰,真实与否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看到的与感受到的内容。这种虚拟影像不是摄影对客观事物形式上的呈现,而是由数字化技术、由电子计算机运算凭空产生的虚幻世界,是人想象世界的现实化,其本质是计算机程序编码。观众通过展览中个性化的观展方式在数字环境下实现了自我构建。
在这样的拟真环境中,艺术的创作机制也发生了变化,艺术创作不再依赖艺术家个人,而是一种运行机制,鲍德里亚被称为“模式”。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只有纳入模式才有意义,任何东西都不再按照自己的目的发展,而是出自模式,即出自‘参照的能指’,它仿佛是一种前目的性、唯一的似真性。”[6]98近年来,沉浸式艺术展览在国内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模式化的、爆发式增长的过程。2013年草间弥生《我的一个梦》展览在上海巡展并大获成功[7]79,此后“沉浸式艺术展览”便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迅速铺开。这些展览有着相似的运行机制:通过震撼的灯光、音效等技术手段增强沉浸感,引导观众拍照打卡并广泛使用社交媒体手段实现推广宣传,具有极强的模式化的特点。如果说草间弥生、Team Lab等团队的作品在沉浸式艺术展览中具有先锋开创性的作用,是“参照的能指”,那么后续涌现出的一系列沉浸式艺术展览则是参照草间弥生、Team Lab团队的模式化表达。
二、直面质疑:沉浸式艺术展原始的审美转向与艺术的再出发
沉浸式艺术是新媒体艺术发展过程中利用技术手段实现别样艺术展示的积极尝试,但是技术的介入以及沉浸式艺术展览的商业性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首先,是对于技术介入艺术导致的艺术性主体丧失的忧虑。目前的沉浸式艺术展览似乎陷入了过分依赖以视觉效果为代表的技术手段的怪圈,绚丽的视觉装置成为沉浸式艺术展览最重要的目标,也是吸引观众参观最主要的因素,展览背后的艺术内涵逐渐被技术稀释,部分观点认为这容易使艺术成为技术的附庸甚至走向消亡。其次,是沉浸式展览商业性与艺术性之间的矛盾。由于规模效应、沉浸效果等条件的影响,沉浸式艺术展览对于技术、资金等要素要求较高,现阶段国内的沉浸式展览大都是纯粹的商业性项目,日本Team Lab团队在上海无界美术馆的门票高达288元,造成大众对于沉浸式艺术展览过度商业化、盈利性的质疑。对于技术、艺术的结合可能造成的艺术主体性的丧失以及艺术的商业性等问题,结合鲍德里亚的美学思想以及“艺术终结”的观点,可以给出一个较为不同的看法。
(一)诱惑:沉浸式艺术展的审美特征转向
沉浸式艺术展览生成“激进的幻觉”,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鲍德里亚认为,当代艺术的审美幻觉正随着绝对清晰化的审美过程而逐渐消失,对此,他提出了作为诱惑存在的“激进的幻觉”[8]47概念,认为这是相比于审美幻觉体验感更加强烈的审美体验。他提出,“诱惑其实就是靠边或偏离”[8]49。沉浸式艺术展览以沉浸的方式诱惑观众从当下时空中迷失,从现实的生活轨道中短暂的偏离,通过逼真的视觉效果,取消了现实生活与虚拟空间的界限和区别,观众全身心投入到由数字艺术建构的世界中,极度逼真与体验感强烈的数字艺术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近乎原始的审美体验。从这个角度看,数字艺术的审美获得了全新的发展,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观看距离的审美体验,沉浸式艺术所产生的“激进的幻觉”带来了新的审美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与艺术的关系并非技术主导艺术或者技术取代艺术,而是在技术的推动下产生新的艺术审美体验。技术参与到了以沉浸式艺术为代表的数字艺术的创作过程,技术改变了艺术的呈现形式与呈现内容,人们的审美方式、审美过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二)平庸的美感:艺术的全新出发
艺术价值的消失并不代表艺术的终结,要在接受艺术平庸的过程中让平庸成为美感。在传统的观点中,人们赋予艺术以极高的审美价值,并热衷于解读艺术作品所指涉的现实情境。在传统观点中,艺术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崇高的存在,是感性情感的理性表露,认为背后总会有一个形而上的东西需要人们将艺术摆在高位解读。鲍德里亚否认了消费社会中艺术的崇高价值,也无需计较艺术本来的“灵韵”,艺术与商品别无二致,都是符号的表达。鲍德里亚在《艺术的共谋》中提出,当代艺术的气数已尽;同时,他也反对神化艺术的观点。在鲍德里亚看来,“艺术并没有特别的优越之处”[8]79,他将艺术摆在一种全新的状态,艺术作为商品与平庸而存在。在超真实的环境中,真实的消失导致艺术缺失了与现实的对应,再也不需要解释艺术背后的真实,艺术不再拥有形而上的特殊意义而沦为了现实的庸常,艺术头顶的神圣光环消失不见。成为商品的艺术改变了其固有的存在方式,给观众带来与传统艺术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鲍德里亚欢迎商品中“震撼的、陌生的、惊讶的、焦虑的、流动的、自我毁灭的、瞬时的、非现实的”因素进入艺术,艺术由此获得了新的发展。
从鲍德里亚的思路以及前文对于艺术内涵的分析可以得出,沉浸式艺术展览作为一种符号的存在,其背后的形而上的艺术内涵的确消失了。然而,艺术并不是本来就蕴含着价值的,应以一种更加平常的心态面对这种现象,冷静地接受艺术沦为庸常的事实,甚至当成艺术发展的全新契机,并从平庸中寻找一种新的美感,让平庸成为美感。[9]正如鲍德里亚所言: “如果商品的形式破坏了对象先前的理想型,那么无需通过否定商品的本质来尝试使其得以恢复。相反,必要的是——并且这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反常和冒险的诱惑之物——使这一断裂更加绝对化。”[10]240在“超真实”环境下,艺术不是消亡了,而是走向了一个新的开始。作为当代艺术的一种全新形式和重要发展方向,沉浸式艺术以高科技作为主要特征带给观众别样的艺术体验,是鲍德里亚观点中作为符号的商品性艺术的较为恰当的表达形式。当符号成为了一种常态,艺术的理念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鲍德里亚指出的,“我们不再相信艺术,而只相信艺术的理念”[8]46,艺术作为一种理念与思想共舞。因此,在充分利用科技带来“诱惑”体验的同时,沉浸式艺术也要在技术创作中增添更多的人文社会情感,避免在对感官猎奇过度追求的同时而忽略艺术的理念作用,为沉浸式艺术的未来发展端正方向。
结 语
沉浸式艺术展览在成为当下展览的热门形式的同时也饱含着争议与质疑。基于鲍德里亚的艺术思想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以沉浸式的形式获得审美感知是未来美学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不一样的时代背景下,艺术的发展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沉浸式艺术正是5G、人工智能、全息成像等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艺术呈现的全新形式。沉浸式艺术以高科技搭配声、光、电效果,是艺术商品化、符号化的集中展现,沉浸式艺术通过“激进的幻觉”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需要使这种“庸常”成为美感。当然,鲍德里亚的观点也有其偏颇和激进之处,但却给我们如何看待艺术的发展以及新艺术形式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借由鲍德里亚的艺术思想,不必带着悲观消极的心态看待艺术领域出现的新形式,也不必对于科技的介入保持过于保守的态度。面对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积极探索艺术展陈“模式生成”上的全新可能,在给予艺术全新的发展方式的同时保持其理念上的创新,才能使艺术保持创造力与生命力。
参考文献:
[1]让·鲍德里亚,夏莹.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仰海峰.超真实、拟真与内爆——后期鲍德里亚思想中的三个重要概念[J].江苏社会科学,2011(04).
[3]雅克·拉康,让·鲍德里亚等.视觉文化的奇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刘世文.论新媒体艺术的“虚拟沉浸”审美[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
[5]江凌.论5G时代数字技术场景中的沉浸式艺术[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6).
[6]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7]张婷.草间弥生的“梦境式”波普艺术解析[J].四川戏剧,2015(08).
[8]让·鲍德里亚.艺术的共谋[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
[9]郭婧.鲍德里亚拟像视角下的艺术终结问题[D].浙江师范大学,2020.
[10]周宪.艺术理论基本文献:西方当代卷[M].北京:三联书店,2014.
(责任编辑:万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