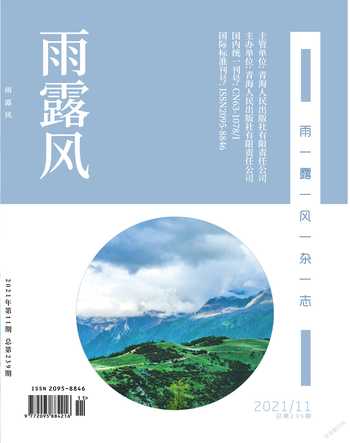疾病与衰亡
摘要:诗集《恶之花》是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的代表作品,其中《忧郁之一》一诗包含了许多关于疾病与衰亡的意象,通过解读诗人使用这些意象的现实原因,分析其中的隐喻,并由此理解诗歌对忧郁情感的非理性表达方式和意象本身以丑为美的特点,可以一窥波德莱尔作品中的现代性。
关键词:忧郁之一;恶之花;波德莱尔;现代性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的诗集《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最早出版于1857年,当时19世纪末象征主义的浪潮尚未掀起,20世纪现代派文学也还在历史的前方遥望,但他的诗歌却已捕捉到了许多“现代”的闪光与阴影。后期象征主义诗人T·S·艾略特在1930年写下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波德莱尔“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了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但同时他又属于那个时代”①。这一评价不仅说明了波德莱尔和自身所处时代的复杂关系,更是肯定了他惊人的超前特质。《恶之花》第一部分“忧郁与理想”的第78首《忧郁之一》最初于1851年发表在杂志《议会通讯》上,其中存在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透过对它们的分析,或许能够窥见波德莱尔笔下精妙幽微的现代性。
一、阴暗意象与创作源泉
《忧郁之一》里的意象被置于巴黎雨月湿冷多雾的环境之中,显示出奇诡阴暗的情调。总体上看,它们与两个方面的内容相关:疾病与衰亡。尽管诗名已经坦白呈现了诗人要表达的心境,但字里行间却并未直抒这番忧郁之情,而是借这一系列意象唤起悲哀与压抑。《恶之花》中“忧郁与理想”的第36首诗题名为《猫》,大约写于《忧郁之一》发表的次年,充满灵性的动物在诗人笔下和危险迷人的让娜·迪瓦尔合为一体,展现出既娇柔又锐利的情态,全诗流淌着令人沉醉的愉悦氛围。而在《忧郁之一》的第二节中,同一意象“猫”却有着“生疮的瘦身”②,如美人“褐色的肉体”③般的生命在彼时陷入了病态和孱弱。诗歌第三节写到了“大钟在悲鸣”和“伤风的钟摆之声”,原本应当声音洪亮的钟却如人一般病痛缠身,只能发出嘶哑的呜咽;该诗节还提及一位“患浮肿的老妇人”④,也是与疾病相关的意象。此外,整首诗一共只有三句话,每一句中都出现了散发着衰亡气息的意象。除了第一节的“墓地”与“亡魂”之外,第二、三节中出现了两个人物——诗人和妇人,但他们已经失去了创造力和生命力,不再是风华正茂、激情昂扬的年轻人,而是衰败的老人。
波德莱尔会在创作时采用这些阴暗的意象也许并非毫无缘由。诗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中度过,父亲早逝,母亲的改嫁使他长久介怀。强烈的孤独感以及和继父之间的不合,早早地在波德莱尔心中埋下了敏感忧郁的种子。法国诗人泰奥菲尔·戈蒂耶称其“心灵极为柔细,智力极为敏锐”⑤,拥有着“神经质的、似乎受着一种热病煎熬的天才”⑥,这使得他极善于捕捉人的感受中模糊易逝的影子,剖析心灵深处隐秘复杂的成分。与此同时,波德莱尔一直对资产阶级的传统道德价值充满蔑视,他的创作也随之挣脱并反叛着资产阶级的传统美学,大胆表现生活中丑恶的一面,注视人世间的病态、情欲和死亡。也正因如此,他在创作过程中屡遭诽谤和中伤。到了三十岁,忧愁和疲倦已让波德莱尔感到了生命力的衰颓,连嗓音也变得嘶哑,不再洪亮。他在这一年发表的《破钟》和《忧郁之一》都表现了病弱的“钟”,正符合诗人自身的境况。以此看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向来受到波德莱尔赞赏的“猫”,也会在诗中成为可怜丑陋的形象了,而弥漫着衰亡之气的“老诗人”“老妇人”甚至“坟墓”等意象更是将颓态显露无遗。
二、意象中的现代性
由于诗人将“忧郁”隐藏在深处,读者只能试图通过疾病与衰亡的意象抓住其中的隐喻。这一修辞手法大不同于传统诗歌,已表现出了象征主义的现代特征。破败的钟与当年的波德莱尔情形相似,在落水管里哀号的“老诗人的魂”也映射着诗人自身的衰颓与悲戚;波德莱尔喜爱咏猫,戈蒂耶认为他“本人就是一只骄奢淫逸、惯会拈花惹草的猫”⑦,因此诗中“我的猫”也未必不是诗人的自喻。但与此同时,从“生疮” “伤风”“浮肿”“老妇人死后留下的发臭的扑克牌”中,也能找到现代人精神的病态和失落感,关于“衰亡”的意象则更是与恐惧感紧密相连。诗中的意象既未直接指向特定的含义,也没有明确比喻的对象,而是以“暗示”的手法,将读者引入巨大的联想空间内,使其在多重隐喻之中体验“忧郁”。
这一“忧郁”之情的表达方式也体现出了强烈的现代性。比起19世纪浪漫派文学中对情感的大胆宣泄,波德莱尔选择了向内探索人的感受。尽管全诗对“忧郁”不置一词,但疾病造成的身心俱损与衰亡,令人倍感无力,两者都能自然而然引起人内在的情感反应,进而在想象力的作用下使忧郁得以滋生。其过程中涉及的思维方式不是清醒理性的推导,而是通过意象来触动心灵当下的感受,是非理性甚至变幻莫测的。同时,诗人所使用的意象本身透露出浓郁的不祥气息,亦无关乎以往文学作品中对人的理性的宣扬,反而暴露了人的痛苦和弱点。疾病与衰亡在生命中往往难以为人类所控制,更是常与恐怖、丑恶相联系。无论是《忧郁之一》泛着凄凉色彩的意象,还是诗歌开头阴暗寒冷的背景,都难以在传统文学中轻易与“美”相连,波德莱尔却以丑为美,毫不遮掩地将之呈现,令人唯恐避之不及。而赤裸又真实的丑陋事物,在颠覆古典审美范式的同时,率先一步洞察了现代文明异化作用下反常的精神世界。“老诗人”已成亡魂,传统的诗意似乎也随之而逝;老妇人患病“死后留下的发臭的扑克牌里,红心侍从和黑桃皇后在一起/闷闷地交谈他俩过去的爱情”⑧,扑克牌象征着人与人之间建立的联系与欢乐,爱情则意味着生命的激情与活力,但二者皆已“发臭”和“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理想缺失、孤独空虚的现代灵魂。
三、结论
《忧郁之一》篇幅不长,却包含了一系列关于疾病与衰亡的意象,诗人自身的经历状况和反叛精神使其超越了传统,运用暗示、隐喻、向内探索和化丑为美等方法,借助这些意象传达了忧郁情感,深入了现代人的精神孤独,表现出超前的现代性。但读者需要明确的是,正如高尔基对波德莱尔的评价,后者是生活在邪恶中却心向善良之人,《忧郁之一》运用的意象雖然丑恶,然而“诗人是以最大的轻蔑和义愤来做这种描绘的”⑨。呈现现代人精神世界中病态和衰败的一面,并不意味着诗人在道德意义上对此进行了鼓吹,反而因波德莱尔以超前的感知力发现了这种复杂、隐秘的现代性,并承认了“恶”的存在,才得以进一步化丑为美,赋予了“忧郁”这种负面情感以新的美学价值。波德莱尔并不是丑陋与堕落的宣扬者,他大胆表现“恶”,正是为了让其开出世人前所未见之花。
作者简介:杨怡蕾(1998—),女,汉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注释:
①托·斯·艾略特:《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李赋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86。
②④波德莱尔:《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钱春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65。
③波德莱尔:《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钱春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81。
⑤泰奥菲尔·戈蒂耶:《回忆波德莱尔》,陈圣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4。
⑥泰奥菲尔·戈蒂耶:《回忆波德莱尔》,陈圣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6。
⑦泰奥菲尔·戈蒂耶:《回忆波德莱尔》,陈圣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49。
⑧波德莱尔:《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钱春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66。
⑨波德莱尔:《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钱春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5。
参考文献:
〔1〕托·斯·艾略特:《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李赋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波德莱尔:《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钱春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泰奥菲尔·戈蒂耶:《回忆波德莱尔》,陈圣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杨希,蒋承勇.西方颓废派文学中的“疾病”隐喻发微[J].外国文学研究2019,41(03):70-80.
——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