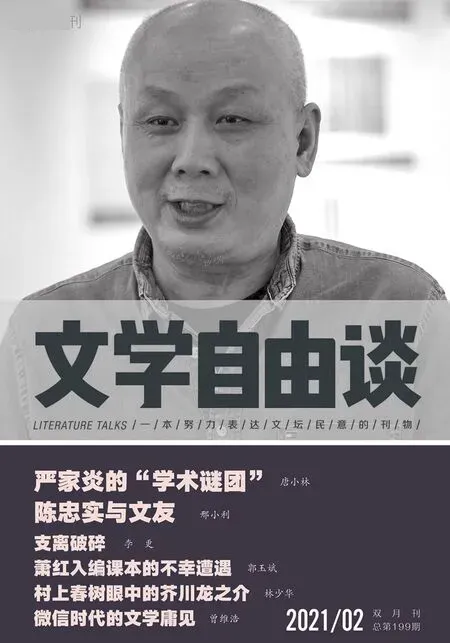“文人子弟”与“文人弟子”
□狄 青
索菲亚十八岁的时候嫁给了三十四岁的列夫·托尔斯泰,之后数十年间,先后为这个男人生了十三个孩子。起初托尔斯泰是想把索菲亚改造成为他精神上的“同路人”的,但遗憾的是,终其一生,索菲亚深深爱着却又始终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丈夫,他遂把希望转向了自己家族的子弟们。他用自己编撰的《识字课本》《阅读园地》等教材来教授这些孩子,并让他们与农民的孩子一起在他创办的“草鞋学校”里上学,而老师就是他自己。托尔斯泰希望自己的“二代”们能够身体力行去改良社会,而且不仅仅是改变农奴制。
对于中年以后的托尔斯泰而言,文学创作只是实现改良社会的诉求手段,金钱与所谓名望在他的创作中几乎不占份量,就像他在《忏悔录》中所说的那样:“虽然我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作家信仰就是欺骗,并且抛弃了它,但是人们由此赋予我的头衔我却没有抛弃:诗人、艺术家、导师。我竟然天真地以为,我就是诗人,就是艺术家,就是导师了。”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翻脸,其中一个原因是屠格涅夫要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上流社会的名媛千金。一次聚会,托尔斯泰当众指出屠格涅夫培养女儿的方式是错的,而这个女孩恰巧又是屠格涅夫的私生女。托尔斯泰说:“如果她是你的合法女儿,你就不会这样教育她了。”为此,屠格涅夫险些跟托尔斯泰动起手来。
事实上,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屠格涅夫,都没有设想抑或希望把他们的“二代”培养、扶植成为诗人、作家,二人的后辈子弟中也的确没有人靠文学创作扬名立万。虽然几十年后,阿·托尔斯泰自称与列夫·托尔斯泰系本家,但他与列夫·托尔斯泰毫无交集,二人的世界观也相距千里。我想,这可能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皆系贵族出身有关,他们包括其“二代”的生计都无需稿费和版税来支撑,只是与他们的创作理念关联很大,那便是,文学本质意义上并不是一种供人安身立命乃至风光无限的行当。即使放眼文学史,能拿出来的父子相传的例子,基本上也只有大仲马和他的私生子小仲马,还有写“兔子系列”的厄普代克——他的母亲是一位专栏作家,尽管名气不大。在世界文学史上寻找成功的“文二代”范例,远比某些人想象的要难得多。但凡读过安德烈·莫洛亚《三仲马》一书的人都清楚,当年小仲马写作的初衷,恰恰是源于其经济上的捉襟见肘。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靠写作摆脱经济窘境的方法,且对此也并不讳言。很多作家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并不希望子弟传承自己的“文学基因”。塞林格写作的房间,他的儿女是绝对不能踏入半步的;冯内古特因为崇拜马克·吐温,也给大儿子取名马克·吐温,但他从不与儿子交流任何文学话题;狄更斯的前妻给他生了十个孩子,竟然没有一个借老爸的名望来经营个人事业的家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唯一的儿子少时倒是喜爱写作,但即使在因身体原因被英国皇家海军“刷”下来后,吉卜林仍然通过个人关系,将他送到英国陆军赴欧洲战场参加一战,只因为吉卜林觉得,作为男人,没有比上战场更合适他去做的……
在我小时候,流行过一个词语叫做“顶替”。实行“顶替”政策的单位,基本是国营和大集体性质的厂矿企业,以及部分机关、小集体企业。所谓“顶替”,就是父母退休或者提前内退,让儿女去顶替他们的工作资格。此可算是彼时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良策。“顶替”顶的是工作机会,未必是工作岗位,所以就经常有干部的子女当了工人,而工人的子女也有可能会做干部。这里面,托关系走后门的事情肯定有,但较之后来,比例还是要少很多。我就知道一个电焊工的孩子,因为能写能画,“顶替”进厂后,直接进工会做宣传干部。这些“顶替”的年轻人统称为“子弟”。所谓“子弟”者,不只包括儿、女、弟、妹,也包括子侄辈。要说他们一点儿没受照顾,肯定不客观,毕竟都有父母和叔叔大爷的人脉在,但与我们当下所说的“子弟”抑或“二代”还是有明显不同的。如今,但凡媒体十分关注、群众纷纷“吃瓜”的“二代”,基本上都在有利可图、有名可沾、有内幕可挖的行当,你看有谁会盯着产业工人的“子弟”和种田老农的“二代”不放来着?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人子弟”也好“文人弟子”也罢,原本属于衍生概念,系诸多“二代”中的一类。由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演二代、画二代,再到文二代,“二代”的范畴基本囊括了社会上所有热门的“行当”。就说“文二代”吧,有人总把“三曹”“三苏”拿出来说事儿,实际上古代但凡在官僚阶层混的,广义上都属于文人,因为舞文弄墨是最起码的要求,而平民百姓舞文弄墨的不多,所以说,古代的“文二代”更多的是指精神意义上的传承。但现在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多半是利用“代际优势”而具有了财富性的诉求。“文二代”可以更轻易地进入官方体系,同时也有更多机会被商业体系和金钱衡量体系所接纳,因而占据了稀缺的社会资源。如今有很多老画家,经常以办父子画展、母女画展的方式,利用权力和影响力,为下一代尽快上位创造条件;一些老作家老诗人亦然,以开研讨会、做活动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子弟”和“弟子”助力。相形之下,没有背景的平民百姓子弟,想要在这个圈子里站住脚,原本就十分困难,如今更加千难万险。
2020年6月,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四册“文学家风”系列丛书,每册都由女儿和父亲共同创作完成。特别的是,这四册书的爸爸们都是国内较有名气的作家,四个“二代”也是赫赫有名。不能说出版社功利,在纸媒出版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如此运作,当然也是为了更好地吸引各方眼球。对于许多“文二代”来说,选择一条和父辈相似的道路,或许不能够使他们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但足以令他们在现世活得衣食无忧甚至风生水起。有人说,目前的“文人子弟”实际上也不多。正所谓“河里没鱼市上找”,倘使你去各地作协访访,去里面闲散的科室或掌握发稿权的刊物编辑部调查一下,你就知道有多少人属于“文二代”了。
与其他“二代”们相比,“文二代”及文人子弟们即使拼爹,也多半不会拼得大张旗鼓,至少不会出现“我爸是李刚”那类新闻热点,但也架不住周围始终有各类帮闲文人起哄架秧子。原本有人的确是想低调做人的,结果被争先恐后前来捧臭脚、蹭热度的这个家那个家“出卖”了。记得某“文二代”的处女作出版时,新书的腰封上赫然列着长达三十人的推荐名单:铁凝、余华、苏童、阿来、方方、吴亮、陈思和、陈忠实、马原……阵容之豪华,几乎涵盖了中国小说界、评论界所有具有话语权的人。倘若没有“主席+主编”的“文一代”父辈,这三十个人能请出一位来,都非易事。倒是该“文一代”说得清楚:孩子从小就跟这些作家前辈们认识,他们也就都愿意出来帮个忙。
据说,评论家陈晓明先生多年来一直都殷切关爱着“文二代”茁壮成长的历程。他说:“这些‘文二代’出手都很高,比起同龄人,他们的写作也更有特点。有意思的是,这些‘文二代’的写作风格与他们的父辈大都相去甚远,从这一点也看到了他们的叛逆性。”关键是,陈先生是如何判断出“二代”们比同龄人更有特点呢?如果“文一代”用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出的是“高玉宝”,其子弟和弟子还会用同样手法接着创作“高玉宝”吗?实际上,除了“文人子弟”外,如今的“文人弟子”也是某种身份的“标识”。随着“创意写作”专业本硕博学位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随着“作家班”此起彼伏地开办,谁教过某某某、某某某是谁的学生、某某某毕业或结业于某院系的某一届,便成为一种师长与弟子之间的“互认标识”,也就有那么一些刊物,每期所发表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多一半都是作家导师推荐来的自己“弟子”的作品,对作品的评论有的甚至就是导师亲自操刀的。
大家知道,如今,书籍不好卖,书号更是紧张。一位文坛新兵想要出书,已是千难万阻,想要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地宣传,更如梦幻泡影。当下喜欢写东西的人多了去了,写的好的人也不在少数,而往往只有“文人子弟”与“文人弟子”得以直接进入关系圈。我认识的一个文人子弟,大学毕业后一直高不成低不就地混迹于四五个行业,哪都干不长,结果还是被作协收纳,以“文二代”的身份,不长时间就风生水起了。
当所有人对此都假装看不见,甚至谋划如何能与之利益均沾的时候,有人站出来,对某些“文二代”的作品提出质疑,却又有某些掌握话语权的这家那家急火火地跑出来站台。说实在的,我以为他们多半是“站”给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文一代”们看的,因而行动必须迅速,立场必须鲜明。“文二代”能成这般蔚为大观的气象,实际上与书商和院所助力炒作也有关系。要拿到“文一代”的稿子,要被接纳和认可并进入某些“文一代”把控的文学评价体系,要靠“文学子弟”和“文学弟子”的名分炒作赚钱,他们当然要出来为“文一代”的子弟和弟子们站台。我就听过一位作家讲:“某某那是我学生,咱的人,他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和我说,还是要爱护。”他没说错。他嘴里的青年作家某某在某大学读“创意写作”,该作家被邀请去讲过几堂课,并与某某结了“一对一”的对子,当然就算是这位青年作家的老师了。
当“文人子弟”与“文人弟子”占据了大量的稀缺资源、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展示平台,你让其他人一点儿没有想法,的确是不人道的。当然,一定会有人告诉你说:你就不能有这种想法,人家某某的妈妈一年赚的钱够你妈妈五十年赚的钱,这就是国情啊,你受得了受,受不了滚!而且,往往还会有满嘴鸡汤的道德义士站出来,说:有本事你写得比谁都好啊,就不信谁能埋没得了你!你看谁谁谁最早就是一个农民,人家如今都是作协主席了……这种话,你要说完全没有道理,说明你这人不讲道理;可你要说他们讲的就是真理,它还的确不是真理。有许多事情只能属于个例,没有复制的可能性。就像每个说相声的孩子都想像郭德纲一样成功,可郭德纲就是一个个例,你无法复制他,这和你是否努力了、努力够不够关系不大,也和你是否说得不如郭德纲好关系不大。几年前,郭德纲回天津探亲,我与他有过一次接触。他说,谁也别跟谁比,你命里没有嘛,白搭。我理解他说的话。比方说天津是一个“相声窝子”,可你让天津再出来一位单枪匹马去北京闯世界的主儿,即使他比老郭更努力更勤奋,但想要再造一个“德云社”出来,怕是也难上加难,搞不好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都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不过我想说的是,既然有权威人士有相关媒体总是在给如今遍地的“文人子弟”和“文人弟子”们披上各种合理化的外衣,也就必须接受被指点被指摘的结果,况且明明就是有那么多可被指摘的东西摆在那里,哪有不让人指摘的道理?我还以为,文学圈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父子兵、母女团来袭,有那么多放着其他营生不干,偏往文学圈里扎堆,且四处认师拜祖的“文学弟子”,第一,说明当下的文坛的确是有名有利可图,第二,说明与其他行业比较,文学圈的门槛更低,也更加好混,且风景独好——当然这是在你掌握了相当一部分资源的前提下。我不是说“文学子弟”“文学弟子”都写不好。确有“二代”写得很好,但相比于乌央乌央享受着“文一代”荫庇的“文二代”来说,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色的,在作协系统编刊编得出彩的,同样是凤毛麟角。既如此,就不能想想办法,让“二代”们去干点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