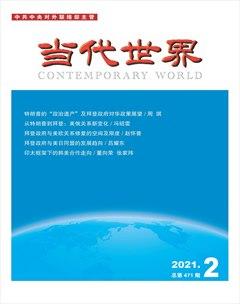欧洲社会中的穆斯林问题:历史、冲突与影响
张冠男
【关键词】欧洲穆斯林;泛伊斯兰主义;穆斯林移民;伊斯兰极端主义
【DOI】10.19422/j.cnki.ddsj.2021.02.011
近年来,欧洲爆发多起由伊斯兰极端分子实施的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大多是由欧洲相关国家本国穆斯林策划实施的,使得欧洲内部的穆斯林问题愈发凸显。同时,民粹主义思潮也在部分欧洲国家日益兴起,与一些穆斯林不断寻求的“泛伊斯兰主义”形成激烈碰撞,使得欧洲穆斯林问题更加复杂,且存在外溢风险。欧洲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移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存在于多个层面,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从历史演变、现实冲突以及影响等维度观察和分析欧洲内部的穆斯林问题,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前欧洲相关民意思潮、政策走向以及内外关系等重要问题。
穆斯林与欧洲社会关系的演变
穆斯林与欧洲的交往融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穆斯林占领西班牙时期,奥斯曼帝国扩张时期以及近现代穆斯林迁移时期。穆斯林对欧洲国家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穆斯林跨海征服西班牙
西班牙历史上曾作为伊斯兰教进入欧洲大陆的第一站,被穆斯林统治了近8个世纪(公元711—1492年)。711年,阿拉伯名将塔里克率部横渡直布罗陀海峡,登陆伊比利亚半岛。此后,倭马亚王朝非洲总督穆萨率军深入腹地,进而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收入囊中。756年,倭马亚王室后代阿卜杜拉赫曼在伊比利亚半岛自称埃米尔(意为“统治者”),史称“后倭马亚王朝”。在阿卜杜拉赫曼三世统治时期,后倭马亚王朝宗主权辐射至摩洛哥及柏柏尔海岸,使其成为当时欧洲文化最发达、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11世纪起,王室内部争权夺利加剧,国家政局陷入混乱。1031年,末代哈里发希沙姆三世被废黜,国家分裂为20多个封建小国。1492年,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失守。
后倭马亚王朝时期,伊斯兰教在欧洲迎来了第一轮传播高潮,当地宗教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除阿拉伯征服者以外,早先皈依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此时也大量由北非涌入,亦有大批当地基督徒在优惠政策吸引下改信伊斯兰教。与此同时,阿拉伯文化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阿拉伯文学、历史、哲学、天文、艺术等在这一时期达到较高水平,与正处于黑暗时代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大量阿拉伯文的古希腊典籍和学术著作被译成拉丁文,推动东西方文明精粹传入欧洲。
二、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扩张
奥斯曼人初居中亚,后迁至小亚细亚并日渐兴盛,由一个突厥部族发展为横跨亚欧非的大帝国。14世纪,奥斯曼军队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先后征服了马其顿和整个希腊北部。1453年,奥斯曼帝国消灭拜占庭帝国,随后又占领了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伯罗奔尼撒半岛,并三次兵临维也纳城下。17世纪,奥斯曼帝国盛极而衰,国力被经历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超越,加之战场上失利不断,被迫撤出欧洲。
与当年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情况类似,奥斯曼帝国向欧洲扩张造成当地穆斯林人口激增。伊斯兰教在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希腊等地广为传播。奥斯曼帝国势力从欧洲撤出后,基督教国家虽试图消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收效不大,巴尔干半岛至今仍有大量穆斯林人口。伊斯兰教的本轮传播掀起了欧洲学者研究伊斯兰教的热潮,催生出欧洲学界的“东方主义”运动。
三、近现代穆斯林向欧洲的大举迁移
穆斯林第三轮大规模向欧洲迁移始于19世纪末,时值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欧洲多国在非洲、东南亚等地加速殖民扩张。与前两轮不同的是,此时欧洲从被动接收穆斯林移民转为主动吸纳。这一时期,作为巩固殖民统治的手段,欧洲国家乐于邀请并资助所辖殖民地国家社会上层特别是年轻人赴欧留学工作,以培养其对宗主国的文化亲近和政治认同,其中有不少人选择留在欧洲安家立业,多数为穆斯林。更大规模的穆斯林移民潮出现在二战结束之后。为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推动经济复苏,欧洲国家开始鼓励和接纳移民,从而吸引了大量来自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劳工。[1] 20世紀70年代后,更多穆斯林赴欧洲就业、投亲。同时,近年来叙利亚、阿富汗、利比亚等地局势持续动荡,导致辗转入欧的战争和政治难民数量达到历史高位。[2]
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现状
当前,穆斯林移民潮仍在继续,加之早期入欧的穆斯林移民已生育第二代、第三代,欧洲穆斯林人口在欧洲总人口占比持续快速增长。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少数族裔,欧洲穆斯林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人口占比高,数量增长快。2016年,欧洲穆斯林人口已达2580万,约占欧洲总人口的5%,居欧洲少数族裔之首。从国家分布看,法国、德国穆斯林人口最多,分别为570万(占比8.8%)和500万(占比6.1%),且法国25岁以下年轻人中,穆斯林已占25%。从增长趋势看,与非穆斯林相比,欧洲穆斯林人口结构更加年轻化、生育意愿更强,因而人口自然增长率更高。以当前的增长速度,到21世纪中叶,欧洲穆斯林人口占比或将翻番;若考虑到未来欧洲的移民政策尺度变化,穆斯林人口占比预计为7.4%—14.0%。[3]
二是小聚居、大分散的人口分布格局。在历史上前几轮移民潮的影响下,穆斯林在欧洲东部、东南边界的巴尔干半岛、高加索等地呈聚居分布,其中塞浦路斯25.4%的人口为穆斯林且大多世代久居于此,使其成为穆斯林人口占比最高的欧盟国家。而在西欧发达国家,穆斯林多为近现代移居而来的劳工或难民,故分布较为分散,且来源以各国的前殖民地为主。如英国穆斯林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法国穆斯林主要来自马格里布国家,德国穆斯林以土耳其后裔居多。[4]
三是文化隔阂深、社会地位较低。受宗教文化、历史嫌隙、生活习惯、外界宣传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欧洲穆斯林与主流社会间长期存在隔阂,且该问题随着穆斯林人口比例的上升愈发凸显。加之欧洲穆斯林受教育水平总体不高,就业率和收入也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导致其本就作为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更受影响,甚至遭受歧视,陷入了“阶层固化——形象矮化——声量弱化——机遇恶化”的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持续对欧洲穆斯林进行宣传造势、组织渗透及人员诱拉。一是以网络社交媒体为手段开展“空中宣传”。以“伊斯兰国”为例,其宣传战略清晰完整,组织内部设有专门的宣传部门,建立起体系化的外宣矩阵;宣传活动猖獗泛滥,极盛时期在推特上支持“伊斯兰国”的账号最多达到9万个,仅在法国,“伊斯兰国”的宣传机构每天发送4万条推讯;[18]宣传内容遗毒深远,既有曲解教义的,也有美化“圣战”的,还有策划恐袭的实操指南,可谓费尽心机满足极端主义潜在受众的多重心理需求。二是见缝插针地对欧洲进行“地面渗透”。极端组织将目标瞄向某些伊斯兰宗教机构和慈善组织,钻法律漏洞,躲避监管审查,暗中开展讲经、培训、资金输送等活动。[19]在极端组织的煽动下,身披宗教外衣的暴恐分子近年来在欧洲接连制造“独狼式”恐袭事件。此外,曾有超过5000名欧洲穆斯林赴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参与跨国“圣战”,而后其中约30%的“圣战分子”陆续回流,[20]他们带回了极端主义思想和杀戮技能,成为威胁欧洲安全的定时炸弹。
穆斯林移民对欧洲多国政治生态和内外政策的影响
穆斯林移民与欧洲主流社会间的长期隔阂乃至矛盾未见消解,导致社会安全问题接连爆发,在社会层面引起舆论热潮和民意反思的同时,更是在政治层面带来多重影响。其中,既有相关国家执政当局从维护稳定团结出发在移民、反恐、文化等方面作出政策调整,又有政治思潮、政党声量、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形势演变。
一是欧洲民粹思潮和种族主义抬头,极右翼政党借机扩张。欧洲民粹主义分子抓住民众“伊斯兰恐惧症”“难民恐惧症”等思想苗头,高举反移民旗帜,煽动排外情绪、挑动族群仇恨。欧洲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矛盾越尖锐,极端民族主义、盲目保护主义和“本国优先”等主张越有市场。法国国民联盟一度声名大噪,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超过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异军突起,目前已进入德国16个州议会中的8个。奥地利自由党、瑞典民主党、丹麦人民党以及匈牙利、波兰等国的极右翼势力也进一步扩张,甚至进入政坛第一梯队,成为左右政府施政的重要力量。
二是多国收紧移民政策,大力打击伊斯兰分裂主义。不少欧洲国家曾采取“文化多元主义”思路处理移民问题,试图在尊重人权、接受差异、保障自由的前提下,为包括伊斯兰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留出足够发展空间,同时推动社会大融合。但这一政策收效甚微,甚至成为别有用心之人在欧洲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的“挡箭牌”。为此,欧洲国家纷纷提高移民接收门槛,并将对欧洲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作为重要接收标准。法国近来重拳出击,加快制定“反伊斯兰分裂主义法”,采取停止接收外国伊玛目、关闭非法宗教场所、改革教育体系等手段,力图将宗教活动纳入本国法律法规和世俗原则框架之中。巴黎教师斩首案后,法国进一步加大反恐力度,提高安全警戒级别,对51家穆斯林学校、文化场所及团体进行每日巡查,取缔10余家涉恐伊斯兰协会,驱逐200余名外国极端分子。
三是欧洲内部族群矛盾外溢,波及与伊斯兰国家关系。欧洲穆斯林普遍与祖籍国存在一定情感联系,加之宗教问题十分敏感,欧洲各国在处理涉伊斯兰问题时,尺度稍有偏差便会激起伊斯兰国家不满,且容易与地缘政治博弈交织互动,最终导致双方关系紧张、互信受损。本应在欧洲与伊斯兰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穆斯林移民如今却不时成为双方冲突对立的导火索,双方矛盾愈演愈烈且短期内难以调和。
結 语
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兴盛于西亚北非地区的伊斯兰文明与欧洲西方文明长期存在历史交往与人文互动,其结果之一便是形成了小聚居、大分散的欧洲穆斯林群体。他们是拥有文化特质的“使者”,为推动文明相交相融发挥着纽带作用,同时也是身处文化他乡的“异客”,其现实处境深受文明关系大环境的影响。
不同于历史上前两次伴随战争而形成的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元对立模式,近现代穆斯林赴欧迁移是以劳工移民和政治、战争难民为主体并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的,因此起先并未引发欧洲社会高烈度、大范围的穆斯林排斥潮。然而,随着欧洲人口结构的持续变化,欧洲对异质文明接纳效果不彰、穆斯林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结果不佳等内源性矛盾以及伊斯兰激进思想蔓延、极端组织渗透等输入性压力愈发明显,进而激起欧洲内部宗教和价值观冲突,引发社会安全问题。
随着欧洲民粹思潮沉渣泛起,多国政府施政路线右转趋势明显,在穆斯林移民、难民问题上态度日趋消极。与此同时,欧洲穆斯林仍存在一定的文化适应力短板,且被外界误解、疏离乃至歧视的境遇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如何在尊重多元文化和私人空间的同时遏制社会离心倾向,在追求自由平等和市场效率的同时平衡社群利益分配,在承担人道责任和国际义务的同时确保国家安全稳定,考验着欧洲妥善处理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政治智慧,也是世界各国在推动多元文明交流交融、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基础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亚北非局)
(责任编辑:苏童)
[1] 李维建:《“伊斯兰威胁欧洲”?——政治的想象与宗教的建构》,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第75-80页。
[2] Pew Research Center, “Number of Refugees to Europe Surges to Record 1.3 Million in 2015,” December 14,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6/08/02/number-of-refugees-to-europe-surges-to-record-1-3-million-in-2015/.
[3] Pew Research Center, “5 Facts About the Muslim Population in Europe,” December 14,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11/29/5-facts-about-the-muslim-population-in-europe/?amp=1.
[4] 李维建:《欧洲穆斯林:历史与现状》,载《世界知识》2003年第5期,第52-53页。
[5] Sarah Lyons-Padilla, Michele J. Gelfand, Hedieh Mirahmadi, Mehreen Farooq, & Marieke van Egmond, “Belonging Nowhere: Marginalization &Radicalization Risk Among Muslim Immigrants,” December 14, 2020, https://behavioralpolicy.org/wp-content/uploads/2017/05/BSP_vol1is2_-Lyons-Padilla.pdf.
[6] 王宇洁:《征服与被征服:穆斯林与欧洲关系的历史考察》,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6期,第44-49页。
[7] 宋全成、温婧:《欧洲缘何泛起排斥穆斯林族群的思潮?》,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5期,第22-41页。
[8] Pew Research Center, “Europeans Fear Wave of Refugees Will Mean More Terrorism, Fewer Jobs,” December 14,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6/07/11/europeans-fear-wave-of-refugees-will-mean-more-terrorism-fewer-jobs/.
[9] IFOP le Figaro,“Limage de LIslam en France,” December 14, 2020, https://www.ifop.com/ publication/limage-de-lislam-en-france/.
[10] 紀红蕾:《法国穆斯林移民问题研究》,外交学院硕士论文,2017年5月,第26页。
[11] 储殷、唐恬波、高远:《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维度:阶级、身份与宗教》,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20页。
[12] 宋全成:《穆斯林移民在欧洲:身份认同及其冲突》,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1期,第22-37页。
[13] Pew Research Center, “Muslims in Europe: Economic Worries Top Concerns About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dentity,” December 14,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06/07/06/muslims-in-europe-economic-worries-top-concerns-about-religious-and-cultural-identity/.
[14] Rogers Brubaker, “Categories of Analysis and Categories of Practice: A Note on the Study of Muslims in European Countries of Immigration,” December 14, 2020, https:// citeseerx.ist.psu.edu/ viewdoc/ download?doi=10.1.1.720.5737&rep=rep1&type=pdf.
[15] 张友国、董天美:《泛伊斯兰主义的逻辑演化与现实悖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84-91页。
[16] 钱雪梅:《达瓦宣教团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36-159页。
[17] 崇明:《教法与自由:当代欧洲的伊斯兰教挑战》,载《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第132-151页。
[18] 李宁:《“伊斯兰国”影响下的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6期,第88-106页。
[19] Prime Ministers Task Force on Tackling Radicalisation and Extremism, “Tackling extremism in the UK,” December 14, 2020,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63181/ETF_FINAL.pdf.
[20] Richard Barrett, “BEYOND THE CALIPHATE: Foreign Fighters and the Threat of Returnees,” December 14, 2020, https://thesoufan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Beyond-the-Caliphate-Foreign-Fighters-and-the-Threat-of-Returnees-TSC-Report-October-2017-v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