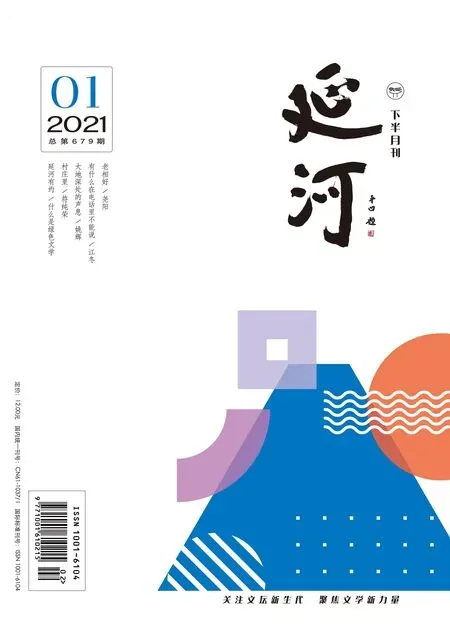什么是绿色文学
杨 克 穆 涛 荣 荣 吴克敬 刘笑伟 林 雪 李 瑾 袁 梦
什么是绿色文学?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在我们眼里,绿色不单纯代表一般意义上的绿色,可以视之为社会环境背景下的文学理念和话题,它可以针对自然与社会,针对我们共同的生存问题,还可以针对写作时的创新意识与构思。而无论从哪个方面谈起,我们追求的绿色与绿色文学将是永恒的。
在各类自然资源越来稀缺的今天,我们倡导绿色与绿色文学,令人看到希望,看到未来。就像相比于其他色系,无人不钟情于绿色:蓬勃旺盛,充满生机,预示生命长盛不衰。在一个文化格局出现多元化的时代,绿色文学无疑是令人向往和值得追求的创作态势,我们面临的挑战、语境、发展趋向,绿色显然构成了我们的生命底色。它传播的范围之大,信息之广,是丰富的,可持续性的。承载绿色文学的,不一定是一篇意蕴深远的散文,也不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诗歌,而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比如在生存危机、道德领域、人生价值等方面,作为精神象征和对人类生活的反思,绿色文学构成我们的写作使命,也是不无可能的。
参与本期话题“什么是绿色文学?”由8人组成,其中有多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有省作协副主席,有资深文学期刊主编,还有在大学任教的教授,可以说,阵容非常强大,阐述“彩色文学”这个话题各抒己见,颇有见地。
——王琪

杨 克
现居广州。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台湾华品文创有限公司等出版《杨克的诗》《有关与无关》《我说出了风的形状》等11部中文诗集、4部散文随笔集和1本文集,日本思潮社、美国俄克拉赫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8种外语诗集,翻译为16种语言在国外发表。
吹绿东风的青草,初绽的嫩叶,潺潺清溪,澄澈新月,这些物象,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绿色。回到人本身,青春,鲜活,靓丽,生猛,这些词才属于绿色。故而绿色文学,我以为首先指青年文学。豆蔻年华或英姿勃发才堪称绿色,老态龙钟白髯飘飞的作者,哪怕再老当益壮,亦是金秋。以生命年轮划分,绿色写作,特指青年作家的写作。
绿,也是无污染之意,衍生天真、本色。从题材论,有关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的作品,写大自然、江河湖泊、野莽草原的作品,山水诗、田园诗,包括散文,甚至书写农村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非虚构”,都可以看作绿色文学。童话、成长小说,关于青少年的写作和青少年所写,例如小学生创作的诗文,都可视作绿色文学。
语言清新,文字干净,语感明快,读来如清风拂面,沁人心脾的文章,亦是绿色写作。而性意识浓郁,或者揭示人心大恶,写尽人性卑劣,撕开历史深处鲜血淋漓惨烈伤口的小说,当然也不乏好作品,甚至伟大作品,但在我看来不能归类于绿色文学,它们呈现的是生命的杂色,是社会混沌的灰色地带。
从作品格调或者文人的腔调看,温暖、明亮,励志,让人向上的作品,是绿色文学。将颓废写到极致,渲染阴郁黑暗或悲悯黎民苍生疾苦的作品,似也不好划归绿色文学。举个例子,《瓦尔登湖》肯定是绿色文学,可杜甫写安史之乱的“诗史”难以叫绿色文学。结论,绿色文学是好文学,非绿色文学确实也不乏好文学,我们必须尊重艺术规律。

穆 涛
《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国务院特贴专家。《先前的风气》一书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2014年中国好书”。201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中国古人对天地的认知,是在敬畏天地的基础上逐步展开的。
比如对一年之中四个季节的发现和界定,既循守日月星辰运行的自然法则,又充满非凡的艺术想象思维。首先被认知到的是春和秋,1987年,在河南濮阳老城区的西水坡,考古出土了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大墓遗址,惊动了考古界和史学界。依墓葬规制判断,大墓主人应该是那个时代重量级的一位部落领袖,男性,年龄鉴定56+岁,骨骭身高1.79米,仰身直肢葬,头南足北,在墓主人骨骭的左右两侧,极具匠心地摆塑着一龙一虎图案,摆塑材料为贝壳。龙在右侧,体长1.78米,虎在左侧,体长1.39米,龙虎图案鲜明逼真,栩栩如生。人、龙、虎的考古编号为M45(B1、B2、B3),碳十四测定时间节点在公元前4500年代,比传说中黄帝的生活时代迟后五百年左右。
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四象”中的龙与虎。四象,即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在空间方位上指示东、南、西、北,在时间方位上指一年之中的春、夏、秋、冬。这一时期人们对春和秋已经有了清晰的定位和辨识。青龙指春,白虎指秋。春分和秋分这两天昼夜均分,古人称为“日夜分”。对夏和冬的天文学界定要晚,已到了尧帝时代,公元前2100年前后。《尚书·尧典》中记载的是,“日永,以正仲夏”,“日短,以正仲冬”。古人称夏至和冬至为“日永”“日短”,这两天白天的时间分别最长和最短。夏至和冬至中的“至”,不是到来的意思,是极致,是高点。
“四象”与“二十八星宿”是一种物质元的两种表述,都具有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中国古人观测天象,以“七曜”为观测目标。七曜,即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二十八星宿”在“七曜”之外,是“七曜”的观测背景,也是日月等七星在太空运行的轨迹途经地,称为“宿”,是客栈的意思。也就是说,“二十八星宿”是“七曜”运行中歇脚的“太空客栈”。这种想象力是何等的恢弘又入微。
“二十八星宿”是银河系中的恒星群,由四个组团构成,每组团七星。春分这一天的黄昏时分,“角,亢,氐,房,心,尾,箕”七星出现,在天空中宛如青龙;夏至这一天黄昏时分,“井,鬼,柳,星,张,翼,轸”七星出现,在天空中形似大鸟(朱雀);秋分这一天黄昏时分,“奎,娄,胃,昴,毕,觜,参”七星出现,在天空中状似白虎;冬至这一天黄昏时分,“斗,牛,女,虚,危,室,壁”七星出现,在天空中如龟蛇缠绕(玄武)。“二十八星宿”就是这么对应着构成“四象”。
“四象”指示着春、夏、秋、冬,在一年四季的轮回流转中,蕴含着五行原理,“天有七曜,地有五行”,木主春,火主夏,金主秋,水主冬,土居四季中央。五行之中有五色,青(青龙),赤(朱雀),黄(中央黄土),白(白虎),黑(玄武)。
绿色,是青色和黄色的有机融会贯通,在季节中处于由春到秋的发生发展阶段。中国的民谚里有“青黄不接”这个词,是“新粮未熟,陈粮已尽”的意思,以天意警示人间疾苦。
绿色文学不是一种写法,也不是某类题材,更不是环保文学,而是一种文化理念,指向自然与人心的交流互映。绿色文学,是一个新鲜术语,源自外国的一本小说,是进口产品。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中,进口产品居多,至今似乎仍是主流。但“绿色文学”这样的意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仅早已存在,而是以此为基础的。中国老百姓有一句口头禅,就是“谢天谢地”。
中国大历史中有一个长达三百年的特殊阶段,就叫春秋,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这一时期,基本处于诸侯自治的国家分裂状态。紧随其后又是二百五十多年的国家大分裂阶段,史称战国,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之后秦始皇统一全国,但秦朝只存在十五年的时间。再之后汉朝建立,中国才走上大国之路。春秋时期,大约有120个诸侯国,大多数诸侯国的国史都叫《春秋》,“吾见百国《春秋》”(墨子)。以季节命名国家历史,自身就是天文与人文的有机交融,这些史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孔子在鲁国国史基础上,又综述120个诸侯国的史料而成就的那部大《春秋》。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去世三年后,春秋时代结束。
“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春秋》这部书,在写法上形成了传载千年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有两层深意,一是“微言大意”,用最少的文字,写出最深刻的道理。再是“记衰世”,书写一个时代,既写出高大上的地方,也写低洼泥泞地带。《春秋》在精神面貌上,呈现着“敬天地,循制度,察世道,辨人心”的硬核,天地自然与世道人心的交融互映,自此构成了中国史书,乃至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内存。
在孔子著《春秋》之前,天地与人心交融的意识形态也是鲜明存在着的,《易经》是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融哲学、政治、天文、文化、艺术于一炉。《易经》第二十二卦,是贲卦,贲是“文饰”的意思,贲卦的要义,是君子之德在“正而质”,不在“美而饰”。这一卦的《彖辞》是,“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绿色文学是大的倡导,但要警惕写成“美而饰”的那种表面文章。

荣 荣
原名褚佩荣,1964年生,出版多部诗集及散文随笔集,参加诗刊社第10届青春诗会,曾获《诗刊》《诗歌月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年度诗歌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
丰子恺先生说到他的老师弘一法师为何出家时,有了“人生三层楼”的说法。也就是人的三种境界,三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生活,求温饱,求物质财富,这都是身体和物质层面的。一种是精神生活,文学艺术,名誉地位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还有一种是灵魂生活,清心寡欲,追求大道。
不难看出,这人生三层楼,登楼一层难上一层。
联想到《延河》有关“绿色文学”这个议题。仔细想来,有些感动。《延河》并不想来场文学的颜色革命,《延河》对于“绿色文学”的倡导,纯粹是严肃文学意义上针对艺术精神追求的宣言,而不是文学类别上的区划。她更多的是指向上的积极的,以情感或灵魂力量引导为精神内核的文学,给人以艺术愉悦和享受的文学。
这样的文学怡情养性,自然是绿色的,有益的。开卷有益,就是开绿色文学的卷,得绿色文学的益。按丰子恺先生的三层楼说法,绿色文学肯定停留在二层及以上的,是能真正带给读者,站在日常生活之上,宽容大气会心一笑的阅读体验,感受到登高望远的文学气象。
与绿色文学相对的肯定是垃圾文学,垃圾文学与垃圾食品一样是不用定义的。但阅读市场需求多样,我们无法一统难调的众口。作为一本刊物,拒俗,拒劣,拒游戏等选稿发稿上的自律,非常可贵,当要给点个大大的赞。

吴克敬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市作协主席,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初婚》热播央视、优酷、腾讯等多家电视台及网络平台。
张嘴要有饭吃,是人的基本需求。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一种需求,人把办法想尽了,目的无他,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饭辙。像我们操练文学的,其中就有那么一些人,一会儿鼓噪一个词儿,给某个时候的文学冠一个名讳。我不能说那么做就不好,譬如曾经的红色文学,就很使人振奋。与之对应的,还有一类文学,就需要我们甄别了,特别是被冠之以黄色文学的东西,就更要为人所不齿了。
我好奇的是,经常听得见有人在声嘶力竭地喊叫什么女性文学,就让我特别困惑,不晓得文学怎么就还有了性别之分?
为此我欲找来两个人,以他们为例,证明那样的说法是不靠谱的。譬如身为女性的李清照,她诗性地喊出“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句子,男性的人,有谁说得出来?再是坐上皇帝位子的李煜,一个完完全全的男人胚子,他皇帝做得不怎么样,词填得还是很不错哩。但他所填词句,太少男人的气概了,“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是《清平乐·别来春半》里的句子,我一点也读不出男性的阳刚之气。再是《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他所喟叹的,依然难觅男性的气质,而多是女性的幽怨与缱绻,“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因此我要说了,文学就是文学,没有什么性别之分。
但要进行一种色彩的划分和区别,倒是非常不错的呢!像我文中举例的红色文学一样,近些年来,有个“绿色文学”的提法,突然地横在了大家的面前,且还十分的靓丽,十分的吸引人。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说法,并乐于投身其中,使自己亦然成为一个绿色文学的践行者。这是因为,绿色文学的提出,非常的及时,也非常的有针对性。其背景是,我们今天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资源越来越少,人类生存危机感越来越大。正如践行这一理念的先行者说的那样,“将生活中的绿色,及环境问题,以文学的形式展示出来,传播不可缺失的绿色理念。”
绿色文学兴起的今天,可否视其为一种精神,让更多人加入进来,寻找并发现生活中的绿色元素,壮大我们对于绿色的崇拜。
试想一下,人类生活的自然界里,如果没有绿色的存在,个体的人还能存在吗?答案该是肯定的,一定难以存在。我因此想到,从文学出发,似乎还不只是个自然的绿色问题,还扩而广之,引申进人的精神与灵魂中去,以此观察和考量我们的文学立场,是环保的?还是非环保的?是积极向上的?还是颓废落后的?不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作家的笔头,就把握不准方向,就写不出鼓舞人、激励人的绿色作品来。
我向往绿色文学,我立志绿色文学。

刘笑伟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现任《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大校军衔。出版有《强军 强军》《家·国:“人民楷模”王继才》等16部著作,多次获得军内外文学奖项。
“绿色文学”首先是给我的印象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学。试想,在文学的“高山厚土”之上,一片片绿色的草木在蓬勃生长,这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
“绿色文学”从陕西这片黄土地上“生长”出来,是非常符合历史与现实逻辑的。从历史上看,从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救亡大旗,吸引了无数文学青年奔赴延安,经过黄土地的哺育与滋养,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指引与改造,那一代青年作家的创作焕发出勃勃生机。涌现出《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等文学作品,艾青、何其芳、丁玲、贺敬之、柳青等一串串闪光的名字,让青春与文学的延安璀璨夺目。从现实来看,陕西的青年文学也充满了蓬勃生机与活力,“陕西青年作家走出去”丛书影响不断扩大,初步形成了文学“青年陕军”的人才方阵,这是可喜可贺的事。
此外,“绿色文学”应该是健康的文学。这个健康,一是创作方向,二是创作内容,三是创作者队伍。“绿色文学”就是要坚持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的创作方向,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讴歌时代的风云变迁;创作内容上要杜绝低俗、庸俗和恶俗,让文学中充满青春的阳光;青年作家要注意涵养修为,力争做到德艺双馨。这也是“绿色文学”对创作的内在要求。
一言以蔽之,“绿色文学”就是青春的文学,健康的文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学,就是像大树一样扎根于生活、像树叶一样富有绿色生命力的文学。

林 雪
现居沈阳。曾参加诗刊社第8届青春诗会。2006年获诗刊社新世纪全国十佳青年女诗人奖,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出版诗集《淡蓝色的星》《蓝色钟情》《在诗歌那边》《大地葵花》《林雪的诗》等。随笔集《深水下的火焰》、诗歌鉴赏集《我还是喜欢爱情》等。
还是新千禧年之初,偶然读到一本《沙郡岁月》,是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看到书评界称其“是紧步伟大的女性雷切尔·卡逊(Re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后尘的又一传世之作”,于是引发了阅读的连锁反应,又找来了雷切尔·卡逊的书,且一发而不可收。转眼十几年过去,翻译成中文、流行于世的世界生态文学代表作也几乎通读了一遍,但最难忘的仍然是《沙郡岁月》。尽管它后来变身《沙乡年鉴》或《沙郡年记》,曾被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评为“本世纪自然写作领域十大好书之一”,并拥有“生态平等主义的圣经”、“大地伦理的倡言书”等诸多美誉。而我心中优秀的绿色文学应有的特质,就是像奥尔多·利奥波德作品那样展现价值观中自由、民主的高级阶段,既厚重绵远沉思、又细致婉约的人文情怀,锐利、鲜明的责任担当,传统和先锋完美结合的崭新风格。遵守大地伦理,就是在狩猎文化、农业、林业、城市绿化,以及所有的植物学科中重新找到人与大地的新的平衡点,绿色精神则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和谐共进,并能使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契约。
我是被绿色精神开悟者。每当忆起我从书店里漫不经心浏览了一页,继而对大师的理念、精神和语言风格惊为“天书”、视为知己的“灵光”行为,对自己由无意邂逅到主动关注、履行绿色文学使命,都有一份幸运和欣慰。

李 瑾
山东沂南人,历史学博士。曾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发表作品,并入选数十种选本。曾获东丽文学大奖、长征文艺奖、李杜诗歌奖、名人堂·年度十佳诗人和十佳诗集、中国诗歌年度十佳诗人等若干奖项,出版诗集、故事集、评论集、儿童文学作品及学术作品多部。
我倾向于认为,绿色文学是一个现代性的“诗学”对象。也就是说,作为“诗学”对象的绿色文学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逻辑框架或历史事业,也是一种行动:即如何对待个我和自我、个我和他者/社会、个我和自然/时间的思维方式和文化选择。显然,绿色文学内在理论体系中,这一概念和“诗”一样具有象征意味——假如承认“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样的判断,那么“诗”和“思”在人/存在问题具有共同源头,二者统一在绿色文学或文学的价值判断宏大模式中。故而我们可以如此设定绿色文学的叙事/表达目的,它追寻或思考的不过是人的诗意生存和栖居。这样一来,所谓“绿色”、生态、自然都不过是迷人的幌子,该概念或理想统摄下的文学处理的是自然/生态危机下精神或人性危机问题。因此,无论《塞尔彭自然史》还是世界自然文学三部曲的《寂静的春天》、《瓦尔登湖》、《沙乡年鉴》都以环保/生态为由头探讨人自身的困境和难题。必须指出,绿色文学具有庞大而深厚的历史渊源,即便中国都可以追溯到诗经和骚辞传统,但发展到今日,则具有人和自然何者是中心的启蒙意义。进一步说,绿色文学的出现改变了文学的传统定义和精神谱系,即文学必须去创新性阐释人的位置和人同自我、社会以及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是绿色文学要经手的三个维度或层次)——绿色文学是反个我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它尊重他者和万物,即他者和万物都有不依赖于“我”/人的标准的内在价值,它们都推崇再生性而拒绝侵犯和灭绝,和谐地、超越性地生活在一起是共同意旨。因此,绿色文学是自带光性的,作为一种可期的理想国文学或乌托邦文学并非完全不着边际,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精神追求是同频共振的,恰如《中庸》所作的精神性总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袁 梦
80后,武汉理工大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安徽省作协会员,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挥着翅膀的女孩》,小说集《七零八落》,绘本《墨语闲缘》。另有学术专著《动画剧本创作与分镜头设计》(全国规划教材)《有巢氏文化中的设计美学》等。
也许,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看不懂或者无聊,恰恰是因为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的触角不再敏锐,心变得粗糙,不再对自然的痛苦感同身受,同时也失去了感知安宁的能力。即便作家,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像梭罗一样,愿意抛弃安逸的城市生活,独自在瓦尔登湖畔这样人迹稀少的地方常住,并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真正做到对自然进行感悟,对人生进行思考呢?
我对《逍遥游》一直心有戚戚焉,我猜想庄子笔下的鲲是不是就是现实中的鲸?可是来不及探寻,或许鲸就要如同龙一般,即将成为传说。
曾和民俗学刘宗迪老师讨论《山海经》,他说这并非是一本怪物志,而是一本博物志。只是到了今天,很多动物都灭绝了,有些进化或退化了,有些因为科技的发展,还原了传说的原貌,褪去了神话的外衣。一件东西一旦不再神秘,也就容易让人失去了对它的敬畏之心,觉得不过如此。
1854年,梭罗就对着崇拜时尚和物质享受至上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大声疾呼:“简单,简单,再简单!”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也在《寂静的春天》深刻地指出:“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就是埋葬自己。”
人们终究认识到,自然万物都有其独立的价值并相互联系成为统一的整体,人只有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才能拥有完整真实的生命。
这些认知得益于这个涌出越来越多绿色文学的时代,饱含了对生态危机的担忧和对过往生活的思考,正影响着更多人的生活方式和与世界相处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