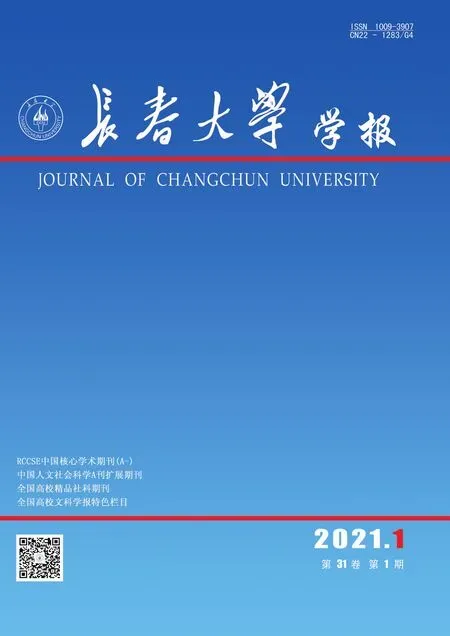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
白燕玲
(山西大学 商务学院,太原 030031)
19世纪前后,西欧经过了资本主义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共同洗礼,在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革。然而,当时的清政府排斥乃至拒绝接受这样的变革。因此,蒋廷黻先生说:“在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中华民族丧失了20年的宝贵光阴。”[1]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内忧外患的现实让中坚阶层中部分知识分子有所觉悟,他们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寻求与探索新的治国方略,郭嵩焘就是其中之一。郭嵩焘(1818—1891年),字伯琛,号筠仙,晚年自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郭嵩焘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郭嵩焘日记》《郭侍郎奏疏》《使西纪程》《罪言存略》等,郭嵩焘先生的著作中多有其洋务思想及其具体洋务主张的体现,是研究其洋务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一、郭嵩焘洋务思想的独特主张
(一)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批评洋务派只学习西方军事
(二)提倡发展工商业,主张商民自办发展近代工商业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开始逐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导致一大批官办的工商企业既具有封建性,又对外国资本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对此,郭嵩焘出使外国之后对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有了初步认识。他提出,中国发展近代工商业时,应坚持商民自办,他反对官办或官商合办。郭嵩焘之所以反对官办或官商合办,是他认为这一类性质的企业,只会照搬封建社会的衙门作风,依官样行之,最终成为官僚们谋私的工具。光绪元年(1875年),郭嵩焘上奏光绪皇帝:“……窃谓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明确主张应让商人自己开办机器局,并分析了让商人自办的理由,其中之一就是因为目前国家财力有限,若资之商贾,则可以官商两利。郭嵩焘在英国期间,曾记录了伦敦《泰晤士报》对招商局的评论:“讽刺中国……直谓相沿制度及各衙门所办事件及官人德行,相习为欺诈已数百年。”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提倡“商人自办”的主张可以避免官商合办后产生的不良后果,有其进步的一面。并且这一主张的实质正是提倡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郭嵩焘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
(三)主张发展近代教育事业,提倡教改培养新式人才
郭嵩焘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也在于中国人才缺乏,学校不修。其指出:“诚诚欲挽回人心风俗,必自学校始。两千年来,人才所以日下,由学校之不修也。此关天下全局,非一时一事之计。”[4]他将教育提到关系“天下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并指出中国要“求富自强”,就必须要向西方国家学习,要培养出精通西学的人才,这就需要创办新式教育。郭嵩焘在出使国外期间对英国的教育发展程度也赞叹不已。《使西纪程》中提道:“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开而专习之。”由此可见,郭嵩焘看到西方国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愈出愈奇,与其重视学问、善动脑筋是分不开的,他批判中国的士大夫们仍沉醉在自己的“虚骄大言”之中。为了深入了解西方近代教育制度,郭嵩焘还参观了英国的各类学校,他在给沈宝桢的信中这样写道:“嵩焘读书涉世垂四十年,实见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可见,郭嵩焘强调教育是国家振兴的迫切需要,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学校、书院早已沦为朝廷取士的工具。郭嵩焘企图效法西方经验,以改革中国教育模式,因此在回国后便积极从事教育制度的改革,试图将西方的教育思想和科学技术引入中国,为中国的自强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在郭嵩焘等人的大力推行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被宣布正式废除。由此可见,郭嵩焘对创办新式学校为国家多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思想开启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先声。
二、郭嵩焘“洋务思想”形成的阶段分析
(一)鸦片战争爆发,全面侵华开始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郭嵩焘决定赶赴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僚。这一年,鸦片战争正式爆发。郭嵩焘抱着“好谈形势向鲛门”的想法到了浙江,开始关注中英战争的发展态势。然而,他却目睹了清军惨败在了“夷狄”的坚船利炮之下。郭嵩焘在前线考察中,目击了侵略者屠杀掳掠的暴行,更加激发了他满腔对西方侵略者切齿的痛恨和对人民深切的同情。他在《丰乐镇书壁六首》的前言中道:“西夷内犯,略其家,其妻投水而死。诗词婉咽,恻恻动人。既读哀之,依韵以墨其后,庶来者之有知与。”这种亲身的感受,直接激发其爱国意识,对郭嵩焘后来洋务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
郭嵩焘在其所著《罪言存略》中提道:“当庚子辛丑间,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这里的“庚子、辛丑间”,指的就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之间。这表明,郭嵩焘洋务思想形成的契机,正是源于英国的侵略,探讨“战守机宜”而激起的不可遏抑的“忠义之气”,集中表现了郭嵩焘强烈的爱国热情。由此,郭嵩焘迈出了探索洋务的第一步。
(二)研习外域外情,深入研究洋务
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直接激发了郭嵩焘的爱国意识。从那以后,他开始认真研读各种介绍西方的译著,主动与来自西方各国家的人员交往,了解西方。不仅如此,他还认真阅读和研究中国古籍,总结历代累积的防御“夷狄”的经验与教训。郭嵩焘在他的《〈罪言存略〉小引》中写道:“嗣是读书观史,乃稍能窥知其节要,而辩证其得失。”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郭嵩焘开始意识到,清王朝之所以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原因在于不懂外情,因而措置失宜。于是,他开始努力了解外情,思考“洋患”,试图能全面地了解西方,认识世界。
咸丰六年(1856年),郭嵩焘在杭州为湘军筹款。在这期间,他与浙江学者邵懿辰就“西洋测天之略”的问题曾进行过探讨。《天津条约》签订后,郭嵩焘认为,朝廷在“夷务”上举措失当,原因在于不了解“夷情”,缺乏“解事者”。为了使国家“自立”,就要有“解事者”,真正做到“守正以明理”。郭嵩焘通过读书观史以“解事”,开始深入了解、研究洋务思想及洋务运动。但此时,郭嵩焘对洋务思想还停留在理论表面,尚未真正在实践中开展、办理洋务。
(三)亲自办理洋务,接触西学西政
虽然郭嵩焘早期通过读书观史,对洋务已经有了初步了解,但是一直到同治二年(1863)九月任广东巡抚之后,才真正开始直接办理洋务。郭嵩焘在他的日记中也有所提及,“其处置洋务以理求胜”。而郭嵩焘所谓的“以理求胜”,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洋务,应深入体察中外各方面的情况,并实事求是地采取相应对策;二是通晓外交和外事惯例,严格根据法律原则与西方人员打交道。
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七日,郭嵩焘从上海搭船赶赴英国。次年,总理衙门正式颁发国书,十一月间,郭嵩焘将国书呈与英王。从此,郭嵩焘成为近代中国名副其实的首届驻英国公使。在英国期间郭嵩焘常到各处进行考察,对英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十分欣赏西方国家以议会制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现在西方国家存在“庶人上书,皆与酬答”的现象。通过在为官期间直接接触西学西政,郭嵩焘更深入地了解到,西方国家如此高的民主与透明,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为了得出更确切的结论,对于英国税收、遗产法、邮电、消防、城市建设、人身保险等社会各方面,郭嵩焘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最终发现:“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所以利国者,即寓于便民之中。”[5]在郭嵩焘看来,英国把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直接联系起来,比起中国,显然是历史的进步。不仅如此,为了形成对西方文明更加全面的认识,郭嵩焘还对西方的教育、宗教思想、社会习俗等各方面,从多角度都进行了查访与探究。由此可见,为官期间直接接触西学西政是他独具特色的洋务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历史价值
(一)开创近代思想解放先河,打开近代外交之门
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对比同时代李鸿章、刘坤等人的洋务思想更具有思想解放性,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近代思想解放的先河。在郭嵩焘将国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结合到一起进行推行阐述后,人们不再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奇巧淫技”,民智逐渐开启。而郭嵩焘“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主张学习西方治国理政、法律制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意味,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启蒙力量。学者高立群在深入研究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历史意义时指出,郭嵩焘相比同期其他洋务运动的提倡者,是首位打开近代中国外交之门的人[6]。一方面,郭嵩焘是首届驻英国公使,也是清政府从闭关锁国后的第一位驻外国公使,其不仅在实践中起到了沟通中外交往的桥梁作用,还在思想上大力批判晚清士大夫“天朝上居”的思想,主张摒弃“夷夏之辨”的观点,启蒙了当时人们的外交思想。另一方面,郭嵩焘通过自己的外交经验,总结了“和为贵”“知时”“审己”的外交观及“以礼相待”的外交方式,为当时及以后人的外交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参考[7]。
(二)深化人民西方思想认知,促进维新变法开展
郭嵩焘解放、独特的洋务主张深化了人们对西方思想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维新变法从洋务运动中的分化,对维新变法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中也有不同的流派,其各有各不同的来源。维新变法中,以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为主的“历险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的维新思想,同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法”的维新派走的是不同途径。陈寅恪指出,陈宝箴的维新思想就是深受郭嵩焘“颂美西法”的洋务观影响[8]。陈宝箴支持创办《湘学报》、创立南学会等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学习了郭嵩焘提倡近代教育、培养新式人才的思想。学者王俊桥也指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对陈宝箴湖南维新运动有深刻影响,而戊戌维新在理论上虽然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但其实践的基础则是由陈宝箴的湖南变法运动所提供的[9]。可见,郭嵩焘的洋务观对当时的文人志士有一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维新变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重视国家主权,为治国理政提供启示
鸦片战争后,郭嵩焘面对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自认“忠义之气不可遏”,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在当时晚清政府被列强欺压的背景下提出维护国家主权的观点,具有振聋发聩之意义,对于后世治国理政也具有启示意义。郭嵩焘上奏《请纂成通商则例折》强调国家需通过立法来捍卫国家主权,只有用“法”来维护中外通商,才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此后,以王韬为首的洋务派也纷纷响应郭嵩焘《请纂成通商则例折》中“维护国家主权”的思想,反对清政府对外国人额外开放的“治外法权”,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10]。可见,郭嵩焘的主权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为其他官员治国理政提供了启示。除此之外,郭嵩焘的重视国家主权思想与当前我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可见,郭嵩焘的部分洋务思想在脱离当时代的背景下仍然是可取的,在现代仍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四、结语
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其所倡导的洋务主张虽没有实现清政府国富民强的复兴梦,但其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却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制度在我国的传播,并打开了国人的视野、改变了国人的观念,推动了维新变法的积极开展,为近代历史上清政府的救亡图存活动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后人思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