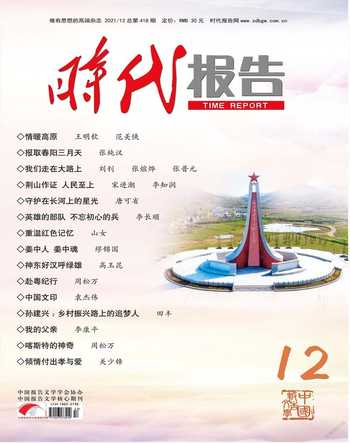我的父亲



此时此刻,父亲就那样静静地、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神态安详得像进入熟睡的梦乡一样。父亲一定是在做一个甜蜜的梦,在美丽的梦境中,父亲决然义无反顾地去往那個无忧无虑、无病无痛的天界仙境了。父亲终于把一切都放下了,放下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放下他一生为之操劳的幸福家庭,放下他一生相濡以沫的恩爱妻子,放下他一生挚亲挚爱的骨肉儿女。从此天地相隔两茫茫,不堪思量永难忘。我知道,父亲此别是再也回不来了。顿时,我泪如泉涌,用心铭记下这一痛心的时刻:公元2021年10月13日(农历辛丑年九月初八)17时36分,父亲在北京香山医院溘然长逝,享年98岁。
革命一生不忘初心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1924年农历三月初三,陕北黄土高原已是冬去春来日暖花开的时节,父亲出生在陕西米脂县郭兴庄镇李兴庄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爷爷奶奶育有四子两女,父亲为长子,按李姓辈分排为锦字辈,四子取名最后一个字分别为荣、华、富、贵,因此,爷爷给父亲取名为李锦荣。父亲长大参加革命后,觉得荣华富贵仅仅是农民的个人愿望,而革命人的志向应当更远大、更理想。于是父亲便自己改名为李景云。《淮南子·天文训》曰:“虎啸而谷风生,龙举而景云属。”景与锦谐音,辈分不改。景云则为祥瑞之云,但父亲是取革命者壮志凌云之意。
父亲从小就读于久负盛名的陕西米脂中学。米脂中学是1927年4月由著名爱国人士、教育家杜斌丞先生和地方贤达共同赞助创建的,已有90多年的办学历史。创建之初名为三民二中,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之后,更名为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米脂中学建校90多年来,培养出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科学家,可谓桃李满天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父亲在米脂中学就读时,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也打下了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
1944年6月,20岁的父亲从米脂中学毕业后立刻投身革命,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志丹县二区工作。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红军东征战役英勇牺牲的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更名为志丹县。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奠都志丹县,党中央、毛主席曾经在这里战斗生活了6个多月,被誉为“中国革命的红都”。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战的中心,也是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指挥中枢所在地和总后方。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边区军民一边要开展武装斗争,一边还要搞好经济生产和文化建设。父亲参加工作之后,充满革命的热情和活力,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中,积极下乡组织农村农业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前线。由于父亲好学上进,工作积极勤奋,只工作了半年,就被党组织推荐到以革命圣地延安命名的延安大学继续深造。
延安大学最早是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讨论,将1940年5月成立的泽东青年干校、1939年7月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1937年10月成立的陕北公学院三校合并组建的。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为延安大学首任校长。父亲在延安大学就读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已于1944年4月将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周扬为延安大学校长。父亲是在延安大学行政学院教育系,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学习,在圣地延安革命摇篮的熏陶下,提高了理论素养,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更加坚定了革命的理想信念。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爆发全面内战,对解放区大举疯狂进攻。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党中央、毛主席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1946年8月,父亲从延安大学毕业回到米脂县人民革命政府,立刻投身到转战陕北的备战工作中去。1948年4月,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父亲在米脂县又积极参加了习仲勋同志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土改工作。当年,习仲勋同志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精神,力排土地改革中“左”倾思想的影响,通过调查研究和整顿党的领导,结合边区现状,探索出一条适合陕甘宁边区实际的土改路线,为其他各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年8月,父亲在土改工作一线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随着大批陕北干部南下,先后担任陕西户县永定区区长、户县城关区委书记、咸阳地委干事、镇坪县团委书记、县委组织干事、安康地委办公室秘书、安康行政专员公署办公室主任。我看到1963年12月安康专署办公室给父亲的一份组织鉴定说:“1.对党一贯忠诚,政治立场坚定,在工作中能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坚持原则,按政策办事。2.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如认真地细致地审阅和修改公文,并经常亲自动手起草。对领导布置的工作,认真地贯彻执行,积极去办,按时完成。3.民主作风好,遇事能和大家商量,如自己写的材料和修改后的公文,总是征求同志们的意见。4.吃苦精神好。如经常主动提出要求下乡,下乡工作常常到困难的地区去,并及时写报告,反映情况。5.个人学习抓得紧,学习中能联系实际。6.关心同志生活,主动帮助解决同志们生活困难……”
这份组织鉴定是对父亲在专署办公室工作的肯定,又何尝不是对他一生革命工作的肯定呢!
文革后期,安康地委、专署“靠边站”的老干部分批从“五七”干校下放到农村劳动。父亲从“五七”干校下放到紫阳县蒿坪河区农村劳动,当时我在安康县岚河区知青点插队,我便步行50多里山路去看望下放劳动的父亲。我去的那天父亲正在地里劳动,农民听说我找父亲,先把我领到父亲的住处,然后下地去叫我父亲回来。父亲住在一间农民的房子里,屋子的一角铺着父亲的木板床,支了一张木桌,屋子另一角柴火堆上架着陕南农村常见的铁吊锅,烧水做饭都是用吊锅,屋子被柴火熏得黑乎乎的。原以为老干部下放劳动都是被人看管得很严,可是父亲下地并没有人看管,一个人很自由地就回来了,只是父亲全身上下整个就是农民模样,全然融入到下放农村劳动生活中了。父亲看到我来非常高兴,立刻架起柴火给我做饭。父亲本不会做饭,下到农村竟然自己也学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了。记得那天父亲给我做的是拌汤,水烧开了,把拌好的面疙瘩往吊锅里一搅和,煮开了再倒进炒好的酸菜,一锅酸菜拌汤就做成了。酸菜拌汤是陕南人最爱吃也经常吃的饭食,在生活困难时期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拌汤是当主食几乎天天要吃的。但是父亲那天做的那锅酸菜拌汤很稠,做好后还给我碗里滴了几滴香油,在我的味觉记忆中,那是我吃过的最香最好吃的拌汤了,我连吃了三大碗,直到吃得锅光碗净,才突然发现,父亲早就放下碗在一旁开心地看着我吃完。
1970年,“靠边站”的老干部有限地分批恢复工作,父亲被下放到陕西省旬阳县,先后担任神河区任区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区长一职)、旬阳县文教局長。1975年再次落实干部政策,父亲调任安康地区卫生学校党委书记。
文革时期,学校是受冲击最严重的重灾区之一。父亲到任前,安康卫校几经搬迁,甚至一度停办,学校发展十分缓慢。1977年9月,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父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带领教职员工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校,学校逐步走向正轨,教学质量不断提高。1982年、1983年连续两年在全省中等卫校毕业统考中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1984年再获第一名,受到了陕西省卫生厅、安康地委、行署的表彰。1986年,父亲以副厅级职级离休,2014年,获批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1995年、2005年和2015年,连续3次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抗战老战士老同志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60和70周年纪念章,表彰父辈的历史功勋,彰显他们的荣誉地位。
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父亲又获党中央首次向党龄50年以上老党员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而这年,父亲实际已经光荣在党73年了。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父亲一生牢记使命,毕生都努力践行为崇高革命理想而奋斗终生的钢铁誓言。
学习一生孜孜不倦
父亲一生酷爱读书学习,这与父亲从小就读于治学严谨、人才辈出的米脂中学有关。在米脂中学,父亲在接受革命教育的同时,如饥似渴地饱读诗书,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直到他96岁高龄住进医院时,还常跟医护人员大段地背诵唐诗宋词古文佳句。
在父亲的书桌案头上,总是摆满了俯案时比人头还高的一摞摞书籍卷册。读书人惜书如珍。父亲的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部看不到书籍原来的封面装帧设计,几乎清一色都用画报纸,没有画报纸就用报纸包上一层书皮,然后在书的封面和书脊位置写上书名。
父亲读书的兴趣很广泛,除了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之外,最喜爱的书便是《鲁迅全集》了。1973年,人民文学社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当时印量有限,父亲非常喜欢,立刻托书店的朋友帮助购买一套回来,连夜捧读。读过之后,父亲还是有点遗憾,他说,也许是因为特殊年代出版,所以这套全集并不能全面展现鲁迅的作品。因此,当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鲁迅全集》,父亲又全套购买回来收藏阅读,直说这个版本收得全,出得好。
父亲还喜欢读《史记》《资治通鉴》《春秋》《东周列国志》《红楼梦》《古文观止》《聊斋》等中国古典名著以及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契诃夫等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常常用书中的故事来教育我们。一本《聊斋》上面真是红笔圈来蓝笔点,显然读过不止一遍。有次父亲给我讲述了雨果《悲惨世界》主人公冉阿让的故事,给我以强烈的震动。父亲给我讲,书中的主人公冉阿让为了养活孩子偷了一块面包被判5年苦役,却在监狱里蹲了19年。冉阿让出狱后心怀报复社会的扭曲心理,又偷窃收留他的主教的银器再次被警察抓住。而主教体谅了冉阿让的生活困境,没有指证冉阿让的偷窃行为,反而再赠送他一些银器以解生活之忧。正是因为主教善良的以德报怨之举,给冉阿让心灵上带来巨大震动和感化,从此他弃恶扬善,痛改前非,为社会做出贡献。书中所展现的正是人性善良博爱的伟大光辉。
父亲讲述冉阿让的故事,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善良与道德力量的伟大所在,吸引我不但立刻找来此书仔细阅读,还常常把书中冉阿让的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教育孩子与人为善、以德报怨成为家庭的一种道德传承。
小时候,我对父亲书架里大部头的理论书籍不感兴趣,但是意外地发现书架里竟然还有几本苏联科幻小说强烈地吸引了我。书中长长的外国人名字难读难记,可是有一本讲述宇宙、星球、太空和21世纪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乘坐火箭飞船到太空去旅行,地球人也大批移民到外层空间,住进环绕地球轨道的美丽太空城市的故事,却给了我无限的遐思和向住。父亲还有一本《科学家谈21世纪》的科普书,也激起我对科学知识的极大兴趣和丰富想象。当年最流行的少儿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记得父亲最先买的是第三册,讲的就是天文学知识上的为什么。与其说这本书是父亲给我买的,倒不如说是父亲引导我和他共同阅读。书中我读不懂的地方,父亲就把他知道的天文学知识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给我听。从父亲的讲述中,我从小就懂得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开启科学智慧大门的金钥匙,这也正是我从父亲读书生活中汲取到的最大能量。
父亲80多岁的时候,突然询问我电脑方面的知识,原来,他从报纸上不断地读到有关互联网的消息,说网上世界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读书、看报、聊天更加方便。因此,父亲要学习电脑,要用电脑学习上网冲浪。于是,我赶紧给父亲配置了一台电脑,教父亲怎么联机,怎么上网,怎么点击打开链接等。父亲着实过了一把“网瘾”,但还是因为多年的阅读习惯难改,最终还是弃网,重新拾起散发着油墨香的纸质书报阅读。
2010年,父亲陪伴母亲来京治病,母亲病愈之后,我挽留父母在北京单独居住在我的另一处住所。父母也非常乐意,常说老了之后和子女同城不同屋居住最好,互不干扰。这样,我和在北京的姐姐李冰、二弟康力全家每逢周末便买些营养品和水果去看望父母。一大家人四世同堂团聚北京,共享天伦之乐,是父母晚年最大的欣慰。我知道父亲有酷爱读书学习的嗜好,每次去看望父母的时候,都要将一周来的各类报纸带给父亲看。父亲每每从报上看到有新书出版的消息,凡是他感兴趣的,都开列一个书单给我,让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买了给他。有一次,父亲让我买一本《时间简史》,我吃惊的是我只听说过这本书是英国物理学家霍金所作,却从没有读过。于是赶紧上网查了一下,原来霍金的这本书讲述的是关于宇宙本性的最前沿知识,包括我们的宇宙图像、空间和时间、膨胀的宇宙、不确定性原理、黑洞、宇宙的起源和命运等内容,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遥远星系、黑洞、粒子、反物质等知识,并对宇宙的起源、空间和时间以及相对论等古老命题进行了阐述。霍金在书里探究了已有宇宙理论中存在的未解决的冲突,并指出把量子力学、热动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存在的问题。该书的定位是让那些对宇宙学有兴趣的普通读者了解他的理论和其中的数学原理。当时,父亲已经是90多岁的高龄,竟然要读如此高深的科学专著,令我自愧不如!还有一次,父亲问我区块链的科学原理,同样把我问得目瞪口呆,赶紧找来有关资料恶补区块链的知识,然后再给父亲介绍。
当年,父亲两手空空拎个小包就来了北京,一住10多年,如今,父亲在北京的书房里又是满满当当的满书柜、一书桌的书,墙角上堆着的纸箱子里都是看过的报纸和杂志,也总舍不得当废纸卖掉。
父亲看报学习还有个习惯,就是看到报纸上好的文章,就剪下来,分门别类用心贴在旧书或旧杂志上,重新编辑成书交给我说:“这便是我编给你的书,好好地读吧,写的都是做人做事的至理名言!”
我惊喜地双手接过父亲的“书”,其实是一本笔记本,用旧报纸包的书皮,书名是用重笔描写几个粗黑大字《留给康平的书》。翻开里面一看,原来都是父亲读报剪贴下来好的文章汇集而成,旁边批写着父亲的读后感。有的短文父亲工整地抄写下来。名人名言励志人生,凡人琐事感人心怀,篇篇精品,字字珠玑,读来爱不释手,受益匪浅。
好人一生平平安安
正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好人一生平安……”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好人,一生都平平安安!
1965年,父亲到安康县恒口区千工人民公社蹲点参加社教运动,也叫“四清”运动,是当时党在农村开展的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和清组织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父亲带我和弟弟到他蹲点的地方,和他一起吃住都在农民家里,要我们从小感受农村农民的生活。一天,我拉开父亲晚上写材料的桌子抽屉,发现抽屉里有两沓全是一角的纸币和半斤的粮票,便问父亲这么多零钱干什么用的,父亲说这是每天给农民的饭钱。那时干部下农村都是吃派饭,今天派在这家吃,明天派在那家吃,每顿饭父亲都把事先准备好的零钱和粮票交给农户。父亲说,给农民大票如果找不开零钱就不收饭钱了,可是农民生活不易,白吃不给钱那怎么能行!从这件小事可见父亲下乡很能体恤农民。
十年动乱开始不久,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父亲也不例外,顶着一顶“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帽子靠边站了。那时,大街上和专署大院到处都贴着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引来“革命群众”争相观看。我们住在大院里的孩子谁要是看到有批判自己父亲的大字报,顿时脸上无光,抬不起头来。可是我们很少看到有批判父亲的大字报贴出来,有天我竟然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不等父亲回答,母亲便说:“还不是因为你爸是个好人,造反派就不批判了呗,好人还是有好报啊!”那段时期,批判父亲的大字报从来没有上过街,专署大院即使贴有批判父亲的大字报,也是轻描淡写地作样子写几句,很快就被人以贴新的大字报为由给覆盖了。后来我才知道,这都是因为父亲为人善良,赢得了群众的尊重、敬重,他们暗中在保护父亲。其中有一个在专署机关烧开水的锅炉工,谁要是说父亲一个“不”字,他就上前跟谁极力辩论,非要争赢不可。原来有一次,父亲去医院排队挂号看病,听到一个中年妇女抱怨说,她丈夫在专署机关忙得不顾家,孩子病了也不回来看看,她手里这点钱也不知道够不够孩子看病的,真是难死人了。父亲听到她讲的情况,大致猜到她丈夫是谁了。便从自己身上掏出钱来给那妇女,先给孩子看病要紧。那妇女回家给丈夫说今天遇到一个大好人,丈夫问妻子怎么回事,妻子告诉他今天带孩子看病可能钱不够,一旁有个操陕北口音的大个子陌生人,没留姓名就掏钱给孩子看病。这个妇女的丈夫正是专署机关的锅炉工,他立刻猜到给妻子钱的是我父亲,对父亲感激不尽,逢人便说父亲是个好人!
1967年8月19日夜,安康发生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一派攻打另一派占据的地委、专署机关大院。事后才知道,这次武斗打伤地委、专署机关干部百余人,砸毁了办公设施,抄了档案室部分档案。武斗还在激烈地进行中,突然有人急促地敲我家的门。父亲开门一看,原来是专署机关的一个干部,曾经他还给父亲写过大字报,可是眼下他正被武斗人员追打,情急之下跑来家属院求救。父亲不计前嫌,赶紧把他让进屋,叫他藏在床底下躲避,并递给他一些水和饼干。这时,武斗人员已经追到家属院挨家挨户地搜查。等搜到我家时,父亲把我叫到前面开门。因为父亲已经是“靠边站”的当权派,而我就算挂个名,也还算是“红卫兵”,兴许还能抵挡一阵儿。碰巧敲门搜查的人我正好认识,是我初二同班同学的哥哥、初三年级学生,这才没进我家搜查,父亲也没有因窝藏“武斗人员”而遭祸殃。听说当晚被抓走的安康地委、專署干部被一派押解到军分区向军方施压,又被另一派“营救”出来转移农村,几经折腾,伤人无数。后来我有点想不通,便问父亲,为什么要救给他写过大字报的人,父亲淡淡一笑说,他也是身不由己,如果不救,我们能眼看着他被抓被打吗?
果然父亲的好心得到了好报。安康武斗愈演愈烈,为躲避武斗枪炮,我们从武斗前沿专署大院迁到安康老城东关,有好心人收留我们;父亲和城内一批老干部被“劫持”到城外,父亲没有遭到“劫持”人员的打骂;又有好心人护送我们出城和父亲团聚。据史料记载,1967年8月31日至1968年5月,安康县两大派造反组织连续发动的大规模武斗造成734人死亡,烧毁大街小巷11条,炸毁防洪堤8357立方米,安康城内第一座自来水厂的水塔被炸毁,县委档案大楼被焚,53所机关、学校成为废墟,380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惨重的教训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永远抹不去的伤痛。而我们一直处于派性武斗的战火中心却毫发未损,也应归因于父亲好人好报的造化。
父亲参加革命就离开家乡,长年在陕南工作,但是家乡建设发展却一直挂在父亲的心上。每次父亲回老家,都要在前庄后村转转看看,给家乡建设出谋划策。从李兴庄村到村前的公路要过一条无定河的小支流,别看小河沟平常水浅蹚着就能过去,可是遇到雨季洪水来袭,小河沟立刻水漫金山,拦住村里人出不去。父亲从小就梦想着将来能在小河沟上修座桥那该多好啊!有一年,父亲听说村里终于筹钱要在这条河沟上修桥了,父亲立刻捐钱助力修桥。桥建成之后,村里人在桥头立碑,感念捐助者,父亲的名字赫然其中。
2020年3月,父亲因病住进北京香山医院。父亲此时97岁高龄,已经卧床不起,照料父亲的护工是一位中年妇女,她不怕劳累不怕脏,悉心照料父亲饮食和大小便,令父亲非常感动,连连称赞护工这样的好人难找。当父亲听说护工收入并不高,而且家在山西农村生活困难时,便将我们看望他带去的水果、点心拿给护工嘱咐一起吃,还让我们每月给护工一些零用钱贴补家用。护工很感动,连说照料父亲也是遇到了好人。
父亲一生为善,皆因信念使然。父亲常用三国时刘备告诫其子刘禅遗诏中的话来告诫我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讲的便是做人的道理,切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
慈爱一生恩重如山
父亲一生心怀爱心,充满大爱。父亲对他的父亲、我们的爷爷敬爱,对弟弟妹妹、我们的叔叔姑姑关爱,对妻子、我们的母亲恩爱,对我们儿女更是倍加慈爱,恩重如山。
父亲15岁那年,奶奶刚生下三叔还没满月,军阀胡宗南的匪兵进到村子抢东西,奶奶踩着梯子正在把家里一点值钱的东西藏起来,听到匪兵枪响,奶奶一慌张从梯子上摔了下来,从此落下重疾卧床不起,很快撒手人寰。父亲是长子,很有担当地帮助爷爷分担起家庭的生活重担,每天放学回家,父亲放下书包就下地帮爷爷干农活,照料几个年幼的叔叔姑姑。有一次,父亲下地帮爷爷干农活回来晚了,看到几个弟弟妹妹蹲在自家窑洞门口,正眼巴巴地望着别人家孩子端着碗在院子吃饭,一个饿得忍不住哭出声来,其他几个也都跟着大声地哭起来。父亲从小就性格刚强,看到弟弟妹妹看人家吃饭就哭,气得给他们每人头上一巴掌,撵回家训斥说:“人穷要有志气,看着人家吃饭就哭,就是没出息的样子,今后谁也不许这样!”说完便赶紧自己动手给弟弟妹妹做饭。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从陕北南下工作,离家远了,但他仍然时刻惦记着在家的爷爷和叔叔姑姑们。每个月发工资的当天,父亲便到邮局给爷爷寄去15元作为赡养爷爷的生活费。20世纪60年代,15元钱在当时的农村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接近当年城镇平均工资的一半,最低生活费的3倍。二叔长大成人以后,父亲给二叔在安康安排了工作,办了婚事成了家。三叔参加工作以后又想当兵,征求父亲意见,父亲全力支持,三叔上了对印自卫反击战前线,在火线入党提干,父亲为三叔感到自豪,说,真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两个姑姑出嫁以后,父亲每次回老家探亲都要去探望,关心她们的生活。有次父亲探望二姑回来,充满感情地对三叔说:“你二姐长得跟咱妈一模一样!”这句话表达了父亲对母亲、我们的奶奶深藏在心底的无限思念。
父亲一生对妻子、我们的母亲非常恩爱,工作再忙,只要回到家里总要帮着母亲多干点家务活,关爱体贴之情非常感人。有时父亲干家务活有点笨拙,出了力反而不讨好,甚至帮了倒忙,父亲和母亲也争吵,吵着吵着又一笑了之,和好如初。
陕南冬天家家都要腌盐菜准备过冬。有一年,母亲将要腌制的大青菜洗净晾着,还没等晾干,父亲就主动帮母亲把青菜切碎了。切菜是个力气活,父亲也是好心帮母亲。谁知道母亲看了却数落父亲切菜切得块太大了腌不透,也不好看,青菜也还没完全晾干,这样腌出来的盐菜水分大,容易坏。一点小小的分歧,竟然酿成一场争吵。父亲心里好委屈,却也不再言语,默默地拿起菜刀重新将大块的青菜细细地剁碎,母亲便也默不作声帮着一道拌盐装坛腌菜。那坛盐菜是我们那年冬天的主打菜,每次母亲切了葱、姜、蒜,过油炒了,父亲也总在碗里挑块大的吃,还自嘲地笑着说“大块的有嚼头”,母亲听了也不好意思地笑出声来。大块的盐菜里就这样透出父母的千般恩爱。
父亲对儿女不善于情感表达,我们几乎从来没听过父亲对我们说过爱啊、想念啊这类动情感人的话,父亲是把对儿女的慈爱深藏在内心里,表现出来的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的严父形象。特殊时期学校停课,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从未停过,经常给我们上课。上课时,让我们立正站在他面前,眼睛望着父亲听他讲课。父亲给我们讲春秋战国五霸七雄相争的智慧故事,讲唐诗宋词的唯美诗句,讲中华传统美德礼仪规矩,记得父亲反复告诫我们一定不要抽烟时,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按一天平均抽一包烟计算,那时最普遍抽的“宝成”香烟两角钱一包,抽一个月的烟就把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抽没了,或者一条新裤子、两支新钢笔就抽没了。没烟抽又没钱买的时候,在地上捡烟头的样子是丧失尊严、非常狼狈的。父亲一边说,一边给我们学人在地上捡烟头凑到嘴边抽的可笑样子,我们忍不住笑起来。父亲却严厉地瞪着我們,吓得我们赶紧止住笑望着父亲,眼睛再不敢朝别处望一眼。正是因为父亲的谆谆教导,我们兄弟三个这辈子都像父亲一样不嗜烟酒。
因武斗全家被困在安康城内时,城内居民每人每月只能供应两三斤口粮。没有吃的,供销社便把库存的黄花、木耳、葛根粉都拿来定量卖给城里的居民,每每用黄花、木耳煮一锅汤,然后倒进调好的葛根粉煮成浓稠的汤来充饥。这时,父亲和地委、行署的一些老干部都被派性组织控制起来,集中在原安康科委的院里办“学习班”,虽然学习班的食堂也管吃,但也没有正经的米面做饭,常常把黄豆用水泡胀了再油炸了当饭吃。就是这份按顿定量的油炸黄豆父亲也舍不得吃,常常拿回家来给我和弟弟吃。当时只觉得这是天下最好最香的吃食,此时再回味起来,才能体会到那都是满满的父爱的味道。
清廉一生明志修身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清廉一身正气,勤俭两袖清风,正是父亲一生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写照。
父亲在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下的时候,干部一律都实行供给制,由单位给干部个人供给生活所需,吃在食堂,住在宿舍,春秋两季发放换季衣服,每月还发给几元到十几元不等的零用津贴,用于购买肥皂、牙膏等个人生活用品。因此,在参加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根本没有个人家庭财产的概念,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在安康行政专员公署任办公室主任,同时分管专署机关后勤服务工作,我们一家还住在父亲的一间不到12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房间的一角是父母的床,靠床安放着父亲的办公桌,另一角支一张单人床再加一块不到一尺宽的木板,是我和二弟的床。我们出生后先是住在保姆家里,上幼儿园是在全托班,上小学是在食宿班,只有周六和寒暑假回来和父母一起在办公室住,在专署机关大食堂吃饭。父亲没有家务负担,把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直到三弟出生,办公室实在住不下一家五口人,父亲在与专署机关大院相通的小家属院找了一间15平方米大的房间,一家人这才搬离了父亲的办公室。
20世纪50年代初,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以后,父亲的工资定为113元,这在当时属于高工资,高出当时安康城镇职工平均工资3倍多,再加上母亲的工资,我们一家人应当是生活无忧了,但是那时的日子依然过得非常节俭。小时候家里的家具除了机关公用桌椅和木板床之外,便是父亲买来的3个樟木箱子,说是准备将来给3个儿子一人一个,另外就是父亲用钉子钉几块木板自己做的一个两层的碗柜,放在一张桌子上。做饭用的炭炉和柴火灶都是父亲用碎砖块和黄泥糊的,父亲糊炉灶的时候我们在旁边看,父亲一边糊,一边告诉我们炉膛要大,收口要小,便于聚焦火力。父亲教会我们以后,再糊炉灶就由我们自己动手了。炭炉烧的是当地产的大块石炭,父母和我们自己用铁锤砸成小块填到炉内烧,碎炭末再和上黄泥做成炭岜子掰成小块再烧,一点都不浪费。文革期间,专署机关食堂停办,小家属院几家人做饭都在自家门口,一家炒菜,各家闻香,倒也其乐融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品供应紧张,父亲骑着自行车到乡下农村去买萝卜、白菜回来以“瓜菜代”填饱肚子。为了让我们能吃饱一点,父亲也多买一点,结果回来的路上还重重地摔了一跤,自行车胎也漏了气,父亲推着自行车走了好几里路。父亲下放到旬阳县神河区当区委书记的时候,有一次,神河街上的食堂杀了猪,特意留了一些酱猪头肉问父亲要不要,父亲没舍得买酱猪头肉,只买了两个酱猪蹄拿回来给我和二弟一人一个。当我们确认父亲不是让我们当菜就饭吃,而是就这样吃掉时,又是惊讶,又是惊喜,很快就狼吞虎咽地吃个一干二净。我们吃的时候,父亲就一直在一旁看着我们,自己却没舍得多买一个一起吃。这只酱猪蹄是我人生第一次奢侈大餐,酱猪蹄也成了我喜爱吃的食物,但是,从此再也没吃到父亲当年给我们买的那只酱猪蹄一样的美味来。
20世紀70年代末,一时兴起比家里的家具有多少条腿,比如说桌子、椅子、柜子都是4条腿等,据说最多的要达到72条腿。当时我们家的家具不管多少条腿也都是公家的,自家没有置办一个像样的家具。于是,我们撺掇父亲也给家里添置一点像样的家具。父亲不屑地说,比家具腿有意义吗?多几条、少几条不都是一样过日子嘛!把工作干好了比什么都有用,都有意义!但是经不住我们一再缠磨,父亲最终还是同意添置一个大衣柜。但是为了省钱,父亲没有去家具店买现成的漂亮家具,而是去木材厂买了半立方木材,请了木匠来家里做衣柜,然后自己买了一种叫哈巴粉的棕色颜料和清漆,自己打磨染色上漆,说这样能省不少钱。父亲总是这样生活节俭得过且过,从不追求时尚购买大件物品。家里后来添置的第一对沙发是我自己动手做好拿回家的,第一台电风扇是我给父母买的,第一台单门电冰箱是弟弟家换下来的,一台显像管彩电看得色彩还原都失真了还舍不得换新的,后来还是长孙李乐从北京回老家给爷爷奶奶买了一台液晶彩电。2010年,父亲陪伴母亲来北京看病,病愈后我挽留父母:留在北京不回安康了。父母说,来的时候都没带什么换洗衣服,我和在京的姐姐李冰、二弟康力便争相给父母买衣服。父亲赶紧叫停,说现在的衣服质量好,怎么穿都穿不烂,有两件能换够穿就可以了,买多了也是浪费。父亲对这样俭朴的生活非常满足,常说,过去皇帝也没看过彩电,没用过这么多的家用电器,要懂得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啊!
父亲长期担任领导干部,少不了有人来请父亲帮忙解决实际问题,事后也有人拿来礼品登门感谢。但是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父亲往往一口答应,事后感谢父亲就一概谢绝,拿来了也拒收,怎么拿来的还怎么拿回去。有时弄得对方很尴尬,父亲也不管不顾。有一次,以前一个在专署的下属对父亲一直心存感激,他知道父亲的脾气,因此来家里敲开门一句话也没说,放下礼品就走,父亲叫也不回头,追也没追上。于是,父亲和母亲商量,找一个过节的日子,买了同等价值的礼物也到他家去看望。那位下属见父亲亲自来看望他,更加感动,又找了机会再次到家里来登门感谢,父亲再以同等价值的礼物回敬对方,这样你来我往一直持续了好几年。父亲以此为例告诉我们:“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礼记》的经典名句,一定切记。”还专门告诫说:“不义之财君莫取,这是古训,也是做人的底线。为官一任,造福四方。党员领导干部修身养性,绝不可贪取不义之财。”
新时代党内深化反腐败斗争,父亲非常关注,每看到打倒一只“老虎”,或者拍到一只“苍蝇”,父亲都拍手称快,痛斥他们这是咎由自取,活该。但也每每告诫我们千万要引以为戒,防微杜渐,做共产党员就要像共产党员的样子。每次听到我们说在外面和朋友吃饭了,父亲都要询问有没有吃公款,有没有收礼送礼,听我们说没有,父亲才放心地笑了。
亲爱的父亲啊!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您高风亮节,堪为典范;作为我们母亲的恩爱伴侣,您无私奉献,真情陪伴;作为子女慈祥父亲,您哺育情深,父爱如山。如今,您虽然离我们远行,但是您的大爱依然润泽子孙,您的大德永远启迪后昆。我们此生无法回报,来生我们还做您的子女,再报您的大恩!
作者简介:
李康平,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铁路作协会员。自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200余万字,散见于报刊杂志并获多种奖励。撰稿、编导《京九铁路》《写在雪域高原的忠诚》《拉林铁路》等多部电视专题片;编剧电影《U57次谜案》在央视播出;著有报告文学集《中国高铁时代的新生活》(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风雪新天路》获2019年第二届全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大赛网络人气奖,与他人合著长篇报告文学《开拓者之歌》(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中),2018年起,在《中国报告文学》杂志开辟专栏《来自拉林铁路建设一线的报告》,连续两年多刊发系列报告文学30余篇共35万余字。
责任编辑/卢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