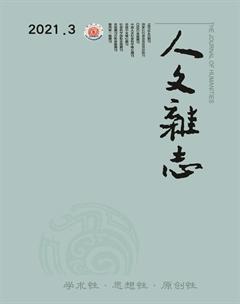先秦古籍“伪书”说清算、正名及反思
关键词 先秦古籍 伪书说 清算与正名 出土文献 先秦文献辑佚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3-0041-11
从事先秦思想史研究,碰到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是“伪书”说。一方面,研究者着手研究的许多先秦古籍在历史上戴着“伪书”的帽子,相关研究会遭到带着这种成见的学者的责难,认为其不辨材料真伪,学风不严谨;另一方面,如果完全听信了这些“伪书”说,将这些所谓的“伪书”排除在研究评述之外,势必给先秦思想史的著述留下大量空白,同时使这些古籍的校勘注疏成果失去使用价值,变得毫无意义。于是,对笼罩在这些先秦古籍上的“伪书”说来一次系统的清理和甄别,作出一个更为合适的权衡取舍,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先秦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轴心文明”时代,其存世的典籍并不很多,是可以被研究穷尽的。但当我们以扎实的态度展开穷尽式的研究时,却发现,被后世怀疑或断定为“伪书”的,据笔者不一定完整的统计,竟多达18部。这就使得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到处充满了雷区,动辄得咎。但当我们深入进去时,就会发现这种担心基本上是多余的。一来,这18部“伪书”中,有8部被20世纪70年代后的出土文献证明是真实不伪的,戴在这8部古籍头上的“伪书”说是后人强加的、不合事实的,不能成立,应予正名。二来,另外10部古籍尽管尚未得到先秦出土文献的证明,但或因为旧有的“伪书”说存在漏洞而被新的研究成果证明“伪书”不伪,或因为这些“伪书”实际上属于先秦古籍的辑佚、修补、复原的整理成果,有作为先秦古籍使用的价值和理由,“伪书”的名称并不符合实际。“伪书”原本不伪,但“伪书”说何以产生、流行?究其实质,是因为唐宋以来的疑古思潮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缺失。由此产生的“伪书”说或被事实粉碎,或被新的研究成果击破,就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了。
一、从汉墓出土文献为8部先秦“伪书”正名
先秦古籍的疑伪之声,是从唐代柳宗元开始的。南宋继之,大面积疑古,到清代愈演愈烈。“五四”之后的“古史辨派”有过之而无不及,立论更为极端。在汉墓简帛文献出土之前,学界沿袭旧说,不敢逾雷池一步。这些先秦古籍的“伪书”说成为不容怀疑的“铁案”。然而,20世纪70至90年代的6次考古发现,将过去信誓旦旦的8部“伪书”的“铁案”彻底推翻。
1972年至2011年,中国境内共进行了6次相关的考古发掘,分别是: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出土了用汉代隶书书写的先秦文献竹简。共有完整简、残简4942简,另有数千残片。简文书体为早期隶书,写于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内容主要是先秦兵书,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韜》《尉缭子》《晏子》及《守法守令十三篇》等。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西汉墓出土了竹简文献。由于该墓曾被盗被焚,竹简已炭化,残碎严重,不少字迹难以辨认。从可辨认的文字中,发现了《文子》《太公》《论语》《儒家者言》等部分内容。
1973年冬至1974年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帛书、竹简和帛画。其中以帛书为多,有20多种,共12万余字。字体除个别篆书外,绝大部分是早期隶书,带有秦隶风格,是汉文帝年间通行的文字。内容有《老子》甲乙两种写本、《易经》及《战国策》等。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前期汝阴侯墓出土了简牍文献,史称“阜阳汉简”。经整理编纂,分为10多种古籍。因原有书名标题无一残存,今名或用传本原名,或据内容另拟。其中内容涉及《苍颉篇》《诗经》《周易》《吕氏春秋》《庄子》《孔子家语》等。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的一座战国楚墓出土了共804枚楚文字竹简,史称“郭店楚简”。其中字简730枚,共13000多个楚国文字。三种是道家学派著作,其余多为儒家著作。所记载文献大多为第一次发现。
2011年4月,江西省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出土5200余枚简牍,包括书籍简和公文书牍。书籍简主要包括儒经类(《诗经》《礼记》《论语》《孝经》《春秋》经传)、诸子类、诗赋类、六博类、数术类、方技类等文献。公文书牍为海昏侯及夫人分别上书皇帝与皇太后的奏牍和朝中关于刘贺本人的议奏或者诏书。杨军等:《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文物》2018年第2期。
在上述6次考古发现中,20世纪70至90年代的5次发现,改变了此前笼罩在《晏子春秋》《文子》《鹖冠子》《鬼谷子》《六韬》《尉缭子》《孙子兵法》《孔子家语》8部古籍身上的“伪书”命运,给它们洗去了不白之冤。
唐代的柳宗元是位敢作敢当的革新运动倡导者。政治上他是王叔文永贞新政的重要成员,文学上他是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被贬永州之后,他潜心治学,继承刘知己的“疑古”精神,将辨伪的触角指向先秦诸子,写下过《辨〈晏子春秋〉》《辩〈文子〉》《辨〈鹖冠子〉》《辨〈鬼谷子〉》《辨〈列子〉》《辨〈亢仓子〉》及《〈论语〉辨》,从而开启了古籍疑伪的先河。林艳红:《柳宗元与古籍辨伪研究》,《桂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然而他疑伪的诸子典籍中,有四部被后来的出土文献否定。这四部古籍是《晏子春秋》《文子》《鹖冠子》《鬼谷子》。在《辨〈晏子春秋〉》一文中,柳宗元依据《晏子春秋》中存在大量墨子思想,怀疑此书是“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宋代官修《崇文总目》亦断定,《晏子春秋》“非婴所撰”。后世学者多赞同这个观点,因而《晏子春秋》长期被研究界冷落。柳氏《辩〈文子〉》指出,《文子》或出自“人之增益”,或出自“众为聚敛”,总之,“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是一部“驳书”。此后,人们普遍据此怀疑《文子》是后人假托伪造的一部“伪书”。徐慧君、李定生校注:《文子要诠》,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页。柳宗元《辩〈鹖冠子〉》又断定:先秦道家殿军之作《鹖冠子》是“好事者伪为其书”所致。后世多认同此说,为其翻案的几乎没有。李学勤:《读〈鹖冠子研究〉》,《人文杂志》2002年第3期。在《辨〈鬼谷子〉》中,柳宗元对先秦纵横家著作《鬼谷子》给予“妄言乱世,难信”的指斥,主张“学者宜其不道”。后世据此多将其视为伪书,因而长久湮没不彰。
事实究竟如何呢?1972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一号汉墓中挖掘出4900多枚竹简,其中整理出来的《晏子》竹简共有102枚,内容分为十六章。参与挖掘研究的专家认为“很可能”是《晏子春秋》的“节选本”。骈宇骞:《晏子春秋校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序言”。1973年,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发现《文子》残简。其中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六章。还有一些不见于今本《文子》,研究者认为可能是《文子》佚文。徐慧君、李定生校注:《文子要诠》,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頁。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帛书,“有《黄帝书》,很多观点和语句与《鹖冠子》相同”。李学勤指出:这“确证后者是先秦古书,而且是黄老一派的重要古籍”。李学勤:《鹖冠子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序言”,第3页。黄怀信在《鹖冠子校注》前言中考证说明:“《鹖冠子》作者确系一名出生于楚、游学并定居于赵,喜以当地所产鹖鸟羽毛为冠饰并以之为号,曾做过庞煖老师的已佚名的隐士。”⑤黄怀信:《鹖冠子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3、10页。“今本《鹖冠子》的最终撰写年代,当在公元前236至前282年之间”,它“确是一部先秦文献”。⑤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有《战国纵横家书》,1993年郭店楚简中有《语丛四》。《战国纵横家书》的性质类似《战国策》,内容是侧重实践的游说辞;《语丛四》类似《鬼谷子》,内容侧重游说理论。这就引发了学界对《鬼谷子》是不是伪书的重新思考。人们根据郭店楚简《语丛四》,认为作为游说理论总结的《鬼谷子》诞生在战国时期是完全可能的。《鬼谷子》是战国中期鬼谷先生及其后学所作,确属先秦古籍。许宏富:《鬼谷子集校集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5页。
宋代是一个崇尚自家心性之学的时代,疑古、辨伪的思潮由此发端。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中华书局,2011年,第2页。到了南宋,疑古思潮全面铺开,《太公六韬》《孙子兵法》《尉缭子》和《孔子家语》均被疑为伪书。到了清代,过去的伪书说得到进一步加强。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汉墓出土文献面前,这些“伪书”说同样不攻自破。
《太公六韬》又称《六韬》《太公兵法》,是姜太公回答周文王、周武王关于政治与军事问题的对话记录。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有《太公》五十多枚,部分内容与今本《六韬》基本一致,简文提及“文王”和“太公望”,被认为就是《六韬》。1973年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竹简中,也发现许多有“文王、武王问,太公曰”字样,内容与今本《六韬》相同或近似。《文物》2001年第5期公布了这批简的释文。银雀山简《六韬》文字不避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之名讳,定州简《六韬》也不避汉文帝刘恒的名讳,证明《六韬》是一部成书在西汉之前、古已有之的兵家信书。它或许经过后人整理,但成书当在先秦。
《孙子兵法》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孙武。但关于孙武的生平事迹,先秦除《荀子》《韩非子》外很少有典籍涉及,《史记》关于孙武的记载未涉及籍贯、世系、结局等细节,因而自南宋起,产生了孙武是否实有其人、《孙子兵法》是否属伪作的怀疑。叶适断言《孙子兵法》的作者不是孙武,而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46,中华书局,1977年,第675页。当代学者钱穆断言:“《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孙武辨》,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46页。但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的出土,否定了传统的妄断,证明今本《孙子兵法》出自孙武的创造。陈曦译注:《孙子兵法》,中华书局,2011年。
关于《尉缭子》,《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都有著录,本来是没有疑义的。不过,自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疑其为伪书后,从宋元之际的马端临,到清代的姚际恒、姚鼐,再到现代的钱穆,作伪之论络绎不绝,愈加绝对。但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先秦兵书文献中,包括《尉缭子》竹简残卷,其内容与今本《尉缭子》基本相同,也使原来的妄断不攻自破。残简释文见《文物》1977年第2期、第3期。
《孔子家语》的最早著录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说有“二十七卷”,未注明编著者。三国时魏国王肃为《孔子家语》作注,成为“十卷本”,已非班固所见本。唐初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时,注明“《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非今所有《家语》”。颜师古所云“今所有《家语》”,即十卷的王肃注本。此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代王尧臣的《崇文总目》、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孔子家语》都是王肃作注的十卷本。但在南宋晚期的疑古风潮中,《孔子家语》由魏国王肃杂取秦汉诸书自作自注的“伪书”说应运而生。宋代的王肃注《孔子家语》刻本到明代已很难寻觅。明末藏书家毛晋在《孔子家语》跋中叙说自己历经千辛万苦寻找宋代刻印的王肃注本,但始终找不到全本,最终只找到两个残本才得以补全。清代虽然出现过陈士珂、沈钦韩、马国翰等人为王肃注本正名,认为《孔子家语》十卷本并非王肃伪造,但这种观点不占主流。影响更大的观点是伪书说,如孙志祖、范家相、姚际恒、崔述、皮锡瑞、王聘珍、丁晏等等所云。《四库总目》也采信此说,下了定论:“反复考证,其出于肃手无疑。”现代“古史辨派”代表顾颉刚认定《孔子家语》为王肃伪作,“无任何取信之价值”。于是,《孔子家语》属于伪书成为定论,并流传到韩、日等国。②③④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中华书局,2011年,“前言”,第3、4、4、5页。如果没有出土文献,这个定论是永远翻不了案的。不过,“上个世纪末期,出土文献中忽现与《家语》类似的原型文字,王肃伪造说不攻自破,从此柳暗花明,诸多考证文章问世,基本都不赞成伪书说”。②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孔子家语》相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名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同样和《孔子家语》有关。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今本《孔子家语》并非伪书,不是王肃杜撰,属于孔子“七十子后学”所为,③“此书为孔安国编辑一说也是可信的”,王肃注本引用的孔安国序,也是可信的,不是出于王肃伪造。④
综上可知,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出土文献,推翻了此前戴在先秦8部古籍头上的“伪书”帽子,这8部先秦古籍是《晏子春秋》《文子》《鹖冠子》《鬼谷子》《六韬》《尉缭子》《孙子兵法》《孔子家语》。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为之“正名”,对它们加以研究。
二、另10部被后世疑伪的先秦古籍名为“伪书”不当
原来铁板钉钉、不容置疑的先秦“伪书”被出土文献推翻,这个教训引起了笔者对于其他戴着“伪书”帽子的先秦古籍的注意和警惕。在先秦被疑伪的古籍中,另有《司馬法》《吴子》《周礼》《鬻子》《尸子》《列子》《公孙龙子》《古文尚书》《墨子》《关尹子》目前没有得到出土文献的证明。它们是不是“伪书”,该不该进入先秦思想史的研究视域呢?
根据现有材料,综合各种研究成果,笔者发现,这10部著作,或基本上属于先秦成书的原著,如《司马法》《吴子》《周礼》,或属于后人对先秦古籍的辑佚、补撰、整理之作,如《鬻子》《尸子》《列子》《公孙龙子》《古文尚书》《墨子》《关尹子》,名为“伪书”也不恰当。剔除后世辑佚、补撰、整理者无意窜入的时代痕迹,它们依然可以作为先秦思想史料进入研究领域,据以使用评述。
下面让我们逐一甄别。
《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是先秦时期的军事著作。从汉代到明代,一直未见怀疑。《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说:“《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汉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荀悦:《申鉴·时事篇》,黄省曾注,孙启治校:《申鉴注校补》,中华书局,2012年,第62页。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加以征引,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晋唐之间,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根据。宋元丰中,《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是将校必读之书。但是到了清代,在一片疑古的风潮中,《司马法》也未能幸免,被姚际恒、龚自珍等人疑为“伪书”。但他们的质疑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当代有学者对他们的质疑详加考察,发现根据明显不足。《〈司马法〉书考》,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今天学界的最近研究成果,认为《司马法》“成书于齐威王时代”,陈曦译注:《司马法》,《吴子·司马法》,中华书局,2018年,第204页。是战国中前期齐威王派人追论齐景公时期的司马穰苴阐释姜太公《司马兵法》的产物。换句话说,《司马穰苴兵法》既包括古代姜太公所创的《司马法》内容,又有司马穰苴对《司马法》的诠释和自己的著述。
《吴子》又称《吴起》《吴子兵法》《吴起兵法》。《汉书·艺文志》记录“《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均记录“《吴起兵法》一卷”。今本《吴子》二卷六篇,定型于北宋《武经七书》本。关于此书的作者及成书时间,本来未见争议,但明清出现了疑古之声,认为《吴子》是西汉或魏晋以后的人伪托或杂抄成书,陈曦译注:《吴子》,《吴子·司马法》,中华书局,2018年,第6页。另参李硕之、王式金:《吴子浅说》第一节,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姚际恒、姚鼐等人直指此书是伪书。徐勇译注:《尉缭子·吴子》,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51~156页。不过,他们的怀疑并未被今天的学者采信。“而今学者大都认为此书不伪,其作者就是吴起,成书于战国前期。书中虽有后人整理加工的痕迹,但基本反映了吴起所处战国前期的战争特点和吴起的军事思想贡献。”陈曦译注:《吴子》,《吴子·司马法》,中华书局,2018年,第6页。可以肯定:《吴子》的基本思想是吴起的,徐勇译注:《吴子》,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52页。可当作研究吴起的史料。
对《周礼》的疑伪也大可重新认识。本来,自《周礼》在汉代出现之日起,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一部周公“致太平”之书。如西汉末年的大学者刘歆认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十三经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36页。汉末给《周礼》作注的大注家郑玄认定:“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郑玄:《周礼·天官·叙官》“惟王建国”之下注,《十三经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39页。唐代的孔颖达、给《周礼》作疏的贾公彦,宋代的司马光、朱熹等大学问家都力主此说。但由于《周礼》在现存的先秦典籍中没有被提及,它描述的周代官制未能在先秦其他记录周代官制的文献中找到对应,因而被后世今文学派怀疑。围绕着《周礼》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古代学者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四库提要》指出:《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近代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等学者,都加入了这种争论。大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比较、甄别诸说,笔者认为:周公制礼作乐是不易的史实,离先秦较近的汉唐训诂大师均以周公为《周礼》作者,因此《周礼》出自周公之说最值得采信。但先秦所有文献都没有提到《周礼》,说明《周礼》的编订颁行不会早于战国后期,很可能成书于战国后期。与此相较,认为《周礼》成书于秦汉之际之说不可信,因为《周礼》在西汉景帝时就出现于世了,不太可能诞生于兵荒马乱、惊魂未定的秦汉之际。依据《周礼》在王莽时代被立为官学,就说它诞生于王莽时代,也太过仓促,不合情理,难以采信。若此说成立,刘歆、郑玄也就太容易欺骗,枉为一代训诂大师了。周代金文资料的研究表明,《周礼》具有珍贵的周代史料价值。综上研判,笔者倾向于认为《周礼》是一部由周公组织编撰、到战国后期编订成书的先秦古籍。祁志祥:《〈周礼〉:设官分职,得民为本》,《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当然这部书在流传中有所散失,今本《周礼》冬官《考工记》乃为西汉时补入,此篇另当别论。
关于今本《鬻子》的真伪,历来有争论。一般认为,《鬻子》在历史上实有其书,不仅是道家之祖,而且是子书之首。《汉书·艺文志·道家》首列《伊尹》《太公》《辛甲》三书,第四为《鬻子》。前三书早佚,《隋书·经籍志》诸子道家类列《鬻子》为第一。梁代刘勰《文心雕龙·诸子》说:“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于兹。”唐逢行珪《鬻子序》亦云:“实先达之奥言,为诸子之首唱。”南宋高似孙《子略》引唐贞观间柳伯存言:“子书起于鬻熊。”宋濂《诸子辨》云:“《鬻子》一卷,楚鬻熊撰。为周文王师,封为楚祖。著书二十二篇,盖子书之始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云:“今子书传于世而最先者,惟《鬻子》。”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云:“世传子书,始于《鬻子》。”俞越《诸子评议补录》云:“《鬻子》一书,为子书之祖。”今本《鬻子》虽出于后人搜罗,不是先秦原本,但将其视为“伪书”并不合适,实为原本《鬻子》残卷辑佚,“确为先秦时重要典籍”。马晨雪:《〈鬻子〉真伪考》,《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另参见刘建国:《〈鬻子〉伪书辨正》,《长白学刊》1992年第4期。
再看《尸子》一书的真伪。先秦典籍中未见“尸子”记录。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留下“楚有尸子”的记载。“尸子”名佼,战国中期人,曾为商鞅谋士,留下《尸子》一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世多有其(指尸子)书,故不论。”可见《尸子》曾在汉初广为流传。关于《尸子》的篇幅,刘向《别录》《汉书·艺文志》记为二十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记為二十卷。南朝裴骃《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尸佼“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原书自宋以后佚失。元、明、清陆续出现了不少辑佚本。④魏代富:《尸子疏证》,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4~5、9页。清代先后有惠栋《尸子辑本》刻本、任兆麟《校订尸子》刻本、孙星衍《尸子集本》刻本。后来汪继培根据三人辑佚本重加厘订,成《尸子校正》二卷。吕思勉《经子解题》称之为《尸子》“最善之本”。李守奎:《尸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朱海雷:《尸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魏代富:《尸子疏证》,凤凰出版社,2018年。《尸子》本为先秦尸佼思想的辑佚之书,但在清代疑古风潮中亦被戴上“伪书”的帽子。这种说法最早受到现代学者吕思勉的驳斥。他在《经子解题》中称:今本《尸子》,“其文极朴茂……今虽阙佚已甚,然单词碎义,足以取证经子者,实属指不胜屈……此外典制故实,足资考证者尚多。”《尸子》作为后人对先秦尸子思想史料的辑佚,实可“作为先秦古籍”④使用。
《公孙龙子》是先秦名家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原有十四篇。扬雄《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似为十四篇全本。后散佚,北宋遗失八篇,只留下六篇,保存在明代《道藏》中,即今本《公孙龙子》。关于该书的真伪,宋代以后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今本《公孙龙子》失去了先秦《公孙龙子》的本来面目,是晋朝人根据零碎材料编纂起来的。清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根据《公孙龙子》虽为《汉书·艺文志》所载,但《隋书·经籍志》没有记载的情况,将《公孙龙子》定为后人伪作。民国学者王琯在《公孙龙子悬解》一书中通过考证指出,伪书说似是而非。由周至梁,该书完好无缺;隋唐之际,该书佚存未定;唐武后时重建著录,仍为完本;宋绍兴前,亡八篇存六篇,为今本。王琯:《读公孙龙子叙录》,《公孙龙子悬解》,中华书局,1992年,第10页。1992年,王琯的《公孙龙子悬解》重新出版,学界仍然认同王说,将今本《公孙龙子》视为先秦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部名学著作。另据谭业谦《公孙龙事迹及学术思想之记载》,⑦谭业谦:《公孙龙子译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109~119、1页。关于先秦公孙龙的事迹及思想,先秦两汉间不少古籍均有记载。如《战国策·赵策》,《庄子》的《秋水》篇、《天下》篇,《吕氏春秋》中的《应言》篇、《审应》篇、《淫辞》篇,《列子·仲尼》,《史记》中的《平原君虞卿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刘向的《别录》,《淮南子》的《诠言训》《道应训》,扬雄的《法言》等等。谭业谦据此采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书出自先秦”论断,⑦不复讨论。序言作者朱祖延亦认为《公孙龙子》系“周秦之书”。朱祖延:《公孙龙子译注》,中华书局,1997年,“序一”,第1页。故今本《公孙龙子》不应视为伪书无疑。
列子和杨朱,分属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十豪”。二人的思想,主要见载于《列子》一书。关于《列子》一书的真伪,历来有争议。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是晋人所造的伪书。随着许多原来被断定为“伪书”的先秦古籍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汉墓文献中的出土,其他被戴着“伪书”帽子的先秦古籍也受到重新考量。《列子》未必全伪、可当作先秦古籍参考使用成为新的观点。
先秦不少古籍提及《列子》。该书在西汉时仍盛行。西汉末期刘向整理《列子》时,存者为8篇。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道家”类亦载有《列子》8卷,当为原本。西晋永嘉之乱后,《列子》残缺。经东晋张湛搜罗整理,得以补全。今本《列子》8卷,为张湛整理注释本,其原文在唐以前一直被视为信书。然而,自柳宗元《辨列子》起,历代疑伪之声渐起。历代辨伪文章、文摘见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近现代学者梁启超、吕思勉、钱钟书认为,今本《列子》是一部魏晋人假托的“伪书”。⑩叶蓓卿译注:《列子》,中华书局,2011年,“前言”,第1、3页。杨伯峻根据以往的辨伪之说,结合自己的语言学考辨,断定今本《列子》“肯定不是班固所著录的原书”,④⑤⑥⑧⑨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2、4、3、4、348、305页。而是魏晋人杜撰的“赝品”。④根据张湛注中有时不明文义的情况,杨伯峻断言:“此书伪作于张湛之前,张湛或许也是上当受骗者之一。”⑤《列子》中的《力命》《杨朱》两篇,“更是晋人思想和言行的反映”。⑥1979年,杨伯峻《列子集释》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影响很大,《列子》伪书说几乎成为定论。笔者过去受此说影响,在写《中国美学通史》的时候,就是将《列子》置于魏晋时期,当作魏晋人的美学思想资料加以研究评述的。见祁志祥:《中国美学通史》第1卷《列子》1节,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9~218页;《中国美学全史》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7~195页。
然而,细考今本《列子》,发现将它视为魏晋人杜撰的“伪书”并不恰当。连断定伪书的杨伯峻也承认,《列子》“作伪者不是毫无所本的”,“其中若干来源,我们已经从现存的先秦古籍中找到了”。⑧清人马叙伦《列子伪书考》指出:“盖《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假为(刘)向序以见重。”⑨他不否认该书聚敛了若干先秦古籍史料。虽然该书还结合、参照了一些记录先秦古籍史料的汉代文献,“附益”了一些魏晋“晚说”,也不应否定《列子》的先秦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列子》中的《周穆王篇》“可信于秦以前书”。张岱年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一书中指出:《列子》“抄录了先秦的一些材料”。《列子》最近的研究成果是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叶蓓卿的《列子》译注。在前言中,叶蓓卿指出:“今本《列子》保存了包括古本《列子》在内的若干先秦文献资料,此外也有一部分内容为后世附益而成,应当是由魏晋人在《列子》佚文的基础上多方杂取编订成书。”⑩今本《列子》属于后人关于古本《列子》的辑佚补撰。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就不能同意《列子》是“伪书”的成见。显然,辑佚补撰是不同于主观臆造的“伪书”的。其实,在叶蓓卿之前,当代研究者许抗生着眼于《列子》保留了大量先秦文献资料,就明确否定“伪书”说。他在1992年发表《列子考辨》一文,明确指出:“《列子》基本上是一部先秦道家典籍,基本保存了列子及其后学的思想。它大约作于战国中后期,并非一时一人所著,而是列子学派后学所为,并夹杂有道家杨朱学派后学的著作(《杨朱篇》)。具体地说,《黄帝篇》《汤问篇》很可能成书较早,先于《庄子·内篇》,而《天瑞篇》则作于《庄子》外、杂篇同时或稍晚。其它诸篇大抵亦作于战国中后期。但《列子》一书,在历史上曾遭前后两次散佚而后复得的命运,以此它不免流落于民间,为人们所伪纂、增删或文字上的润色,这是不足为奇的。”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这就完全推翻了《列子》“伪书”说。笔者结合对《列子》文本的仔细研读及与先秦古籍的比较互证,改变了原来对杨伯峻晋人作伪说的迷信,更倾向于同意许氏之说。祁志祥:《本同末异:列子“贵虚持后”说与“贵己恣意”说比较研究——重写先秦思想史系列》,《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一方面,我们应当肯定:今本《列子》基本上属于古本《列子》的辑佚,而非随意臆造的“伪书”。《吕氏春秋·审分览》称“列子贵虚”;《淮南子·缪称训》称“列子学壶子,观景柱(测度日影的天文仪器)而知持后矣”。列子“贵虚持后”的主张,在今本《列子》的大部分篇章中都可以看到有力的证据。《吕氏春秋·审分览》又说“阳生贵己”,刘向《列子新书目录》称“杨子之篇唯贵放逸”。杨朱的“贵己放逸”主张,也可以在《列子》的《杨朱》《力命》等篇中找到具体的证据。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不是被指责的魏晋“好事者”给我们保留了今本《列子》,战国时期两位影响力很大的人物——列子与杨朱的思想主张今人将无由得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当感谢魏晋“好事者”在先秦《列子》辑佚整理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而不是以偏概全、危言耸听地指责其“作伪”。
另一方面,今本《列子》乃失而复得、多次修复的产物,这个修复工作不是出自一人之手(笔者不同意叶蓓卿《列子》译注前言“成于一人之手”之说),而是出自不同时间、不同学者之手(笔者赞同许抗生《列子考辨》“并非一时一人所著”之说),这就给今本《列子》带来了一些文意割裂、自相矛盾、令人费解之处。今本《列子》八篇中,主张纵欲享乐的《杨朱》《力命》与主张清虚无欲的前后各篇主旨明显矛盾、对立。无论主张无智无虑、超越是非的列子,还是主张纵情任欲、及时行乐的杨朱,与主张仁爱忠信的孔子、墨子都无法统一到一起,但《列子》中确实窜入了这类文字。这是我们在使用《列子》评析列子、杨朱思想时应当注意的。叶蓓卿认为《列子》“首尾呼应”“自成一体”,基本“成于一人之手”,叶蓓卿译注:《列子》,中华书局,2011年,“前言”,第3页。其实很不符合实际。
再来看《古文尚书》“伪书”说是否万无一失,研究先秦思想史时是否应当排除。《尚书》成书于周代,有孔子的编订本。经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末战火,《尚书》散失。汉代偏尊儒术,《尚书》得以重见天日,并被定为五经之一。汉代出现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个《尚书》版本。《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由惠帝时伏生所传、汉隶所写。《古文尚书》四十五篇,由武帝末年孔安国从孔子故居墙壁中所得,用古文字书写,其中二十九篇与伏生本大体相同。西晋永嘉年间爆发战乱,汉代《尚书》的两种版本又一次散失。东晋初期,豫章内史梅赜献出一部《孔传古文尚书》,将伏生本二十九篇分为三十三篇,另增加二十五篇,合计五十八篇,称“晚书”,稍后立为官学。从东晋到隋唐,人们一直相信这是孔壁本《古文尚书》,《传》出自孔安国无疑。唐初孔颖达以此为根据主持《尚书正义》,作为官方定本颁行使用。南宋《十三经注疏》收入的就是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的这个《尚书》版本。此后流传至今的《尚书》就是这个梅赜所献的《孔传古文尚书》。不过,就在南宋时,有人开始怀疑《孔传古文尚书》的真伪。吴棫首先怀疑“晚书”二十五篇是伪作,朱熹也表示认同。明人梅鷟《尚书考异》认为不仅“晚书”,包括“孔传”都是伪作。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列举一百多条证据说明整个《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作。清人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列举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说明整个《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作”。后代学者虽然未必完全赞同这个论断,但一致认定《孔传古文尚书》中除与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相同的三十三篇可信外,其余二十五篇晚书都是“伪作”。③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7页。所谓“晚书”即晚出之《尚书》,也就是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本《尚书》中与汉代伏生所献今文本《尚书》不同的篇章。这二十五篇分别是《虞夏书》中的《大禹谟》《五子之歌》《胤正》,《商书》中的《仲虺》《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三篇),《周书》中的《泰誓》(上、中、下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和《冏命》。这些其实都是反映《尚书》思想极为重要的篇章。这些《古文尚书》中的“晚书”是不是出于晋人想当然的臆造呢?回答是否定的。惠栋的《古文尚书考》、程廷祚的《晚书订疑》,乃至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都揭示,《古文尚书》“晚书”中约有一百二十条材料为先秦经史诸子所引《尚书》之文。因此,当代有研究者指出:《古文尚书》“晚书”二十五篇“主要是《尚书》的辑佚”,它“补充、丰富了《尚书》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③比如被视为“伪书”的《大禹谟》《汤诰》《泰誓》诸篇,在《论语·尧曰》中曾被明明白白地征引。如《论语·尧曰》说舜曾以“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告诫禹,见于《大禹谟》;说汤曾自我反省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见于《汤诰》;记载周武王曾说:“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见于《泰誓中》。《孟子·梁惠王下》引述说:“《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这段话与现存《尚书·周書·泰誓》所载基本一致。原文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4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充分说明,被清人视为“伪书”的《孔传古文尚书》中的“晚书”,其实在《论语》《孟子》成书前就已存在,可作为认识、研究先秦人思想的证据。作为对先秦《尚书》的辑佚、补充和丰富,《孔传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应视为一个不可分割整体来认真对待。祁志祥:《〈尚书〉“民主”学说新探》,《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古文尚书》“晚书”作为对原本《尚书》的辑佚复原,给它强行戴上“伪书”的帽子是轻率的、鲁莽的、不合实际的!如果听信了“伪书”说,将二十五篇“晚书”都从《尚书》思想的研究评述中排除出去,将会留下多么大的缺憾!
关于《墨子》的真伪也存在争议。今本《墨子》五十三篇分为五组。第一组为前七篇,即《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一般认为系汉人或魏晋人“伪造”。其实,与其说“伪造”,不如说“辑佚补撰”更准确。作为对墨子主要思想的补充和诠释,这七篇是可以兼顾,而且应该兼顾的。抛弃使用,将给我们认识墨子思想的丰富性造成很大缺憾。比如《亲士》提出的主张就与《墨子》中《尚贤》论述的主张完全一致;《辞过》提出的主张与《墨子》中《兼爱》《非乐》《节用》论述的主张互补参证。
再看《关尹子》。该书是与老子同时期的道家代表人物关尹子思想的记述。早先实有其书。西汉后期刘向《列仙传·关令尹》、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都有记录。但汉以后亡佚,《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新唐书》中的《经籍志》均不著录此书。南宋孝宗时,徐藏从永嘉孙定家得到《关尹子》,前有刘向校定序,后有葛洪序,此书重见天日。《宋史·艺文志》复见著录。但自《关尹子》见书之日起,人们便对此书的真伪产生怀疑。一种观点认为,此书系宋人伪作,作伪者就是孙定。如明代宋濂《诸子辨》便持此说;另一种观点认为,《关尹子》是唐、五代间方士文人所为。如明代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及《四库全书总目》均持此说。要之,流传至今的《关尹子》被普遍疑为唐五代或宋人假托。笔者案今本《关尹子》中多有佛家用语、道教用语,亦认为今本《关尹子》已非原本,而是出自唐宋间后人的整理补充。但若冠之曰“伪书”,亦不能赞同。因为唐宋整理者并不是无中生有、凭空造构的,而是依据先秦两汉史料弥补而成的。今本《关尹子》与《庄子》《列子》《吕氏春秋》等古籍所记载的关尹子思想基本上是吻合的,作为研究关尹子的参考依据并无不可。林希逸指出:《关尹子》虽然“杂处尽杂”,但“好处尽好”。张之洞《书目问答》肯定:《关尹子》“伪而近古”。这些都说明,今本《关尹子》在认识、研究先秦关尹子思想时有可取之处,不可以“伪书”说一概否定。只要本着不绝对化的参考态度,注意甄别、扬弃唐宋补撰者的时代痕迹,依据今本《关尹子》来了解、评述历史上的那个关尹子的思想风貌,是有理由的,也是很必要的。
综上而论,先秦另外10部过去被疑伪的古籍虽然目前尚未得到出土文献的支持,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出土文献推翻8部信誓旦旦的“伪书”说的教训中吸取启示,对唐宋之后的其他先秦古籍“伪书”说加以重新审视和深入反思,珍视从汉代的司马迁、班固、郑玄到唐的孔颖达等大史家、注家的意见,兼顾当代注家最新的研究成果,摘去唐宋以来疑古思潮加在《司马法》《吴子》《周礼》及《鬻子》《尸子》《列子》《公孙龙子》《古文尚书》《墨子》《关尹子》头上不实的“伪书”之辞,把它们视为先秦原著或先秦古籍的辑佚补撰,在研究、评述先秦思想史时加以参考使用。
三、唐宋以来疑古思潮“作伪”说失误之反思
上述考辨发现,原来笼罩在先秦18部古籍头上的“伪书”说,或者被事实推翻,完全错误,或者存在漏洞,不尽准确。要之,先秦古籍的“伪书”说基本上都不能成立。这个发现让笔者深感震惊,也引发笔者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笔者想指出的是:中国古代一直崇尚诚信为本、主张修辞立诚,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说汉晋学者托古作伪实际上是缺乏社会依据的。周代以德礼治天下。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是对周代道德礼教学说的一次总结。儒家学说一再强调:“诚”是“天之道”“不诚无物”(《礼记·中庸》)。人必须加以遵守。“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诚”于是也成为“人之道”,文字著述上诞生了“修辞立诚”的基本原则。《周易·乾卦·文言》记载孔子的话:“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汉代确立了“独尊儒术”、以儒家仁学治理天下的大政方针。武帝时,董仲舒将与“诚”同义的“信”增加进来,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五常”之一。先秦及后代历史著述中不避杀身之祸“秉笔直书”的传统,就是“修辞立诚”原则的典型体现。在道德天尊、诚信为本、修辞立诚的思想信仰和文化氛围中,汉晋间文人伪造先秦经籍的社会依据也就很难想象。
其次,凡托古作伪,总得有心理动因,在既无名也无利的情况下,托古作伪也缺乏心理依据。先秦思想家一再揭示:趋利避害、好荣恶辱是人的天性,名与利是人类活动的两大心理动因。在商品经济元素发展得比较充分,书商可以假借名人来促销获利的明代,确实产生过见利忘义、托名立论的“作伪”现象。如现存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就出自叶昼受书商之邀的假托。叶朗:《叶昼评点〈水浒传〉考证》,《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86页。作者是叶昼,为什么托名“李卓吾”呢?因为“李卓吾”比“叶昼”更有名,假托“李卓吾先生”评点的《水浒传》更有助于销售牟利。然而在汉晋之间,商品经济尚未萌芽,图书市场未见记载,文字古奥、文义艰深的先秦古籍没有销售谋利的可能。所以,说汉晋文人托古伪造先秦古籍,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伪书”说在解释汉晋学者何以作伪时的一个理由是“托古以自重”。但将自己的劳动成果假托在古人、古籍名下,既无名可言,也无利可图,何以“自重”?
再次,按照常理,早先史学大家、训诂大家、文化大师普遍认可的原著说显然比后起的“伪书”说更值得采信。先秦古籍“伪书”说发端于中唐的柳宗元,南宋以后广泛铺开,愈是往后,距离先秦愈远。而它们怀疑、否认的先秦古籍,恰恰是距离先秦更近的汉晋学者置信不疑的原著。依据常识,距离古籍越近,占有的资料、信息就越多,对古籍的真伪判断就越有优势和发言权,他们的观点也就越有可信性。更重要的是,汉唐之间持先秦古籍为原著见解的学者,大多是这个时期的飽学之士、训诂大家、文化宗师。如司马迁、班固是考辨严谨、贯通古今的历史大家,刘向、刘歆是校阅群书的目录学家,郑玄、孔颖达是遍注群经的训诂大师。他们著录的先秦古籍,是史实性要求极高的《史记》列传、统计古籍目录的《别录》和《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这样的古代经籍目录。而唐宋明清“伪书”论者大多数的学问不能望汉晋文化大师之项背,疑伪之说不少出于比较随意的读书札记;即便是专书考辨,其考辨过程亦非万无一失。在距离先秦古籍更近的大师级学者的普遍结论与距离先秦古籍更远的一般学者的随性感言或考辨新论面前,我们究竟应当更信谁呢?何取何舍,岂非一目了然?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先秦古籍本来不伪,那么,为什么后世会给它们戴上“伪书”帽子呢?这就不得不反思唐宋之后出现的疑古思潮的失误了。古代典籍在抄写、印刻、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后世读书人发现这些差错后加以质疑、订正,乃是正常合理之事。但将先秦古籍疑为汉晋间人别有用心伪造的疑古思潮,则出现在唐宋以后。其积极意义,是订正了古籍流传中的差错,推进了文献校勘,打破了迷古传统,有助于思想解放。其负面后果,是出现了主观武断、以偏概全的判断失误,造成“伪书”说的结论与事实的严重错位。
唐代是疑古思潮的起始阶段,出现了三股疑古潮流:一是以刘知几为代表,对一些儒家经传提出质疑;二是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对儒家之道在质疑后进行理论重建;三是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倡导“舍传求经”的新经学运动。杨世文:《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正是在此氛围之下,柳宗元写下了质疑《文子》《鹖冠子》《鬼谷子》《列子》《亢仓子》真伪的一系列短札。
宋代是疑古思潮的铺开阶段。宋代经学继承唐代发端的疑古端绪而加以发展,重义理、好创获、重发挥、喜新说,高扬主体意识和怀疑精神,广及史、子、集各个研究领域。其疑古思潮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宋初到庆历以前为第一阶段,柳开、王禹偁、孙复、胡瑗、石介等人批判传统经学,尝试创立新儒学。庆历年间到北宋末为第二阶段,疑古思潮全面推开,涌现了欧阳修、李觏、司马光、王安石、张载、二程、三苏等大量的疑古学者。庆元前的南宋前期为第三阶段,疑古思潮走向深化,代表人物有郑樵、叶梦得、朱熹、陆九渊、叶适、吕祖谦等。嘉定年间至宋末为第四阶段,从实证走向空疏。部分学者走向考据之学,主张实事求是,形成实证派。另一部分学者以理衡经,以理疑经,最后以己意为理,肆无忌惮,演变为空疏派。
明代疑古思潮承接晚宋唯理空疏之风,其恣意而为的偏向得到进一步发展。清代疑古思潮继承晚宋实证派一路的学风,力图纠正明代疑古的空疏之弊,涌现了不少以古籍考据辨伪著称的学者和成果。与此同时,以辨伪为学问、以学问相矜夸的不实之风也在学界蔓延开来,抓住一点、否定全部的片面之见、惊人之谈屡屡出现。由疑文献之伪,发展到疑史实之伪。发展到康有为那里,则推出尧舜、三代历史均不可信的激进论断。佟大群:《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開大学,2010年;邱志诚:《〈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及近代疑古思潮研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辛亥革命后不久,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在这种风潮下“古史辨派”应运而生。他们继承晚宋空疏派、清代激进派的疑古路子,并走向极端。这些疑古论文收在1926至1940年出版的《古史辨》中。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宣称“全部古史皆伪”,邱志诚:《〈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及近代疑古思潮研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主张打破“治古史考信于六艺”的传统,对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古史辨派”过度夸大古代历史传说的不经不实之处,对上古经籍乃至历史全盘加以否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给人们认识先秦古籍真相和先秦历史造成了严重混乱。先秦古籍“伪书”说所以成为中国学界的主导观点甚至不易之论,与“古史辨派”密切相关。
要之,起始于唐代、铺开于宋代、承续于明代、激进于清代、极端于现代“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潮,催生了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辨伪动机和以偏概全、主观武断的疑古方法。大量先秦古籍的“伪书”说正是这种疑古思潮的产物。因而,带有这个疑古思潮荒谬不实、漏洞较多的弊病,也就不难理解了。
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汉墓出土的先秦文献推翻了部分先秦古籍“伪书”的定论,但传统的“伪书”说影响巨大,成见尚存,至今仍然束缚着研究者的手脚,掣肘着学界的进步。打破这种流传日久的成见,对这种“伪书”的定论来一次全盘的澄清、公开的正名和彻底的反思,从而让这些古籍堂而皇之地进入先秦思想史的研究视野,显然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学术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政法学院国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