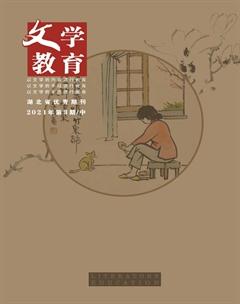“幼者本位”文学作品中的儿童角色分析
陈桂花
內容摘要: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儿童文学”并没有作为单独的类别进行介绍。儿童角色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常常被漠视,虽然影响了儿童本位思想的传播,但并不能在本质上否认儿童文学存在的价值。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个十年(1928—1937年)鲁迅、冰心、叶圣陶、萧红和张爱玲等人体现儿童本位思想的作品可见:儿童角色的呈现方式有自说和他说,呈现时态有现在、过去、将来三种,通过不同时代现实可窥见儿童的不同的命运。对这类包含“幼者本位”思想的作品,无论是一般阅读,还是阅读教学,都应该重视其中儿童角色的呈现特点及其时代意义。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 儿童文学 幼者本位 角色呈现
别林斯基如是说:“望大家莫把自己的注意力花在消除孩子们的缺点和恶习上,重要的是多费点心血,用富有生命力的爱来充实孩子们的心灵,因为有了爱,恶习就会消失。”[1]鲁迅先生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明确指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可见把对儿童的关怀带进教育领域加以重视既是发展儿童本身的需要,也是时代命运的迫切要求。儿童作为正在发展中的人,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儿童文学是人类生命世界发展进程中值得加以重视的文化现象。王黎君在《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明确指出:“只有当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和儿童的个体独立价值被肯定的时候,人的发现才是完整的。”[2]儿童文学从周作人对中外文学与教育等相关领域的学习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儿童本位论思想主张。本文拟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个十年中体现幼者本位思想的文学作品为例,主要探讨儿童角色的呈现方式、呈现时态及文学家对儿童角色的情感态度三个方面。
一.他说和自说:儿童角色的呈现方式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作品中,关于儿童角色的呈现方式有他说和自说两种。前者指的是在作品中儿童角色只出现在成人角色的话语中,自己没有发言权,即儿童角色间接呈现;后者指的是作品中儿童角色直接出现,作品呈现出儿童角色的言行思想。
(一)他说
曾有国外学者指出:“从儿童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会有人主张儿童并没有发言权,他们的文学是由别人创造出来给他们的,而不是由他们自己创作的。不过这并不正确,儿童其实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口头的和书面的,包括自己独立完成的,或是通过别人的协助,而且形式也很多元,韵文、笑话、歌谣、咒语、长篇故事、剧本、故事等等。”[3]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儿童经常作为接受教育与呼吁被重视的对象出现。
儿童文学先锋人物冰心,善与儿童搭建沟通桥梁,创设乌托邦世界,意在感化儿童心灵,培养真善美情感。这实质是大人与小孩在进行谈心,儿童作为纯粹的文学接受者存在。冰心在系列通讯作品《寄小读者》中,将儿童假设为儿童为忠实聆听者。读罢,冰心不同时期儿童文学创作有着明显时代特色转变,终归是成年人在开导孩子们善待生活。再如教育家兼作家叶圣陶先生,其教育思想倾向尤为突出,儿童文学惯于构建一系列具有教育意义的童话故事。郑振铎认为:读叶圣陶的早期童话,“显然可以看出他努力想把自己沉浸在孩提的梦境里,又想把这种美丽的梦境表现在纸面”,他要用自己的笔去描画“一个美丽的童话的人生,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
鲁迅先生《祝福》一文中祥林嫂的孩子阿毛的不幸是大人对弱者生命的疏忽而引发的悲剧;作者在《狂人日记》发出内心深处“救救孩子”的呼吁,希望能解救儿童的大人早日觉醒。萧红的《生死场》则反应大人对待儿童生存所持态深沉度思考,小说这样记载着:“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4]作者以一种成熟姿态提出“应对儿童生命进行关注”的观点,作家们在以独特的语言方式揭示引人深思的儿童问题。
(二)自说
吴晓东在《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领域》中这样定义“儿童视角”,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5]
萧红的《呼兰河传》还原儿童生长的农村生活。在这样的乡村“舞台”上,儿童角色主动表现情感世界,如:
场景一:
他跑得非常之快,他去追着他的姐姐。他的第二个哥哥,他的第三个哥哥,也都跑了上去,比他跑得更快。再说她的大姐,那个拿着大麻花的女孩,她跑得更快到不能想象了。已经找到一块墙的缺口的地方,跳了出去,后边的也跟着一灰烟的跳过去。等他们刚一追着跳过去,那大孩子又跳回来了。在院子里跑成了一阵旋风。
场景二:
但是天天这样想,天天就没有买成,卖豆腐的一来,就把这等人白白的引诱一场。于是那被诱惑的人,仍然逗不起决心,就多吃几口辣椒,辣得漫头是汗。他想假若一个人开了一家豆腐坊可不错,那就可以自由随便的吃豆腐了。
果然,他的儿子长到五岁的时候,问他:
“你长大了干什么?”
五岁的孩子说:
“开豆腐房。”[6]
上述作家们在发出有力的号召——儿童作为弱者形象需要“被保护”,这在当代育儿方式中仍普遍存在,大部分家长仍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策划进行。而张爱玲旨在表达儿童不仅需要被保护,还得有发言权。张爱玲的《小儿女》提到作为教师的继母在走进新家庭之前,需要两个孩子的“批准”方能实现。两个孩子看到邻居继母虐待孩子时,他们一起去捉弄她;当发现父亲要娶新妈妈、姐姐和对象亲密时,他们很有危机感,本能驱使他俩以离家出走(来到亲生母亲坟前)作为最直接的抵抗。他们深知父亲和姐姐不会舍弃自己,便以自己的方式反对大人“破坏”安全感。儿童天性终究善良,他们的情感需要更为真挚。新妈妈在最紧急时给予他们最温暖帮助时,心随母爱融化,最后欣然接受大人追求幸福的现实,同时自己重获母爱与安全感。《小儿女》突破了儿童话语权被限制的文学樊篱。张爱玲自小失去亲生父母的呵护,而继母的出现更使生活不得安宁。也许作者假想若能遇到这般温柔有爱的继母,尚且能扭转一生沉浮漂泊的命运。
二.过去、现在、将来:儿童角色的呈现时态
从时间角度分析,小说中儿童角色在作品中呈现的时态可分为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
(一)过去
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先生作品中儿童命运的呈式常以过去时出现,《祝福》中的阿毛一出场便是已被野兽叼食,祥林嫂形象展示封建时期人们精神悲哀。阿毛的悲惨在发生之后才唤起作为母亲的悲痛追忆,而阿毛的不幸只配是“听众”的一种消遣方式或借此抚平自己内心某处伤痕。再者,《故乡》中的“我”返乡时,儿时闰土不再,他已肩负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对鲁迅的称呼由“迅哥儿”到“老爷”,这称呼背后是等级观念在作怪,儿时“不懂事”的闰土已成为过去,再次相遇已成为时代中的“成熟人”。
《在酒楼上》里阿顺姑娘从天真单纯到茫然麻木、再到死亡,她顺从命运、听从家庭,独自默默地承受一切安排,既扮演姐姐角色又过早肩负起母亲“未完成的任务”。吕维甫带着从外省特意买来的剪绒花来找她时,她却已因病逝去,多么卑微的儿时心愿尚未实现。阿毛、闰土、阿顺既是时代产物,也为时代所抛弃,过去的遗憾成为永恒的教训。
(二)现在
冰心的作品语言如其性情亲切近人,她善于以正在进行时讲述过去与未来,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寄小读者》读来如长辈(姐姐或是母亲或是老师)在同儿童谈心,让人不由耐心听其把故事讲完。“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时为止,我恳切的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诸如此类很有亲和力的文字,在冰心的文章中时常出现。
另外,冰心在《小橘灯》中这种对话沟通的方式也很明显,里面这样写道:“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冰心假设读者一直在场,以一种正在进行时的语气与读者形成无声的交流互动。
(三)将来
对儿童过去与现在的关怀,旨在未来的改善,这一写作意图在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記》中呈现尤为显著。作者目睹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甚至中老年群体麻木之后,作为旁观者力求借助笔的威力发出呼吁——救救孩子。这几个简单的字用无比沉重而严肃得语调坚定地告诉我们:儿童就是民族的希望,社会应对这个群体充满期待。
鲁迅先生在《故乡》中,再次离开故乡时,“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这里宏儿和水生未来的担忧,也体现了“我”对未来期待、迷惘、焦虑的复杂心理。“我”不想让时代继续改变自己,也在担心于宏儿、水生重蹈覆辙自己的命运,但终究夹杂着好转的期待。鲁迅先生一向秉承着“怀疑希望,但绝不对未来失望”的人生态度。
儿童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不同时态,总体而言是对过去的思考、现时的揭示与未来的引向。某一个作家的某一文学作品中儿童角色的呈现时态可以多种,儿童角色的呈现时态随生命意识发展交替进行。
三.同情、担忧、热爱:作者对儿童的情感态度
第二个十年相关儿童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呈现着各自人文情怀,如同情、担忧、热爱的情感态度在文本有所体现。
(一)同情
三十年代对儿童文学颇有贡献的作家张天翼,他把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主动再次提到新高度,“解放后他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开山祖,我国为儿童文学至今还未超他的水平”。[7]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大林与小林》、《葫芦的秘密》、《秃秃大王》、《罗应文的故事》等,笔者在此文将对此进行补充:除这类带有神秘色彩、充满想象、夸张对比的讽刺儿童文学作品之外,我们还应把张天翼的另一类讽刺作品放进研究领域。张天翼《砥柱》中的父亲对女儿进行禁欲主义“教诲”,“贞妹子”这个名字是对其父亲行为一种反讽。父亲的举动等于将女儿的幸福推向无底洞,对性知识一片空白的未成年人被卖出去,悲剧已成定局。《砥柱》中的小女孩有如《边城》中翠翠的原始可爱纯朴,但贞妹子的命运更是时代的牺牲品。
《春风》里,张天翼塑造了典型的“为人师者”形象——丁老师和金老师,丁老师利用孩子“癞痢头”、“麻皮”、“流鼻涕”、“发亮的袖口”等“脏”形象在课堂上进行嘲讽,冷嘲热讽在不停扭曲这些孩子的生命价值观。更为可悲的是老师对学生的嘲讽更为一种赤裸裸的自讽。《春风》这一种富于狄更斯式的喜趣,是植根于一种讽虐的观照:如何一个事实上毫无希望的阶级,在略胜一筹的经济情况下,会回过头来憎恨一个更低的阶级。[8]“脏”孩子遭到取笑,“爱干净”的孩子却在一次次恶作剧中丢失善良本性,即同情心。《春风》里一段对话给笔者印象颇深:
这老头儿就感到肚子里有什么塞住了,呼吸也调不匀称。眼珠差点没跳出了眼眶子,冲着贞妹子直冒火。他打定主意要好好教训她一顿,骂她一顿,舌子可打着结:
“贞妹子!……哼……,该死,这……这……我告诉你——晓得吧,一个人……一个人……那个那个——唔……”
嘴巴动了几动,稀稀朗朗的几根胡子梗耸了几下,他就咳了一声,猛地爆出了一句——
“非礼勿听!……”
那个对他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
“莫光看着我!”他老人家打牙缝里压出了叫声。“一个人总要时时刻刻自——看做了什么非礼之举没有……一个人一一一个人——嗯,非礼之言——听了非礼之言——也就是自己非礼!晓得吧!'
贞妹子愕住了:
“怎么?我听了什么呢?”
讲的是一位父亲为着自身利益在将出卖自己女儿途中,以为女儿在船上听到一些色情内容而恐惧不安起来,小女孩的幼稚无知衬托出大人世界残忍无耻,贞妹子这种天性需要呵护才能健康成长。实际上这位父亲对于这些官能享受却颇感兴趣,这与他对女儿的反应形成鲜明的对比,让读者更觉得可鄙可笑。再者,《在酒楼上》中阿顺姑娘出现严重身体问题却没及时被父亲发现,可见儿童并没得到其监护人本该给予的关怀。时代命运导致人文关怀与爱的缺失,这两位父亲对女儿生命的漠然是儿童命运的时代缩影。
(二)担忧
张天翼从父女、师生等极有现实生活代表性的关系中对儿童角色进行关注:在时代背景下,失去正确指引,导致儿童心理畸形成长。连最弱小的群体都没能得到正常保护,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大过错。这两种学生联想到刘心武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班主任》。新时期典型人物谢惠敏作为“好学生”,她的思想不断僵化;宋宝琦作为“差生”在课上欣赏《牛虻》的审美价值,“好学生”和“差学生”的标准如儿童天性一样被不断扭曲。
前面提到的《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阿毛被叼食、阿顺因疾而逝、贞妹子被卖等人,无不体现现代作家对未来儿童的担忧。
(三)热爱
对儿童命运的关怀需以正确方式从书本走向生活实践,郑振铎曾在《儿童世界宣言》中说:“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教育,只要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他头脑里,就以为满足了……然而小学校里的教育,仍旧不能十分吸引儿童的兴趣,而且这种教育,仍旧是被动的……儿童自动阅读的读物,实在极少,我们出版这个《儿童世界》,宗旨就在于弥补这个缺憾。”[9]从儿童命運视角出发,《幸福》、《在酒楼上》、《故乡》皆为鲁迅先生返乡之作,这类文学作品体现作者对生命的思考与热爱。鲁迅先生不同文学风格体现于不同文本,从《幸福的家庭》细节描写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有着母性温柔的一面,严峻的外表下隐藏着温情。如:“阿阿,好好,莫哭莫哭,”他把那些发抖的声音放在脑后,抱她进房,摩着她的头,说,“我的好孩子。”于是放下她,拖开椅子,坐下去,使她站在两膝的中间,擎起手来道,“莫哭了呵,好孩子。爹爹做‘猫洗脸给你看。”他同时伸长颈子,伸出舌头,远远的对着手掌舔了两舔,就用这手掌向了自己的脸上画圆圈。[10]笔者赞同文学为人生而艺术的观点,它与教育坚持以人为本相契合,关注儿童文学教育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周中和编译.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M].河南少儿出版社,1983.
[2]王黎君.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彼得·亨特.理解儿童文学[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211.
[4]刘绍棠.萧红乡土小说选[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7.10(41).
[5]吴晓东等.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J]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丛刊,1999(01).
[6]萧红.呼兰河传[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20-22).
[7]刘再复.《高度评价为中国现代文学立过丰碑的作家》见《张天冀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57(27).
[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161).
[9]郑振铎.郑振铎全集——儿童文学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153.
[10]鲁迅.彷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36).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