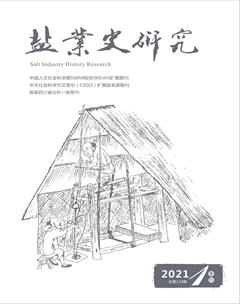盐政腐败与州县激变:嘉庆年间云南巡抚江兰“讳灾”事件考析
摘 要:经过康雍乾百余年的发展,19世纪上半叶的清王朝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其中制度层面导致的社会问题尤为突出。以云南为例,乾嘉之际的云南盐政败坏,各地因盐而起的“州县激变”层出叠见。其中,巡抚江兰对嘉庆初年发生于云南威远等地盐井的水灾“讳灾不报”,是造成激变最为直接的原因。讳灾不办实为一种变相的政治腐败,其危害不亚于贪腐,给国家和地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江兰讳灾在继任巡抚初彭龄的弹劾下事发,一度变味为大臣间的权力倾轧,最终嘉庆帝介入,经朝廷到地方层层调查,方水落石出。江兰讳灾事件在中国盐政史和政治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却长期隐没,本文通过爬梳档案等原始材料,希图还原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厘清督抚“讳灾”给国家与地方社会带来的危害,以及皇帝与督抚、中央与边疆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江兰;初彭龄;嘉庆帝;讳灾;盐政中图分类号:K249.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21)01-0014-13
至嘉庆初年,清朝经过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后,社会发展开始走下坡路,嘉庆帝亲政后实行“新政”①,力图挽救。整体而言,比之于康雍乾盛世,以及鸦片战争以后的研究,关于19世纪上半叶嘉庆朝的研究相对沉寂②。在既有的嘉庆朝政治史的相关研究中,集中关注于贪腐、“京控”等大案要案③,对于“讳灾”这类特殊的政治腐败案件目前鲜有专门关注者。
在乾末嘉初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中,尤以制度层面导致的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盐政即为大端。以云南盐政为例,通过“地方”与“全国性舞台”的互动,在更为清晰的层面上展现历史的细节和“地方社会的脉动”,并最终兼顾到整体的历史④。在清代“盐税所入与田赋国税相埒”⑤,盐课在清前期成为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源⑥。于云南而言,盐政是清王朝控制西南边疆的重要手段⑦,被举为“大政”①,盐课更是清代云南重要的财源和利薮②。康熙末年,云南确立官运官销的盐政体制,学界对此予以较大的关注③。该体制行至乾末嘉初已是百弊丛生,云南各地因盐而起的社会矛盾此起彼伏④,江兰因盐政而导致的讳灾案即发生在矛盾较为剧烈的嘉庆初年。江兰讳灾案被列举为嘉庆初年整肃吏治的督抚大案之一⑤,此案屡被嘉庆帝用作警示官僚系统的反面典型,这也提示着该案具有特殊的背景和意义。
目前,关于江兰讳灾案的具体内容和影响,及其与云南官运官销的盐政体制之关联,与嘉庆帝亲政后推行的“咸与维新”的新政间的关联,以及该案中暴露出清王朝和最高统治者的关切等问题,都是学界尚未厘清,也是本文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文所探討的江兰讳灾案,因盐政而及于吏治,对于理解乾嘉之际盐政腐败和“州县激变”的关系,督抚“讳灾”给国家与地方社会带来的危害,以及皇帝与督抚、中央与边疆之间的互动与关切,乃至清中期的国家政治变动与地方社会因应,都有重要意义。
一、云南巡抚江兰“讳灾”事发
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嘉庆帝一连接到新任云南巡抚初彭龄的三封弹劾奏疏,其弹劾的对象是刚刚离任的巡抚江兰。
在第一封弹章中,初彭龄指出江兰对嘉庆元年云南抱母、恩耕等盐井发生水灾而“讳灾不办”:
各该井均处山谷之中,两面高山夹峙,中有溪河,源流甚远。其井口或在河心,或紧临两岸之旁,均系用石垒砌,高低不等。灶户、盐仓、衙署、居民均在两岸。(嘉庆元年)六月二十一、二、三、四等日,大雨倾盆,昼夜不息,山水汇注,一时宣洩不及,遂致漫淹。虽存蓄不久,而水急石随,沙泥湍壅,井灶、民房、衙署、盐仓皆被冲塌,井口沙石填满。量验各处水痕,自一丈至二丈余尺不等。沙石堆集成阜,两岸原砌石磡,尽被冲刷倒塌,淹毙大小男妇三十三人,冲坍房屋一千四百三十一间,被灾人户共计三千四百七十九丁口,均已照例抚恤。惟各井皆有月额,今井口填塞,灶户停煎,礟岸坍塌,工程浩大,应请动项修理,并续据该厅州禀请领项前来。经巡抚江兰批饬,以抱母等井受灾不重,曾经亲勘,水已涸出,坍塌无多,其存仓盐斤并未冲去,所禀被灾情形均属捏饰,不准动项……乃江兰既不将该井水灾据实奏报,又未查有捏报情弊,一味偏执己见,只以被灾未重驳饬。迟至二年(1797年)九月内,又捏奏勘不成灾,希图粉饰,以致井盐停堕至五百二十余万之多,实属办理错谬。应请既将此案被水赈 ,及冲失停堕盐课银五万三千九百六十七两六钱九分,请旨饬部,着落江兰赔补。①
在第二封弹章中,初彭龄指明江兰任内所谓自行捐养廉银六万两办理嘉庆元年八月云南威远牛肩山“倮黑”② 军务一事亦存在不实③。初彭龄奏称:“此项银两,江兰并未自行捐办,派令属员垫交。而云南州县又无项可摊,因于盐规内先行垫出。”此即彼时云南各州县盐款亏缺的实际缘由④。在第三封弹章中初彭龄指出,威远抱母井被水以后无法正常煎盐,但由于江兰讳灾,地方官仍在境内压派盐斤,于是威远水灾后仅两个月,境内倮黑即在牛肩山啸聚起事⑤,而嘉庆二年七月发生的禄丰县刘如美案亦“系由盐务起衅”⑥。
第一封弹章中提到江兰所谓的“勘不成灾”属于清代灾害分数中较低的等级,其赈济也不属于正式的灾赈范畴⑦。初彭龄的弹劾所关匪轻,一旦属实,前巡抚江兰则属将州县潦灾“成灾报作不成灾”⑧,并于军务等事“应奏而不奏”⑨,数罪并发,须依律定重罪。因而初彭龄的三封弹章就如一记重磅炸弹,引爆了嘉庆初年的云南官场,也揭开了乾嘉之际云南盐政腐败局面的序幕。那么,江兰和初彭龄是何许人?为何初彭龄上任伊始即对其进行弹劾?
江兰(?-1807),字芳国,号畹香,安徽歙县人⑩,由贡生捐纳入仕○11,曾两度在云南任职,分别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任云南布政使○12 ,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四年(1795-1799)任云南巡抚,嘉庆四年五月从云南巡抚调任兵部侍郎①。初彭龄(1749-1825),字绍祖,号颐园,山东莱阳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御史出身,早年即以“弹劾不避权贵”,与弹劾和珅的御史钱沣并名②,时人冠以“鸣凤朝阳”之誉③,后“朝廷每有参案,暨各省吏弊,又多委彭龄澈查”④,嘉庆四年五月从兵部侍郎调任云南巡抚⑤。
嘉庆元年至二年,云南境内爆发了数起由盐政积弊而导致的州县暴动,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压盐致变”大案:嘉庆二年三月,大理、楚雄等迤西一带十余州县因官府强行压派盐斤而聚众暴动,当地民众畏官而杀吏戕差,一时间社会秩序失控,滇西大扰,云南地方在迅速平定叛乱以后,进一步善后⑥。时人谓此次变乱“诚边省从来未有之大变”⑦。初彭龄于此背景下抚滇,他此行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督促并妥善解决云南盐政积弊问题⑧。在初彭龄的调查之下,前任巡抚江兰因云南抱母等盐井“讳灾”不办、“匿情不奏”的陈案遂被牵出⑨,这即是新任巡抚初彭龄弹劾江兰的缘起。
翻检档案可知,前巡抚江兰确在嘉庆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所上的《奏为普洱边外野猓贼巢已破贼猓已擒并沿边一带地方宁谧及起程回省日期恭折奏报》中奏报威远抱母等井被灾一事:“威远一带,查勘并无被水村庄,收成极其丰稔。其抱母等井,俱系倚近低洼山河,雨大水涨,随长随消,年年常有之事,向系盐道督同管井大使捐廉调剂,不动正项。”⑩
根据江兰前此的奏报和初彭龄的三封弹章,因彼时江兰已贵为兵部左侍郎○11,且身领缉盗要任、在外钦差○12 ,因而嘉慶帝高度重视,即刻谕令军机大臣询问此事,并“着江兰明白回奏”○13。江兰接获圣谕以后,对初彭龄的弹劾一一回应。江兰先对初彭龄的第二封弹章进行反驳,说明其曾将山东布政使、护理山东巡抚、云南按察使和云南巡抚任内总共六万两养廉银,分三次捐入云南藩库,“均经奏咨有案”①。后经户部查明:“与江兰所称捐廉银数相符,是此项银六万两,江兰已将伊应得养廉扣抵,并非悬宕无著。”江兰“六万两养廉银”一事由户部直接出面否定,并指出:“初彭龄所奏并未交出之语,自非确实。”②
接着,江兰对初彭龄第三封弹章中威远倮黑一案和禄丰刘如美案“皆由盐务起衅”进行了反驳。他声明两起案件发生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嘉庆二年禄丰刘如美案时,自己当时正在贵州带兵平乱,系交由时任臬司孙藩和盐道敦柱前往查办,当时涉案的首从各犯并未有因盐起衅之供③;对于初彭龄所言嘉庆元年八月的威远倮黑起事亦因盐而起,江兰回奏“并无其事”④。
对初彭龄较为重要的第一封弹章中所弹劾的抱母等盐井“讳灾不办”一事,江兰随后进行登答。他指出恩耕井和抱母井遭灾以后,即派同知福桑阿前往恩耕井查办修复,而抱母井亦令盐法道颜检发银三千两赈恤,并据颜检等称:“此项(赈灾)银两,向来俱系盐道及管盐同知大使捐办,并不动支帑项,不准开销。”江兰的回奏使嘉庆帝一度认为:“若果如所言,则江兰于盐井被淹并非置之不办,特因盐井雨水涨发,系该省常有之事,径照向例,不准支销,系为慎重帑项起见。业经附折奏明,尚非有心讳饰。”⑤
初彭龄的弹劾实际想要表达的是,嘉庆元年的天灾已经给云南抱母和恩耕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然而由于巡抚江兰“讳灾不报”,人为给这一地区,乃至整个云南盐政造成了更大的伤害,使得这场“天灾”逐渐演变为“人祸”。但江兰在云南久任封疆,熟悉情形,对初彭龄的三封弹章“得以有词”⑥,一一予以反驳。
因抱、恩二盐井被淹的具体情形如何,还未详悉确查,且江兰与初彭龄各执一端,一时之间,此案陷入较为扑朔迷离的阶段。但根据初彭龄的弹劾和江兰的回奏,此案焦点在于:嘉庆元年抱母、恩耕二盐井被淹的实在情形如何?江兰是否存在讳灾不办?威远倮黑和禄丰刘如美两起案件是否因盐起衅?
二、“讳灾”升级:从“讳灾不报”
到“大臣倾轧”
因此案还牵涉其他一些关键人物,如已升任直隶布政使的原云南盐法道颜检(1757-1832)即“深知此事原委”,嘉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颜检,继续调查⑦。颜检覆奏道:
云南恩耕井为镇沅州所辖,抱母井为威远同知所辖,二井相距数十余里,均处河身之中,诸山环列,势极陡峻。嘉庆元年六月内,雨泽稍多,山水骤发,以致二井咸被水冲,贮仓盐块亦多浸失,沿河之民灶、房舍,并同知公署、盐场大使衙署,俱被冲坍,□人口未有损伤,时镇沅州孙俊德益署威远同知,勘明禀报,当经臣转禀督抚两臣,请于盐道库内酌动银三千两,委今元江州施廷良前往按户接恤,并查勘盐井情形,赶紧修复。缘山水旋长旋消,其退甚速,前任抚臣江兰于秋间往勘,遂谓被水不重,不致成灾,委员施廷良散放抚恤银两,转系捏冒,不准照数开销。此抚臣江兰从前未经细体被水情形之实情也。①
颜检认为江兰“办理过刻”②之处在于,二井被水以后,其“以云南向不办灾,遂谓被水不重,未经特行具奏,并将抚恤银两,不准开销”为由拒绝上报③。同时,颜检还否认了江兰所谓用于赈灾的银两“向系盐道督同管井同知大使等捐廉调剂,不动正项”的说法④,他明确指出“并无今地方官捐办之议”⑤。颜检的覆奏解决了两个问题,即抱母井和恩耕井被灾确实严重,且巡抚江兰虽然委施廷良领银抚恤,但确实未向朝廷报灾⑥。
针对颜检的覆奏,嘉庆帝认为:“云南虽系边远省分(份),而地方民瘼总属一体。抱母、恩耕二井既经被水冲淹,自应据实查明,妥为经理,何得以该省向不办灾为词,隐匿不办?即云该处并未损伤人口,但彼时灶户不能照常煎盐,因未经报灾,致有堕欠。在井官已不免追赔,而灶户等尤为苦累。”因此,嘉庆帝给出的处理意见是:“江兰讳饰之咎,实所难辞,着交部严加议处。”⑦
经过初彭龄的弹劾和颜检的覆奏,内阁形成初步的处置意见,建议将江兰“照例革职”,“以为封疆大吏玩视灾务者戒”⑧。嘉庆五年正月,江兰“以云南巡抚任内讳灾夺职”⑨。为审慎起见,嘉庆帝对内阁的处理意见作出批复:“本应照部议革任苐,念江兰在滇抚任内尚有盐务堕欠,及各井被灾实在情形,现交书麟查办,江兰着暂行改为革职留任。俟书麟覆奏到日,再降谕旨,钦此。”⑩
嘉庆帝随后将颜检的覆奏发给江兰,江兰又具折进行申辩。在回奏中,江兰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承认自己仅以附折陈明灾情,不请正项赈灾“实属糊涂”。随后,江兰指出颜检和继任盐法道敦柱“延挨”时限,“并未亲往”勘察灾情。并且江兰暗指颜检曾“徇纵井员、灶户偷卖盐卤,希图堕煎”○11。江兰还指出其曾令盐法道颜检发银三千两抚恤,但后经其本人督同道府等勘明实用银一千余两○12,暗指颜检等人以“水灾为名,希图扶同捏冒”款银①,将矛头引向颜检。
一定程度上,江兰对颜检和初彭龄的驳饬,起到了混淆视听的作用。江兰一再巧言驳饬,“并不据实陈明,含混登答”②;且就在初彭龄弹劾江兰前不久,已有云南籍给事中谷际岐(1740-1815)上《奏滇省行盐派夫诸弊疏》,痛陈云南盐政之害③,但事为已内召兵部左侍郎的江兰所阻,而新任巡抚初彭龄又恰为“际岐门下士”。④ 这些使本来已经基本清晰的讳灾案,逐渐转变成现任云南巡抚初彭龄和原盐法道颜检等官员对前巡抚江兰的构陷和倾轧。嘉庆帝开始怀疑初彭龄“连参江兰数次”的用心,并申斥初彭龄道:
汝自到任后,连参江兰数次,总未得要,是以未治伊罪,朕非庇伊。然不得实迹,如何严办?汝应公正居心,不可偏听属官架词诬构,吹毛求疵,必欲置伊于絕地。汝与伊有何不解之怨?若伊果有劣迹,据实严参,朕必立置江兰于法,断不姑息。汝试思和珅之事,朕能断绝否?但无罪之人,不能因一二言即行治罪,亦不能摇惑朕之耳目。汝审思具奏以闻,钦此。⑤
嘉庆帝搬出“和珅之事”的前车之鉴,一方面表明他整肃吏治和证据确凿后不会对江兰手软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使案情已较为清晰的前云南巡抚江兰“讳灾不办”案有些变味。现任巡抚初彭龄背后复杂的关系网络,使得嘉庆帝颇有顾及,已然弥漫着大臣之间权力倾轧的气息。初彭龄接获圣旨后,连忙回奏:“臣于上岁甫经到任,未能将江兰劣迹查询确实,率行奏请将伊革职治罪,实属冒昧。”⑥
此外,嘉庆帝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看法,还在于彼时云南威远一带正逢李文明、铜登和尚等率领的倮黑再度起事,且时任云贵总督富纲又身陷“总漕任内得受馈送银两”贪案之中⑦。多起案件交织在一起,使得嘉庆帝不得不多此一虑。他认为“江兰平日办事粗率任性在所不免,其待属员过严,伊又系捐纳出身,人望不能服众”,担心可能有人“于初彭龄前造作蜚语,以图倾轧”⑧。
三、官盐压派下的“州县激变”
由于江兰“具折剖辩,与颜检各执一词”⑨,且初彭龄“节次参奏江兰各款,俱未确实,如江兰未交养廉一节”,反被江兰驳饬,给嘉庆帝留下了“参奏不实”的印象①。因此,嘉庆帝要求新任云贵总督书麟(?-1801)“详查具奏”②,不得因初彭龄素有直名而“稍存偏护”,亦不得因江兰“具折剖辩即据以为实”,务须“秉公查办”③。
书麟督滇甫月余④,他与初彭龄都是嘉庆帝亲政后重塑官僚体制时任命的地方督抚重臣之一⑤,被嘉庆帝寄予重望,调查以后,其覆奏上达天听。书麟的覆奏在与初彭龄的弹劾基调基本一致的情况下,还牵出江兰其他一些参奏不实的地方:首先,江兰此前回奏中坚称“无一夫失所”⑥,书麟明确指出抱母和恩耕井被灾淹毙男妇共32丁口⑦;其次,书麟还专门驳斥了江兰关于禄丰“刘如美案并非由盐务起衅”的说辞:
嘉庆二年禄丰县刘如美等聚众滋事一案。臣吊查原卷内地方官原禀均已缺失讯,据承办经承禀称,系江兰吊取,未经发出。询之原办之盐道敦柱,据称当日敦柱与升任臬司孙藩先后带兵前往,拿获首犯刘如美等,据供因地方官派销盐斤,民间苦累,是以聚众滋事。敦柱等因戕害之人系属军犯,并非办盐书差,似非尽由盐斤而起,复加究诘,始据供明,实因历年各乡民欠交盐课,县官按卯提比,无可措交,多向军犯蔡禄等那(挪)借。每受重利盘剥、恃强逼讨之害,起意仇杀。因恐不能,号召众人,遂借盐斤派累之名,耸动乡愚。并声言此番夅动之后,盐斤可以永不领销,欠课亦可不纳。愚民被其搧惑,因而集众随行。江兰审奏时,以该犯等挟仇肇衅,究由军犯放债盘剥而起,故将盐务一层删抹等语,臣复加访问无异。查刘如美等聚众滋事,虽因军犯蔡禄等重利盘剥,而其借欠蔡禄等利银,系为地方官比追盐课所致。是此案起衅实因派销盐斤,地方官办理不善之故。情事显然,江兰焉能是诿为不知?若果无删抹情节之事,何须将卷抽匿?是初彭龄所奏,并无不实。⑧
书麟的覆奏点明了江兰与云南禄丰县暴动之间的关联,即江兰明知刘如美案来龙去脉,却在知情之后“豫将此案卷宗抽匿,以为消弭”⑨,在后来给朝廷的奏疏中,改换情节并“捏造案由”,“将抗官首犯作为聚众仇杀办理”,实则该案是由于盐务而导致的“州县激变”⑩。书麟不但明确表示支持初彭龄,且坐实了江兰故意规避灾情和在禄丰刘如美案后的奏疏中“增减紧关情节,朦胧准奏”两项大罪,按律须严惩①。此外,书麟在给嘉庆帝奏折的附件中,密陈江兰在云南巡抚任内的居官情形,言其“鄙倍猥琐”,不知自重,“为人訾议者不一而足”,滇人有“江疯子”之称,且克扣中军操赏银②。与此同时,江兰出身背景亦被深挖,其本“商家纨袴”③,劣迹斑斑,“人望不能服众”④。滇人对江兰“江疯子”之称,在初彭龄的弹劾中亦得到证实⑤。书麟的覆奏甚合嘉庆帝之意,他认为书麟的参奏“甚属公正”⑥,成为此案最终定案的关键,江兰被“即日革职,斥逐回籍”⑦。
那么,江兰讳灾背后所展现的云南盐政之弊到底如何?其与当时云南地方频发的“州县激变”之间有何关联?滇省盐法在官运官销制下,州县官赴省盐店领盐后分派里甲,按户销盐,并以销额为考成,谓之“门户盐”⑧。乾隆中期,银钱比价的变动导致的盐价日益增昂在全国是普遍现象⑨,与此同时,朝廷规定的官盐价格却基本上是恒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只能在销量上做文章,于是就有掺合灰土之弊⑩。云南某盐井提举金之昂在本井所出之盐中掺合灰土,诡称余盐,几倍正额○11。后来者竞相效尤,“将井出净盐四十斤掺和沙土六十斤为一石,按口比销。居民生子女即计户口,而病故数十年者不除其籍。又牛一口比人三口,其牛转卖则既科买者,而已卖之户亦不除民备课。市盐不可食,率缴价而弃盐于署前。价稍不足,则刑求之苛急,民不堪命。”○12 官盐质量粗劣,百姓率相食用私盐○13,以致官盐堕销,盐课无出,而盐课又事关官员考成。因而在盐患“甚于寇”的情况下○14,地方官员“始则计口授食,继则按户分摊;始则先课后盐,继则无盐有课。各属士民诉之大府,大府故商籍,左袒州县。而州县之昧良者,深以士民为仇,追比愈急,或立毙于庭,或羁死于狱。呈控督抚,仍批州县。”① 威远及迤西一带民众遂聚众起事,而致州县激变。事后,云南地方迅速平定变乱,然“抚臣止以斗杀拟辟,不肯将配盐、派夫激变之情上达。狱既成,官吏骫法如故”②。
江兰讳灾后,云南地方官员中鲜有敢言者,即便有曾参与调查抱母和恩耕二井灾情的护理迤南道、临安知府江濬源的调查报告③,但水灾导致的堕煎堕课实情却为巡抚江兰隐匿,这也不难理解书麟所言,云南各地的“州县激变”,实由“地方官办理不善之故”④。书麟所表达的云南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与嘉庆帝亲政之初训示军机大臣时的说法一致,即嘉庆帝认为白莲教等各地变乱“皆由地方官激成”⑤。
四、嘉庆帝的关切与讳灾事件的重新评价
至此,讳灾案尘埃落定,江兰最终因“玩视民瘼”被治罪⑥。讳灾事发后,江兰“节次巧辩”,已从一开始的有心“讳饰”,最后径直上升为“欺妄”朝廷⑦。但嘉庆帝对江兰的处置却显得乖张:嘉庆帝先是将江兰痛斥一番,后指明江兰“系属盐商,家赀丰厚”,回籍后“不准再行渎辩,及具呈捐项、自赎等事”,其子江平本在万年吉地效力,亦“着即掣回”,并书麟所奏抱母、恩耕二井堕销盐课及垫用赈恤银共五万三千九百六十余两,“皆系江兰讳灾所致”,令江兰赔缴,解往云南藩库归款,毋得延缓⑧。
不久,嘉庆帝又颁《严诫督抚讳灾》上谕一道,其中这样评价江兰:“近因军务未竣,节次所拨帑项甚多,封疆大吏遇有地方紧要之事,应行请帑者,或不免意存迁就,不敢直陈,以为晓事,即如前此云南盐井被淹,江兰讳灾不报,皆因惜费所致。”⑨显然这道上谕之中,嘉庆帝对于江兰讳灾事件已有了新的认识,即其认为“江兰讳灾不报,皆因惜费所致”,是为“晓事”。“惜费”,即为朝廷节省经费,这也说明嘉庆帝实际上关切的重点在于经费问题。并且,这则上谕也从侧面说明,讳灾不报在当时应非个案。
要之,上面两道上谕都表明嘉庆帝决定对江兰从轻发落。为何如此?首先,由于乾隆晚期以来和珅擅权被目之为政治壅弊败坏的渊薮,因此嘉庆帝亲政后诛除和珅集团,一度成为其推行旨在“振刷风俗”⑩、整肃吏治、加强皇权的“嘉庆新政”的重要内容①。此案即爆发于这样的背景之中,江兰讳灾所表现出来的欺蒙疲玩之弊,是嘉庆时期吏治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诚然如此,此案仍有其特殊性可循,虽然江兰存在讳灾和欺君之处,但终究是为朝廷节省帑项开支起见,比之于乾嘉时期一些情节恶劣的侵贪案件②,嘉庆帝也认为江兰“在任并无贪黩款迹,尚属可信”③,江兰自然情有可原,这也是该案长期被隐没的重要原因。从嘉庆帝对江兰的处置可以看出,嘉庆帝关心的是江兰贪腐与否,以及经费问题,这也是其屡屡对江兰法外开恩的根源。而这起事件的“肇事者”江兰仅被处以革职、赔款,后仍被温言劝诫,嘉慶帝处置力度不免失之于“软”④。不过应该明晰的是,江兰虽然不存在贪腐行为,但却给云南地方制造了比贪腐更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其次,与江兰的家族背景和个人品质密切相关。江兰出身的盐商之家⑤,系晚明至清代著名的淮盐“总商”之家,家族资本雄厚、规模庞大,家族成员中有不少人在朝廷为官,江兰的堂兄江春颇受乾隆帝宠遇,乾隆帝六下江南时,其皆有参与招待之举⑥。这样的巨富豪商家族,是朝廷在处理江兰时不可能不顾及的因素。此外,江兰始终以较为干练的“能吏”形象面世,比如其安豫省穷黎、剿松桃苗乱、捣威远倮黑、平畿南巨盗、董治山陵、公明取士等皆有功⑦。江兰的干练还表现在日后的再度起复,嘉庆八年十月,江兰名下应赔军需银两“全数完缴”,并解运至滇省藩库归款,嘉庆帝法外施恩,“着赏给(江兰)七品小京官,前赴南河,交吴璥听候差委”,继续为朝廷效力⑧。嘉庆帝对江兰先示以惩,后又弃瑕录用,这也符合其对官员一贯的处置原则⑨。江兰也未让嘉庆帝失望,在南河办理“催儹重运回空”期间,“跋涉河干,不辞劳瘁”。嘉庆十一年上谕:“江兰在南河效力,尚为奋勉,着准其回京,加恩以郎中升补。”⑩
余 论
19世纪上半叶的清王朝留给后人两种矛盾的历史记忆:一方面,面临着吏治败坏和白莲教起义等重重危机;另一方面,其又成为后世所怀念的咸丰以前的“黄金岁月”①。在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外患到来以前,王朝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引起了统治阶层的深切忧虑,他们首先以整肃吏治为突破口,对官僚体系和制度进行调整,以图挽救时弊②。江兰讳灾案成为这一时期颇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事件。
首先,将其置于全国的视野之中,此案肇始于云南巡抚江兰讳灾不报,牵涉从嘉庆帝到中央阁部、军机再到云南地方省道府厅县各级层面,且牵涉之人多系当时位高权重的部臣和督抚大员,牵连人数甚多、层面甚广。讳灾实质是一种变相的政治腐败,给国家和地方造成的伤害不亚于贪腐,因此江兰成为嘉庆初年因“贪欺害政”而被整肃的直省督抚之一③,而敢于弹劾揭参“虎而冠者”的前云南巡抚江兰的初彭龄,也為时人多所称道④。此案无疑是嘉庆初年一起较为典型的吏治大案,同时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比如当嘉庆二十三年六月云南抱母井再次发生特大水灾时,时任巡抚李尧栋飞章入告即是明证⑤。
其次,可将江兰讳灾案置诸中国和云南盐政史的大环境中去考察。盐政是中国封建时代由国家权力主导的大政之一,在清代各盐区实施的盐法虽有不同,但体制性的弊端是共同存在的,诸如盐课繁重、盐引壅滞、盐课堕欠和私盐泛滥等,因而不断有盐法的改革和损益⑥。云南盐政难治,这是清初人即有的认识,所谓“天下盐政之弊,未有甚于云南者也”⑦。康熙末期,云南确立官运官销的盐政体制⑧。乾隆中期以后,清缅战争的军需、经费定额化、煎盐成本的增加和官员舞弊贪腐等因素,致使云南盐课堕欠越来越严重⑨。从清缅战争结束后的乾隆三十五年至嘉庆五年(1770-1800)盐法改革以前,“滇省盐务积弊已有二三十年”,历任督抚“俱无善策”⑩。问题的症结在于“滇省官办盐斤实为地方重弊”○11,但积弊重重的官运官销体制仍在运转。各级官员迫于考成,想尽办法罗掘盐款,将堕欠的盐课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按户压盐,强行派卖,“各州县压领严催,过于急促,遂有聚众戕差之事”①。在云南因盐政局面败坏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已经比较激化的时候,身膺巡抚重任的江兰不惟不设法化解矛盾,反而讳灾不办、隐瞒事实,任其自流,酿成了以“压盐致变”为首的一系列严重的“州县激变”。实质上,此案背后更为深刻和复杂的关切在于,江兰讳灾所反映的云南盐政积弊,导致了境内的“州县激变”,这些民变是乾嘉之际云南“官运官销”盐政体制积弊的总爆发,而后朝廷和地方督抚致力于盐法改革,云南盐政进入“民运民销”的历史时期。
总而言之,江兰讳灾案特别能呈现清代中期制度弊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以及地方民众作为国家制度最直接、最敏感的受众,对其弊端所做出的回应。对以盐政为大政、以盐税为主要财源的云南来说,盐政是彼时地方行政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仰赖盐税为兵食、官员薪廉等,以维持基本的行政运转。因江兰讳灾而致盐课堕欠,使后续政治环节都受到影响。当堕欠的盐课被转嫁到地方民众身上时,他们即以最为激烈的方式进行回应。地方官员因应于“嘉庆新政”的大背景,开始在云南实行盐法改革,以求消除旧政弊端,缓和社会矛盾,挽救地方危机。
(责任编辑:王放兰)
The Corruption in Salt Administration and Riots in Counties: An Analysis on the Incident of Jiang Lan Hiding Disasters, the Governor of Yunnan Province during Jiaqing Period
CHEN Yiren
Abstract: After the one hundred years development of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periods, a quantity of social issues emerged in the first half of 19th century, especially the issues caused by politics. At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the salt affairs of Yunnan became corrupt, and the riots caused by salt corruption erupted frequentl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Emperor Jiaqings reign, flood attacked the salt mines of Weiyuan and nearby, but Jiang Lan, the governor of Yunnan Province, did not report the flood to higher authorities, caused riots directly. Concealing the disaster situation was actually a kind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its harm was no less than corruption, which usuallyhad brought great harm to the country and local society.Then, Jiang Lans successor, Chu Pengling, impeached Jiang Lan for he hid the disasters, triggered a series of political crises between officials. Finally, under the intervening of Emperor Jiaqing, the incident was investigated in detail by centr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Although the incident of Jianglan hiding disasters is momentous in the history of salt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s of China, it was overlooked for a long tim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store the origin and expansion of the event by archives and other raw materials. Through restoring the incident and understanding the harm of governor hiding disasters, the researcher tries to outlin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mperor and local official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borderlands.
Key words: Jiang Lan; Chu Pengling; EmperorJiaqing; conceal the disaster situation; salt administration
作者简介:陈懿人(1991-),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清代云南盐政与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YWHX19-01)的阶段性成果。
①苏珊·M·琼斯,菲利普·A·库恩.嘉庆的改革[M]//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23-125;张玉芬.论嘉庆初年的“咸与维新”[J].清史研究,1992(4);关文发.嘉庆帝[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59-114;米丹尼(Daniel McMahon).Dynastic Decline,Heshen,and the Ideology of the Xianyu Reforms[J].台湾清华学报,2008(2).
②关文发.嘉庆帝:前言[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1;罗威廉.乾嘉变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J].师江然,译.清史研究,2012(3).
③唐瑞裕.清代吏治探微[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1-134;关文发.试评嘉庆帝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王开玺.从李毓昌案看嘉庆朝的吏治[J].历史档案,2004(2);崔岷.山东京控“繁兴”与嘉庆帝的应对策略[J].史学月刊,2008(1);崔岷.洗冤与治吏:嘉庆皇帝与山东京控[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④王汎森.“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J].近代史研究,2015(6).
⑤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三:食货四:盐法[M].北京:中华书局,1977:3606.
⑥郭正忠.中國盐业史:古代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804.
⑦陈懿人.清代边疆整合中的盐与云南威远[J].清史论丛,2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