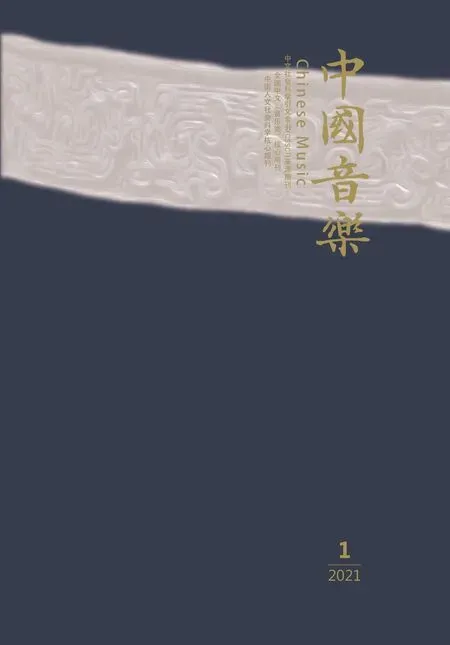二胡演奏中美的生成
——为首届“闵惠芬艺术周”而作
很荣幸有机会参加在周口师范学院召开的首届“闵惠芬艺术周”①首届“闵惠芬艺术周”由中国音乐家协会、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周口市人民政府、周口师范学院联合主办,2019年11月8日-11日在周口师范学院举行。本文是会后根据当时发言的提纲撰写而成。。我虽然在年轻时也业余拉过二胡,并始终保持着对这一艺术的热爱,但从专业上说,我纯属外行。闵惠芬女士,我们倒是有过一两次交往,那是在1995年的第六届全国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广州番禺)上。这次会议除了学术研讨外,还邀请了四位艺术家进行示范演出,其中就有闵惠芬。会间,我趁空找到闵惠芬女士,向她表达我所任教的中国科技大学想请她前往讲学的愿望,不料她很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年四月,终于成行,在科大容纳三千多人的大礼堂举办讲座音乐会,连续三天,每天一场,场场爆满,走道和门口都站满了人,场内气氛安静而又热烈,真可谓盛况空前。闵惠芬的二胡演奏艺术,我早已不陌生,在番禺会议上更是有了现场的震撼体验,直到目睹科大的三场演出,我才真正感受到她的演奏所形成的“场”是多么强大!在这强大的“场”中,既有她艺术上的魅力,也有她人格的魅力,其内涵十分丰富。所以,张丽博士当初选择以闵惠芬为研究对象时,我是坚决支持;当她代表主办者邀请我参加“首届闵惠芬艺术周”时,我也爽快地答应了。
参加会议就要发言,而我又不是二胡业中之人,讲什么好?考虑再三,逐渐形成下面的想法:二胡艺术从刘天华开始,经过闵惠芬,到了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相当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二胡演奏家和作曲家。也就是说,二胡艺术的实践包括演奏与创作,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当代人音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对它的理论研究,则明显滞后。既然如此,我是否可以从这方面着手,来谈谈二胡演奏的美学问题,看能否说出些有意义的东西。理论和实践本来就是相辅相成,有时候实践走在前面一点,为理论提供材料,有时候理论略略超前一点,为实践提供引领。整个艺术,就是在这前前后后的交替中不断前进。有了这个认识,我就做了一些准备,带来这样一个题目:“二胡演奏中美的生成”。
一、声音张力
讨论“二胡演奏中美的生成”,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在二胡演奏中生成的“美”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它是以声音的方式存在的,它就在二胡演奏所产生的声音之中。音乐是声音的艺术,那么,它的美也一定存在于声音之中,那些所谓非音乐性的内涵,也一定是以声音为媒介才得以传达的。例如演奏者的文化修养、精神气质、个性品格等非声音性元素,也都得通过声音才能得以传达和表现。凡是不能或没有转化为声音的,对于音乐和演奏来说,都没有意义。即如古琴中的“求之弦中如不足,得之弦外则有余”(徐上瀛)的声外之意,说是在“弦外”,其实也是通过弦上之音实现的,是以声音的方式指引或暗示给我们的。当然,演奏中美的生成,仅仅讲到声音是远远不够的。美的生成离不开声音,但并非演奏出来的声音都是美的。美的声音和不美的声音一定有本质的区别,找到这个区别,就意味着找到美的声音的基本属性,有了它,演奏出的声音便可以为美;没有它,则必然不会有美。
那么,决定声音成为“美的声音”的是什么?我们日常听音乐或在音乐会上听人演奏,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优秀的演奏家,只要他奏出第一句,就能够紧紧地抓住你,吸引你往下听,但也有人把乐曲从头到尾演奏完了,却还没有打动你,吸引你。在这里,那能够紧紧抓住你、吸引你的是什么?是音乐表现的题材?是题材中内含的思想情感内容?但同一首乐曲换一个人演奏,效果却完全不同,为什么?或者是演奏时情感的强度?技巧的高超?但有人演奏时情感是相当投入,技巧上的功夫也很棒,其演奏仍然无法吸引人,又是为什么?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某一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上述各种要素综合的产物。但是这样说等于没说,因为它仍然处于混沌状态。我们需要的就是在这综合之中找到关键因素,并给它一个概念,使我们在认知上有一个下手之处。这个关键因素是什么?我的体会,就是“声音张力”。
但是,为什么是“声音张力”,而不是其他,比如说音色。的确,好的音色,如纯净、柔和、漂亮的音色,确实能够使听者感到悦耳、舒畅,能够给人带来愉悦,但仅有音色的美还难以打动人、吸引人,难以有震憾人心的力量。这是因为,音乐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主要不是由静态的音色承担的,而是由动态的声音张力实现的。根据心理学的研究,艺术美的力量不是来自直观的形式本身,而是由形式所生成的张力样式。声音运动中的张力样式与人的情感、情绪、思维、意志、性格等精神活动形成的张力样式相同构,人的听觉心理便会产生感应,发生共鸣。不同的张力样式引发不同的心理共鸣,张力的不同变化也会引发不同的心理变化,这就是音乐审美的机制所在。正是从人的审美心理机制出发,我们才能够确定,声音张力是音乐美的最为直接、最为基本的表现形式。
那么,何谓“声音张力”?直白地说,就是有“张力”的声音。“张力”一词,最早出现在物理学上,《辞海》对它的解释是:“物体受到拉力作用时,存在于其内部而垂直于两相邻部分接触面上的相互牵引力。”②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083页。它的意思是,物体受到外力作用时会产生张力,这个外力作用,《辞海》界定为“拉力”。实际上,不仅只有“拉力”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外力作用方式,最典型的就是弹簧。当没有任何外力作用时,弹簧处于松弛状态,没有张力;当我们用力压迫弹簧,即施加“压力”时,它就有了反向的张力。由于外部施力,改变了物体原有的松弛状态,使其在内部产生某种“势”和“力”,进入“紧张”状态。所以,张力,就是在外力作用下物体所形成的紧张度。在物体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其紧张度与所施之力的大小成正比。后来,“张力”理论又延伸到心理学,主要是指事物的形体或运动的形式在其构成过程中引起人对某种力的感知,这种力的感知也是以某种紧张度为内容的。这里的关键在于,要有两个相反方向的力(如“压力”和“挺力”、“拉力”和“拽力”)的互相作用——对峙、抗衡、博弈。单方向的力是构不成张力的,例如匀速直线运动是没有张力的,只有出现另一种力对它进行干扰,从而改变或扼制直线的运动方式(方向、速度、强弱),张力(亦即紧张度)才会产生。“声音张力”,顾名思义,就是在发声过程中通过施力(压力和拉力)而使声音产生一定的紧张度。就音乐演奏或演唱中的“施力”而言,其实有两个层面的东西。一是在演奏(唱)发声时发声体要形成一定的紧张度,这个紧张度来自演奏(唱)时基本的施力方法。但这只是发声,无此则无声。二是演奏(唱)时的这种“施力”必须是有控制的。所谓“有控制”,就是施力过程中实际上包含着相反方向的两种力在起作用。正是因为有两种相反方向的力相互作用,所以,声音在进行和持续过程中通过对立形成一定的紧张度,使其形态有一种聚合从而坚挺的效果。只有这种聚合、坚挺的声音才会引发人的听觉心理的紧张感,形成音乐音响中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基础。
那么,二胡演奏是如何使声音获得张力的?简单地说,就是善于控制。二胡演奏主要有两大类型的技法——右手运弓之法和左手按弦之法。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这两大类技法都只有一个方向的力,左手是手指往下按弦之力,右手是运弓推拉之力。实则不然。经过良好训练的人演奏二胡,总是在按弦之力或运弓之力的同时还有一种相反的力在起作用,我们称之为“控制力”。也就是说,你在往下按弦的同时就有一种向相反方向控制的力在起作用,你在推弓拉弓时也同时有一种相反的力在起作用。如果没有上述反作用力,也就是说,没有合适的控制力相佐,所奏出的声音就或者是松散无力,或者是粗糙刺耳,没有丝毫美感可言。初学二胡者的演奏其声音之所以比较难听,就在于他们还没有学会使用控制力,不会以相反方向的力来使声音聚合而坚挺。越是成熟的演奏家,就越是能够自如地使用自己的控制力。因此,按弦和运弓时要有控制力,这是每一个想成为二胡演奏家的人必须完成的功课。不同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两种相反方向力的相互作用而已。
那么,“声音张力”,或者说,“有张力的声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它有哪些特点?首先,它是一种连贯的、具有有机性和整体性的音形态和音结构。二胡演奏出来的音响形态,应该是一个完整的音乐进行,呈现出的是一条完整的、有机的、有一股气脉贯穿其中的音线,没有突兀,没有例外,所有的音符都完满地融入这个音线的律动当中。所以,张力首先是一个音乐进行中的整体概念。其次,因为有一气贯注,所以这条音线是坚挺的、有“筋”有“骨”的,充满弹性的,有着内在压强的。这种“坚挺”,并非通常所说的强弱。声音的张力不仅体现在较强较快的音上,同时也体现在较弱较缓的音上。而且,越是较弱较缓的音,就越是离不开张力。失去张力,较弱较缓的音就会变得拖沓、疲软,无生气,无活力,无精神,无光彩。
我们说许多演奏者没有意识到声音张力问题,并不是说他们在实践中完全忽略这个问题,更不是说他们没有奏出“有张力的声音”。实际上,他们之中很多人的演奏实践已经体现了这个原理,有经验的老师也已经在自己的教学中不知不觉地遵循这个规律来指导学生。十年前,为了庆祝著名二胡演奏家、教育家马友德教授八十寿辰及从艺六十周年,我有幸受邀躬逢其盛。马友德教授以培养出众多一流二胡演奏家而享誉天下,被称为“二胡界的马家军”。这一定不是偶然的,其中奥妙值得好好研究。遗憾的是,我不是二胡界人,未能成为马老师的弟子,甚至也没有机会临场观摩其教学过程,于是只能从他的论文和教材等众多著述中寻其蛛丝马迹。在经过反复研读之后,有一条轨迹慢慢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马老师在教学中所采取的一招一式,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我当时把它称之为“音乐内在张力”,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声音张力”。马老师在自己的文章中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但他的演奏理论正是指向它的。例如他特别强调演奏时左手指按弦时要“划圆”,右手运弓时要特别注意“音头”的处理,强调运弓时要有一定的“阻力感”,等等。“划圆”是要使出音柔和光滑,强调的是在弯曲中形成张力;“音头”处理是要避免音的不连贯,强调的是张力所需的连贯性、整体性;“阻力感”则直接就是有意识地寻找反向的力进行控制,是张力生成的重要法则。综合起来,它们都是为了使奏出的声音有张力。再如他所提出的“三点论”模式和“中间位置”说,其实也是异曲同工。所谓“三点论”,是指在持弓法、食指平拖弓杆法、扶持弓杆法、运弓轨迹以及左手持琴的手型位置和揉弦法等各种技法,他都将其一分为三,如上中下、左中右、前中后等。“中间位置说”就是在上述三分中,以取“中”为原则。为什么?就是因为中间位置最便于技法的变化,从而有利于音的控制,而变化与控制正是张力形成的重要机制。
在营构声音张力方面成效特别突出的,无疑要数闵惠芬。她的演奏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只要一接触她的琴声,你就会被它紧紧地抓住,吸引你一直听到最后。这就是声音张力在起作用。闵惠芬的演奏风格本来就奔放豪迈,激情洋溢,这为声音张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她又特别善于在演奏中导入反向的力,注意根据乐曲的内容作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控制,所以她奏出的声音才有张力,听众才会从中感觉到强大而持久的吸引力。
二、声腔化
声音张力能够吸引人,抓住人,但真正要“打动人”,还需要介入情感方式。“声腔化”就是其中的一种。
“声腔”原为传统唱论中的概念,它是艺术家利用汉语中字的声调和音的头、腹、尾的处理方式来加强音乐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较早表述这个思想的,是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他率先用“腔”来表示具有特定演唱方法、艺术风格和美学品格的唱曲形态,并把它与“声”区别开来,指出:“声”仅仅是指歌唱中所发出的声音,包括演唱中对字音的处理;“腔”则是对此种演唱中具有特殊方法和美感韵味的曲调的指称。这两者的不同是:“声要圆熟,腔要彻满”,而使声“圆熟”、腔“彻满”的方法和过程,后来叫作“润腔”。“润腔”的作用有三:第一是美化音色,即通过润腔使发出的声音更优美悦耳。第二是使表情更真切、生动。由于汉藏语系的语音有声调变化,润腔使演唱中所发之音有升降起伏,能够更加贴合唱词中的情感表达。第三便是上面所讲的,营构声音张力,就是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法运用能够使所发之音始终饱满有力,即所谓“腔要彻满”。
声乐中讲究声腔,是因为唱腔中有歌词,歌词由字构成,而字是有声调变化的。四声的变化处理不好,要么听不清字义,唱腔语义模糊;要么字义清楚了,但音乐疙疙瘩瘩,不成腔调。所以声乐演唱才特别重视腔词关系,强调声腔问题的重要。
但是,二胡音乐中没有文字,不涉及声调变化,为什么也要声腔化,也要运用润腔技法?首先,音乐的本质是表达人的生命体验,其中最主要的是情感。而情感的表达方式,通常是伴有语音的语言。因此,无论在哪个民族,音乐都同自己的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语言中,又以语音与音乐的联系更为直接。就拿中西音乐与语言的关系来说吧,我们知道,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欧语系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轻重而无声调。这样,他们在表达思想情感的时候,其语音也就会以轻重变化的方式进行,而不会出现声调变化。音乐是模仿语言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西方音乐有轻重而无声调的特点。无声调,所以他们的音乐,每一个音都是一个光滑的、圆溜溜的点,在音乐进行中尽可能地保持点的形状,不作任何变化。中国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它无轻重变化而有声调变化,即每个字不仅有声母和韵母,同时还有平、上、去、入等声调变化。这个声调,一方面,它是表义的,由相同声母和韵母组合的字音,不同的声调标示着的是不同的字,因而具有不同的涵义。这样,当我们要表达一个思想或情感时,就会时时、字字都要涉及声调的变化,否则,我们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准确地表达。另一方面,声调变化还是强化语气、渲染情感的重要手段。同样一个字音,其声调变化的幅度(如长短、轻重)不会改变这个字的“字义”,但却能够改变表达中的“句意”,改变其情感色彩。比如将“平”声拖得长一点或短一点,“上”声弯曲的幅度大一点或小一点,或者“去”声更重一点或轻一点,都可以在句意和感情色彩上有所变化。所以,字音声调的不同形态和不同幅度,是有着直接的表情表意功能的。语言要表情表意,音乐也是要表情表意,那么音乐的表情表意就不可能忽略其语言特点,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语音和语音中的声调变化。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音乐的最小单元——音,就不都是像西方音乐那样一个个圆溜溜的点,而是还存在着大量形状各异的线:平直的、弯曲的、转折的、回环的,等等。这个现象,有学者做过深入的研究,并将其称为“音腔”③参见沈洽:《音腔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期连载。。也是因为这个道理,中国民族乐器演奏法中,都会使用某种技法使音发生变化,弹弦乐器有吟、猱、绰、注、撞、逗、进复、退复,拉弦乐器则有各种各样的揉弦和滑音,其目的都是为了将点状音变为线状音,形成“音腔”,亦即在音的基本形态上做到声腔化。
润腔的功能除了有利于音乐的表情达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强化并保持声音的张力。这方面,我们可以参照声乐来获得理解,因为润腔本来就源于声乐。
声乐中润腔的第一个涵义,是演唱中要施以足够的能量。早在先秦,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力度的重要性,提出“上如抗,下如队(坠)”的发声要求。这里的“抗坠”,就是演唱中气息要饱满,不论是上行之高音还是下沉之低音,都要坚实有力,不能有丝毫的虚飘,否则,就无法做到“上如抗,下如坠”。有了初始音的坚实饱满,才可能出现“声振林木、响遏行云”的效果。这个道理在弦乐器上亦同样适用。例如古琴,就十分强调“实”和“劲”,认为“弦有性……欲实而忌虚”,若“按未重,动未坚,则不实”;又说:“指求其劲,按求其实”(《溪山琴况》);“弹欲断弦,按欲入木”,等等,都是强调弹琴要有力度。这个力度,就是声音张力的基础。根据这个道理,在二胡这类擦弦乐器上,也应该将演奏建立在充足的能量和力度上。左手按弦要坚实有力,重若千钧;换指移位要紧密连贯,一如胶漆;右手运弓亦要凝重有力,既要有相当的摩擦力和阻滞感,也要有行弓的劲健敏活,而且是,有了劲健,才可能敏活。
有了初始时足够的能量,并不意味着演奏能够自始至终都能保持张力。这时候就需要另一方面的功夫,那就是控制能量的释放。如何控制?一是在能量释放时要适时中断,使之重新蓄积,即所谓“断音润腔”。声乐演唱是以气为体,演唱的过程就是气的释放过程。如何使气在释放中不使放完,或在释放的过程中能重新蓄积,是他们着重要考虑的问题。回顾古代唱论的论述,就能够发现,他们最常用的方法是停顿,是中断。早在《乐记》里,就有“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之说,“折”“止”就是停顿,就是中断。后来这样的主张就更多。清代徐大椿专门论述过“断腔”和“顿挫”,认为唱曲时“惟能断,则神情方显”。这是因为,“一人之声,连唱数字,虽气足者,亦不能接续。顿挫之时,正唱者因以歇气取气,亦于唱曲之声,大有补益”。断腔、顿挫就是演唱中有意识的控制。其实,在演唱中,控制是无所不在,例如高腔和低腔,他说:“凡高音之响,必狭、必细、必锐、必深;……如此字要高唱,不必用力尽呼,惟将此字做狭、做细、做锐、做深,则音自高矣。”④[清]徐大椿:《乐府传声》,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75、176、178页。这里,“不必用力尽呼”,强调“做狭,做细”等的“做”,就是演唱中的控制。同样,在二胡演奏中,也十分讲究控制,运弓擦弦和按弦取声,无不以善于控制为上。比如讲,擦弦和按弦都应实而不死,这不死,就是要留有反向的空间,要实中有虚。有虚,即体现为有所控制。即若泛音的演奏,表面上看是虚,是轻,实则也是虚中有实,轻而不浮。当然,二胡演奏是擦弦出声,同声乐演唱以身体内部之气力发动、身体器官之声带振动发声不同,相对而言可以持续更久,似乎不需要断与顿挫,实则不然。运弓虽然可以比气息更能持久,但也有变弱的可能,因而也需要一定的断与顿挫来重新蓄积能量。至于在慢板的演奏中,为了使音平滑、连贯、坚挺,运弓之力也就更需要控制。“润腔”的核心是调动足够的能量,并有控制地释放,目的就是使演奏的声音能够始终保持坚挺有力。
实际上,声腔化本来就是二胡的天性,因为二胡以及其他拉弦乐器都是伴随着戏曲发展起来的。拉弦乐器的伴奏,其主要功能是托腔,因而天然地具有声腔性。二胡成为独奏乐器后,对声腔化的自觉追求是从闵惠芬开始,她在这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自然,成就也最为突出。闵惠芬的声腔化实践,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致力于从声乐作品移植而来的声腔化,留下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二是将声腔化的技术运用在器乐曲的演奏上,丰富了二胡的音乐语言,增强了二胡音乐的民族韵味。闵惠芬的声腔化实践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张丽博士的《闵惠芬二胡演奏艺术研究》,即为这方面有份量的成果。在这本书中,他从微观(技法)、中观(结构)和宏观(文化)三个层面对闵惠芬的声腔化工作做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她说:“闵惠芬的艺术理念‘器乐演奏声腔化’目的不在于模拟唱腔,不在于为了‘像’而探索,而是内化为她的艺术认识,外化为二胡演奏语言,为二胡艺术寻找表现民族神韵的可操作性。”⑤张丽:《闵惠芬二胡演奏艺术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113页。这个定位是准确的。
二胡音乐如果没有声腔化,当然也能够表现思想情感,但是难以生动,也难有深度,二胡音乐所应有的民族风格与韵味,也会损失不少。⑥不是所有乐曲都必须声腔化,有些乐曲,例如《光明行》等,就很少或基本不用声腔化。所以,是否需要声腔化,声腔化到什么程度,应根据乐曲的性质来定。
三、语气与乐感
以“声腔化”为代表的情感元素可以产生“打动人”的力量,但这“打动”的效果如何,则有待于音乐性的完美呈现,亦即演奏者的乐感状态。
对于演奏来说,乐感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它几乎就是音乐的灵魂。演奏者首先面对的是乐谱,如果我们认为,演奏就是照着乐谱把它熟练地、流畅地以音响形式呈现出来,那是相当不够的。这里关键是要有乐感,奏出来的音响要有音乐性,而这是需要演奏者反复体会乐谱之后自己创造出来的。没有演奏者的音乐感觉,乐谱只不过是一系列无生命的符号。可惜的是,没有乐感,只是机械地演奏乐谱,在古今中外都是最常见的弊病,许多高明的演奏家都曾指出过这种病症,并努力寻找解决的方法。还是以古琴为例。徐上瀛在《溪山琴况》中三次提到这一弊病,他说:“往往见初入手者,一理琴弦,便忙忙不定。如一声中,欲其少停一息而不可得;一句中,欲其委宛一音而亦不能。”⑦徐上瀛:《溪山琴况》,引自吴钊等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第312;307;313;305页。又说:“究夫曲调之清,则最忌连连弹去,亟亟求完,但欲热闹娱耳,不知意趣何在。”⑧徐上瀛:《溪山琴况》,引自吴钊等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第312;307;313;305页。还有:“若不知气候两字,指一入弦,惟知忙忙连下,迨欲放慢,则竟索然无味矣。”⑨徐上瀛:《溪山琴况》,引自吴钊等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第312;307;313;305页。这样的演奏可能很熟练,很流畅,但却没有乐感,因而也就无法打动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徐上瀛提出“候”的概念,他说:“篇中有度,句中有候,字中有肯,音理甚微。”这是说,音乐在进行中自有其规律存在,演奏者首先要把握这些规律,处理好各个关节点,演奏才会有乐感。其具体做法是:“细辨其吟猱以叶之,绰注以适之,轻重缓急以节之。”⑩徐上瀛:《溪山琴况》,引自吴钊等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第312;307;313;305页。就是说,通过技法使音乐有抑扬顿挫、轻重疾徐,使所奏能够“宛转成韵,曲得其情”。这“韵”,就是乐感,就是音乐性。
说乐感是靠演奏中的抑扬顿挫、轻重疾徐实现,这没错。但并不意味着,有了这个认知,乐感问题就能够解决。因为抑扬顿挫、轻重疾徐只是表现乐感的手段,而不是乐感本身。只有找到决定乐感、支配乐感的东西,乐感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当代琴家成公亮(1940-2015)提出的“语气”说,可能是一把有效的钥匙。
成公亮的“语气”说主要体现在《秋籁居琴课》中,这本书是根据他在天津音乐学院讲授琴课的录音整理而成。书中他经常提到“语气”一词,如“弹琴一定要有语气”,“你刚才弹的缺乏语气”,“弹琴要有自己的语气”等等,前前后后共出现百余次。其核心思想就是:弹琴的要害就在“语气”。例如他说:“(古琴)技巧上并不是很难,为什么还会有人弹得好,有人弹不好?这就在于对音乐语气的把握,或者音乐语气的表达。……必须要有音乐感觉,必须要有对音乐语气的掌握。能够把琴乐里最细腻的东西表达出来,把内心深处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这样的音乐才会好听,这样的音乐才会动人。”⑪成公亮:《秋籁居琴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70页。
那么,什么叫“语气”?它有什么特点?为什么音乐离不开语气?
“语气”是语言学术语,《百度百科》的释义是:“表示说话人对某一行为或事情的看法和态度。是思想感情运动状态支配下语句的声音形式。语气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一定的思想感情,一方面是一定的具体声音形式”⑫https://baike.baidu.com/item/语气/9624317?fr=aladdin。关于语气的内涵与特点,我们可以这样表述:首先,它是以内心思想感情的色彩和分量为灵魂,是由思想感情所决定、所支配的。其次,它是以具体的声音形态为躯体,是通过特定的音高、音色、音量和声调及其变化得以表现的。再次,它通常无法独立存在,而总是存在于一个个有具体语境的语句当中。最后,它通常不能单独表达意义,但可以辅助性地将要表达的意思更准确更贴切更完满地表达出来。音乐演奏中之所以也有“语气”,是因为音乐也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之表现思想感情,正是通过语气实现的。不同只是,在语言学中,语气是辅助言说者表情达意的。其本体是语句,语气只是对语句的不同处理。语句是由字词组成的,而字词是有语义的,因此,没有语气,或语气不充分,它也能够表达出语句所要表达的内容。而在音乐中,语气虽然也是辅助性的,但由于其本体——旋律(曲调)没有语义,故语气与音乐总是粘合在一起的,这样,语气几乎就成为音乐的本体,也可以说,就是音乐的全部。这个被称为“本体”和“全部”的东西,从音乐上说,就是“乐感”。“乐感”,实际上就是“语气”在音乐中的体现。音乐有乐感就是它符合我们的语气逻辑。音乐,说到底,它并没有一套独自的逻辑,它的逻辑就是我们的生活逻辑、情感逻辑、思维逻辑,其最直接的形态,就是语气逻辑,因为语气是人的思想感情表达的最为直观、最为感性的形式。
在语气的支配下演奏音乐,有哪些基本原则?首先,要寻找各个音符间的逻辑关系,用自己鲜活的感觉将它们贯穿起来,使音乐的进行有生气,有活力。演奏者所面对的乐谱,基本上是没有语气的,它只是提供了乐思,描画出乐曲的构架。演奏者的任务就是赋予它生动的语气,使它变得有血有肉,有精神,有灵魂,有个性,总之,变成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其次,要以句为单位进行乐曲的演奏,这可称之为“句思维”。也就是说,演奏乐曲,不能只是照着乐谱一个音一个音地奏出,而是要像说话一样,一句一句地说,每一句都有一定的语意,因而也一定伴随着特定的语气,有快有慢,有高有低,有急促有舒缓,有紧凑有停顿;句与句的衔接,也应该符合整体表意抒情的语气逻辑,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前后相接。这一点,古人即已认识到,他们在论乐文字中经常使用“句度”“句读”等概念,就是“句思维”的体现。
古琴演奏需要语气,二胡演奏也同样需要。在现实中,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的二胡演奏,其音乐支离破碎,疙疙瘩瘩,好像要表达很多东西,但终究不知所云,听来也毫无美感。究其原因,不是技术不行,也不是对乐曲不理解,而就是在演奏中没能融入自己的感觉,没能将音乐化为自己的心声,因而整体上缺乏合适的语气。这个状态下的演奏只能是机械的、生硬的、“照葫芦画瓢”式的演奏,其音乐也就只能是杂乱无章,毫无乐感。优秀的演奏家则全然不同,比如闵惠芬,她的演奏之所以成功,她所演绎的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首先就在于,她善于用心体验,重视语气表达,因而乐感很强。据记载,贺绿汀曾经称赞16岁时的闵惠芬,说“她的演奏最有音乐”。“有音乐”就是“乐感好”,就是音乐中有语气。乐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来自天赋,即天生就能够快速地、贴切地赋予音乐以语气。闵惠芬有这样的天分,所以她容易成功。但乐感更多地还是来自后天的揣摩与练习,闵惠芬又是一位极其认真、极其执着、极其勤奋的演奏家,她的“声腔化”工程就包含了“语气”这门功课。天分好,再加上后天努力,所以她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
在如何训练二胡演奏中的乐感方面,我以为,成公亮提出的“语气”,应该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抓手”。⑬关于“语气”说的详细论述,可参看拙文《对琴乐演奏之道的潜心追求——成公亮的古琴演奏艺术及其美学理路》,《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6年,第3期。
四、技术的定位
二胡演奏所呈现出来的是声音,其中张力也好,声腔化也好,乐感也好,无不是通过声音呈现的。而声音的呈现又都是由特定的技术(亦即技法、技巧)实现的。那么,技术在这里是如何起作用的?决定技术、支配技术的又是什么?
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音乐离不开技术,音乐的演奏也离不开技术,音乐演奏要想创造出美,更离不开技术。但是,同样也很明显的是,尽管音乐的美离不开技术,但美不就是技术,不等于技术。那么我们要问:音乐演奏中的技术与其创造出的美,究竟是什么关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用庄子“庖丁解牛”的寓言说明过“技”与“道”的关系,我以为,这“技”与“道”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技”与“艺”、“技”与“美”的关系。⑭参见刘承华:《古琴演奏中的“技”与“道”——从庄子“庖丁解牛”谈起》,《艺术百家》,2009年,第3期。
这个寓言载于《庄子·养生主》,说的是庖丁解牛,动作迅速敏捷,成效极高,引来文惠君的极口称赞:“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听后却不以为然,说那个东西不是“技”,而是“道”,它“进乎技矣”。⑮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页。接着便解释为什么是“道”而非“技”。他先从自己学习解牛的经历说起:“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⑯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页。这是说,他的解牛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所见无非全牛”,即对牛只有整体的外观知觉,而无内在机理的认知。第二阶段是“未尝见全牛”,即把握了牛的内在机理。这比前一阶段要深入得多,但还不是最高阶段,因为它主要还停留在认知的层面,尚未落实到实践之中。第三阶段就是将对牛的内在机理的认识落实到实践之中,不仅落实到实践,而且达到技术与对象的完满统一,亦即“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第三阶段就是庖丁所说的“道”。
庖丁所说的“道”的状态和“技”的状态有何区别?“技”是如何在自己的运作中进入“道”的?首先,技要进入道,就要有自己的对象与目的,无对象无目的的技不成为技。其次,技术面对其对象,必须是充分把握其内部的机理(亦即规律),没有把握内在机理的技,是不自由的。再次,技术必须能够在实践中完满地介入对象,完全遵循对象的机理来运作。而且,这时的运作必须是完全自由的活动,这就是解牛的最高境界。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此时你不仅把握了要处理的对象的内在规律,而且在行动中完全遵循了这个规律,并在遵循中做到自由无碍,游刃有余,即“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⑰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页。由此可见,由“技”至“道”,实际上并不神秘,它就是“技”不断进入对象,并最终与对象融而为一的过程。
“庖丁解牛”对技——道关系的理解,是否对二胡演奏中的技——艺关系有所启发?当然有,这两者完全相通。首先,二胡演奏要想以自己的努力创造出美,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使自己的“技”越来越深入地介入作品,与作品的精神内涵达成水乳交融的境地。没有介入对象的技术是抽象的、无灵魂的,如脱离作品情韵的表现而刻意地“炫技”即属此类。阿炳之所以反对孤立的、模仿性的技巧展示,就是因为它是孤立的,无目的的,是抽象的。而刘天华、闵惠芬等将同样的模仿技巧(如鸟鸣声、马嘶声)运用到音乐中,则是成功的,因为它是有目的的,有表现力的。其次,技术要想介入作品,首先必须深入地、彻底地把握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这个内容是广义的,它既指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同时也包含音乐所要呈现的感觉、情绪、意态、个性、韵致等更微妙、更隐蔽的内容。像庖丁那样“未尝见全牛”,演奏者也应该对自己作品的结构、节奏,各个环节的轻重疾徐、抑扬顿挫与其所表现内容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的认知和真切的体验。如果没有这个功夫,你的技术一定无法完满地介入对象。不能完满介入作品的技术,它与表现内容是错位的,因而是机械的、生硬的、笨拙的,没有生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抽象的。
那么,技术完满地介入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一个高度自由、心手两忘、物我为一的状态。就好像庖丁解牛进入“道”的状态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演奏中的这个状态也是如此:高度自由、忘我,是技术的消解,是演奏的非演奏状态。在这方面,闵惠芬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她在回忆自己获得世界万强唱片比赛“十佳之最”第一名《江河水》的演奏时说:“那是一遍成功,没有一个音是败笔,情感极其投入,手法的把握……完全忘我,半天都拔不出来,自己内心痛彻肺腑,很长时间都浑身颤抖,无法平静。我超越了自己。”⑱同注⑤,第121页。当时在场的加拿大录音师马濬也回忆说:“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收录《江河水》一曲时,从控制室的窗,看到她闭目全神,恍如已与乐曲及她的胡琴融汇为一体。每个拉出来的音符都充满着忧伤,人间的苦痛,使人戚然于其中。当时几个美、加籍的录音师,虽不懂中乐,均不期然地站起来,肃穆地聆听,终曲良久,仍然黯然无声。当闵女士走进控制室重听录音时,各人都不约而同地鼓掌,对她致敬。”⑲同注⑤,第121页。从演奏者自己的体验和旁观者的聆听感受,共同地说出了二胡演奏进入“道”的境地后的真实状态。当然,这样一种高度自由、心手相忘、物我融一的演奏状态,并不是某种混沌和麻木,亦不是完全的非理性。一如庖丁所说,“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⑳同注⑮,第15页。“族”即筋骨交错情况复杂之处,每遇到这样的地方,他也还要集中自己的注意力:目光要专注,动作要谨慎,要充分调动自己的意志和能量,这样才能出现“动刀甚微,謋然已解”的效果。二胡演奏也是如此,不是完全的非理性,而是将理性融解到自己的感性之中,一般情况下,理性是不需要再以自己的面目出现。但是,当遇到一些特别的地方需要理性出面时,它又会适时出现,保证演奏的顺利进行。
二胡演奏进入“道”的状态,也就是音乐之“美”的真正诞生。音乐演奏也有声音美不美,亦即音色是否悦耳的成分,但不是主要的。音乐演奏所产生的美重点也不在所表现的内容,不在于它表现了什么题材,不在于表现了什么思想情感,而在于技术如何完满贴切地表现了内容,而且是无滞无碍,自然浑成。因此,对于音乐演奏来说,“美”并非音乐表现的内容,而是音乐对内容的表现本身,是音乐表现内容的“副产品”;因为音乐有了表现力,所以才会产生出感染力。也就是说,“技”在克服了自身的抽象与欠缺之后,进入完满表现的“道”的状态,音乐的“美”于是产生。
当然,我们知道,技术只是工具,而不是主体,它之所以能够进入“道”的境界,说到底还是演奏者的作用。从最直接的因素来看,支配技术的是什么?是“乐感”,将音乐的曲调转换为生命感觉和表达语气的乐感。没有良好的乐感,再好的技术也难以发挥作用。
到这里,我们可以对文章小结如下:二胡演奏中的技术处理,其分寸是由乐感支配的,而乐感的本质是语气,决定语气的是乐曲表现的内容,它要求演奏者对乐曲内容有鲜活生动的体验。有了鲜活生动的体验,才能够产生合适的语气表达;有了技术上的得心应手,才能够将此语气准确地转化为音乐的声腔和张力,使演奏获得生动的表现力和强大的感染力;而“美”,也就在此时被创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