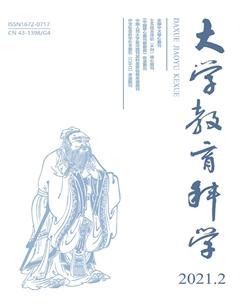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机制变革:逻辑、困境与路径
摘要: 学术评价机制被认为是科研体制的核心,不仅能够直接引导和规范高校教师个体的学术行为,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创新。从根本上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是一项复杂的学术活动而非简单的管理活动,但目前的评价机制却因受到强烈的绩效管理主义思想影响而呈现出过度的量化倾向、单一化倾向和行政化倾向。故而,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视角重新理解教师学术评价的权力运作逻辑、分类管理逻辑和程序规制逻辑对于推动评价机制变革具有独特价值。通过实践考察发现,多重权力交织导致的主体边界不明晰、缺乏对知识生产创新规律的充分尊重、基于程序正义的制度性规范不稳定、学术关系寻租造成的评价结果公信力不足等诸多疴疾正在破坏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中的主体性地位。推进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机制变革需以管评办分离为基础,重构基于程序正义和知识生产规律的学术评价生态,从而更好地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主体性功能。
关键词:学术共同体;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21)02-0062-09
学术评价机制被认为是科研体制的核心,不仅能够直接引导和规范高校教师个体的学术行为,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创新。从政策层面看,为优化教师学术评价机制、破除研究过程中的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科技部、教育部等先后印发了《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等诸多政策文件。从实践层面看,国内高校也纷纷启动了相关的改革措施,但与英美高校建立的以学术共同体为基础的同行评议机制相比,这些措施因对学术共同体重视不足而导致的功利性色彩浓厚、公信力不高等问题仍然饱受诟病。从根本上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是一项复杂的学术活动而非简单的管理活动,其实质上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调控与认定。但目前的评价机制却因受到绩效管理主义思想影响而严重制约着学术共同体作为高校教师评价主体的自主性,以至于产生评价过程中的“二律背反”[1]。
诚如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所言:“评价一位学者的研究贡献(或者是否为共同体所认可)的标准只在于合乎构成真理的技术性和学术性要求以及新知识的重要性。”[2]与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导的评价相比,学术共同体理论主张学术自治、发挥专业团体的自主性,评价标准基于教师对知识生产创新的贡献,在谁来评、评什么、怎么评等本质性议题上更加遵循学术研究和知识创新的内在规律。从已有研究看,尽管学界已对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存在的理念非理性、程序不公平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不足之处仍然广泛存在。因此,从学术共同体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视角重新理解教师学术评价的权力运作逻辑、分类管理逻辑和程序规制逻辑,对于推动评价机制变革无疑具有独特的指导价值。鉴于此,本研究以学术共同体理论为独特视角,考察分析了我国高校教师学术评价过程中存在的政策与实践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发挥学术共同体主体性功能的变革路径。
一、变革逻辑:学术共同体视角下高校教师评价机制的理论生成
教师学术评价机制变革实质上是教师、高校和政府等不同主体的复杂博弈過程,不仅引导和规范着高校教师个体的学术行为,而且深刻影响到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创新。从深层看,学术评价不仅是一个静态结果,更是一个动态过程。学术共同体视角下的教师学术评价是在遵循学术规律的基础上,依据知识生产、创新与应用的内在逻辑,采用同行评议方式对研究成果进行价值判断的学术活动过程。
(一)学术共同体的理论生成与分析框架
共同体的概念最早见于古希腊,表达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价值规范的群体生活方式。学界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理论发轫于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较早论述了共同体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共同体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对真实的共同体的科学预判[3]。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基于人类意志以及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持久的、真实的、有生命的有机体[4],其本质特征是人类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享有共同领会的信念、意志与规则。齐格蒙特·鲍曼则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将其定义为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和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并分为有形的、无形的两种类型[5]。从发展演变看,共同体理论的滥觞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社会背景。尽管不同学者在共同体概念的表述上存在一定分歧,但在实质上却达成了高度的共识性。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认为共同体理论主要关注社会发展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基于思想和社会认同之上的一种共同生活、权威机构或精神指引,并逐渐由实体性存在转变为一种社会关系分析工具。
20世纪后半叶,英美学者基于共同体理论系统探讨学术研究领域的社会行为,掀起了一股学术共同体理论研究热潮。从研究内容来看,关于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讨论主要从外在与内在两方面展开:对外保障了以学术研究为志业群体的社会身份和共同利益;对内提供了科学信息的评价、交流和储存的平台与条件。而关于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则以默顿和库恩的研究最具代表性。默顿提出学术共同体必须遵守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的集体价值取向[6]。库恩使用“范式”概念对学术共同体的共识与规范进行说明,并将其定义为一致遵从的有关实践、范例、规则与信念的承诺[7]。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逐渐关注到学术共同体理论,并对学术共同体的权力架构[8]、内在精神[9]等进行探究。但就整体进展而言,我国学者较多介绍与移植西方学术共同体理论,缺乏本土化的实践探索。从国内外研究总体来看,学术共同体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历史的、多元的理论体系,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对其理解、建构方法各异,但仍达成了许多共识。
正如麦克莱伦所言:“学术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我管理,它们赋予成员以社会认可的角色和地位,提供资格认可,建立一系列制度,在各个层次上组织和激发科学发展的活力。”[10]学术共同体固有其内在价值标准与程序性规范,并以此推动学术的繁荣与进步。基于已有的研究共识与理论框架,我们可围绕四方面审视学术共同体理论。首先是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主体性。所谓学术共同体是以学术研究为志业的学者们主要依据研究范式和研究旨趣上的共有因素而结成的学术组织或团体的集合体。这个组织或团体本身并非是对成员具有强制力的实体组织,但其平衡着内部力量与行政、市场等外部力量之间的关系,维护着学者的自由探究精神与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其次是客观的学术价值标准。学术共同体内部具有特殊的伦理规范、价值取向和学术认定标准,这使得不同知识领域与学科矩阵的学者既拥有共通的资源、文化和信念,又能保持各自的学科特色。再次是公平正义的学术评价程序。在学术评价过程中,共同体遵循制度公平和程序正义原则,在学者个人聘任与晋升、科研基金申请、成果发表、声誉获得等学术生涯的关键点上发挥监督保障的作用。最后是学术共同体的权威性。学术共同体所具备的专业性和自律性,能够保障其被学者们视为情感、理念和精神的归属,从而使内部成员自觉认同和遵守共同体的学术准则与伦理规范,并对自身的学术行为负责。
(二)学术共同体视角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 机制的变革逻辑
从本质上看,学术评价被认为是学术共同体内的一种自我认定和自我调控,它无法独立于学术研究之外[11](P125-129)。学术共同体理论自产生以来,都在不断优化和完善评价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机制以推动学术生产模式的选择优化。根据高等教育系统“三角协调模型”理论的观点,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机制变革实际上主要受到三重逻辑的叠加影响。
1.权力运作逻辑:明确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主体地位
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机制中存在着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政治权力和民主权力等多重权力的交织与博弈。在实际运行中,多重权力在博弈的过程中极易产生不协调乃至严重失衡的状况。调查研究显示,行政力量既可能是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有力推动者,也可能是限制其发展的主要障碍[12]。高校教师学术评价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项学术性活动,理想状态下的教师评价应由也只能由学术共同体承担。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其一,高深知识体系及其发展的逻辑构成了学术共同体评价权力运作的认识论基础和合法性根源。只要离开对知识的占有、分配或保留,权力的运作就无法发挥作用[13]。换言之,知识彰显了权力运作的某种自明性,使权力客体自然而然地接受权力运作的逻辑与状态。高深知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致使外行根本无法涉及和把握对高校教师的学术评价,而来自同一或相似研究领域的学者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构成了其成为评价主体的必要条件;其二,学术自主是学术共同体评价权力运作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追求。学术自主是学术职业的核心价值,但行政的强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始终无法兑现的根源所在[14]。在此种情况下,教师学术评价也进一步被抽象与简化为以绩效管理主义为基础的“产出激励”“以刊代文”和“以数字论英雄”等。“基于学者是高深学问的看护人这一事实,人们可以逻辑地推出他们也是他们自己的伦理道德准则的监护人。”[15]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只有由学术共同体主导的学术评价才符合学术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的,真正体现出学术自主或自由的特征。
2.分类管理逻辑:尊重不同学科的内在差异和 发展规律
无论是托尼·比彻提出的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用硬科学和应用软科学分类,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分类,都强调在遵循知识生产创新的属性差异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开展差异化的学术评价。伴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深入发展,不同类型高校所承担的使命与职责也更加清晰,迫切需要构建起符合不同类型高校特点的教师学术分类评价机制。博耶在《学术水平的反思——大学教授工作的重点》一书中将学术分为的“发现的學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16],这种学术分类思想为高校教师的学术分类管理机制变革提供了新的理解框架和实践路径。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知识生产特征和规律,其评价方式也应当有所差异。但当前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指标、评价方式和评价内容的趋同,使不同学科、不同岗位、不同类型高校教师的学术评价“五唯”倾向日益突出。与同质化的外在评价机制相较,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评价机制按照不同学科的性质特点,可以是多元的,其价值评判尺度也应因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17]。不同学科在研究对象、知识发展的逻辑、研究程序、研究标准以及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等基本研究范式上存在着明晰的界限,因而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学术框架的学术评价工具。
3.程序规制逻辑:捍卫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 公平与公正
程序规制,就是用正当程序的手段与方式约束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权力行使,其根本目的在于以防范的方式达到“善治”之目标。学术共同体行使的学术评价权是一种非典型意义上的公权力,但因其对学术事务的评判和甄别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相对一方的合法权益而必须接受正当程序的约束。这种正当程序既包括国家法律法规与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度设定,也包括学术共同体内部无形的价值、信念与“行规”。它并不是针对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某一个成员而言,而是约束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权力行使行为,从最大程度上预防“学术权威异化为操纵内部评判标准、限制潜在竞争者”[18]等学术权力寻租现象。事实上,20世纪中期美国联邦法院即认定高校教师享有宪法上的“正当程序”权利,如在面临解聘时,享有知情权与申辩的机会[19]。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高校学术权力行使也应当服膺于依法行政原则”[20]。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个体很容易出现某些机会主义的行为,公众也难以评判学者是否诚恳对待公众的利益。“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根本差异”[21],惟有以程序的方式与手段才可能规范学术评价权的合法、正当行使,回应公众对学术共同体及学术权力的信任,从而在更高层面实现学术自由。
二、变革困境:学术共同体视角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机制的问题审视
学术评价是一个由多重利益主体和力量主体协同参与的复杂过程,受到多重因素的动态影响。从学术共同体逻辑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在本质上是知识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坚持学术自治和同行评议的基本原则。但从实践层面看,由于高校内外部力量的牵制,学术共同体的主体性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导致了教师学术评价过程的主体异化和价值失衡。
(一)不同主体间权力边界不够明晰,限制学术共同体作为主体的自主性
学术共同体理论认为,尽管教师学术评价既受到学者个体和学术共同体等内部权力作用,也涉及政府或机构的行政权力及社会力量等外部权力,但对于学术评价这一有着独特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规范的活动而言,多重权力间应保持清晰的界限。外部力量必须在尊重学术共同体自主性的基础上,以有节制而适当的方式介入教师学术评价。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高校这一复杂场域中的多重权力交织,彼此间权力范围和边界尚不清晰,导致学术权力过度依赖于行政权力的调节和干预,严重限制了学术共同体作为教师学术评价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内部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到学术评价的过程之中,破坏了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学术性基础。高校作为事业单位,政府对其行使的管理权具有强制性。在这种集权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在教师聘任、职称晋升、职务任命等重要人事权上的垄断就自然而然渗透进成果认定、项目评定、量化考核等方面的评价中。然而,管理者可能并没有“超能力”去直接考察学术生产中的知识生产创新问题。因此,就必须对复杂的评价工作进行层层的抽象与简化,再用简化的工具识别、测量、表征與反馈,才能实现对社会组织的“更直观”认识[22]。论文数量、刊文层次、职称高低、奖项级别、被引次数等简化指标由此获得了评价中的现实合理性,进一步限制了学术共同体作为教师学术评价主体的自主权。此外,不同规章制度和属性界定上的矛盾冲突(譬如,校长需兼顾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以及校长办公会议等行政事务),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非学术权力干预留有了余地。
另一方面,评价机构及其相关主体在教师学术评价中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难以保障,限制了学术共同体的主体性功能发挥。评价机构及其相关主体基于文献计量理论和集散规律对学术成果进行的分科评价,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这迎合了行政部门分配和管理学术资源的需要,因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产生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等七大评价机构与体系。用SCI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的话来说,“引文索引的主要作用是一个检索工具,科研评价只是衍生性功能”[23]。因此,过分陷入以刊评文和追求量化的迷思,将助长评价机构及其相关主体“利益至上、多头格局、越位评价、权力膨胀”[24]之风气,导致学术评价政出多门,乱象纷纭。
(二)缺乏对知识生产创新规律的充分尊重,难以体现评价标准的客观性
评价标准被认为是高校教师评价机制的核心,承担着彰显评价客观性、科学性和专业性价值的作用[25]。遵从学科、专业知识生产创新规律的评价标准应是多元的、有差异的,能够科学合理地评价不同学科、学校类型下高校教师的学术生产力与知识贡献。依据吉本斯等学者的观点,高校的知识生产创新过程已被纳入社会发展和市场领域之中[26]。这种转型也在客观上要求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机制作出变革,探索构建更加适应于新时期需要的差异性的学术评价标准。当前,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文件试图扭转教师评价标准差异性不明显的困顿局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就再次重申推进分岗位、分层次、分学科评价的具体要求。从现有研究看,学界已对此作出一定的回应。有研究者提出应基于教学型、科研型、教学科研并重型、应用开发型等类型的教师构建合理的教师学术评价标准[27]。也有研究者通过访谈美国中部某公立研究型高校的数学、机械、历史、会计学科教师,发现美国高校实施的教师学术评价制度存在明显的学科差异[28]。
但在实践操作中,构建基于知识生产创新规律的教师学术评价标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由于学科差异不仅存在于学科大类之间,同一学科大类下的不同学科和同一学科下的不同领域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如同属于基础学科的历史学和数学也会因学科的知识生产规律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再者,教学和科研评价要求的矛盾关系,也使制定相对应的评价标准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诸多高校都在不断尝试构建分类评价标准,但行政导向的评价标准、功利主义的产出激励、“高产”对“优产”的排斥等饱受诟病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事实上,构建高校教师的差异性评价标准首先应当是一种学术事务,但中国高校却常因行政化的权力运作逻辑占据上风,而严重制约了学术共同体的自主自治以及教师评价职能的有效履行。现行的“行政化了”的评价标准,诱发了高校内部成员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高校教师成为追逐与相关指标挂钩的物质报酬和各种帽子背后蕴藏的经济收益的博弈者、“买卖人”[29]。殊不知,忽视学术评价标准的差异性要求,甚至可能面临马克斯·韦伯担忧的局面——“在‘国家支配下,学术所享有的利益,对科学出于兴趣的选择和学术特长的发挥,在更多方面愈加恶化”[30]。
(三)基于程序正义的制度性规范不稳定, 难以凸显学术评价过程的正当性
制度性规范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学术共同体评价自主权的式微,加剧行政部门或第三方机构干预和操控学术共同体的风险,继而威胁到学术自由和自主。虽然《高等教育法》和《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学术委员会等学术共同体组织的权力运作,但整体观之,仍较少涉及学术共同体评价权行使的程序制度安排。在高校教师评价问题上,这不仅会导致学术共同体组织因程序上的“自由裁量”而出现随意评价、纵容权力寻租等学术不端的隐性腐败问题,也会使学术评价权面临司法的拷问。譬如,“于艳茹诉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位”一案中,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处理撤销学位审议过程中未听取当事人意见而有违程序正义。据此,一审二审法院均作出“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学位决定前,未能履行正当程序,构成程序违法”[31]的判决。
具体到高校内部,教师学术评价制度性规范不稳定表现为:首先,以实体性规定为主,较少涉及程序性规范。现有规则较多涉及学术共同体组织人员构成、任职资格、会议制度、权利与义务等方面,而鲜有对争议处理、学术问责与学术纠纷等关键性程序给出明确的操作规范。其次,对相关权利救济的方式和规则设置不甚健全,对关于教师对学术委员会等学术共同体组织的评定存在异议需申诉的处理规则语焉不详,大多数高校仅允许一次校内复议,而对异议未消除或需进一步申诉的情况未作明确规定和说明。最后,公开程序上的制度性缺失。高校现有章程大多都提到“学术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应当予以公示”“每年度对学术委员会的运行及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总结”,但虚化了“对谁公开”“公开什么”“不公开对谁负责”“对谁总结”“谁来负责”等关键议题,进一步威胁到学术共同体评价程序的正当性。
(四)学术“守门人”空置与学术寻租,损害 评价结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从理想的学术共同体评价机制看,同行评议充当着学术“守门人”角色。它对于开展科学评价、分配学术资源以及维持学术共同体的自我生产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同行评议是学术共同体评价自主的重要环节和集中体现。然而,由于我国目前的学术共同体机制并不完善,评价过程中存在着权力与利益寻租等有损学术权威性与公信力的诸多现象和问题。在“权力支配、人情主导、标准缺失”[32]的学术关系网络中,同行评议这一学术共同体最為重要的评价方法难以发挥其功用,评价结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饱受公众质疑。近年来,北京电影学院翟博士“不知知网”、南大“404”教授、中国学者学术论文屡被国际期刊撤稿等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学术“守门人”空置及学术寻租现象的存在。尽管这些现象并未直指高校内部学术共同体的教师评价活动,但其充分暴露出的学术品德失范、学术精神式微等问题,无疑进一步损害了学术评价结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当一个切实可行的理想即将消逝的时候,实用主义抬头,庸人欢声雷动的时候,虚假的科学已经畅行无阻,所谓学术未从拘泥、庸俗的范畴中解脱出来,这是一种悲剧。”[33]同行评议这一学术“守门人”的空置,引发了高校教师对学术共同体公平公正性的多米诺骨牌式质疑。相关数据显示,教师对于学术资助方式及其分配的公正性认可度不高[34]。事实上,同行评议经历漫长的演进过程,其优越性早已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被广泛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评价领域。如英国“研究卓越框架”采用同行专家评议为主、文献计量为辅的评价方法;德国高校“卓越计划”要求,对于人文科学的评价不以引证率为标准,只能通过学术同行基于代表作及其影响力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成就,以最大程度上确保学术资源分配的公正性。目前,我国相关部门破除学术评价“五唯”、“SCI至上”的系列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学术不良风气。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在短期内仍无法破解教师学术评价中对声誉、权利或利益的功利性追求而导致的学术寻租问题。
三、变革路径:学术共同体视角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机制的优化
评价机制的优化最终有赖于以学术共同体为基础的评价主体的独立和成熟。自治且自由的学术共同体机制是保障评价达到最大限度客观公正的前提和基础[11](P125-129)。为保障学术共同体的主体性功能发挥,发达国家普遍设立学术评议会,在机构设置、基本职责、运行机制及与行政团队的关系等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制度设计[35]。尽管国内外学术生态存在诸多差异,但学术共同体对于维护教师评价公允、促进学术发展的特殊价值和不可替代性却是毋庸置疑的。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机制的优化必须以学术共同体理论为支撑,打破传统评价过程中公平性、专业性和客观性难以保障的实践困境,有效激发学术共同体的主体性功能。
(一)健全基于学术与行政分离的学术评价权力运作机制
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机制变革实质上是多重权力主体的关系博弈。如果评价主体之间的权力边界不够明晰,那么仅靠规章制度维系的教师学术评价机制就会陷入越管越乱、越乱越管的恶性循环。政府推动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机制变革需明确学术与行政的关系边界,将学术评价的权力交给学术共同体。
首先,从制度设计上破解管办评分离的现实障碍,完善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和职责。在当前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这一举措是必要且紧迫的。我们要变革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行政权力主导的教师学术评价机制,将会面临权力与利益分配格局固化所带来的强劲路径依赖,需要在政府公权力的配合与主动调适下,完善同行评议的基础性制度供给,明确同行专家评价权利与义务、组织与管理、监督与问责等关键性活动的操作规范,引导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落实学术共同体在教师学术评价中的主体地位。
其次,科学看待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学术评价功能,合理利用外部评价和内部评价。客观上看,第三方评价确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SCI、SSCI、CSSCI指标设置的初衷也是为了使学术评价有所依据,但遗憾的是当学术研究与利益分配挂钩之后产生了狂热追求指标的异化。因而,行政部门需尽快摒弃“一刀切”“数工分”式的评价方式,通过规范学术市场中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准入、准出、监督制度,形成以学术同行评议为主、第三方评价和政府评价为辅的多元化评价机制。日本《关于国家研究开发评价的大纲性指针》中对第三方外部评价与学术共同体内部评价结合的科学性探索(如鼓励创办第三方评价机构、发挥第三方评价的监督和审查作用等),对我国高校教师学术评价中的第三方参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最后,健全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评价制度,提升学术评价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在具体的学术评价中,高校层面要做好学术共同体组织的专家遴选与配置。因应学科专业高度细化的需求,高校可实行“小同行”专家评价,由相同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范围内的专家对所在学科的学术前沿和创新性成果进行评价更具专业性与科学性。同时,高校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媒体技术突破地域限制,将国际学术同行专家引入到教师学术评价之中,客观评价教师代表性学术成果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力,实现评价中国内与国际、学术与社会的兼容。
(二)优化基于知识生产创新规律的学术分类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对于规制学术发展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价值。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变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不仅涉及科技、财政、教育等多层级政府行政部门,还与多地区高校以及多类型的社会评价组织高度相关。这意味着制定新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一个耗时长、难度大、高敏感的过程。所幸从知识生产创新的角度看,博耶、托尼·比彻、舒尔曼、赫钦斯等学者均结合高校定位和教师职能提出了不同的学术分类观,为学术分类评价标准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一方面,应让学术共同体在高校教师分类评价标准制定过程中发挥主体性作用,促进分类评价标准的科学化与合理化,要在充分尊重学术专家和同行对于学术和学科发展的本质规律和前沿趋势判断的基础上,建立科学性与针对性相结合、水平业绩与发展潜力相结合、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相结合的可动态调整的价值标准。同时,赋予基层学术共同体组织一定的评价自主权。高校作为底部沉重的组织,基层学术共同体组织自治是激活其学术心脏地带的内在要求[36]。基于基层学术共同体组织的教师评价可以根据学科差异合理设置和使用评价指标,实现差别化评价,鼓励不同类型、不同岗位的教师追求卓越。
另一方面,应根据知识生产创新的内在逻辑,推动教师成果认定、聘任与晋升、资源配置等分类评价标准的具体化和精细化。不同学科间在知识结构、培养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学术产出形式和影响因素均存在显著差异[37]。基础学科以探求知识本源为主要任务,是一种内生型的知识发现方式,评价其所属学科教师时需更加重视知识的本体价值及其学术影响力。应用学科更加强调知识的实用性和社会价值,相应的教师评价应注重经济社会效益和实际贡献的评价导向。因此,应基于不同类型高校的使命与职责,制定差异化的教师分类评价标准和评价改革推进方式。以“双一流”为代表的研究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应侧重于科研,应用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应侧重于教学与应用,高职院校教师学术评价则要更侧重于技能。此外,不同类型高校的教师学术评价还需兼顾社会价值导向和非学术性影响。
(三)重塑基于程序正义的学术共同体自治保障
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社会的合法性是基于产生法律的正当程序。正当程序同样适用于教师学术评价,学术共同体成为学术评价主体的基本前提是其提供信息的程序公正无私且符合专业规范。但当学术专家主要依赖道德自律对高校教师学术水平进行价值判断时,就难以用较为客观的方法判定带有主观倾向的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合理公正的评价程序才可以让被评者尊重和信赖评价结果,程序正义实质上成为实体正义的必要条件。亦即,只要程序正当,结果的正当性就是必然的。因此,以制度规制维护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程序的公平正当,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降低学术不公与冲突出现频率是必要且紧迫的。
从具体方式看,一是要完善学术评价权力行使的制度规制。学术共同体行使学术判断权、学术评价权以及自由裁量权均是学术自由的集中体现,但不加以限制的学术自由容易滋生权力寻租和学术不端行为。学术评价结果与高校教师发展息息相关,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活动有必要建立明确的学术权力行使制度并严格遵守学术评价规则,在符合制度规制的前提下行使学术评价权。二是要形成及时有效的信息公开制度规制。高校应在事前、事中、事后及时向不同利益相关者选择性公开评价信息。如对评价当事人公开基本评价信息,但不涉及评价专家的个人信息;对学院、学校及社会公开被评者基本信息和相应的评价结果,主动接受多渠道的民主监督。三是要构建学术与司法并行的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权利救济的制度规制。鉴于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自治性,不宜将所有的学术纠纷交由司法部门处理,可在完善学术申诉制度、学术裁决制度及学术复议制度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司法审查,这样既能保证高校处理学术事务的相对独立和自由,又能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
(四)培育基于良性学术研究生态的共同体评价环境
在学术语境下,学术生态是由学术共同体及其在学术活动中生成的规则规范、道德准则、学术风气等聚集而成的。实质上,当前学术“守门人”空置以及学术寻租乱象频发根本在于学术研究生态失衡,致使学术共同体未能充分发挥其学术评价自主性和能动性。换言之,学术生态与学术共同体评价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学术研究的特殊性在于仅靠行政、社会等外部力量的约束和规制难以真正解决学术问题,必须要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形成强大的学术自律与自洁机制,才能由内到外、由点到面地革新学术生态,重塑高校教师学术评价公信力。
一方面,要建立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共生共长机制,以学术个体内在的学术品格和道德准则约束规范其评价行为。第一,培养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在高校教师评价过程中能够基于学术个体的学术价值观而作出的纯粹自觉的学术价值判断。第二,铸就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品格。尊重高校教师学术成果的价值应是学术个体进行评价的基本学术品格。学术评价合理与否不仅会对被评者个人发展造成重要影响,而且对高校乃至学术界的学术声誉意义深远。学术专家作为评价的权力主体必须具备良好的学术品格,合理公正评价突破性、原创性、颠覆性学术成果。第三,坚守学术共同体内部的道德准则。道德准则是形成学术自律机制的决定性因素,是学术个体进行学术活动的基本要求。学术个体必须在具体的教师评价中坚守对道德、真理的永恒追求,捍卫学术忠诚。
另一方面,要完善学术共同体发展的学术自洁机制,以集体内部的学术氛围和制度约束规范其评价行为。第一,建立评价专家学术诚信体系,记录与评价直接相关专家的基本信息、学术不端行为信息等。评审专家是高校教師学术评价的主要参与方,其学术诚信直接影响到评价质量和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因而,需建立尽可能公开透明的学术诚信体系,使非学术性因素的介入无处遁形。第二,构建评价问责和退出制度。教师学术评价影响深远,专家的评价活动应基于对学术史负责的学术立场,其评价结果应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对待任何评价都应谨慎,因为谁也无法逃脱历史的裁量[38]。在此基础上,还应明确评价专家退出情形,允许专家自行申请退出评价,禁止受过行政、刑事处罚者或有冒名顶替、滥用职权、泄漏评价信息等行为者参与教师学术评价,妨碍评价公平。
参考文献
[1] 沈红,林桢栋.大学教师评价的主客体关系及其平衡[J].中国高教研究,2019(06):48-53.
[2] Gaston J.The Reward System in British Science[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0(04):718-732.
[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4]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87.
[5]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
[6] [美]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M].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63.
[7]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7-43.
[8] 阎光才.学术共同体内外的权力博弈与同行评议制度[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01):124-138.
[9] 唐松林,魏婷婷.学术共同体的契约精神:本质、背离与回归[J].教育发展研究,2015(07):70-75.
[10] Mcclellan J E.Science Reorganized: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250.
[11] 王学典.将评估学术的权力还给学术界[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2).
[12] 杜嫱,刘鑫桥.高校教师离职倾向及学术权力感知的作用——基于“2016年全国高校教师发展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9(09):48-53.
[13] Joseph Rouse.The Dynamics of Power and Knowledge in Science[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91(11):658-665.
[14] 阎光才.我国学术职业环境的现状与问题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1(11):1-9.
[15]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121.
[16] [美]欧内斯特·L·博耶.关于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演讲[M].涂艳国,方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65.
[17] 许纪霖.回归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尺度[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4):78-82.
[18] [英]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2.
[19] John S B,Willis R.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1636-1976[M].New York:Harper & Row Press,1976:326.
[20] 董保城.教育法治与学术自由[M].台北:月旦出版社,1997:5.
[21] Osakwe C.“The Bill of Rights for the Criminal Defendant in American Law”in 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dure[M].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2:260.
[22] 陈晓娟,任增元.高等教育评价:超越“五唯”的价值意蕴与体制支撑[J].大学教育科学,2020(06):9-12+15.
[23] [美]尤金·加菲尔德.引文索引法的理论及应用[M].侯汉清,等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53.
[24] 张耀铭.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其治理[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6):73-88+190-191.
[25] 田贤鹏.高校教师学术代表作制评价实施:动因、挑战与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20(02):85-91.
[26] [英]迈克尔·吉本斯,卡米耶·利摩日,黑尔佳·诺沃提尼,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陈洪捷,沈文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1.
[27] 张泳,张焱.多元下的统一——关于高校教师分类发展的探讨[J].江苏高教,2018(12):82-86.
[28] 沈红,王建慧.一流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院系责任——基于四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实地调研[J].教育研究,2017(11):130-139.
[29] 李立國,赵阔.超越“五唯”的学术评价制度:从后果逻辑到正当性逻辑[J].大学教育科学,2020(06):4-7+15.
[30] [德]马克斯·韦伯.韦伯论大学[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7.
[31] 王亦君.北大一博士被撤销学位诉母校终审胜诉[N].中国青年报,2017-07-27(06).
[32] 李剑鸣.自律的学术共同体与合理的学术评价[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4):73-78.
[33] 陈孝禅.一个现代大学的理想[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89(02):33-42.
[34] 张斌.我国学术共同体运行的现状、问题与变革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12(11):9-12.
[35] 郭为禄,林炊利.美国大学评议会的运行模式[J].全球教育展望,2012(04):67-72.
[36] 姚荣.激活学术心脏地带:中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自治如何走向制度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02):72-79.
[37] Pelz D C,Andrews F M.Scientists in Organizations:Productive Climate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6:21.
[38] 杨玉圣.高校学术评价“去SCI化”评议——论大学问题及其治理(之三)[J].社会科学论坛,2010(09):55-68.
Logic, Dilemma and Path of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Reform of University Teache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Community
ZHANG Xi-lin
Abstract: Acade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is considered as the cor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which can not only directly guide and regulate the academic behavior of college teachers, but also affect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innov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even human society. Fundamentally, academic evalua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is a complex academic activity rather than a simple management activity, but the current evaluation mechanism has shown excessive quantitative, simplific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tendency due to the strong thought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herefore,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community, it involves unique value to re-understand the logic of power operation,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and procedural regulations of teachers' academic evalu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evaluation mechanism.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many problems caused by the interweaving of multiple powers are destroying the subjective status of academic community in academic evaluation, such as the unclear subject boundary, the lack of full respect for the law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novation, the instability of institutional norms based on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he lack of credibility of evaluation results caused by rent-seeking in academic rela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acade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ecology based on procedural justice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law on the basis of separation of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operation, so as to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subjective function of academic community.
Key words: academic community; university teachers; acade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責任编辑 黄建新)
收稿日期:2020-11-04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破五唯背景下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机制变革研究”(2020SJZDA106)。
作者简介:张曦琳(1992-),女,山东德州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政策研究;上海,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