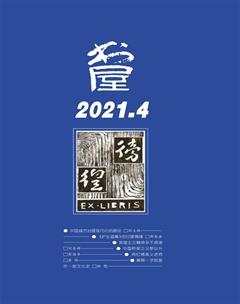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祖慰(以下简称祖):冯教授,您这部刚杀青的《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当属概念史论著吧?我检索相关资料,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发生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即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讨论中涉及的一个工具性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接着,德、英、法的史学界开始跟进,他们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启迪,认为语言不仅是思维和交流的工具,语言中的“概念”还像出土文物和史上典籍一样,同样是历史积淀的载体。于是,史学家开始通过对语言中那些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的形成、演变、运用及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来揭示历史变迁的特征。由于他们认为历史沉淀于语言的概念中,于是就诞生了从概念史入手的新史学。我想询问,这些来自西学的理论与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如训诂学)是否有相似性?您是何时发现并运用这种新史学方法论的?又是如何与训诂学一类中国传统学术相贯通的?
冯天瑜(以下简称冯):我步入概念史领域,主要受传统的考据学引导,中晚年方涉猎西欧学者“语言学转向”的前卫论著(如福柯的《词与物》之类)。
少时从先父庭训中略知许慎《说文解字》的释字方法,又时常翻阅俞正燮《癸巳类稿》等考据学书籍,养成逢重要字词便考证一番的习惯。之后,尤其服膺清人戴震“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之说,更从近人王国维倡导“新语”之论、陈寅恪“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诸教言中获得启示,故从1980年治文化史之始,每涉论题,必先辨析关键概念的来龙去脉,以使运思网络获得较为坚实可靠的纽结(这一点又受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影响)。壮年期习作《明清文化史散论》(1984)、《中华文化史》(1990)、《中华元典精神》(1994),已对“中华”、“文化”、“文明”、“封建”、“民主”、“自由”、“共和”、“经籍”、“元典”等概念的古今演绎、中外对接加以探究。世纪之交的十年间(1996—2006),应邀赴日本讲学、访学,结识谷川道雄、沟口雄三、梅原猛等日本史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又与史有为、方维规、孙江、陈立卫等从事概念史推介的旅外华人学者交游,同时还浏览日本出版的几十种“一个词一本书”的“口袋书”,领悟概念史研究在汉字文化圈的具体操作方法,将其运用于汉字文化诸术语的实证考析,遂有《新语探源》(2004)、《“封建”考论》(2006)的撰写,注意于核心概念在中—西—日之间的迁徙与互动,后书还致力于概念的纠谬反正。
总之,我进入概念史研究领域,导因于中—西—日学术的综合影响,而中国近古、近代学术的启迪是基本的,西学则引发探究概念史的自觉意识,而现代日本学术起到中介作用。
祖:《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區分“普通词”与“关键词”,界定曰:“基本词汇数少而质高,在语言的意义链中位居枢纽,表达文本要旨,可称之‘关键词(Keywords)。”请问,如何选出“中国、文化、社会、民主、革命、物理”等三十个词,并确定其为“位居意义链枢纽、能表达文本要旨”的呢?
冯:这又回到刚才说的文化史研究了。做文化史有一入口,那就是把握在文化史演进中所形成的一些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物化为“关键词”。透过“关键词”演绎这一窗口,可以看到历史与文化的场景。
祖:这就是说,“关键词”是历史选择出来的。我从尊著中读到,在文化史演进中,尤其在变法、革命期间,必然会催生出一批新的概念词来表述历史内容的更化。还有一种情况是,当外来文化进入,如中古时印度佛教传入,又如近古及近代西方宗教、科技、人文传入,还有留日学生带回日本在消化西方文化时参照汉语古典义对译出的新概念词等,也在催生汉语相对应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词成为语言的枢纽,能夠表达变革时期的文化要旨。正因为这个历史选择机制,才能在关键词中揭示历史的变迁。我这么理解对吗?
冯:这么理解很对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字义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也是世界上很早的字典之一,收入并诠释达一万多个字(词)。《尔雅》则是最早的训诂学论著。训诂学研究古书中的词义,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先父的老师黄侃先生创发了近代性的训诂学。可以把“章黄学派”看作中国概念史研究的前导。
受戴震与王国维、陈寅恪的启迪,我在研习中国文化史的过程中,隐约步入概念史的实体研究,通过辨析若干关键词,进入这一新的史学领域。应当说,我做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准备并不完备,尤其对西欧新创的概念史理论未作深入研习,只是观其大要,主要用力于做一些关键词的个案研究,试图由斑窥豹,但远未达成对概念史的系统把握。
祖:我在南京大学教授李里峰的《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读到下面一段文字:
冯天瑜是较早实践概念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其代表作《“封建”考论》、《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也是国内较早的略具概念史色彩的著作。《“封建”考论》以中国历史为线索,对“封建”一词作概念史的考察与探究,分析这一词语的本义(古义)、西义(世界通用义)以及马克思的封建原论、现代中国的“泛化封建观”,试图为聚讼未决的中国历史分期提出新的观察视角和较精确的概念坐标。由于“封建”概念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此书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一再重版。冯天瑜的其他研究还涉及“革命”、“共和”、“经济”、“科学”、“人民”、“社会”、“自由”等概念在近代的流变过程。
您的概念史研究走了一条自己的路,您认为应当如何开辟中国的概念史发展路径?
冯:《“封建”考论》是2004—2005年在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完成的。此书以很大篇幅回顾近现代史学家的“封建论”,从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张荫麟、李剑农等,一直到晚近的吴于廑、齐思和等,这些史学家或对封建制度有正面阐述,或对泛化封建论提出质疑,均言之凿凿。我只是往前走了一大步。
祖:我在巴黎当过十二年记者,发现在采访人文学科讨论会时无法进行合乎逻辑的讨论,居然在同一概念下违反同一律而吵得不可开交。我很困惑。后来读十九世纪研究人类自由史的英国阿克顿(Lord Acton)勋爵的论著,他收集到两百多个关于“自由”的定义,我忽然开悟:人类的语言为记忆节能,不愿造太多新词,就在旧瓶里不断装新酒,即不断地对老概念进行新的界定,千年万年积累下来,几乎日常语言(自然语言)中每个概念都有几百个定义,充满歧义。人文学者们企图对自己使用的概念进行严格界定,但是根本做不到。因为,定义一个概念要使用两个概念——一个属概念、一个类概念,而这两个概念又充满歧义,需要先对所用属概念、类概念进行定义……如此无穷定义下去,永远不能得到一个如自然科学用数学定义的无歧义概念。当一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都不确定,就满足不了逻辑学三段论的要求,因此,所有人文学科的推理成了伪推理。这就导致了把自然语言作为符号体系的人文学科不能得到无歧义的结论。我想问:概念史用的恰恰是自然语言的概念,充满歧义,那么由概念史开掘出来的文化史,会不会是不能合乎逻辑的一团乱码?
冯:概念史研究的是概念在历史演进中的不断变化,也就是您说的旧瓶装新酒的各种新义。换言之,概念史研究的对象就是概念的歧义。通过概念在历史演进中的歧义,寻找所对应的历史。因此,它不是逻辑学的三段论推理,也就不会产生人文学科推理的不确定性。按照概念史开创者的说法,概念史询问的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由谁、为了谁、出于何种目的或者哪种形势、如何进行定义。故,词义的演化既是在自然语言环境中进行的,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社会的因素影响,而且这种非自然的影响力在日益强化。
就拿您刚才谈到的阿克顿搜集到的有两百多个定义的“自由”概念作例,讨论上述问题。
“自由”在古汉语中是“自”与“由”两语素组成的主谓结构名词。“自”与“由”组合成“自由”一词,兼纳“自”的自我义,“由”的不受限制义,合为“由于自己、不由外力”之义。在汉字文化圈,“自由”的古典义为“任意、随意、自恣、自专”,与“限制、制约、约束”相对应。古汉语中的“自由”,使人联想到的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式的旷达与洒脱,孟子称之“自得”,庄子称之“自是”、“自善”,佛家谓之“得大自在”。在重礼教规范的史典中,“自由”多作为一个消极的贬义词使用,而在文学作品中则往往表述“放达”、“逍遥”境界。
祖:“自由”含义的这种状态,大体是在自然语言中演进的。那么,“自由”含义如何在非自然的情形下发生改变呢?
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合作,推动东、西方自由观交汇和反映自由观的语词的译制。十九世纪入华的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合作者发展此一译事,把西方积累的多义的“自由”用“自主”、“自在”等多种译词翻译过来。
近代日本,将“自由”逐渐从含有“放任、自恣、自专”义的生活用语,通过对译西洋概念,演为近代政治术语及哲学术语。留日人士将译有西义的“自由”带回中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梁启超等在一些具有启蒙思想倾向的书刊竞相从积极、进步义上使用“自由”一词,以与专制主义相拮抗。这期间,严复创“自繇”一词来代替“自由”,以防范“自由”根据古义而走向放任,可谓用心良苦,既表明严复对西方自由主义真谛的把握,也显示出他对中国容易从专制主义极端走向放任主义极端的担心。但他所制作的“自繇”一词并未得到社会认可,因其笔画繁复,含义隐晦,又有生造之嫌,无法推广,故后来流行的仍然是“自由”一词。到新文化运动,李大钊宣示“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须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胡适将“自由”诠释为“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
被称“五四之子”的殷海光,是自由主义的发挥者,他将“自由的神髓”概括为:“个人必须依其良心的指导而自由行动,这种自由行动以不侵犯别人的相等权利为界限。”殷海光还特别强调自由经济,认为“一旦经济自由不存在,便不能有任何自由”。
总之,“自由”在中国,由于概念义的不断嬗变,导引着与此相关的文化史的变迁。古典汉字词“自由”意谓放任、自恣、自纵,此义至今仍在使用。而近代义的“自由”,是有约束的、理性的自由,在政治上是指受法治制约的公民自由权,观念上是指基于自身主动意志的思想自由,法律上是指在不违法前提下的行为自由,伦理上是指在道德自律前提下的操守自由。这种自由观日益深入人心,逐渐被大众所认可和实行。这是中西语汇涵化的结果,而“自由”一词正通过这种涵化获得共识的现代性,并成为思想和行为的准绳。
祖:我在您《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书中的“名实错位”一章读到,您批评现代汉语在翻译西方经济學、哲学术语时,将古典汉语词的名实错位了,例如“经济”,还有“形而上学”。我想问: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他把语言符号的“能指”(声音、文字)认定是随意的约定俗成,即一个概念名称是群体约定俗成的自由选择,例如汉语把用羽翼飞翔的动物称作“鸟”,而英语的能指是“bird”。但其概念的内涵、即“所指”是一致的,否则就不能进行跨语言的交流。那么“经济”这个概念,其“能指”可以确定任何一个新名称,也可以在古汉语中找出“经济”现成名称,只要大家约定俗成就行了,您为什么认为是一种概念命名的病态呢?
冯:你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个人以为,概念演绎过程发生偏误是常见现象。如果词义偏误已经约定俗成,又无重大危害,可以任其自然演化,不必人为干预,但在适当场合,须作必要说明(如“经济”、“形而上学”等关键词可这样对待)。若导致路向性失误,造成严重学术紊乱,则又当别论。如流行大半个世纪的泛化“封建”,既有悖古义(贵族分权政治、世袭领主经济),亦有悖西义和马克思的封建原论。因“封建”的误用,造成中国历史分期陷入混乱,侯外庐先生称“封建”语用之误导致“语乱天下”,钱穆先生称之“削足适履”。对于这样的案例,便有纠谬反正的必要。拙著《新语探源》、《“封建”考论》已有详论,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