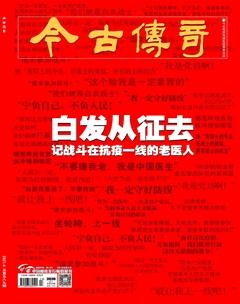张和武:武汉市感染新冠肺炎后返岗的最高龄医务工作者
每周五,是武汉肺科医院结核病区疑难病例大讨论的时间。2020年8月的一个上午,张和武查完房之后,回到医生办公室。一群年轻的医生将他围在中间,从身边的影像袋里抽出一张张胸片,等待答疑。有时是一早上,有时是一整天,视疑难病例的数量而定。一问一答,旁人都在仔细聆听,偶尔有笔尖沙沙摩擦纸张的声音。
此时,距离他在抗疫一线罹患新冠病毒肺炎康复出院还不到一个月。
“我根本不想退休”
张和武是武汉肺科医院教授、中国防痨界知名专家,曾获第九届“中国医师奖”。1958年到武汉市肺科医院工作,2003年退休后,随即被医院返聘。从2003年返聘到2020年抗疫,退休后的张和武又在武汉市肺科医院工作了17年,加上之前,他在武汉肺科医院工作了62年。
“其实很多年来,我的生活一直像一个学生一样。我每天6点起床,下楼运动到7点,7点半吃完早点,8点会准时赶到单位,中午休息1个小时后继续上班,晚上5点再去运动1个小时,下班回家吃完饭就看书睡觉。”张和武说,“50岁的我,和如今80多岁的我,工作的内容和强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张和武对自己近乎严苛。刚进医院时,有个老医生提到,呼吸科的医生一定要学会“看片子”,一个医生起码要看2000张胸片,才能达到主治医生水平。
“在那个年代,主治已经是最高水平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和武每天都抱来100多张胸片,同时把市面上能买到的有关胸部X线学的书籍都买来,比对着肺叶等部位認真钻研,然后提出自己的诊断。
他每晚都研究到半夜。渐渐地,他能发现其他医生诊断中存在的问题。一月后,他已经看完了3000多张胸片。当时医院规定,新来的医生必须由资历老的医生带教实习半年才能上岗,但因为张和武的“经验”丰富,主任允许他独立问诊。
从医60余年,张和武一直从事肺部疾病及结核病临床和科研工作。2006年,武汉市启动全球基金耐多药结核病项目,张和武不顾耐多药结核病的治疗复杂、传染性强,也不顾自己年近七旬,主动请缨,承担起诊疗组专家一职。在全世界耐多药结核平均治愈率仅50%的情况下,张和武团队的治愈率达到70%,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武汉也成为耐多药结核病防治全国示范区。
谈及张和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分会主委李亮曾用六个字形容:“一生兢兢业业。”2017年,张和武获结核病防治终身成就奖,那时他是湖北省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专家。
熟悉张和武的医生都说:“光是到他办公室看看,你就能感受到张教授对自己的那股‘狠劲。”
张和武的办公室,位于医院内的一栋老建筑里,面积不大,除开书桌上张和武与孙子的照片,其他地方堆满了书,“我这人没有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最大的花销就是买书、看书”,张和武说,光是买学术杂志,一年就要花几万块钱。
砖头厚的学术专著,张和武每年都会重新看一遍,“一些年轻医生问我,为什么我什么都记得住?我告诉他们,诀窍只有一个,就是一遍一遍地看”。
张和武的老伴早些年离开了,儿子是大学教授,平时工作也非常忙,张和武多年来一直一个人住。
从办公室到家,距离不过百米,张和武的一生,多数时间都在这个圈子里转。同事、病人、学术,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我做了62年的临床医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病看好。”2020年接受采访时,张和武说,临床医生需要针对患者情况做出精确诊断,并进行合理的治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不断学习。“医学是一门不完善的科学,需要不断学习加深认识。如果只是通过工作积累经验,许多病症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如果不学习,疑难杂症永远都诊断不出来。”
他还说:“我的志向是做武汉最高龄的临床医生。我根本不想退休,我觉得退休之后才会老得快,即使之后身体不允许每天查房,也希望自己能够在门诊工作。”
新冠疫情击倒老专家,趁着清醒,张和武立了一份遗嘱
别看张和武个头不高,又是八旬老人,但他是健身达人,每天晨跑5公里,经常在运动场上耍双杠、练倒立。爬山、走路从来不输年轻人。
“我身高不到1米6,但状态好的时候,百米成绩在12秒左右”,张和武说,晨跑之后,他还会做双杠训练和倒立训练等,每天保持晨练1个多小时,再回家洗漱、上班,“连大年初一下大雪,我都没有终止过”。“也是因为身体一直很棒,所以这次大意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张和武与全院医护人员一样,投身在忙碌的战疫一线。参与院内查房、会诊,出席院外专家讨论……2020年1月20日,他感觉有些不舒服,但他自认为身体强壮,便没太放在心上。“身为一个呼吸科的医生,我一直严格地佩戴口罩,我负责的患者也都会佩戴口罩,会诊回来后,我就感觉到了一些症状,但是因为还有工作,症状也并不严重,就一直坚持上班。”
直到1月25日,张和武才抽空去做了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肺部已感染,必须住院治疗。张和武从医生转变成了患者,“确诊之后的第二天,我的病情忽然间就严重了,并且伴有呼吸衰竭”。
住进医院没几天工夫,张和武就因为肺部发生炎症风暴,全身只有嘴能动一下,“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痛苦”。
临床分型上,张和武属于重症病例。武汉市肺科医院耐多药结核病区副主任杜鹃是张和武的学生,也是他的主治医师。病程初期,杜鹃和团队曾想过将老师送进ICU插管,但被拒绝了,“他说自己80多岁了,知道我们工作量非常大,也知道医疗资源非常稀缺,不肯进ICU”。
肺科医院是武汉当地最早收治新冠肺炎的三家定点医院之一,这里的ICU曾经收治了全武汉病情最重的81名新冠肺炎患者。除此之外,肺科医院还承担着院外的3000多名结核病患者的治疗重任。即便是疫情最严峻的时刻,仍然有20多名结核病重症患者在此救治。张和武的顾虑也来源于此。
趁着清醒,张和武立了一份遗嘱,“如果出现昏迷,不上呼吸机,也不要抢救,把资源留给需要的人”。遗嘱中,每一位给予他帮助的人,他都进行了妥善安排,包括之前照料他起居的护工。
3个月时间,82岁的张和武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张和武不知道的是,武汉肺科医院的医护们背着他达成共识,“不惜一切代价治疗张教授”,因为“救起了张老,就能救更多的人”。
“他(指张和武)一直是我们的精神领袖。”武汉市肺科医院结核一病区主任朱琦也是张和武的学生,看着老师躺在病床上,医院上下都心急如焚:“当时没有特效药,只能对症治疗。但是病毒治疗的药物也就那么几种,并不是每一种都有很好的效果……老师还主动申请参与了针对新冠肺炎治疗的新药临床试验。”
一有新的方案、方法,他会要求在自己身上尝试
在医护人员的抢救下,张和武的病情慢慢好转。病情稳定住之后,他变成了病房里最忙的患者。
朱琦回忆,3月初,老师度过了最难熬的时间,病情有所好转,他甚至可以起身,写一点儿东西了。“然后他开始每天给自己写病历”,记录病情、数据变化、诊断经验。同时,要求医生将国际上关于新冠病毒诊疗的学术内容,通过微信发给他。
“今天是我住院的第46天。护士照顾我的时候总参(打)瞌睡。因为他们值班太频繁,真是辛苦他们了。我非常难受,是我拖累了他们。我很想感谢他们,但感谢也减轻不了他们的疲劳,我希望我的病情好转,生活能够自理,就不需要麻烦他们了……”这是张和武写在自诊病历上的一段话。自诊病历从3月4日起开始记录,这是他住院的第39天。
张和武坦言,新冠病毒“蛮狠的”,“那时候刚刚好转,想发条微信,手抖得字都打不完,也不能看书。”那段日子,他只能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每天记录自己患病的情况和感受。在每个日期之后,张和武还会记录上当天照顾自己的医护名字。
张和武手写会诊、查房记录的习惯,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记录了上百本。他是个严谨的人,“对每一个患者负责,这些信息靠脑袋记不住,记在本子上,方便随时翻阅”。
“等医生去查房时,张老会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心得”,朱琦说,张和武常跟大家一起讨论救治方案,一有新的方案、方法,他会要求在自己身上尝试。
张和武说,“这次生病,是我学术人生最难得的一次经历”。
2020年4月下旬,张和武和最后一批新冠肺炎患者一起陆续核酸转阴,亲历了武汉首次“患者清零”。进入康复期治疗后,他每天坚持做呼吸训练,结合走路、爬楼梯等方式,加速肺功能恢复。到了6月中旬,他已经可以完全脱离氧气辅助。
还没有正式出院的张和武又穿上了心爱的白大褂
出院后,张和武明显感觉身体差了很多,不能进行过去那样大负荷的训练。但他并不气馁,很快调整出了新的康复训练方案。
“生病后,都需要康复训练的”,张和武说,他看很多新冠病人出院后,身体状况不好,精神也垮了,“希望大家振作起来,身体和生活都会恢复的”。
调整训练方案后,张和武侧重呼吸、平衡、跳跃等训练,最后双手举12磅的哑铃30个以上,晨练结束。随着康复训练的进行,张和武的身体渐渐好轉,能做的训练也越来越多,“单腿平衡,我能做2分钟以上了……再等几个月,我就能恢复到6点起床”。
7月1日,张和武要求重返工作岗位,并回到门诊工作,医院为了保护老教授的身体,委婉拒绝了。但张和武依然坚持要求参与到一线病人的诊治中。
那天,还没有正式出院的张和武又穿上了心爱的白大褂。他笑着说:“这次感染新冠病毒住院,是我工作以来‘请假时间最长的一次。”
为了方便工作,他还住在病房里。休息时,他就把床当书桌用。病床上放着满满的文献资料。
每个工作日,他都会和同事们一起,问诊疑难病人。“我们会筛选一些病情特殊的患者,让老教授进行面诊”,朱琦说,“看完病后,张教授会和科室所有医生一起,看片、看资料,讨论诊疗方案”。
张和武康复返岗归来时,已是盛夏。这次经历,让他成为武汉市感染新冠肺炎后返岗的最高龄医务工作者。身为医生,也成了患者,见识了疫情暴发的凶猛,也见证了患者清零的喜悦……“这半年我思考了很多。我想,唯有工作是最好的感恩方式。”
“张老师少年时,一边在布店打工一边学习。年轻的时候被推举参加举重,获省冠军、全国第六名。”朱琦说,后来他成为中国防痨界的知名专家,获中国医师奖,桃李遍天下;他自己省吃俭用,锻炼穿的白背心不烂就不换,却总给困难患者塞红包、给学生买医书,他一直说最大的愿望和幸福就是想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朱琦心里,他是一个自己虽然都82岁了,但听诊器总是先捂热,再放在病人身上的老人。
(责编/陈小婷 责校/闻立 来源/《武汉最高龄!82岁医生感染新冠后康复返岗》,陈凌燕、王敏、张全录/文,《楚天都市报》2020年7月2日;《武汉感染新冠的82岁医生出诊了:总是把听诊器捂热,再放病人身上》,张赫、王艾冰/文,《健康时报》2020年7月3日;《82岁医生感染新冠,治疗6个月后,又回到了临床……》,杨飏/文,《潇湘晨报》2020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