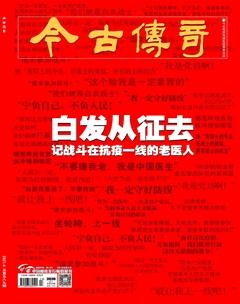张金哲:从“白大褂哥哥”到“白胡子爷爷”
北京儿童医院,每个周一和周四清晨,一位百岁老人都会从人流如梭的门诊大厅穿过,来到外科门诊。他清瘦高挑、白衣笔挺,口袋里永远装着一个诊疗时用的小耳镜,那是他“变魔术”的道具。这位老人就是张金哲,中国小儿外科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中国小儿外科之父”、北京儿童医院的“镇院宝藏”。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张金哲特意写了一幅带哲理的书法:“新冠肺炎,抗疫必胜。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科学政策。”落款:“百岁儿医张金哲。”医院决定不再让张金哲出门诊,老人心里有点不情愿,但他尊重医院的决定。不过,在他的要求下,医院把他的常规工作简化,改成每周三上午去一次医院查房。100岁的老人走在查房队伍的最前面,旁边的学生下意识地伸手去搀扶他,张金哲摆摆手:“不用搀,我能走。”
2020年9月25日,是张金哲的100岁生日。我国小儿外科界一场温馨又隆重的学术“生日趴”在北京举行,张金哲院士学术思想研讨会暨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第十六次全国小儿外科学术年会开幕。在这次学术年会上,百岁华诞的张金哲再次获得三项荣誉——“儿科巨人奖”“终身奉献奖”和“大医精诚”匾额。这三项荣誉意在表彰对张金哲为我国小儿外科作出的突出贡献,并向他敬业奉献、求真务实、勇攀高峰的精神表达敬意,号召医生学习他的楷模风范。
女儿成为他进行“新生儿皮下坏疽”手术的第一个病例
中国自古就有“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莫医一小儿”之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还没有一家正规的儿童医院,更不用说小儿外科了。讲到自己做了一辈子儿科大夫,张金哲说:“我的经历让我有坚实的信念和思想基础。”
1920年9月25日,张金哲出生于天津宁河县(今宁河区)寨上庄,并在宁河顺利完成小学与中学教育。张金哲考大学是在国难当头的1937年,他被迫从河北省立一中转入天津租界内的耀华中学备考。这期间,他经历了轰炸、校长赵天麟上班路上被枪杀等各种血腥事件,郁积了一腔愤懑。
京津两地当时只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及天津工商大学这三所西方国家承办的大学还在招生。他分别报考了这三所大学的医学、美术、建筑三个方向不同的专业。在燕京大学的国文考场上,张金哲引经据典,挥笔写下《良医良相》一文,表达了一个17岁的青年乱世之中思报国,“宁为良医,不为良相”的志向和意愿。
三所大学同时录取了张金哲,他选择读燕京大学的“特别生物系”学医。那是协和医学院委托办的预科。这是他人生第一次重要抉择。
经过严苛的淘汰,1941年,入学时71人的班级,只有16名优秀学生升入协和医学院。张金哲是其中之一。
可没过几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关闭,全体学生被强迫编入当时由日本人控制的北大。张金哲拒绝进入日本人的学校上学,后来听说自己在日军黑名单中,1942年大年初二他连夜只身逃往上海,转至上海圣约翰大学。次年,圣约翰大学也被日本人接管,张金哲愤而转考上海医学院,在颠沛和转插班中完成学业。
这期间,张金哲借住在一个远房亲戚家,医院里没有儿科,亲戚同事们的孩子有了病,就请他帮忙治疗。从那时起,张金哲就深深感受到孩子得了病,父母们比自己生病还要难过。但那时候无论是处在战乱中的中国,还是像日本这样相对发达的国家,都没有儿科,很多孩子得了病根本无法治疗。
1945年抗战胜利,张金哲回到北平,在中和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前身)任外科实习医师。有一天,张金哲在医院值班,恰逢他的一位中学老师带着未满一周岁的女儿来求医。孩子患的是白喉,这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张金哲知道,治疗这种病要做气管切开手术,但他刚毕业,做不了这项手术,于是请示上级大夫。大夫告诉他,没有人给小孩做过气管切开,医院也没有适合孩子手术用的器械。最后,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张金哲。“这明摆着是能治的病,结果就因为没人做过,没有设备,孩子就这样死了。”张金哲痛惜地回忆道。他一直记得,老师抱着孩子离开时,一句话也没有说。
3年后,一种后来被命名为“新生儿皮下坏疽”的传染病席卷了全国各地的产房,感染的患儿死亡率高达100%。那时,张金哲已升任总住院医师,每个病例都要经他拍板,他亲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孩子刚出生不久后就死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这时,他开始查阅大量资料,通过研究分析,大胆提出在感染大面积扩散前将婴儿的患处切开,放出脓血以缓解病情。他的建议得到病理科同事的支持,却遭到临床大夫们的一致反对:中医讲“熟透”了才能开刀,西医讲“圈住”了,不再扩散才能开刀,而张金哲的想法无论中西医都不能认同。
1948年8月,张金哲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尽管一出生就立即出院,但还是未能幸免地感染了“新生儿皮下坏疽”。张金哲当机立断,来不及和妻子商量,就拿起手术刀亲自给女儿按照自己的设想做了手术。“看得太多,我知道,不切这一刀,她必死无疑。这种情况,我也不用再请示谁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孤注一掷。”
没想到,张金哲的女儿成为全国“新生儿皮下坏疽”手术后成活的第一个病例,也成为他进行小儿外科手术的第一个创举。后来,张金哲又用同样的方法成功治疗了几名患儿。很快,他的办法不胫而走,在全国得到推广,使“新生儿皮下坏疽”的死亡率迅速下降至10%,而后又降到5%。
28岁,已在行业内崭露头角,张金哲却心有不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隆隆炮声中,他在思考该怎样以一个医者的良心和使命参与建设新中国。长期受“耀华”“燕京”“协和”等西式教育熏陶的张金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脚步中逐渐完成思想洗礼。
张金哲在中央人民医院挂出了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门诊的牌子
1950年7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代表大会在京召开,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向时任中央人民医院院长胡传揆提出:“能不能支援我们一个外科大夫?”胡传揆指着当时恰好站在他身旁的张金哲笑著说:“你看他怎么样?”诸福棠询问张金哲的意愿,那时专攻小儿外科已成为张金哲的心愿,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不久,张金哲在中央人民医院挂出了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门诊的牌子。那是名副其实的白手起家,一切归零,手里仅有从小儿内科病房分出来的5张床和一本书——儿科主任秦振庭从美国带回的《小儿腹部外科学》。
没有诊断和手术用的器械,何来小儿外科?可那正是西方“卡脖子”的时期,没有什么条件是可以坐等来的。
好在动手创造是张金哲的强项。幼年时他就喜欢蹲在木工身后一看半天。燕大重能力培养的实验教学,养成了他手脑并用的习惯,具有极强的应变实操能力,当年学校话剧队幕后的电闪雷鸣等特效,全是他一个人鼓捣。
这次,他索性在自己家里开“作坊”,动手自制和改良儿童诊断及手术器械。这个能讲一口流利英文的西医才俊,竟然白天上班,晚上做工,变成刨锯凿切全能的小工匠。
可是,让张金哲没想到的是,他遭遇的第一个真正的困难不是疑难杂症,而是没有病人,甚至连挂号的人都没有,因为那时还没人知道有个小儿外科。
就在张金哲快要坚持不下去时,一个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孩子,让他把差点关张的诊室坚定地开了下去。起因是有名产妇生下了一个脑袋后面长着一个比脑袋还大的“球”的婴儿,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呼吸,被扔进了垃圾桶。清洁员看到后,把孩子送到了张金哲的小儿外科。张金哲立即为孩子实施切除手术,孩子后来恢复得很好。“外面说我能起死回生,能切‘大脑袋,其实,手术很简单,这件事情被宣传后,开始有病人来了。”张金哲回忆道。
在抗美援朝期间,张金哲作为手术队队长,两次赴朝,立了两次大功。特别是部队缴获了大量美国的麻醉机和气管插管,前方急需却无人会用,张金哲就地自编讲义,开办麻醉培训班,以精湛的专业优势培养了第一代部队麻醉师。他那些讲义经改编,成为我国最早的麻醉学专著《实用麻醉学》。
1955年,张金哲调任新建的北京儿童医院外科主任,该科设15张病床,两间手术室,这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小儿外科中心了。当时,小儿手术死亡率超过30%,而成年人的手术死亡率仅为4%至5%。张金哲认为,这说明我们的手术技术没有问题,关键在于没有专门从事、钻研小儿外科手术的医生。
要给孩子做手术,首要解决的问题是麻醉。当时我国麻醉水平严重滞后,拖了小儿外科的后腿。经过摸索,张金哲和麻醉专家谢荣合作首创了肌肉注射基础麻醉加局部麻醉的方法,同时还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婴幼儿特点的检查和诊断方法,发明了一系列适合小儿外科手术用的医疗器械。
据统计,先后有50多项发明在张金哲家的“小作坊”里诞生,其中包括后来被国际同行广为称道的用于巨结肠手术治疗的“张氏环钳”、使无肛门手术避免开腹的“张氏膜”、胆道再造手术防返流的“张氏瓣”等原始用具模型。这些发明中有不少在全国免费推广,还有一些至今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被广泛应用。“外科是要动手的,白求恩都说了,外科医生至少是个木匠。”张金哲经常强调,要当好小儿外科医生,务必手脑并用。
2000年,张金哲在意大利获颁被视为国际小儿外科界最高荣誉的英国皇家医学会“丹尼斯·布朗”金奖,理由是:“他代表了中国13亿人口大国儿科医生的技术水平”,他的“张氏环钳”“张氏瓣”“张氏膜”等发明,丰富了国际小儿外科技术。
2010年,张金哲又荣获世界小儿外科学会联合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在张金哲等儿科专家的带领下,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外科到现在已拥有肿瘤、泌尿、骨科、整形外科、心脏外科、胸外科、神经外科及新生儿外科等十几个专业。中国小儿外科从零起步,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在国际小儿外科界拥有了话语权。
“我们都讲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要交给老百姓才是力量”
除了钻研医疗专业技术,张金哲还特别重视科普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时期起,他就开始从事科普宣传。起初,他是为了提高老百姓对医学,特别是创伤的认识。此后,张金哲就发现科普很重要。他一直记得周恩来的一句话:“我们都讲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要交给老百姓才是力量。”
张金哲把科普工作列为自己工作的重点之一,他认为医药卫生知识是群众最关心的,医生看病在三五分钟内把病给患儿家长讲清楚,就是最好的科普;把常与患儿家长谈的话,印成材料就是科普读物;患儿或家长理解了再给别人讲,比医生讲更有效;一个好医生必须钻研如何给不同人群讲病,病人听懂、爱听就是好科普。
他以身作则,先是以个人身份在报刊及电台宣传一些儿科和儿外科常见病知识,后来主编《小儿常见病问答》《小儿家庭急救事典》等著作。
在担任北京市科普作协及全国科普作协理事期间,他积极致力于医学科普组织工作,编写各种科普著作,组织并推动中青年人参加科普写作,除此还参与了科普电影、电视台广播等方面的科普制作,受到各方好评。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儿童医院还曾定期出版专门的科普小册子,效果良好。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科普作者,活跃在科普阵地上,有些还作为主编出版了科普专著。张金哲1964年至1986年任中华医学会科普委员会副主委,在专业杂志上特辟科普专栏,宣传普及小儿外科知识。鉴于多年来他在科普工作方面的贡献,1991年被全国科协授予“突出贡献科普作家”称号。
除了编写科普读物外,张金哲还认为应该在平时的工作中融合科普教育。2002年以前,张金哲一直住在医院内的宿舍,夜间常到病房看看,和家长聊聊,谈谈孩子的病,尽量讲透讲深,病人家长非常爱听。在长途车上,他只要讲病,立刻成为车厢中谈话的中心人物。他的想法是,希望让家长多知道一些医学知识,而家长医学知识的普及必然有益于孩子的健康,这才是科普的力量。
“做医生最大的医德,就是尽心尽力把病人的病治好”
80岁以后的20年中没离过岗,这是张金哲漫漫人生中最“牛”的地方。到医院查房、出门诊已经是他的一种生命状态。
“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要干活。人要是不干活,就算活着也没意思。”虽然张金哲年事已高,院方也曾多次劝他休息,但他仍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患者。除门诊外,他还会到病房查房,和年轻大夫讨论业务。他说:“很多病人看了很久、轉了那么多医院,看到我这一头白发的老头儿,总还能比较信任。我不想闲下来,工作让我长寿。”
2020年8月以来,张金哲来北京儿童医院约见较多的人是他曾经的博士生、小儿肿瘤外科主任王焕民。前些时候还约见贾立群——也是名扬全国的新闻人物、B超达人。
同样退而不能休的晚辈贾立群如今也已67岁了。他说张金哲让他仰视了一辈子,至今见他还是诚惶诚恐。他说那天一进屋,“老人家先从沙发上站起身,迎上握住我的手”,让他一时手足无措。100岁的张金哲思维依然机敏,“见面谈业务常用英文。大概是因为表达准确,好在我还能接得住”。贾立群说老人的工作标准极高,细致、较真又讲方法,早在40多年前,他还在实习期的时候,就见识过先生的“查房艺术”。一次先生发现科里医生为患儿用的扩肛器型号不对,既要狠狠批评,又不能让当事人太尴尬,就加肢体语言幽了一默,逗得一屋子人哄堂大笑。
那次约贾立群的主要目的,是谈超声波疗法怎样更好地与小儿外科,尤其是小儿肿瘤外科合作,同步提升的问题。因为目前超声波已经发展到可以直接引导介入治疗,用射频消融对付实体肿瘤。但是与成人相比,小儿B超发展相对滞后。这是张金哲特别挂心的事。
“恶性实体肿瘤太凶险,弄不好就会拖垮一个家庭。只有不同学科方向的医者一起努力,才能提高治愈率,就是不能彻底治好带瘤生存,也要让孩子少受罪少花钱!”老人这番话言近旨远,语重心长,拉着贾立群的手始终未曾松开过。
王焕民是张金哲博士团队中的金牌“老三”。一次,他向张金哲通报2020年四季度全国小儿外科界两个重要会议的准备情况时,其线上线下结合的会议形式与老人不谋而合,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谈笑甚欢。只听老人爽朗地说:“我发言准备讲五点,但不会超过五分钟。”
王焕民笑称老人常常“约谈”他,这让同事朋友们有点儿酸,说“为什么老先生总是找你?你不能总‘吃偏食啊!可我这哪里是吃偏食,是老先生在不断给我压担子……”
王焕民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发展,任何杂症重疾,小儿普外都有法子从容应对了,唯独小儿恶性肿瘤还很难攻,这让老先生操心不已。”说话间,王焕民忽然想到了什么,转向张金哲:“对了,那个叫某某某的孩子,今天又来复诊了……”
他说的那个孩子是恶性母细胞瘤患者,瘤子很大,2019年12月在决定是否能手术的时候,大家还是心里没底,特意叫张金哲来参加会诊。科里摆出情况,等着张金哲一锤定音。这时他不疾不徐地说:“你们不要总盯着手术,盯着解剖……”大家面面相觑,难道张金哲否定手术方案了?往下听才恍悟:“我们除了要考虑手术治愈的可能性和细节,还要更多考虑术后恢复的预期和费用,替患儿家庭考虑考虑经济承受能力……”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想到老先生时没有太多年龄概念,大家遇到问题总习惯性地想知道‘老先生怎么说。这些年我们科的工作有些进步和起色,老先生所起的作用实实在在,他对我和团队的影响一直是非常直接而具体的,尤其是在医学人文的理念上。”王焕民强调。
“听贾立群说,您一见面就说自己的‘金手被他的B超废了?”一次接受采访时,张金哲被记者的问题问乐了,他立刻伸出的右手比画,手背光滑,并无色斑:“你看小孩子看病总会哭闹,那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手触:我在他们身上这样敲(用几个手指尖)那样敲(用指背骨)再这样敲(空芯手),小孩的反应和我手的感觉都不一样,马上可由此判断和区分病情病灶,被说成‘金手。类似的经验我都有总结,甚至用电脑做成了PPT。这些似乎都没用了,现在哪个门诊医生有疑惑不是直接开B超单?”
可任何时候,机器都不会完全取代人工。张金哲显然认同这一点,“相似的事情是,从《黄帝内经》出现,到隋唐时期的药王孙思邈,发展了1000多年,直到今天2000多年,什么时代谈中药的药理药性还是会追溯到《黄帝内经》那儿去,说明本质的东西不会变太多”。他的意思很明白:人性是机器无法替代的。
“医乃仁术”。其实张金哲心心念念的,是医生、护士、医学研究者怎样把工作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医学、医疗的人性化上。其实当年搞发明、炼“金手”、对付疑难症的各种手术新发明、合理高效开发使用病房病床……都是顾完孩子顾家长的至善之举。
由此可见,医学人文在张金哲的医学生涯中从来不是虚无的说教,而是他坚守的职业行为。
从医70多年,张金哲有一套自己琢磨出来的“接诊学”。比如手诊前先洗手,把手搓热再接触患者皮肤;至今每个病人进来,他都起身相迎,看完病起身相送。为了让病人一进门就知道是谁在为他看病,张金哲用醒目的字体在白大褂的左前胸描出“外科张金哲”5个字。每次换洗白大褂字迹模糊了,他就用签字笔重新再描一遍。他经常对年轻的医生们说:“病人把命都交给你了,你得让人家一进门就知道,他是把命交给了谁。”
在急诊,许多医生因为孩子哭闹无法触摸腹部而感到束手无策,张金哲经常化身为“会变魔术的白头发爷爷”,他白大褂的右口袋总是满满地装着小零食、小玩意儿,他变着小魔術边逗孩子边问诊。也因如此,他又被患儿和家长亲切地称为“宝藏爷爷”。
还有“三分钟口才”和“衣兜里飞出的小纸条”,前者是医患快速有效沟通的本领,后者说的“小纸条”是为小患者家属准备的,每条不过50字,扼要、通俗地释义一种常见病,不光是为了让对方弄个明白,有实物收获感,更是为了增效省时,看更多的病人。说白了就是肯花掉自己的时间,节省有限的诊疗时间,让患者得到更多。
直到90岁以后出诊,张金哲还会这么做。他认为医生首先要尊重患者,这是最重要的,成人世界是这样,儿童的世界也是这样。即使在他担任副院长、社会职务最多的时期,也是要求自己再忙也不能耽搁出门诊。实在不能出诊,必提前向已经约好的病人说明情况,更改日期。
“做医生最大的医德,就是尽心尽力把病人的病治好。”张金哲常对学生说,“好的儿科大夫必然是爱孩子的大夫。医生不管水平多高,永远是个服务者,既要从治疗方面为患者着想,也要从后期护理、经济承受能力等方面为患者考虑,用最简单的方法、最便宜的药治好患者的病,同时,多一点耐心,多一点解释。”
数十年来,张金哲解决了不少医学难题,为成千上万的婴幼儿成功实施手术,挽救了许多幼小的生命,使许多先天畸形的新生儿恢复正常,健康成长,并创造了小儿阑尾炎手术30年15000例无死亡、急性绞窄性肠梗阻包括坏死休克患儿连续100例无死亡的纪录。
“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
“没有奉献精神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具有奉献人生观的医生,治好一个病人就是最高的荣誉、快乐和享受。”张金哲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20世纪80年代初,他用自己的稿费在外科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基金,孩子治病钱不够,他就从基金里拿来凑。
他行医70余年,从未收过红包;他28年如一日利用周末到天津儿童医院义务出诊,没拿过一分钱,他说:“我支持的是儿童外科事业,要讲钱,谁也请不动我。”为了提高技术和治愈率,他不怕得罪人,曾让科室秘书设了一个“医疗不满意”登记……近些年,张金哲一直倡导要“让妈妈参与临床诊疗”,提出“多哄少碰、多教少替”的医患沟通八字方针。他始终关注如何做到外科无痛、如何减轻肿瘤患儿的负担和痛苦。
1997年,张金哲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小儿外科界的第一位院士。很多人向张金哲表示庆贺,他则笑呵呵地写下一幅书法挂在家中:“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这也是他的毕生修身之道。
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100岁,也不是每个百岁老人都能保持张金哲这样的生命状态。除了一头银丝,看老人家的皮肤、体态、语速、举止,确实很难与百岁翁发生联系。
这首先因为他是一位终身学习型百岁院士,他“什么都会”,熟练上网,自由浏览医学前沿最新的中、英文成果资料;用E-mail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往来;甚至还玩微信、上抖音,保持与时代同步。
2020年“六一”儿童节,这位百岁院士还欣然参加了院里安排的抖音直播,在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为异地恶性实体肿瘤患儿变个戏法,送上祝福,庆祝节日。
就在100岁生日前夕,他还亲自为一个患儿做了肛门手诊,说明老人家神经末梢的触觉敏感度并无退化。
张金哲的兴趣也很广泛,业余时间经常练练书画,喜爱戏曲的他,还时不时是唱上几嗓子。他说,人乐观些,每天让自己充实些,感觉前途有光明,活着就有奔头;总感觉有事情要做,就一定会长寿。他曾在多个场合谈长寿的秘诀:“工作可致长寿。其实就是要求自己,今天能做到的,明天尽量也要做到。”
目前,他每天在室内自行车上骑行锻炼,坚持每周到院半天。走过百岁春秋,有人问张金哲对儿科有何展望,他说:“我希望将儿童医院打造成一个无痛、无恐的儿童健康乐园。”怀着这个梦想,百岁院士张金哲的脚步继续前行。
(责编/闻立 责校/黄梦怡 来源/《醫学人文与张金哲的百岁人生》,夏欣/文,《光明日报》2020年9月14日;《行医七十余年仍未“退休”——“小儿外科之父”张金哲院士迎来百岁寿辰》,詹媛媛/文,《光明日报》2020年9月26日;《著名小儿外科专家张金哲院士:大医至仁》,夏媛媛/文,《中国科学报》2014年8月15日;《张金哲:94岁的出诊大夫》,杨杰/文,《中国青年报》2014年8月15日;《张金哲:94岁的儿科医生》,杨姣/文,《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5日;《长寿者的心得都很简单,儿科泰斗张金哲也一样》,江南/文,《燕赵老年报》2019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