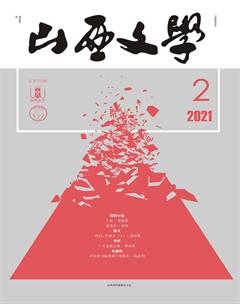乡村消逝的一种方式
袁菁 夏商
上海—纽约 微信语音访谈
2020年8月17日—9月7日
袁菁:2020年是浦东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所有关于浦东的叙事调门都高亢、宏大。但在您的长篇小说《东岸纪事》里,浦东幽暗、暧昧、混杂,能够明显感受到城市与乡村的观念上的不同。根据媒体报道显示,《东岸纪事》似乎动笔于2010年前后,2016年左右再次修订。是怎样的驱动力,让您感到开发前的浦东需要被书写,而且值得被书写?
夏商:说到浦东书写的缘起,2001年,我32岁,搬离浦东,来到浦西的北京西路石门路居住。之后再去浦东,发现跟我青春期的记忆越来越不像了,城市化摧枯拉朽的速度把当年乡村地理的浦东都摧毁了。在《东岸纪事》问世的2012年之前,我最后一篇小说在刊物上发表,大概是在2000年,也就是说,有长达10多年没发表小说,这么长时间停笔,一来是因为我对先锋派文本实验产生了困惑,觉得技术层面的花拳绣腿也就那么回事,二来作为一个“野生动物”也要觅食谋生。笔虽然停下来了,脑子没闲着,一直在琢磨写作的突破口。2006年左右,在陌生感、追忆感的驱动下,我试图把记忆中的老浦东书写出来,这一次,回归现实主义传统,扎扎实实地写好一个故事成为我的追求,前后写了六年。
《东岸纪事》有别于我早年的先锋小说注重形式感——地理和空间甚至人物都呈现符号化的书写特征,也就是往虚里写。它采用一种“照相机式”“工笔画”的方式,但不是美国小说家卡波蒂写的《冷血》那一类非虚构作品,我个人更愿意把它定义为“混合着地理志和编年体”结构的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具有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事件,就像我挺喜欢的美国作家多克托罗的小说《拉格泰姆时代》。
《东岸纪事》里的“浦东故事”主要横跨了四个政治地理的空间,当时的浦东沿江狭长地带分属于杨浦区(大致位于洋泾-东昌路)、黄浦区(大致位于东昌路-塘桥)和南市区(大致位于塘桥-周家渡,包括南码头),所以浦东并不完全是郊区,不都是说浦东土话的土著乡下人,也包含了一部分说“上海闲话”、拿市区户口的居民。
除了杨浦、黄浦和南市,浦东还有一部分沿江地带比如三林塘,属于当时的上海县——后来,上海县逐步拆分,今已撤销,成为了徐汇区、浦东新区、闵行区、长宁区的一部分。另外,小说也涉及到南汇县的周浦和横沔等村镇的人事。
六里桥、浦三路、浦东南路是小说的核心地带,就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一张邮票大的地方。是典型的城镇混合体或者说城乡结合部,地理位置让它呈现双面性:面朝浦西的南码头,属于南市区,这个区域有很多市区户口的住户,也有不少隶属于各局委办的下属企业;我家位于离南码头不远的周家弄,则属于川沙县域。浦东南路是一条分界线,把市区和郊区分开。那些家在南码头,单位在我家门口的上海航天局或化工局下属企业的职工,作为市区户口,骑车上班七八分钟就进入川沙县域,在工资以外可以拿到一份“郊区津贴”。
这样一个内部充满诸多差异的浦东,长期疏离于一般人理解的“上海”之外。世人对上海的印象贴满了“十里洋场”“外滩”“法租界”“奢侈品旗舰店”等等浮夸的标签。围绕上海的文学创作很少有乡村和农民,最多只有老城厢或石库门弄堂场景。浦东那些蛮荒的、泥沙俱下的气质对外部社会来说非常陌生,我也是在《东岸纪事》出版之后,才从读者的反馈中得到了这样一种认知。
袁菁:您曾在《东岸纪事》时说“我的青春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生命经验让您把浦东塘桥、六里、艾镇、南码头、浦东南路这些空间地图串联起来?
夏商:我出生于1969年,两岁起就住在沪西奶奶家,直到九岁回到浦东。浦东上世纪的乡村教育总体水平一般,像我所在六里公社的六北小学的班级,后来考上大学的只有两个女生,一位副班长后来考到行知师范——那时能考上中专就算不错了。很多年以后在路上遇到她,她说在临沂二村小学当老师,我才知道临沂二村小学就是母校六北小学,更准确地说,六北小学是临沂二村小学的前身。记得我还开玩笑说,绕了一圈你又回到六北小学了。那次邂逅说起来也有小二十年了,后来再没见过她,如果還在临沂二村小学任教,过几年也该退休了。
其他的学生,不是考技校,就是干脆不读了。我初二就没读完。许多年后,有一次在徐家汇打的,那位司机竟是我初中同学,我没认出他,他倒还认得我,送我到目的地后执意不收车费,推了几下我嫌难看,就随他去了。他想留微信,我借口不用,就没留,不是不念旧,实在是没什么话题了。短暂的车程中,他说知道我成了作家,以我为荣。我说,我辍学时还不叫夏商,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学校搞过两次大的校庆,有些同学去了,在杰出校友名录里有你。他问我当时为什么突然转学了,校庆也没见我在场。我笑笑。
告别后勾连起不愉快的回忆:我就读的浦东中学坐落在六里桥旁,是一所没落的民国名校,我不算优等生也不算差生,算偏科生。语文课和书法课都不错,还代表学校参加过川沙县的作文比赛。初二上半学期的一个下午,地理课上我做小动作,这虽然不对,但那位教地理的五十多岁老宁波冲过来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我那时跟镇上一个南拳武师学散打,又正是看《七侠五义》的年龄,男子汉怎可以被抽耳光,立刻就和他对打,无奈力气小被打得鼻血直流,当然他也中了我几拳,不久我就离开了学校。同学们不知道以为我转学,其实是被勒令退学。所有体罚的老师都不会是初犯,一定是惯犯。就像去年社交平台上曾流传一个短视频,说外省一个年轻人,在马路上殴打一个老者,结果问下来老者是年轻人的小学老师,曾经常对他体罚,我非常理解那个年轻人的愤怒。
言归正传,过了若干年,当初喜欢我的那个语文老师告诉学校我成了青年作家,校庆办就有人电话邀请我,我谢绝了。又过十年,好像是百年校庆,又转弯找到我,我还是谢绝了,并且希望不要再把我印在杰出校友录里。我不是杰出校友,只是一个被斥退的学生,如果真的坐在主席台上,和学弟学妹们说些什么呢?从内心来说,把当年的弃生放进杰出校友录这个举动,显得市侩。既然当初一别两宽,那就往后各生欢喜。
辍学后,我就开始混社会了。之后很长的一段日子,活得很像上海版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你说的塘桥、六里、艾镇、南码头这些地方,既是现实中真实的地名,也是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都是我熟悉的青春期宣泄“力比多”的地方。
那时交往一些离经叛道的年轻人,从世俗的角度看,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小流氓,当然我也可以算其中一员。可什么是世俗,世俗难道是不可冒犯的吗?年轻人不冒犯世俗和秩序,那多没劲啊。我从没觉得那些无所事事的、看似荒唐的日子是“污点”,相反,对一个未来小说家而言,那是一段精彩的人生,我有个武断的结论,能够写出好小说的必须是“坏”小孩,或者曾经是“坏”小孩,“乖”孩子是写不好小说的,这个观点不允许反驳。
随着朋友增多,骑着自行车不停扩大版图,活动的疆域也会扩大,不再局限在塘桥、六里、艾镇、南码头,会去更远的陆家嘴、十八间、三林塘甚至周浦、高桥等浦东腹地。整天东晃西晃,对浦东的细节了解也会深入。这些细节不是每个浦东人都了解的,而那些外省来沪的新浦东人就更不知道一些事物的来龙去脉。比方现在陆家嘴的滨江大道,亲水平台竖着一只船锚,固定在大理石基座上,游客会以为是锚形雕塑,其实是一只真锚。亲水平台所处的区域,以前是立新船厂,立新船厂不是造船厂,而是修船厂。我玩得最好的一个哥们是这个船厂的电焊工,有时我们约好去溜冰场,我就在他下班前去找他,顺便蹭一把澡。坐82路公交车,终点站下来就是立新船厂,旁边就是发生1988年踩踏事件的陆家嘴轮渡站。
陆家嘴要搞金融城,立新船厂就搬走了,沿江的部分做了绿化带和亲水平台,厂房和船坞悉数拆尽,唯一就保留了这只船锚,算是船厂遗迹。浦东沿江一带,除“立新”之外,还有其他船厂。规模较大的是沪东船厂,除了浦东大道旁的总厂,在南码头轮渡站旁还有分厂。这几家船厂都是公开单位,还有一家船厂就比较神秘,对外挂牌叫“申佳船厂”,可熟悉它的人都叫它4805工厂,我有哥们的父母就在里面上班,说4805是番号,属于军工厂,修军舰的,这样的保密单位其实也不算太保密,住在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它底细。还有一家周浦的玻璃厂,对外挂牌叫“上海平板玻璃厂”,其实是上海监狱局下属的周浦监狱。1980年代严打刮台风,我有个哥们就作为最后一批“流氓罪”案犯被“刮进去了”,他被捕后不久,流氓罪就被取消了。我坐郊区公交车去看他,探监不能从工厂的正门进出,而是穿过大片庄稼地,从一堵高墙的小门走进去,高墙有岗哨,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路途往返三四个小时,探视只有15分钟,中间有铁网隔开。这些关于浦东的细节和我的青春紧密相连,大量鲜活的人生穿插其间,如果让我敞开说,可以说半年。
袁菁:浦东开发,对你产生了怎样具体的影响?
夏商:其实在1990年浦东宣布开发之前,我家所在的浦三路一带就开始动迁了。动迁之前,我和妹妹随我母亲属于川沙县农业户口。动迁后,自用房和宅基地被征用,失去了土地,农民身份自然就名不副实了,户口也就变成了“农转非”。从现实生活来说,户口的变化意味着从“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国家拿走了自留地,作为代价,得安排你一份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征地工。我家私房被拆那年,我被浦东中学勒令退学没多久,作为一个懵懂的半文盲少年——半文盲不是玩笑话,我接受的应试教育比较熟练掌握的也就是拼音吧,这个技能让我后来自学时可以查字典——觉得农村户口换成市区户口挺好的,周家弄那些邻居也挺高兴,因为可以去工厂上班了,还可以住进有煤气和抽水马桶的新工房,不用生炉子倒马桶了。
等到我读了点书,明白了一些常识道理,才知道户口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荒诞的,人生而自由,也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把户口再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更是荒诞之荒诞,等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慢慢开始发表作品了。
从民俗的角度说,户口在大部分时候是隐性的,口音才是显性的,它代表了你是“上海人”还是“乡下人”,口音的差异可以让市区小孩和农村小孩玩不到一起,成为身份差异的活态标签。我虽是农业户口,但很小就住在沪西祖母那儿,那是个苏北人集聚的穷街,家里除了祖母和小姑,还有二叔二婶,二婶的娘家是宁波人,上海话是以宁波话音调为基准的,所以上海的宁波人后代都能说字正腔圆的上海话,说上海话的二婶嫁给了说苏北话的二叔,自己却从不说苏北话,也反对二叔和我说苏北话,非让我们跟着她说上海话。所以我小时候就在浦东土话、苏北话和上海话中来回穿梭,三种方言都说得很溜。因为上海话说得好,还滋生了莫名其妙的优越感,那时喜欢过一个三林塘姑娘,人很漂亮,可三林塘的浦东土话比周家弄还要土,一张嘴就是“个板板,伊板板”(大意:这边边,那边边),我就觉得对方很土气,揶揄过她几次,她似乎也被我流利的上海话搞得有点自卑,可见上海话对沪郊土话而言确实是一种权力。
1985年12月15日前夕,我妈通知我“可以去上班了”。为什么对这个日子记得那么清楚,因为那天刚好是我16岁生日。单位分配在半年前就完成了,我已经知道要去哪个厂上班,但有个硬性规定,征地工不能低于16足岁,否则就是童工。我在家里等了半年多,直到生日那天才去报到。我妈还给我买了件粗纺面料的灰色西装,这是我第一次穿西装。
我进的是上海市化工局的下属单位上海助剂厂,老厂厂址在白莲泾莲南路300号。它属于“全民企业”,大部分是市区户口。我们这些被征地的农民工是被摊派的“指标人”,是这家企业运转经营之外的额外存在,换言之,工厂本不需要这些工人,也没多余的岗位。还有一个问题,征地农民工老弱病残皆有,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也无法胜任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助剂厂是化工企业,就算最基層的化学操作工,好歹也是读了三年的技校生,掌握了化工操作的应知应会,而征地农民工连PH试纸都读不懂。于是,厂里就有了“一国两制”:农民工属于大集体性质,工资奖金津贴等待遇属于“二等公民”。
为了安置这些游兵散勇,厂部也是煞费苦心,将食堂、后勤、仓储、园艺作为安置岗位,同时新增、延伸各种岗位,拉长生产环节,比如把原本外包给乡镇企业的化学塑料桶清洗工作收回来,交给大集体清洗;再比如厂里本就需要塑料袋用来装产品,就买了吹塑机,自行采购塑料粒子交给大集体加工,再以采购的方式卖给厂里。这个大集体后来成立三产公司,好像叫“上海天泰化工总公司”,天泰和天坛发音接近,天坛是助剂厂的产品商标。总公司下属还有后勤服务公司、化工贸易公司等子公司,看起来牌牌很多,其实加起来也没多少资产,这种形式也不是上海助剂厂一家在搞,凡是有征地农民工的企业都这么搞,无非是企业所从事的行业不同,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助剂吃助剂,靠钢铁吃钢铁,靠纺织吃纺织,以此类推。
当然,老是寄生蟹一样依附于助剂厂也不是长远之计,大集体领导也想去市场探探路,记得他们搞过一个精细化工小厂,生产的第一个产品是洗碗用的洗洁精。助剂厂有一种原料叫表面活性剂,是洗洁精的主要原料。洗洁精是千家万户都用得着的快消日用品,虽然市面上有大名鼎鼎的白猫牌,但市场竞争并不充分。助剂厂作为母厂,原料价格比较优惠,从当时来说,选择这个产品进入市场算是不错的决策,大集体领导让我设计包装。在他们眼里,大集体只有我看上去有点文化,因为我经常在报纸上发点豆腐干文章,还被厂部宣传科借过去编过厂报,大集体的黑板报也是我的分内事,所以设计洗洁精包装对我来说一定也是小菜一碟。时间久远,我已记不清那洗洁精叫什么牌子了,可能就叫天泰牌,反正我画了几稿后就交差了,也没给我设计费,可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吧。
那个洗洁精后来销路如何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主要的岗位是在车间,厂部选择了一部分大集体农民工,经过培训后进入生产车间,安排我去的工段,生产的是造纸和印染用助剂,甲醛和冰醋酸是重要原料,气味很呛人,恶劣的工作环境令我对未来产生焦虑,直觉上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就开始努力起来。工友上夜班打瞌睡,我的夜读时光就开始了。那时出现了大量西方小说和人文社科类书籍的译本,我读了不少,虽然我目前最高的学历还是小学,可在工厂的那几年,算是读完了属于自己的中文系吧。之所以尝试写小说,离开工厂就是驱动力,可对农村户口出身的我来说,能当上工人已是鲤鱼跳龙门,真辞职了父母还不把我骂死。
后来有个事让我下定了决心:我工伤了。那是一个冬天的夜班,因为疏忽,冰醋酸喷在了我脸上,左脸的皮肤几乎全被腐蚀。结冰天,我把头放在自来水龙头下猛冲,这是“应知应会”教给我的防护知识,用水稀释冰醋酸的浓度。当晚,我被紧急送往上海市化工职业病治疗中心——多年以后,我搬去浦西静安区生活,发现这个医疗中心就在成都路和南京西路交汇处,距离我住的大田路步行五分钟的样子。
今天想起来依然后怕,幸亏冰醋酸是弱酸,如果是硫酸或硝酸,就成了《夜半歌声》里的宋丹萍了。我们厂还真有硫酸和硝酸,这么大面积的硫酸或硝酸腐蚀,再用自来水冲也无济于事,左眼瞎了,左脸也成骷髅了。兄弟我不是那种身残志坚的人,怕是就跳黄浦江了……即便冰醋酸是弱酸,皮肤也蜕了三次,两个多月整张脸都用纱布裹着,换纱布的时候我也不敢看镜子。听我妈说,第一次换肤是焦黑色,第二次换肤是褐色,第三次才基本恢复原来的肤色。皮肤恢复了,视力还是受到了影响。
照理说这么严重的事故应该算工伤,厂部来了领导,可能是工会主席也可能是副厂长。找我谈,希望我不要算工伤,因为一算工伤全厂的年终奖就受影响,这关系到全厂一千多职工的切身利益,希望我以大局为重,这个厂领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听他这么说当然只能答应了。答应完了总觉得哪儿不对,觉得是离开的时候了。又怕父母不开心,就跟厂部提了个要求,理由也很充分,化工车间这么危险,我有心理阴影不敢上班了,让我停薪留职去社会上找找出路吧。
厂部很快就同意了,二十歲出头的我再次成为社会人,说是停薪留职,其实是为了安慰父母,就没准备再回去,三年后回厂办了正式辞职手续,野生觅食,直到今天。
虽然一直有离开工厂的打算,一旦停薪留职回到社会这个旷野,一下子迷途了。一没学历,二没资金,三没人脉,家里也不能提供任何社会资源,虽然今天我依然喜欢自称野生动物,可那时的我,别说老虎狮子,连郊狼都算不上,只能算野兔松鼠,处于食物链的最底部。
虽然采取的是看似有“退路”的停薪留职方式,父亲还是非常不理解,觉得我放弃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工作,虽然是大集体,但毕竟是全民企业里的大集体,以后退休有保障的。我那时才二十出头,他已经开始考虑我的退休了,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父母的思维方式,找到一个单位,然后一眼看到老,安稳一辈子。其实那时候,下岗这个词已经开始流行,最让职工有安全感的所谓“劳(动)保(障)”,也开始以买断工龄的形式不再兑现。说是买断工龄,其实是非常低廉的赔偿。下岗这样的词也显出了中文的博大精深,明明是失业,却说得跟待岗似的。反正父子闹得很不愉快,甚至一度要断绝关系的程度。
当时能想到的创业项目就是开一个熟食店,还去做了市场调研,很快就打了退堂鼓。单单我们周家弄老街就有三四家熟食店,竞争已经非常激烈。那段日子真是百无聊赖又忧心忡忡,刚好有个编辑朋友想开广告公司,想拉我入伙,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这块料,先试试吧。之后,我就策划了一个企业标志的展览,规模很小,但应该是上海第一个关于企业标志的展览。
袁菁:这也等于把你带到了当年的浦东经济商业涌现的现场,深入参与其中。
夏商:算是误打误撞吧。虽然说广义上也是“广告人”,但业务其实更偏向于“平面设计”,直到今天我移居美国,仍在上海保留了一个设计工作室,就是当年延续下来的。我应该算是上海,甚至是大陆接触到平面设计较早的一批人,也用它作为谋生的手段之一。之所以第一个项目会想到做企业标志展,是由于无意中接触了企业形象识别系统,也就是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CIS。
前面说过,我在工厂上夜班时,如饥似渴地读书,除了文学和人文学科,也读一些杂书。买书是我一笔比较大的开销,幸好我有稿费收入,现在回想起来,我算是工友里的有钱人,1990年代初我已经在《文汇电影时报》开专栏,在《新民晚报》《劳动报》虽然不是专栏但也差不多,基本能保证一个月各发两篇,所以当时每个月200块稿费是可以保证的,这是我工资奖金的三倍,所以和工友吃排档一般都是我买单。
我去得最多的是南码头路上的新华书店,和一个方脸店员小闵成了朋友,他经常会推荐一些新书给我,有时还神秘兮兮地推荐内部发行的书,比如作家出版社的“作家参考丛书”,版权页印着“内部发行”几个字。说内部发行,其实也公开卖,但估计发行量会小一些。我就买过这套丛书里的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有杜拉斯的《情人》。小闵告诉我,他们店是上海市省版书店在浦东的一个门市部,品种少,有时候紧俏书不一定轮得到,我就隔段时间骑自行车去位于老西门的省版书店。后来又听说大世界斜对面也开有书店,石门二路南京西路口、静安寺对面都有书店,一听说有书店就跑去看,每次总会买几本。
有一次跑到延安西路的上海图书进出口公司。一楼卖中文读物,二楼有很多海外书籍,有各种广告创意、电影海报、图书装帧、标志设计的画册。因为是外版书,人民币定价是手写的,用小标签贴上去,每本动辄上百元,目标读者可能是美院老师、美术编辑、导演或摄影师。我虽然有稿费收入,买这么贵的画册还是肉疼,当时很少见到这么精美的画册,又有点爱不释手,心想今天非得买一本回去,不死心每本标价看过去,有一本辞海那么厚的硬皮封面的标志设计画册,标签上写着人民币58 元。粗略翻了一下,喜欢得不得了,想到当初给大集体设计洗洁精包装,绞尽脑汁不得要领,要是早点看到这本标志设计画册,得提供多少启发呀。就咬咬牙买下来了。这本设计画册里有可口可乐、肯德基、宝马等欧美著名商标,当然也有一些不怎么著名但设计得很好的標识,当然,对那时的我来说,包括可口可乐、肯德基、宝马在内的海外商标都是比较陌生的,这些品牌正处于刚进入大陆市场或即将进入大陆市场的状态,有些标识还用方格子框了起来,因为是全英文的,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有些方格子里还有弯曲线条,猜测是画标识的辅助线,后来对平面设计了解多了一些,才知道它有一个专门名词叫“九宫格”。
倒回去看,1949年前,作为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的广告业已非常发达,各企业有自己的主打品牌,店招和商标设计都非常出色了,平面设计那时已经比较成熟,作家鲁迅就是很好的平面设计师,他设计的很多图书封面放在今天仍很耐看。195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城市有计划委员会,乡村有供销社,国家统购统销,物质匮乏时要用各种券来运转日常生活——粮油猪肉都是凭票供应,粮票还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买缝纫机自行车都要用券,农村还有粪券,妇女例假竟然还需要月经带券。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老百姓手里没有余钱,市场上所有的日用品都供不应求,买都买不到,哪里还需要品牌和商标,更不需要广告了。
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把上海企业的识别度下降到可有可无的地步,比如章华毛纺厂变成了上海第一毛纺厂,阮耀记袜机袜针号生产出飞人牌缝纫机,后来变成上海缝纫机一厂。商店也一样,从南京路的市百一店,一路数到长风公园的市百十二店,一串阿拉伯数字编号,彼此之间毫无个性可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意味着在停顿半个多世纪后大陆的市场经济重启,企业之间恢复了竞争意识,商标和品牌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所以说,历史应该少折腾,更不能开倒车。可惜的是,历史不是开往春天的火车,它有时候更像一只陀螺,转啊转啊又转回原点。
袁菁:您还记得浦东出现有商品房是什么时候?我翻阅1990年代中期的《浦东开发》杂志发现,时任主管浦东开发事务的赵启正会在把汤臣集团的老总喊做“汤·浦东”,而类似汤臣集团当时拥有的土地已深入到川沙东部的合庆等地。1994年,对比当时的收入,浦东远郊的房产价格有不少在1000多/平方米,您当年是否也在浦东置业?
夏商:还真问对了人,1990年代中期,我曾在浦电路张家浜河边买过一套三室一厅,商住两用房,用作办公室。那栋楼叫众鑫大厦,现在看很一般,当时还是“弹眼落睛”的。不说是浦东最早的商品房,也是最早之一。为什么会买这个房子呢,有个插曲。赚了点钱之后,我经常买东西孝敬孝敬父母。他们看我突然出手阔绰,很惶恐,怕钱来路不正,后来知道是辛苦劳动所得,我爸就吐槽说,这是你运气好,我们那时候,母鸡下个蛋去菜场卖掉都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听了当然不开心,就怼他,那我要是出生在美英法德,做生意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个权利曾经被剥夺了,然后又还给你,就要感恩戴德,就要说我运气好,是不是有点奴性呢。说完又找人喝酒去了。
因为青少年时在社会上瞎混,沾染了所谓江湖义气,赚了点钱就变得像宋江,仗义疏财,三天两头叫一帮狐朋狗友胡吃海喝,作为朋友眼中的新晋暴发户,当然都是我买单。去得最多的是浦电路南泉路上的一家本帮菜馆,好像叫“跃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反正那段时间挥霍掉不少钱,父母看在眼里,又不好说什么,毕竟钱是我自己赚的,但不开心写在脸上,我妈没事就在我耳边说“天好防落雨”。这是浦东民谚,意思是备点余粮以防饥荒,也可以引申为存点钱以备不时之需。
刚好,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房产广告,抽空跑到驻外滩的开发商办公室,他们说工程地址就在“张家浜边上”,离我家不过20多分钟。我一想,买个房也好,不用借办公室了,公司有个安稳的办公地点,也没闲钱请客吃饭了。抽空跑过去一看,大楼真的在造,还没封顶,搭了工程电梯上去的。尽管还贷了点款,父母还是特别支持,“脱底棺材”终于没钱“瞎污搞”了。
当时,我还住在动迁安置的临沂三村,5楼的一室户,父母与妹妹住在同一栋楼二楼的一套一室半里。小青年有这套独立一室户,当时已经不得了。我有几个特别好的哥们,平时在浦东厮混的据点有这么几个,一个是东三里桥的深夜排档,喝啤酒,吃三黄鸡毛豆螺蛳。一个是昌里路上钢新村的沪南文化宫,有落弹室、录像厅、猜谜室,一个是东昌电影院附近的浦东文化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一室户——那时候轧女朋友,哪有地方开房,住旅馆和招待所还需要单位开介绍信,所以这个一室户就成了免费钟点房。
当年商品房楼盘少,没比较,泥腿子上岸的思维,懵懂得很。对这个商品房唯一的感受就是“大”,房型其实一塌糊涂也没概念,装修好搬进去,从窗口往外看,是刚合拢没几年的南浦大桥,东方明珠电视塔像个光杆司令矗立在陆家嘴,电视塔周遭一片灰蒙蒙的,那时候上海的空气质量已经不太好,影影绰绰中,有很多脚手架和建筑吊车,当时有个夸张的说法,全世界一半的脚手架和建筑吊车都在这块巴掌大的土地上。
我买房时,售楼处在外滩的一个老楼里,墙上贴着一张售房进度表,卖掉的在格子里贴个纸质小红旗,待定的在格子里贴个小黄旗,余下的是空格,我交完订金后,他们就在我那个单位的空格里贴了小黄旗,我问我都买了怎么不是小红旗,他们说小红旗是付了全款的,小黄旗是要贷款按揭的,按揭会有变数,银行有可能不放贷,所以只能算待定状态。因为是在造期房,大概一年后我才入住,入住后还在报纸上看到众鑫大厦的通栏广告。入住的同时,隔壁有个新楼盘奠基,叫京城大厦,开发商是北京城建。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这个楼盘在张家浜旁边拉了很多横幅,写着:2700元/平方米。今天来看,小陆家嘴板块里的住宅才这个价格,岂止是白菜价,简直是白菜帮子价。但这个价,时人都嫌贵,需要开发商大量做广告推销。
1990年代中后期,浦东的房地产业还是开发商“求卖”阶段。浦东包括上海的房地产价格并不是一开始就飞涨的,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一步步诱导出来之后的结果。1998年6月,时值亚洲金融危机,上海市出台购房退税政策,为期5年。我妹夫当时在IBM工作,外企薪水高,退税后有一笔抵扣额度。他在花木看中一个楼盘叫牡丹苑,怂恿我一起买,那时我刚把众鑫大厦的按揭还清,手里略有余钱,心想自己刚结婚又有了儿子,不妨改善一下,有贷款是压力也是动力,就跟着买了一套。牡丹苑在牡丹路上,距离地铁二号线步行十分钟。那时二号线还在建设中,吃过晚饭,把儿子骑在脖子上闲逛,有时也去看地铁的进度,工地附近都是泥泞和杂砖,也不用围栏围起来遮丑,左拐不远,是建设中的世纪公园,大概过了两年,二号线通车了,好像差不多时间,世纪公园也竣工开放了。
袁菁:《东岸纪事》里有对浦东日常生活空间的描述,除了菜场、市集和商店,还有上钢新村长青服饰市场,这个服饰市场的存在意味着浦东人对“行头”的追求,它和浦西的华亭路有什么区别?关于长青服饰市场的描述在其他地方较少看到,想知道它卖些什么,以及它的受众?
夏商:小说里提到的长青服饰市场,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浦东版的华亭路。它位于浦东最繁华的昌里路商业街,昌里路之所以繁华,是因为附近有上钢新村和上南新村两个工人新村,昌里路的位置现在属于世博板块,当时浦东最大的企业上海第三钢铁厂就在那儿。计划经济时代的万人大厂基本就是一個小城市,我有一次去长春,特地去一汽。朋友开车在厂区行驶,完全就是一个独立社会,从幼儿园到火葬场什么都有,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在一汽从生到死。上钢三厂规模当然赶不上一汽,但好像除了火葬场,其他从幼儿园到三钢医院也是一应俱全,还开了当时浦东体量最大的百货店三钢商场。浦东人买东西如果不愿去浦西,三钢商场几乎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可我去昌里路很少进三钢商场,而是去它隔壁不远的长青服饰市场,那是追求时髦的浦东年轻人的潮地。款式基本和浦西的华亭路同步,有几个小老板就是华亭路有摊位,在这里又开了一个分店。不少摊主是“山上下来”的刑满释放人员,是上海最早的一批万元户,也是上海最早一批买摩托车的人,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上海第一批买摩托车的人都车祸死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长青服饰市场有很多港版时装,女装不去说它,男装有横竖条的T恤、200多元一双的宝狮龙运动鞋,还有喇叭裤牛仔裤,但我们这种社会青年瞧不起那些“骚包”款式,我们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搭配:解放军服样式的“黄皮”和警察警服样式的“蓝皮”,只是缺少肩章,这是小流氓最“懂经”的行头,穿上“黄皮”和“蓝皮”,就说明自己路子野,比较有“立升”。到了冬天,上身穿精纺呢的中山装,或对襟织锦缎棉袄,棉袄外面要套一件蓝色布褂,下装穿黄色军裤,脚上是老棉鞋,在浦东街头晃荡,在正派人眼里,就是所谓的“打桩模子”。
记得每次从长青服饰市场出来,总要去对面一家清真点心店吃牛肉锅贴,那个锅贴至今想起来还“馋吐咝淌淌滴”,真的“邪气”好吃。
袁菁: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您觉得浦东还保留了哪些独有的特色?在什么时间节点会让你生出“浦东真的有点变化了”的感受?
夏商:相比青春期的岁月,浦东地理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彻头彻尾的乡村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城市,道路基建、枢纽节点和出行工具的变化,让区位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世纪公园所在的花木地区,今天已经算好地段,而我家动迁时,花木还非常“落乡”,通行极其不便。1993年,我家拿到了临沂三村的动迁房,那时装修流行贴墙纸,市场上有个华美牌墙纸口碑不错,我妈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生产华美墙纸的厂家就在花木乡,直接去厂门市部买的话,只要市场价的一半,我和我妈早上六七点出门,坐上郊区公交车,经过土路野河,颠颠簸簸,七绕八弯,中午才到了工厂。现在从临沂三村开车去花木,大概一刻钟就够了。这不是说自然距离突然消失了,而是地貌被改变了。当初的土路、机耕路、断头路、断头河……填埋的填埋,改道的改道,拉直的拉直,简单说,不再绕了。这种地貌的变化引申出其他变化,比如说周家弄是六里乡的一个自然村,后来六里乡变成了六里镇,前几年,六里镇周边的几个镇或街道办事处,比如艾镇、塘桥、花木、严桥,都陆续合并了,这是因为以前交通不便管辖困难,设立乡镇比较多,现在空间感压缩了,五六个乡镇合并,辖区也没觉得有多大,当然,对个人的感受来说,现在的浦东和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就像一段遥远的初恋,再也回不去了。
这次回纽约,把几千册藏书运走,可能很长时间不会回上海了。竟生出一丝伤感,我上海的家在静安雕塑公园对面,我喜欢夜跑,沿着苏州河往外滩跑,站在外白渡桥看陆家嘴,觉得这个光鲜而陌生的浦东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也许只有距离会产生乡愁,也许只有站在哈德逊河畔才会更逼真地回忆起那个往昔的浦东吧。
【作者简介】夏商,旅美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东岸纪事》《乞儿流浪记》《标本师》《裸露的亡灵》,另有四卷本《夏商自选集》及九卷本《夏商小说系列》。现居纽约长岛。
袁菁,《城市中国》记者。